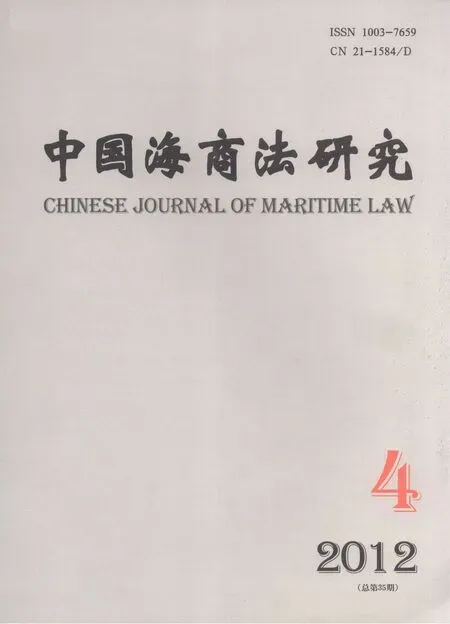《鹿特丹规则》若干疑难问题综述①
荣璞珉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一、《鹿特丹规则》第1条第6款、第7款“履约方”和“海运履约方”的定义中没有“保持”(keep)一词,这是为何
司玉琢教授认为是因为疏漏没有列进去。《鹿特丹规则》起草过程中形成的WP56文件第7页,对“履约方”定义的注释6中,指出“list expanded to parallel specific obligations set out in para.14(1)”。显然,公约并不想使履约方所承担的义务与第14条(最终通过的公约中的第13条)所规定的承运人义务有所不同,而是要使它们完全一样(to parallel)。
阿尔巴教授、兹尔教授、贝林吉尔教授、斯特里教授均同意司玉琢教授的观点。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已于2012年10月11日下发了一份对公约第1条6款和第19条第1款第2项的修改案。在第1条6款中加进了“保持”(keep)一词,纠正了笔误,印证了司玉琢教授的观点。
二、《鹿特丹规则》第47条第2款“不影响第48条第1款”是否应理解为“不影响第48条第2款”或者“不影响第48条”
司玉琢教授认为,这句话应为“不影响第48条”,意思是,虽然第47条第2款赋予了承运人可以根据托运人、单证托运人的指示放货的选择权,但这一规定不影响当构成“货物仍未交付”的情形时,承运人按照第48条的规定行使处置货物的权利;换言之,当货物构成第47条第2款(a)项所规定的无法交付时,承运人既可以选择按照第47条第2款的规定按照托运人或单证托运人的指示放货,也可以按照第48条的规定处置货物,任何人不得强迫承运人按照第47条第2款的规定放货。
贝林吉尔教授认为,把第47条第2款和第48条第1款合起来考虑是恰当的。因为第48条第1款描述的是货物被视为仍未交付的情形,其后的几款介绍承运人在此种情况下的权利。第47条第2款规定了可转让的运输单证上明确载明可以不提交运输单证交付货物的情形。有必要澄清的是:该款的规定不影响第48条第1款的适用,当构成货物仍未交付时,自动适用第48条中的后几款。
阿尔巴教授认为,一般来说,适用第48条可能会更合适,但适用第48条第1款不会改变适用这两个条文产生的结果。若承运人按照第4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交付货物,就适用第47条第2款;若承运人未按条文规定的方式交付,就适用第48条的相关内容。
兹尔教授也同意司玉琢教授的观点。
三、违约赔偿范围,如可合理遇见的经济损失,是否由国内法调整
司玉琢教授认为,第一,根据公约第22条,对货物灭失或损坏(包括迟延交付造成的灭失或者损坏,见第60条)的赔偿范围,必须按照货物交付当时、当地的价值计算。换言之,对此种损害的赔偿范围,公约已有明确的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应按照公约的规定确定赔偿范围。第二,对于迟延交付所造成的纯经济损失,以及因承运人违反公约所规定的相关义务而使货方遭受的其他损失(如承运人未执行控制权的指示而给控制方造成的损失,根据公约第4条第1款,允许货方就此种损失向相关人索赔)的赔偿范围,公约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是否应适用国内法的规定?
贝林吉尔教授表示并不很理解这个问题,因为《鹿特丹规则》中没有出现“可合理遇见的经济损失”这一概念。但他认为司玉琢教授的第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观点,他认为第22条第3款排除了缔约国制定法律调整承运人对纯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但不影响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之间自己约定。
阿尔巴教授认为“可合理预见的经济损失”与货物实际受损、迟延或承运人违背本公约项下的义务产生的合理的经济损失有关。他的理解是,第22条只规定以货物价值来计算货物实际灭失或损害的赔偿额。所以该条第3款也只限于此种损害,且可以获得补偿的最大金额(未适用责任限制之前)要与根据本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数额相适应。第3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赔偿额的不同计算方法并不表示可以适用纯经济损失,也不妨碍缔约国各自规定经济损失是否可以获得赔偿。该款只是表明当事人可以有机会就货物实际灭失或损害遭受的损失约定不同的计算方法。承运人是否应该对货物实际灭失或损害引起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鹿特丹规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国内法去调整。然而,即便根据国内法,这些损失可以得到赔偿,也要受制于责任限制条款,尤其是第59条、第61条。至于其他经济损失,他认为迟延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第60条、第61条调整;承运人违背控制权条款下的义务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是严格地由交付迟延造成的),由第59条、第61条调整。
兹尔教授表示,第22条第1款、第2款来自《海牙-维斯比规则》。通常的解释是排除对经济损失的补偿。《鹿特丹规则》加入了第3款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关于司玉琢教授的第二个观点,他认为《鹿特丹规则》中许多条款都只规定了义务而没有规定相应的责任。这就意味着这种赔偿责任(包括因果关系和赔偿额的计算)由国内法调整。至于迟延,迟延造成的损失基本上是纯经济损失,其计算也由国内法调整。不过,正如阿尔巴教授所说,都要适用《鹿特丹规则》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
四、第1条第13款控制方定义仅包含第50条控制权的内容,不包含第54条的与承运人变更合同的权利,有人认为控制方的定义窄了,应包含第54条的权利,是否正确
司玉琢教授认为,第54条所规定的其实是控制方的法律地位,即只有控制方可以与承运人协商修改合同,虽然这种地位也可以看成一种“权利”,属于一种资格性权利,但其本质上与第50条所规定的实体性权利显然不同,将其包含在“控制权”的范畴中是不妥的。另外,控制权强调其“单方权利性”,即只要关于控制权的指示合理,控制方就可以单方面行使,而不需要获得承运人的同意或认可,承运人有义务执行。而“协商修改合同的权利”,显然不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如果没有承运人的同意或认可,这一“权利”将无法实现。
贝林吉尔教授在同意司玉琢教授意见的基础上指出,定义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同一法律文件中重复对某人、某情形、某文件再进行详细定义。对某人而言,不是为了在定义的限度内限制其权利、权限。实际上,谁是控制方第51条中已有说明,控制方不仅有第50条规定的控制权,还有第54条、第55条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必要在定义中列举这些权利和义务,且不列举也不会影响权利、义务的范围。
阿尔巴教授也同意司玉琢教授的意见,他不认为第1条第13款的定义中未包括控制方与承运人协商变更合同的权利有任何不妥。
五、第66条第2款对承运人的诉讼,索赔方可以从协议中的多个管辖法院中选择一个,但是第75条协议仲裁地点,索赔方只能选择一个地点,不可能有多个仲裁地点,多个地点就是浮动仲裁条款,需双方协议一个地点,否则仲裁协议就是无效协议。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司玉琢教授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虽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仲裁地法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浮动仲裁条款事后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但国际上很多国家认为浮动仲裁条款并不能否认纠纷应当通过仲裁解决这一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公约第75条第1款,非常强烈地体现了“当事人之间一旦存在仲裁协议(包括浮动仲裁),争议就必须提交仲裁解决,而不能通过诉讼解决”这样一种立法倾向。况且,既然第75条第2款第2项规定那些当事人并未事先选择的地点都可以作为仲裁地点,不允许当事人在浮动仲裁条款所指定的多个仲裁地点之一提起仲裁似乎没有道理。总之,司玉琢教授认为,在《鹿特丹规则》下,如果当事人约定的是浮动仲裁条款或浮动仲裁协议,即便他们事后不能就仲裁地点或仲裁机构达成一致,争议仍必须通过仲裁解决;而仲裁地点,货方可以选择第75条第2款第2项规定的地点,也可以选择浮动仲裁条款中所指定的任一地点。
贝林吉尔教授基本同意司玉琢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第75条第2款没有要求在仲裁协议中写明仲裁地。仲裁地点如果写明,也许不能约束索赔方,索赔方有权选择第75条第2款第2项规定的任何地点,在仲裁协议中没有写明仲裁地时索赔方仍有此种权利。
阿尔巴教授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澄清第66条第2款并不赋予货物索赔方“在协议指定的若干法院中选择一个法院的权利”。第66条第2款只是说:即便有法院选择协议,该协议也不影响索赔方在第66条第1款规定的地点对承运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第66条第2款的效果只限于在货物索赔方可以选择的地点以外增加其他地点、法院,供索赔方选择。至于仲裁地点,他赞成贝林吉尔教授的观点。货物索赔方有权在第75条第2款中所列的地点中选择仲裁地,不论仲裁协议或条款(或涉及仲裁事项的规定、条款)中是否明确写明仲裁地或可预计的仲裁地(这种情况下适用第75条第2款第1项)。
六、根据公约第66条和第1条第30项定义,对承运人的诉讼,允许原告选择的法院只能位于在缔约国内;根据第75条的规定,对承运人提起的仲裁,允许索赔方选择的仲裁地点并不限制必须在缔约国内。这是为何
司玉琢教授认为这是仲裁自由原则的体现。公约第75条对仲裁地点给出了选择的范围,已经是对仲裁自由的某种突破,如果再强调这些地点必须位于缔约国内,这样的要求未免太高。
阿尔巴教授在查阅了起草过程中关于仲裁一章争议的总结报告(A/CN.9/576,A/CN.9/591,A/CN.9/616,A/CN.9/642,A/CN.9/645)后没有发现在讨论过程中有任何国家的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对仲裁方面的规定旨在杜绝带有妨碍性的、目的是为了不适用关于管辖权的规定的仲裁条款。这就是为什么把仲裁地点限制在第75条第2款所列的地点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索赔方有机会选择在可以对仲裁负责的地点提起仲裁。这样一来,索赔方选择的地点是否是缔约国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在管辖一章中,有权法院限制为缔约国的法院是为了确保在有义务适用公约的国家中分配管辖权。虽然这种规定本身不足以确保这种效果,但若第十四章规定的诉讼请求(对承运人或海运履约方之诉)未在缔约国审理(最终由索赔人选择),那么判决很有可能在缔约国得不到承认和执行。仲裁庭或仲裁员并不一定要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国的法律,在这一点和其他方面适用的规则就与国内法院适用的规则不同。仲裁中,仲裁地点决定仲裁地法——适用的程序法律,以及仲裁地所在国的法院执行、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利。虽然一些国家的仲裁地法对合同的准据法有影响,但是,一方面,基本原则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适用的法律,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时,仲裁员可以依据仲裁地国法律冲突规范以外的规定来决定调整合同的法律法规。不过,《鹿特丹规则》会作为调整合同的强行法强制适用。首先,仲裁地在缔约国内,可能仲裁地法会限制当事人或仲裁员选择法律的自由以防止规避强行性规则①尽管调整合同的法律的性质无关紧要,但在这些国家第十五章作为调整仲裁的法律,会成为仲裁地法的一部分,并作为特别法和国际公约一样,优先于国内的一般仲裁地法律适用。。其次,在其他(非缔约)国家,当事人或仲裁员决定适用什么法律来调整合同,仲裁员有义务保证裁决在别的国家被承认或不会被撤销,因此《鹿特丹规则》也可能会适用。所以,要求在缔约国内诉讼会剥夺货物索赔方在当前文本下的部分选择权,条文本身不能保证合同都由《鹿特丹规则》来调整,因为还要取决于仲裁地法的规定。条文没有这样要求但也不影响该公约作为强行法在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条件是第75条所列地点至少有一个在此非缔约国境内)的适用。
七、公约第66条和第68条分别规定了对承运人和海运履约方的诉讼地点的选择,除第71条、第72条规定外,第69条规定不得另增加管辖权地,该条并没有把第70条通过扣船取得管辖排除在外,这是为何
司玉琢教授认为,公约第70条规定的通过扣船取得管辖与《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第7条规定的扣船取得管辖有所不同,后者明确规定扣船地法院取得对案件的实体管辖权;前者规定扣船地法院不取得实体管辖权,除非满足一定条件。所以,公约第70条规定的通过扣船取得什么样的管辖权是不确定的,因缔约国不同,结果可能也不同。这一条款既不同于第66条和第68条的规定,也不同于第71条和第72条的规定。因此,第69条没有把第70条也排除,这与第70条的规定本身有关。
阿尔巴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第69条把第71条、第72条作为本条的除外条件,第66条、第68条作为仅有的决定国际管辖权基础的条款,这样就使第69条和第70条的关系很不明确。或者说,第70条的规定可能会基于合同和公约赋予法院对诉承运人的案件的管辖权。然而,第70条的目的既是澄清第十四章不调整对临时措施和保全措施的管辖权,又是为了避免与《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的冲突,所以就扣船取得对案件实体问题的管辖权这一问题没有涉及。第70条本身没有规定本公约内其他取得管辖权的基础,因此,从逻辑来分析,第70条不一定就参考第69条。换句话说,第69条规定“不得在不是根据第66条或第68条指定的法院,根据本公约……提起司法程序”(除非依据第71条、第72条的规定);但是第70条允许在根据其他公约(仅是《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获得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对承运人的诉讼。
八、第1条第10款,持有人定义是否包括“托运人”?结合第1条第8款托运人的定义,似乎不应包括。如果这样理解正确,那么,第1条第10款(a)(i)项中明确提到包括托运人以及第58条第1款的“非托运人的持有人”(a holder that is not the shipper)就是多余的了,同样的问题存在于第58条第2款
司玉琢教授认为,“持有人”的外延包括托运人,即只要托运人符合第1条第10款规定的条件,其当然也可以成为持有人。“托运人”的定义是界定托运人的标准,从中看不出其与持有人的关系,因而不能从托运人的定义得出其不能成为持有人这一结论。
阿尔巴教授赞成司玉琢教授的意见。托运人和持有人是不同的概念和身份。但一人可以兼为二者,这就解释了第58条的措辞。托运人在下列情形中也可以成为持有人。
第一,根据第1条第10款(a)(i)项,签发凭指示的可转让单证且,①托运人在单证中被记载为持有人,且提单签发后从承运人处取得提单(或从收货人、指示方处取得提单);②还存在一个单证托运人,且单证托运人持有单证时,托运人被记载为收货人,或者;③单证被背书给托运人(还存在一个单证托运人,或不存在单证托运人但单证在若干手背书之后又被背书回托运人),因而托运人持有单证。
第二,根据第1条第10款(a)(ii)项,若可转让单证被签发给不记名持有人或空白背书,托运人取得单证(不论是否在签发之后或有无进一步流转)。
第三,根据第1条第10款(b)项,依第9条述及的程序将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签发或转让给托运人。
九、第73条第1款“by a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under…”为何没有“competent”?第66条“(a)in a competent cour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第68条“in a competent cour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都有“competent”
司玉琢教授认为,不管是起诉还是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应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即都应是“competent court”,前后用词应该统一。是否可理解第73条中的“having jurisdiction”一词,已经强调了法院必须拥有管辖权,所以,前面不加“competent”也不影响前后一致。
阿尔巴教授同意司玉琢教授的观点。公约下有管辖权的法院(having jurisdiction,见第73条第1款,承认和执行)就是第14章第66条、第68条、第72条)中的有权法院(competent court)。
十、第46条第2项与第51条第2款是否是衔接的
司玉琢教授认为,第51条第1款托运人可将控制权转让给收货人、单证托运人或其他人,因此,第45条承运人规定的通知对象也是与第51条第1款相对应的,即控制方、托运人、单证托运人;然而,第51条第2款托运人可将控制权转让给收货人,且无须背书,却没有单证托运人,但在第46条第2项中却规定可通知单证托运人,这两条是不衔接的。应该在第51条第2款中增加托运人可将控制权转让给运输单证中指定的收货人、单证托运人。否则,在第46条第2项中承运人要求单证托运人发出交付货物的指示,就缺少权利的来源。
贝林吉尔教授不认为第51条第1款第1项和第45条中都提到单证托运人这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实际上第51条第1款相当于一个开放式列表,列明可以将控制权转让给哪些人,因为说到“单证托运人、其他人”后列表就结束了,第45条第3项是把单证托运人作为最后一个承运人可请求就货物的交付发出指示的人,这样列表也结束了。第51条第2款中没有提到单证托运人,因为该款适用于需要凭单交货的不可转让的单证,此时收货人被记载在运输单证上,托运人只能把控制权转让给他。因此,他认为第51条第2款的规定不需要变更。第46条第2项中之所以会提到单证托运人,是为了给承运人尽可能多的选择,以便于其交付货物解除义务,这一点从第46条第3项就能看出。
藤田教授也认为第51条第2款和第46条第2项不是互相呼应的。他提醒大家注意:第46条第2项中提到的人不一定都是享有控制权的人。第47条第2款第1项也是如此。没有必要为了使单证托运人变为潜在的控制权人而变更第51条第2款的规定。
兹尔教授同意藤田教授的观点。引入“单证托运人”的概念是为了处理FOB的案件,其中托运人是收货人,FOB的卖方是单证托运人。如果第51条第2款第1项适用于FOB的案件,那么“托运人”就自动变为单证托运人,否则这句话就意味着托运人把控制权转让给自己。出于这个原因,并为了使问题尽量简化,单独提“单证托运人”没有必要,且只会带来问题。
十一、第26条与第82条的关系,那一条款应优先适用
对这个问题,司玉琢教授有以下分析。
第一,公约第26条规定,海运前后的其他运输方式,在一定条件下优先适用调整该运输方式的强制性国际文书。这些条件包括:该国际文书对承运人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限制和时效有具体规定;不适用国内法;货物灭失、损坏,或者造成迟延的事件发生在非海运区段。就是说,造成货物灭失、损坏的原因(事件)发生在非海运区段,结果发生在海运区段,或者迟延的结果发生在非海运区段,原因发生在海运区段,仍然适用《鹿特丹规则》,而不适用非海运区段的公约。这种有限的网状责任制已经在《多式运输单据规则》(UNCTAD/ICC)中得到了使用,具备可操作性,而这种责任制也可以说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
第二,由公约条文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第82条是对《鹿特丹规则》与其他非海运公约适用冲突的一般性概括;而第26条适用范围相对较窄,在相关非海运公约有具体规定时方排除《鹿特丹规则》的适用,因此,可以总结出两条规定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但应当如何协调两条规定的应用,学者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指出:“第26条和第82条均为解决法律冲突的条款,当出现冲突时,首先应考虑是否适用第82条,因为所有的其他公约的相关条款可以优先适用;当公约仍然适用时,再考虑第26条限定的责任期间是否适用。”(Both articles 26 and 82 are articles to solve conflicts of law.When there is a conflict,first Article 82 has to be considered because all provi-sions of another convention can then prevail over the Convention.If the Convention is still applicable,then consideration has to be given to Article 26 to decide which liability regime has to be used.)[1]但也有学者认为:“当第26条与第82条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考虑第26条,因为第26条先被适用,而且第82条是第26条的补充。”(As regards the order in which articles 26 and 82 should be considered,it appears that Article 26 should come first,both because it has been the first to be adopted and because Article 82 has been adopted as a complement to Article 26.)[2]司玉琢教授认为,当出现适用的选择时,应首先考虑第82条这一一般性规则,进而确定货损的发生地点,以确定第26条是否适用。
第三,还有一点不同是,第82条规定只对公约生效前已生效的其他非海运公约有效,而第26条还包括了将来生效的法律文件。
第四,第82条仅规定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没有迟延交付。第26条的英文措辞有问题:“货物灭失、损坏或造成迟延交付的事件或情形发生在承运人的责任期内”应该是“货物灭失、损坏或造成迟延交付的事实或者造成前述损失的事件发生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内”。
贝林吉尔教授针对司玉琢教授的上述观点,依次分析如下。
第一,也许像第26条那样,首先规定何种期间内《鹿特丹规则》的规定不得优先于其它国际文书的适用这种方法会比较好,这里的期间是装货前和卸货后。接着,在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根据是货物的灭失或损害之诉还是迟延造成的损失之诉而有所区别,在前一种情形下,“事件”是灭失或损害,而在第二种情形下,“事件”不是迟延本身,而是造成迟延的事件。
第二,“第82条与第26条互为补充”,这么说是对的。如果这样的话,先考虑哪一条只是方便与否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哪一条更具普遍性不是很明确。事实上,第26条的适用范围不像司玉琢教授所说的“相对较窄”,因为与承运人责任相关的规定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诉讼中最主要的就是界定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大小和责任限制。另外,第82条是否满足“一般性规则”也不甚明了:在航空货物运输中可能是这样,但在公路货物运输中一定不是这样,因为该条只适用于船载车辆不卸货的货物运输;在铁路货物运输中也不成立,因为本公约只有相关公约适用于补充铁路运输的海上货物运输时才能适用;同样在内河航道货物运输中也不能成立,因为相关公约必须适用于不在内河航道和海上转船的货物运输。除此之外,正如司玉琢教授在第三点中所指出的那样,第82条只适用于本约生效前已生效的其他公约,而第26条在这一点上就有普遍的适用性,且正如第四点中所指出的,第26条可以适用于迟延的情形。综上,贝林吉尔教授认为,首先考虑第26条可能会更实用、更省时。
第三,贝林吉尔教授对第三点未作评价。
第四,贝林吉尔教授认为,公约现在的措辞没有问题。事实上,就灭失或损害来说,要考虑的是灭失或损害本身发生的时间,考虑引起此种灭失或损害的事件可能会产生问题,因为这些事件不总能被清楚地辨认。反之,对迟延来说,只有引起迟延的事件才有意义,因为迟延的效果可能发生在别的时间。
藤田教授基本同意贝林吉尔教授的点评,在第四点上又做了一点小补充。他与贝林吉尔教授观点一致,认为第26条和第82条的措辞没有问题。就第82条来说,即使在迟延的情况下其他公约也适用。第82条规定,法院可以适用“规范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的国际公约。《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满足这个条件,因为它规范“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如果还满足第82条(a)项的其他条件,那么法院可以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包括其对迟延的规定。第82条开头“规范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的措辞只是表明国际公约的性质。不是说第82条只调整货物的灭失或损坏问题。就第26条来说,“如果货物灭失、损坏或造成迟延交付的事件或情形发生在承运人的责任期内”这样的措辞是有意为之的。这样表述的意思是灭失或损坏本身发生在责任期内,而不是引起灭失或损害的原因。“造成……的事件或情形”是出于技术性原因而加进去的。不能说“迟延发生在……”,因为“迟延”与否是在最终目的地判断的(见第21条迟延的定义)。可以追究造成迟延的原因是否发生在责任期内,但不能追究迟延本身是否发生在责任期内。
兹尔教授表示,就《鹿特丹规则》与调整其他运输方式的公约的关系问题,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下已进行过无数次讨论,最终决定用第82条来解决公约冲突问题,第26条应包含实质性规定(其自身就有避免冲突的效果)。因此,从定义来看,首先考虑第82条以决定是否适用《鹿特丹规则》,这一点确定下来之后,再适用第26条,最终效果会是:其他公约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可能被适用。他赞成藤田教授的补充。
十二、第71条第2款“任何诉讼”是何意?是否应该与货方索赔属于同一性质的诉讼
司玉琢教授认为,该款中所指的“任何诉讼”,应指所有可能剥夺货方根据第66条或第68条选择法院的权利的诉讼,至于其“性质”为何,在所不问,即其不一定与货方索赔属于同一性质的诉讼。事实上,该款中所提及的“寻求不承担赔偿责任声明的诉讼”,主要是指确权诉讼,与货方索赔就不属于同一性质(前者属确认之诉,后者属给付之诉)。
斯特里教授同意司玉琢教授的分析。“其他诉讼”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第71条第2款所禁止的请求禁诉令之诉,即,承运人提起诉讼(通常在运输单证中记载的法院提起)要求获得一项禁令,禁止货物索赔方在根据第66条或第68条的规定选择的法院起诉。
他指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第71条第2款并不影响承运人提起独立诉讼的权利。比如说,承运人要求取得未支付运费的诉讼就可以在承运人选择的任何一个法院提起,当然还要受《鹿特丹规则》以外的其他规定的限制。
十三、海运履约方是否享有积极的权利
对这个问题,司玉琢教授有以下观点。
第一,公约第19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海运履约方必须承担本公约对承运人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且有权享有本公约对承运人规定的抗辩和赔偿责任限制。”根据此条,海运履约方仅享有消极的抗辩权,不享有积极的权利,即不享有索赔权、诉讼时效。
第二,公约第30条规定:“对于承运人遭受的灭失或损坏,如果承运人证明此种灭失或损坏是因为托运人违反本公约规定的义务而造成的,托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并没有提到对海运履约方的赔偿责任。
第三,公约第62条规定:“两年时效期间届满后,不得就违反本公约下的一项义务所产生的索赔或者争议提起司法程序或者仲裁程序。本条第1款述及的时效期间,自承运人交付货物之日起算,未交付货物或者只交付了部分货物的,自本应交付货物最后之日起算。时效期间的起算日不包括在该期间内。”这一规定应该解释为对承运人或货方均适用两年时效,不适用海运履约方的索赔时效。
第四,根据上述分析,海运履约方的义务和赔偿责任完全同承运人,但是权利仅仅是抗辩权。积极的权利仍然不适用《鹿特丹规则》,而是适用普通的法律。如港口经营人向收货人索赔,就不能依据《鹿特丹规则》作为准据法,而应以侵权为由,适用普通的法律。
斯特里教授基本赞成司玉琢教授的分析。他亦不认为《鹿特丹规则》赋予海运履约方对抗托运人或承运人的积极诉由。他承认海运履约方在准据法下享有肯定性权利。如果托运人的危险货物损害了仓库,仓库所有人(海运履约方)可以对托运人提起侵权之诉。当然还需要证明托运人有过错。肯定不能从《鹿特丹规则》的严格责任中获益。此外,在运输主合同下满足“海运履约方”条件的人可以因为分合同关系而享有《鹿特丹规则》下对抗托运人或承运人的权利。比如说,海运承运人可以成为运输主合同下的海运履约方。但在其自己与无船承运人的合同(该合同是无船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运输主合同下的分合同)中他是承运人,因此享有《鹿特丹规则》下对抗无船承运人的权利。
十四、第65条第2项如何理解
司玉琢教授认为,对被识别为承运人的人的诉讼,第65条第2项规定:“自识别承运人之日起,或自船舶登记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根据第37条第2款推翻其为承运人的推定之日起九十日内。”上述二者也应有“以较晚者为准”的规定。不过,考虑到“船舶登记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根据第37条第2款推翻其为承运人的推定之日”,要么早于“承运人被识别之日”,要么二者同一天发生,不可能晚于后者(不可能在已经识别谁是承运人的情况下还没有推翻推定),因此,可否考虑将该项后半句删除,直接将该项改为“自承运人被识别之日起90日内”?
藤田教授认为,第65条第2项“自船舶登记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根据第37条第2款推翻其为承运人的推定之日起”的规定是必要的。假设索赔方于5月1日根据第37条第2款的假设诉登记所有人。登记所有人于6月1日证明运输期间船舶被光租出去且指出光船承租人,推翻了假设。索赔方应该自6月1日起的90日内(截至8月30日)诉光船承租人。这样一来,承运人还没有被识别但时效期从6月1日起算。索赔方必须在8月30日之前起诉光船承租人。如果光船承租人推翻假设并指明承运人,则索赔方又多了90天的时间。但若索赔方在8月30日之前一直没有行动,诉讼请求就超过时效了。如果第65条第2项后半部分被删去,结果就会彻底改变。
斯特里教授同意藤田教授的意见,他认为,司玉琢教授提出的“上述二者也应有‘以较晚者为准’的规定”这个前提不正确。第65条规定了两个提起诉讼的时效期——一个是第65条第1款规定的,另一个是第65条第2款规定的。在二者之间适用较晚者。但是第65条第2款也规定了两个时效期——一个是自承运人被识别之日起,另一个是自假设被推翻之日起。在这二者之间,适用较早者。也许第65条第2款中明确写出适用较早者会使条文更明晰,但条文通常来说就是这么理解的。
[1]NEELS P.The Rotterdam Rules and modern transport practices:a successful marriage[J].Law & Transport Magazine,2011(4):7.
[2]BERLINGIERI F.Multimodal aspect of the Rotterdam Rules[C]//Colloquium of the Rotterdam Rules 2009,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