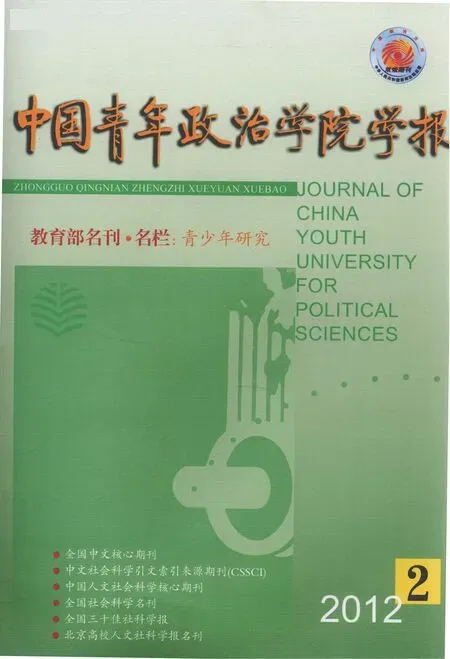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转型社区农村青年的代际交往
高 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重点抓好‘金农’工程和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这充分体现了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但是,除了继续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力度之外,笔者要继续跟踪反思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社会意蕴,即对农村包括家庭、邻里、社区等结构单元的影响何在?尤其是新媒体对于连接人与人之间在不同时空下的交往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貌的重塑。由此,学界探究新媒体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意蕴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一、新农村、新媒体:农村青年的新环境
(一)“新农村”特质影响农村青年的生活和流动
新农村建设使得各地农村普遍踏上了转型之路,因此,大部分农村社区在更宽泛的意义上都是一种转型社区。当然,这种转型相对而言是一种表面的转型,在这背后,是农村社区自身社区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区内人、物、环境等的变迁,尤其是这种变迁已然影响了农村青年的生活和流动。
1.农村青年的面貌和生活渐趋开放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经正确地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黄宗智先生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华北平原的村庄后也指出:“大部分的村庄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从这一角度来看,村庄是一个闭塞的,或许也是紧密的共同体”[2]。上述“地方性”、“封闭性”,主要是针对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农村而言,现在的农村社区则日益呈现出开放性、社会性等特征,只是各地程度不同而已。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农村改革日趋深入,社会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越来越弱,社区转型的速度不断加快。转型中的农村社区创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空间,它们超越了原先固有的地域、体制、身份等一系列社会边界,展示了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成长于转型社区的农村青年,其面貌和生活也越来越具有开放性,视野逐渐向外扩展,生活方式包括消费方式、休闲方式等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2.农村青年的流动趋向多元
单就职业角度而言,传统农村社区的职业主要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伴随着社区转型,传统社区的开放性逐渐变大,它们与外部之间的交往也日趋紧密,农民便逐渐成为转型社区中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而已。除此之外,一些人选择了在本地或者去外地务工,一些人则通过考学或者参军的方式变成了干部或军人,还有一些人则通过操办副业变成了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等等。因此,职业构成上的多元化日渐成为转型社区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农村青年的去向也更趋多元。除了在本地上学的学生一族外,不少农村青年选择在本地或外地打工,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村青年坚守土地,通过不断将技术与土地相结合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因此,总体而言,转型社区的农村青年有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不离土不离乡三类。尤其是对于那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村青年来说,除了学生这一特殊农村青年群体之外,那些脱离了土地,却并没有就业的农村青年往往成了闲散青年,包括这一部分群体在内的农村青年对新媒体的使用,以及对他们的代际交往所造成的影响,是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
(二)农村青年开始广泛接触新媒体
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对于使用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以及电脑、手机的操作能力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在使用群体中,年青人所占比重较高。而就农村青年这一群体而言,其新媒体使用情况主要有如下特征。
1.家庭是农村青年的主要上网场所
在农村社区,网民上网的场所主要有家庭、网吧、单位、学校等,其中,截至2010年12月底,家庭作为最主要的上网场所占比达85.5%,比2009年底提高了11个百分点,农村网吧上网的网民占比为40.5%,在单位、学校上网的网民分别占比为22.7%、20.6%[3]。而另外一项调查也显示,农村地区多数网民上网的地点是在自己的家中,其次是用手机上网和去网吧上网[4]。由此不难看出,农村网民上网的主要场所是在家庭中。
2.手机上网渐趋成为主要方式
手机因具有使用门槛低以及成本较低的特点,从而使其受到了农村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的青睐。因此,手机上网逐渐成为农村青年的主要上网方式。截至2010年底,农村手机上网用户为8,826万人,2010年农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达70.7%,比2009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就上网时间而言,农村手机网民互联网应用程度较深,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17.2小时,手机聊天和手机下载音乐是农村手机网民使用最多的网络应用[5]。显然,这种以手机为代表的网络文化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这种“虚拟在场”的方式已然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3.游戏、信息和即时通信成为农村青年网民上网使用的主要功能
网络作为一个技术平台,由于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各异,导致他们对网络功能的使用也不一样。就农村青年网民而言,游戏、信息和即时通信则成为他们上网使用的主要功能。例如,一位农村青年曾言,我主要是使用手机包月,这样可以上网,也可以打电话、发短信,比较划算。手机上网对我而言很好,炒股方便,还可以看看其他信息。我打电话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有事要说,时间都不长,几分钟就结束了。发短信有时候怕对方看不到,不放心。我每个月手机花费在70~80元之间吧,工资是每个月1,500元[6]。总体而言,农村青年对网络的使用较为偏重娱乐休闲,而对网络的应用并不充分,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二、新媒体语境下农村青年的代际交往特征
(一)“后喻文化”特征明显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文化从古至今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类。传统社会的代际交往是以“前喻文化”为主导的交往方式,老年人往往是年轻人学习的楷模,现代社会的代际交往则越来越具有米德所谓的“后喻文化”特征。米德认为,文化模式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制度的更迭导致的。互联网是当今世界最庞大的信息资源库,农民在理论上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更多更准确的致富信息,通过搜集广泛的致富信息,农民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从中选择合适的致富信息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但网络对使用者的受教育程度、技术使用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显然这对于核心家庭内的父代而言,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许多农民被排斥在网络的海量信息之外。而农村青年在此方面则具有相对的技术和知识优势。农民上网年龄结构严重偏于年轻化,农村上网的主力军是学生,这使许多农民不得不依赖学生来获取互联网信息[7]。
(二)与虚拟空间的交往多于家庭内的交往
网络无疑极大拓展了年青人的交往空间,网络即时通讯技术、网络邮箱、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形式的出现,使得农村青年的交往空间大大变宽。而与虚拟空间交往的增多,则意味着农村青年与家庭内的代际交往相应减少了,这似乎是一种零和游戏。在调研工作中,当问及其孩子现在做什么时,村民董××一脸无奈地说:“在家玩游戏呢,没上班,天天就在家里呆着。”而董××当时正一个人在忙着做煤球。另据一项调查显示,有31.4%的农村青年表示在网上会经常与陌生人交往,有51%的人偶尔与陌生人交往,由此可见,农村青年在网上与陌生人交往已成为普遍现象①参见刘倩生:《网络对农村青年生活方式影响研究》,湖南农业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这一数据至少说明了农村青年正逐步走出“半熟人社会”所构筑的交往关系圈,而把交往的触角通过网络进一步伸入陌生人社会之中。当然,此处所谓的与虚拟空间的交往,实则是与外部交往的一部分,只不过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实现的而已。当今,移动互联技术正迅猛发展,手机上网逐渐成为农村青年上网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技术则将年青人进一步从家庭环境内“解放”出来,使其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家庭之外的环境中交往。如此,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交往的相对减少。
(三)单向交往多于双向交往
当代农村家庭的代际倾斜已经不同于传统家庭。在传统家庭中,老一代在生活资源等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家庭的重心也必然朝着老一代方向倾斜;而今,农村青年多是80后,即使不是独生子女,家庭内兄弟姐妹的个数也比以往要少很多。父代给予子代更多的期望,将更多精力倾注在子代身上,但是,来自子代主动的交往却相比较少。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交往关系。一般而言,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共时段内,来自父代单向度的关心与呵护要比子代对父代的更多,这种情况以那些沉迷于网络之内的“网瘾”少年最为典型;另一种是历时段的,尤其是那些出门在外务工的农村青年,网络无疑方便了他们与家人的联系,但是,这也仅仅是提供了一种与父代交往的可能性而已。实际上,除了将定期打电话作为一种形式上的问候之外,子代对父代很少有其他的关心举措。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技术上的原因,受限于父代对网络技术如发短信等的使用能力,在外务工的农村青年也就很难采用“短信”等便捷的联系方式;另一方面,农村青年家庭道德方面的原因也不应被忽视。
三、新媒体的使用对农村青年代际交往的影响
鉴于以上所列特征,农村青年对新媒体的使用已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核心家庭代际交往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
(一)涌现“文化反哺”现象
在当下“后喻文化”特征明显的情况下,父代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子代习得了一些网络知识,并且通过网络获得一些信息,学者周晓红将这种“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年长者向年轻者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过程解释为‘文化反哺’现象”。例如,杜村的林文生考驾照时多次未通过,但是买电脑联网后女儿把模拟试题给他下载到电脑上,在练习了几天之后便以满分通过[8]。上述案例反映了新媒体的使用对农村青年代际交往的正向效应。
(二)代际交往的质量受到影响
基于前述,农村青年对外交往及与虚拟空间的交往显然比对家庭内的交往要更加频繁。因此,在核心家庭下,代际交往的质量便会受到相应地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沉迷于网络游戏中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网络游戏之中,往往连自己的学习和自身的生活都无暇顾及,更何谈与父代之间的交往。因此,这种交往从“量”上都很难得以保证,更遑论交往的“质”了。
(三)农村青年的家庭责任意识弱化
毋庸讳言,在一些农村青年身上,日益出现家庭责任淡薄的迹象。“啃老族”、“傍老族”等并没有意识到自身作为核心家庭的一分子理应分担一部分家庭责任。这种享受权利和分担义务之间的不对等,无疑增加了家庭内年长者一方的责任和负担,加重了父代的责任,这并不利于青年人的心理成长。部分农村青年家庭责任意识弱化显然受到网络使用状况的影响。
四、增进农村青年代际交往的几点建议
家庭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理性”的入侵之后,从21世纪初开始,又面临着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技术理性”的入侵,研究者有必要正视这种技术理性入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重建充满温情的家庭伦理,增强农村青年代际交往的活力。
(一)转变观念,互相学习
调查发现,年长的一代对电脑以及网络具有一种偏见性认识,忽视了电脑以及网络在传播信息、提供知识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而这种错误的认识无疑制约着他们对于网络知识的主动学习。因此,对于父代而言,要积极转变观念,正视网络的各种积极功能,并且敢于承认自身在网络技术应用上与子代的差距,积极向子代学习,理性顺应“后喻文化”的时代发展趋向。而作为子代,显然也承担着技术知识播种者的角色,要主动帮助父代了解并接触新的知识,消除他们对于新知识的隔膜感,帮助其享受网络知识带给他们的快乐和便利。这不仅能够增进双方的代际交往,同时也有助于建立长期的、持续的代际关系。
(二)注重伦理关怀
诺丁斯认为,关心其实是一种关系。过分强调关心作为一种个人美德则是不正确的。将关心者置于关心的关系之中更为重要。不管一个人声称他多么乐于关心,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创造了一种能够被感知到的关心关系[9]。这种关怀理论强调“关怀和被关怀”也是人的基本需要,对于农村青年尤其是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而这种关怀显然并不是指简单的说教式的“关怀”。伦理关怀倡导建立和维持一种平等、宽容、相互尊重、彼此充满关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农村青年的主体性和潜能能够得到发挥和肯定。所以说,这种伦理关怀,是走进农村青年生命世界的关怀,是充满人性光辉的伦理关怀,是提升双方关系品质的关怀,是两者之间的真正的互动、互惠、共生。
(三)以理解为导向,注重沟通的方式方法
交往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然而,在惯常的家庭代际交往中,并不是或至少并不总是以沟通、理解为目的的。对于父代或子代而言,往往以指责代替沟通,父代指责子女不听话,而子代则指责父代观念保守落后,管得过宽过严。这是一种暴力的语言,家庭中的许多代际冲突,往往起始于冲突双方的相互语言攻讦,随着语言暴力的螺旋式上升,最终以身体的暴力告终。这种沟通的方式方法无疑会导致交往的减少,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我们在此倡导一种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方法,双方不是相互指责,而是以让对方理解自己并理解对方为目的。非暴力沟通关注沟通中语言的组织与表述,强调在语言中灌注对他人的爱和尊重因子。它讲究的是一种理性、平等沟通,强调通过双方共同的友好对话,以协调双方的观点和立场,为冲突的解决创造积极的氛围。
(四)加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
鉴于在农村青年网民结构中,学生仍是最大的上网群体,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加入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核心点便是要提高媒体使用者对于媒体内容的接触、分析、评价的能力。而许多沉迷于网络游戏中的农村青少年却正是缺乏这种对媒体辨别的能力。在面对新媒体时,他们往往因使用过度而迷失了方向。虽然,减少了媒体接触的时间和频率,并不代表相应增加了与父代的交往,但至少提供了增加交往的机会。因此,提高新媒体素养,能够帮助农村青年在面对新媒体时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新媒体,让他们正确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学会明智地选择和正确地分辨自己所面对的海量信息,避免其消极影响,帮助农村青年正确利用媒体并处理好代际关系问题。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页。
[2]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划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http://wenku.baidu.com/view/3ba3169a51e79b-89680226dd.html
[4][5]宋红梅 王 丹等:《中国农村居民互联网接触状况研究》,载《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
[6]李红艳:《手机:信息交流中社会关系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手机行为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7]李 伟:《互联网发展对河北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和作用调查分析》,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年第7期。
[8]刘 娟叶敬忠:《农村互联网的拥有和使用——有关发展的思考》,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9]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基于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