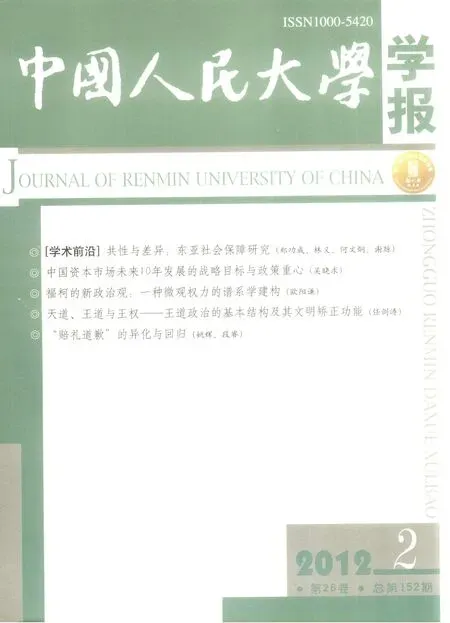福柯的新政治观:一种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建构
欧阳谦
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格局中,福柯的政治观无疑占有独特的位置。他专注于那些边缘性问题 (疯癫与精神病院、监狱与惩罚、性观念与自我塑造等),专注于微观权力的经验证明,由此而促成了一种微观政治的论证模式及其抵抗策略。他以权力谱系学为基础所作的现代政治分析,在遭到一些批评者 (如J.哈贝马斯、C.泰勒、M.瓦尔泽)的质疑和否定的同时,也受到不少新社会政治运动思潮 (如女性主义和同性恋斗争)的追捧。他的新政治观试图突破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主义逻辑,尤其是要突破以普遍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体系,由此而跳出近代以来的种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局限和盲区。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它不是围绕着王权,不是围绕着法律和禁令构造起来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砍下国王的头颅。这是政治理论中还有待完成的事情。”[1](P309)所谓砍下国王的头颅,就是不要再纠缠于那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而是要去关注那些毛细血管式的现代微观权力形式及其政治效应。国家机器当然重要,但是对于权力关系和权力技术的分析不能局限在国家机器的范畴之中。事实上,如果脱离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 (比如对于身体、性活动、家庭、学校、工厂、军队的治理技术),脱离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控制形式,国家机器的强大职能显然是发挥不出来的。从过去的封建专制时代发展到今天的议会民主时代,与传统的君主专制权力相比较,现代的微观权力控制形式更加隐蔽,当然也更加有效。因此,建构一种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应是现代政治批判的一个重要方向。
福柯从来就不承认别人给他戴上的各种 “帽子”。当有人将他说成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反驳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2](P22)每当有人说他是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隐蔽的马克思主义者、技术主义者或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时候,他总是否认这些说法,同时又承认他有些像这些描述所说的那样。但是,他终究还是明确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尼采思想的信徒,承认自己是在尼采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去分析和探询 “真理的生产”及其 “权力的效应”的,即研究真理或者科学是如何塑造和宰制我们的。权力—知识及其运作机制的微观政治问题正是福柯一生的牵挂。[3](P251)从 福 柯 的 权 力 谱 系 学 来 看, 他 的 思 想重心是放在对现代权力形式的分析和批判之上的。当我们用后现代政治思想家来定位他的时候,他那些多变的主题和打破学科界限的探索就有了一个理论的轴心。
一
政治问题和政治理论在今天的复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重新思考政治的本质,似乎构成了当今各种理论思潮 (比如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的基本走向。在这些思潮中间总是不断出现福柯的名字,因为他的微观政治理论已经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打上了很深的烙印。福柯确实是一位很难定位的思想家。如果仅仅按照固有的学科界限来进行归类,我们将无法把握他的思想走向。但是,如果我们从当代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就可能抓住他的理论逻辑。事实上,福柯后期的大量著述和访谈几乎都是在谈论和评析政治,政治问题就贯穿在他的理论探索之中,并且成为他的问题意识。他频繁地使用真理的政治、话语的政治、规训的政治、生命的政治、政治的技术、政治的干预、政治的策略等术语,在质疑传统政治观念的同时也阐明了他的新政治观。从福柯思想的变化曲线来看,他的理论探索大体上经历了从真理政治到权力政治再到伦理政治的过程。尽管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政治答案,但他始终都在挑战现有的政治观念。
我们自然会问一下:他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政治?他为什么要重新定义政治?他为什么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在福柯看来,1968年的法国 “五月风暴”开创了一个社会政治思想的新时代,随后在西方各国兴起的各种伸张群体权利及其生活取向的新社会运动 (诸如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反核运动和生态保护运动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人们对于当代政治实践的重新反思。“我认为60年代和70年代初发生的一些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中,我认为应该关注的一个事实是政治的变革、政治的创新和政治的实验,而这些运动都发生在重要的政党之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政党纲领。事实上,从60年代初期发展到今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变化并不是起因于政党的作为,而是由许多运动所带来的。这些社会运动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精神和态度,也改变了那些并没有参与这些运动的人们的态度和精神。这些变化是非常重要和具有积极意义的。”[4](P172)显然,这些社会运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政党夺权或者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而是表现出一些社会政治运动的新特征,即局部性的、分散性的、权利诉求性的、非阶级性的和非政党性的。它们并没有提出什么改造社会的宏大政治纲领,也没有什么夺取政权的具体设想。这些运动看似散乱和短视,但这不意味着它们的斗争就是盲目的和消极的。它们表现出来的反官僚和反等级的多元化诉求,确实反映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政治趋势。借用一些西方学者的断言就是:“在今天,政治的重要意义大多从政党的政治转向了运动的政治。”[5](P38)福柯正是以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同性恋性权利运动、监狱改革运动和生态保护运动等为例,强调了这些运动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实效性,并且力求用一种多元主义的政治立场来反思和评价这些新兴的政治斗争形式。从这个方面看,福柯的新政治观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政治经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当然,还有一个支撑起福柯新政治观的重要思想基础,那就是他在 “知识考古学”和 “权力谱系学”的理论探索中发现:现代社会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没有过往专制时代那样残忍和恐怖了,政府的管理已经取代了暴君的统治,但是其治理和宰制社会成员的技术手段却更加规范有效了。事实上,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完全被监管和被治理的社会,就像是一座 “圆形监狱”(Panopticon)。如果说过去的君主统治是依靠禁止和惩罚来维持,现在的民主制度则是通过科学和规范来实施。前者看起来非常的威严、血腥和暴力,但往往还是多有疏漏和比较脆弱;后者看起来既理性又文明,但却具有非常隐蔽和严密有效的权力触角。福柯的现代性批判之所以一直聚焦在 “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上面,一直聚焦在现代治理技术的政治问题上面,就是因为他认定现代社会看起来确实是 “合理化”和 “人性化”了,但是在背后对人的宰制和驯服变得更加彻底化和细密化了。只是借助于三个简单可行的治理手段,即“层级化的监视、规范化的裁决和程序化的检查”[6](P170),现代社会在将个人训练成为说话的主体、劳动的主体和生命的主体的同时,也使得这个主体成为一个被塑造和被驯化的客体。殊不知,在理性和科学的名义之下,现代社会建立起来一整套对于社会成员进行监督、管理、训练和惩罚的技术手段。从1961年发表 《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开始,到后来出版有很大反响的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福柯在质询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道路上走得愈发坚定。对于精神病院及其监禁机制的建立,福柯具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政治直觉:精神病学的实践其实是对理性的效忠,是在推行理性独裁,结果是科学被制度化为一种权力。精神病医生因为拥有精神病诊断和治疗的绝对话语权,由此掌握了对精神病人的生杀大权。知识带来了权力,而权力又制造了知识。“权力与知识直接就是相互包含的;没有构建一个相关的知识领域就不可能建立起权力关系,与此同时,离开权力关系的设定和建立也不会产生知识。”[7](P27)事实上,自18世纪以来,医学就具备了一种政治效应和政治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公共健康的政治纲领的实施,并成为国家干预的组成部分。
从监狱这个典型的惩罚场所和规训机构来看,它运用和推行的完全就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监狱这个场所要对被关进来的人进行彻底的监管和规训,其中包括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道德修养和精神状况等。在监狱里,细化的规则、烦琐的检查和随时的监督,都将犯人控制在各种程序的束缚之中。这种强制性的、身体性的、隔离性的和隐秘性的惩罚形式,取代了以前公开性的、集体性的和表演性的惩罚形式。英国近代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构想的 “圆形监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建筑,而且还是对完善的权力运作形式的图解。因此,监狱的微观化惩罚机制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司法之外的领域,如工厂、学校、军队等。在工厂和学校中所实施的管理培训手段,同监狱里面所实施的处罚措施完全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技术细节的政治解剖学才是透视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我们今天在研究权力的时候,必须要避免 《利维坦》的模式。”[8](P102)福柯的言下之意是不要只盯住高高在上的国王权力,只盯住庞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看到权力是弥散性的,是无处不在的关系网络。权力不仅仅是限制性的和压迫性的,而且也是构成性的和生产性的。我们需要同时看到权力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在现代科学知识的作用下,权力的运用不再是粗暴的和血腥的,而是变成了规范化和技术化的东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比较狭隘的传统政治观念。
从国家权力或者国家机器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这是既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所遵循的一种简单化逻辑。政治依附于国家而成为高高在上的东西,作为上层建筑而似乎远离了日常的生活领域。一般传统的政治分析只是关注宏观层面的权力运作形式,而且将权力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司法体系,即通过国家法律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禁止和制裁。在福柯看来,不能将政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国家问题和阶级问题,也不能将权力简单地与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联系起来,这样只能导致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的贫困化、空洞化。面对现实中的微观权力,尤其是面对现代社会中愈发完善的规训技术,我们需要扩大政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拓宽对于权力结构及其形式的认识。在研究疯癫和监狱的过程中,福柯发现必须弄清楚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权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9](P102)对于政治和权力的新解,需要从各种社会力量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政治其实就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和平衡而已,就是用来调节和引导各种力量关系的策略而已,甚至可以说,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因为社会总是充满了力量关系的较量和平衡。福柯的政治泛化和权力泛化的思路,正是他建构其微观权力谱系学的认识论前提。这种思路还引领和催化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政治思想,即将生活世界充分政治化的批判逻辑。尽管福柯不承认他是一个权力理论家,但是,他对权力的双重机制 (压抑性和生产性的作用并存)及其政治效应的技术性分析,还是最终帮助他确立了一种新政治观,即一种走向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的政治观。
二
对于福柯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转向意味着一种传统政治的 “终结”,即要告别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同时也宣告一种微观政治或者大众政治的来临。各种争取民主权利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社会还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大众的政治力量。现在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必须去揭示那些被掩盖起来的控制我们社会肌体的所有关系。我们应该弄清楚的是:我们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要以为权力只是掌握在政府机构、警察和军队手中,其实,政治权力的实施还要取决于一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毫无关系的机构组织,比如那些似乎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学校和医院。人们往往以为学校是一个最民主和平等的、传授和积累各种知识的组织体制,其实,学校是一个为某个阶级掌握政权而将其他阶级排除在外服务的机构。精神病院就直接帮助和支持了政治权力,它的功能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甄别和定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生成了监管权力的特有方式。它的政治解剖学,即一般用来制服各种力量和身体的公式和技巧被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机构和组织之中。”[10](P253)如果说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现代资本积累的技术,那么,社会管理的提升则促成了一种微观权力的政治起飞。这种微观政治的影响力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因为它隐蔽在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权力谱系学的政治目标就是批判那些看起来似乎很中立的机构组织,让人们看到那些暗地里起作用的政治暴力。只要人们“清楚至今社会机制是如何运转的,压抑和束缚是怎样进行的,这样,就可以自己决定并且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11](P50)福柯一再申明,他所建构的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其实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 “批判的存在论”,即从现实的政治问题出发旨在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治理技术及其微观政治效应。对于现代社会的种种批判,自19世纪以来大多只是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出发,而忽略了构成社会经济关系的那些基本权力关系。因此,我们还需要针对政治力量及其效应进行分析,这就是从权力关系入手来审视现代性问题。
什么是权力,权力是不是一种占有物?权力是不是一味地禁止和压制?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问题都是推动福柯建构其权力谱系学的缘由所在,同时也是他走向新政治观的思想基础。在福柯看来,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才使得我们认清了什么是剥削;因为有了弗洛伊德主义,才使得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压抑。然而,人们至今还不知道什么是权力,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观并没有看到权力的两面性,并没有穷尽权力实施的领域。“国家机器”、“权力集团”、“统治阶级”以及 “统治”、“领导”和 “管理”等概念都比较模糊,有待我们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剖析。我们必须看到,权力绝不是一种实体或者神秘的占有物。福柯认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的关系”。[12](P87)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重在关系上面。他说到权力的时候往往指的都是权力关系,而且这种权力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为它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换言之,权力只是存在于关系和行动之中。权力不是仅仅驻足在国王手上和国家机器上面,而是分散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所有方面。在社会的每个节点之间,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甚至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仅是国家统治权力对于个人的投射,而且也是统治权力得以扎根的土壤。当然,这些社会权力关系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简单延伸。男人并不是直接代表国家来统治女人,家长也不是直接代表国家来管理孩子。当我们对社会肌体的运转过程进行多方位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存在着十分复杂和多样的社会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公开的又是隐蔽的,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 “需要超越 《利维坦》的模式,在法律主权和国家制度的范围之外去研究权力,关键是要对统治的技术和战术进行分析”。[13](P184)通过观察学校、工厂、军队、监狱、医院、家庭等机构,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秩序是靠天罗地网般的权力关系来维护的。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就是要去探询在各种权力关系中隐藏得最深的是什么。这种探询一方面要追问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要揭示以学校和军队等亚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关系。
福柯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还看到了权力是如何与知识联结起来的。1971—1972年,他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 “惩罚理论及其制度”的课程。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各种权力关系(连同反对它们的斗争和维护它们的制度)不只是简单地起到促进或者阻碍知识的作用;它们不只是鼓励或者刺激知识,歪曲或者限制知识;权力和知识不是仅仅由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活动相互勾连起来的。因此,问题不是要明确权力是如何征服知识并让它为之终身服务的,或者权力是如何在知识上面打上自己的烙印,并且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限制强加给知识的。如果知识本身没有一个传播、记录、积累和交换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在其存在和作用中还作为一种权力形式与其他权力形式相连接,知识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知识的提取、占用、分配或保存,权力也是无法实施的。从这个层面来看,不存在知识与社会的分离,或者是科学与国家的分离,存在着的就是 ‘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的基本形式。”[14](P17)这段引述清楚地说明了福柯对于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反思。他正是在研究和写作 《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癫史》的过程中发现了权力与知识的内在关系。比如,在精神病院,医生扮演了一个主导者的角色,并且代表着权威和法律的形象。因为医生拥有别人没有的专业知识和医学技术,他对于疯子具有绝对的裁判权力,而这是一种被合法化和理性化的统治权力。正因为如此,他还担当起了捍卫司法和道德的责任。从精神病院的建立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不仅满足了资本的需求,而且适应了城市治理的需要。为什么资本和治理都要依赖于医学?这是因为医学提供了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模型。正如同患病人体需要进行医学干预治疗一样,它也为社会干预提供了一套理性的原则和技术。比如,现代刑罚制度就是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 “真理话语”而建立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除非具有了真理话语的权威,否则,即使是法律的规定也不具有权威性。”[15](P21)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其生产和传播都要与特定的权力体制联系起来。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生产它自己的真理,因为真理话语具有规范和统治的功能。
当然,福柯特别关注的是,权力与知识是通过什么形式结合起来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又是如何得以实施的。为此,他展开了 “权力微观物理学”和 “政治解剖学”的分析,其目标就是现代社会所推行的各种 “治理术”或者说各种政治技巧。绞刑架、火刑柱、断头台和五马分尸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司法化和规训化的监狱机构,当众行刑的刽子手也被监狱看守、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精神病专家、牧师和医生等技术人士所取代。这些技术人士负责对每一个人进行诊断和评价,其依据就是他们手中所掌握的那些规范化假设。什么人是罪犯,什么人是病人,什么人是反常者,等等,都可以由他们说了算,都可以由他们来进行划分和归类。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管理是有一套标准的,其实施是由各种严密而又细微的治理技术来达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治理技术的实施对象就是人的身体。现代的新型权力体制要将人训练成为 “听话的身体”,以便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人的身体被卷入到政治问题之中。现代权力关系对身体的控制和干预,与对身体的经济利用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生产力或者劳动力而言,“只有当身体既具备一种生产能力同时又是被驯服的时候,这个身体才会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16](P26)然而,在对身体进行施压和管控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对 “性”的调度和利用。从古老的乱伦禁忌开始,人类就对 “性”采取了全方位的管制。“我认为,性问题的政治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性处于身体的规训和人口的控制的交结点上。”[17](P312)在福柯看来, “性”从来就是权力—知识的一个重要实施场所。因此,他探询的不是与身体、欲望、色情有关的性冲动和性需要,而是与治理技术和自我技术联系起来的性话语、性规范、性行为、性身份。比如,现代社会对于 “性”就采取了这样一些强化形式:对于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 (认定女性的身体充满了性),对于儿童性行为的教育化 (采取许多预防措施),对于生殖行为的社会化 (人口生产的合法性标准),对于反常心理的治疗化。[18](P105)这些对身体的强化可以称之为 “生命的政治”,它们直接构成了现代权力的基础,从而保证了一个社会的正常和稳定。现代权力就是这样通过无孔不入的控制、全方位的监视、细致的生活空间的安排以及不间断的医学和心理学的检查,使得我们的身体及其行为被完全纳入到权力的网络和程序之中。
三
按照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是一个由各种人际关系交织起来的权力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就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遍布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人的一切都是在权力关系中生成的,包括人的身体、欲望、思想、行为等。换言之,人的各种身份也不过是权力—知识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权力—知识的关系网络及其监管技术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人的形象也是不断变化的。人并没有不变的本质,永恒的人性或者普遍的人性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人道主义的哲学纲领之所以是不成功的,就在于它坚持一种本质主义的人性观,相信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断定个人不仅是知识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的基础。然而,人不过是知识的基本排列变化的产物,不过是社会规范的结果。“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表明,人是近期的一个发明,而且也许正在接近其终点……人就像在海滩上画出来的脸面一样将会被抹去。”[19](P422)福柯自始至终都不相信关于人类解放的各种理论学说及其神话,也不相信以超越和摆脱权力为目标的各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拒绝了传统的关于权力分析的经济学模式和心理学模式,力图用尼采的 “权力意志”学说取而代之。循着尼采的权力主义逻辑,人类只能在权力意志的 “永恒轮回”里面打转。所有人都跑不掉,都要被权力所捕获,无论是权力的实施者还是权力的接受者无一幸免。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围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福柯就这样似乎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人类解放的死胡同里,看不到自由的前景,看不到理想社会的希望,只能坐在权力的铁笼中叹息。有不少批评者认为,福柯只是用他的 “抵抗政治”来抗议现实的不可容忍之处而没有提供什么答案和选择。例如,M.瓦尔泽这样评价说,福柯只是在 “大骂铁笼的栅栏,但是,他并没有任何计划或者纲领欲将铁笼变成一个更像是人类家园的地方。”[20](P239)福柯的新政治观显然没有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替代性纲领,那是因为他不想再掉入传统政治革命的怪圈里面,即用一种新型的权力机制来取代陈旧的权力机制。用他的话说:“或许今天的任务不是去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要拒绝我们是什么……我们时代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哲学的问题不是将个人从国家解放出来,不是将个人从国家机构中解放出来,而是要将我们同时从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系的个体化类型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拒绝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个体性,由此而促进各种新型主体性的出现。”[21](P134)
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辨析福柯的新政治观及其抵抗策略。一方面,福柯从微观权力的运作机制着眼,强调权力关系是伴随着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只要社会关系存在,权力就要发挥作用。即使我们砍下了国王的头颅,权力关系依然存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是去推倒国家机器及其统治集团并不会触动权力的现实基础,我们依旧要深陷在学校、医院、工厂、军队、监狱的监控体系之中。正如当下各种新社会运动所呈现的那样,如果革命的问题不再以过去的形式来推动,那么就需要再造一种新的政治代替形式。另一方面,福柯认为,今天这个时代不再有 “一般的知识分子”(即代表着普遍真理和永恒正义的知识分子),而只有 “特殊的知识分子”(即从局部领域进行批判和实践的知识分子)。[22](P126-133)这种知识分子的特定作用就是:“摧毁本质和普遍性,从当下的迟钝和约束中找出薄弱之处,找到力量的出口和路线,不断地改变想法但并不知道确切的方向在哪里,不知道明天将会遇到什么,关注我们的现状,无论怎样都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值得为革命付出代价?”[23](P124)既然我们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形式还是日常化的和隐蔽化的,那么,我们对于这种权力关系的破解和抵抗就必须是局部化的和平常化的。福柯始终认为:“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落入权力的圈套,我们总是能够通过明确的策略来改变它的控制。”[24](P123)权力与反抗是并存的,或者说,我们随时都要遭遇现实中的权力关系,我们随时都要做出选择:是认可还是质疑?是忍受还是抵抗?选择抵抗就是对于权力的实践批判,就是一种自由的实践行为。永恒的抵抗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它可以是游戏的也可以是严肃的。说“不”或者进行否定,就是一种最日常的抵抗形式,但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抵抗形式。“我们总是有各种可能性来改变我们的境遇。我们不可能跳出周围的环境,因为你无法摆脱所有的权力关系。但是,你总是能够去改变它……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着各种改变的可能性。”[25](P167)显然,福柯并不是一个完全悲观的批判哲学家。
人有没有可能走向自由?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弄清自由的概念。在福柯的眼里,卢梭式的原生态的自由 (人生而自由)、斯宾诺莎式的知识论的自由 (人认识必然即得到自由)以及马尔库塞式的终点性的自由 (人消除异化而得以彻底解放),都是非历史主义的自由观。自由其实是一种历史所规定的可能性。它不是一种可以占有的实体,而是一种可以变化的关系,就如同不断调整的权力关系一样。它不是一种我们要为之奋斗的最终理想状态,而是一种存在于抵抗和逾越之中的日常实践。福柯结合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自身的同性恋实践,再加上他后来对于古希腊人性观念的发掘研究,最后提出了 “生存美学”这样一个立足于身体政治的抵抗策略。围绕着身体,围绕着性,我们可以逾越权力的限制,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生命。既然灯饰和房屋等都可以成为艺术品,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一件令人陶醉的艺术品呢?福柯之所以关注身体和性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他发现,既然身体和性从来都是微观权力的监控对象,那么,让身体和性得到更多的快乐不就是一种动摇权力的抵抗策略吗?“性是我们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我们自由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性是某种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东西——它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我们必须借助我们的欲望,通过我们的欲望来认识各种新型的关系、各种新型的性爱和各种新型的创造。性不是一种宿命,它是一种走向创 造 性 生 命 的 可 能。”[26](P163)古 希 腊 人 通 过“关切自身”的伦理行为,不仅打通了美学与生命的连接道路,而且还打破了美学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古人的积极模式说明,我们可以通过自愿的行为将自己变成一个独特的生命存在,变成一件个性化的艺术作品。福柯的生存美学也大体遵循了当代西方哲学中盛行的审美救世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新政治观似乎就是要落脚在 “生存美学”之上,其目标就是要撕开权力之网,用身体实践来塑造自己多样化和风格化的生命形态。这种身体实践一方面要抵制强加给我们的旧的主体形式,另一方面要发明我们的新的主体形式。针对微观权力的运作机制,我们只能采取微观政治的抵抗策略。权力关系开始从哪里围剿和打击我们,我们就开始从哪里去抵抗和逾越权力关系。今天的女性主义运动和激进自由民主运动,正是吸收并发挥了福柯的微观政治思想及其抵抗策略;今天依然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左派政治运动,也从福柯的新政治观中寻找思想资源。或许这些就是福柯政治思想的实践意义之所在。
[1][17][21]Michel Foucault.The Essential Foucault: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Paul Rabinow and Nikolas Rose ed.New York:The New Press,2003.
[2][3][9][11][23][24]Michel Foucault.Politics,Philosophy,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Paul Rabinow ed.New York:Routledge,1988.
[4][14][25][26]Michel Foucault.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Paul Rabinow ed.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
[5]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ther.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6][7][10][16]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New York:Vintage,1979.
[8][22]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Colin Gordon ed.Brighton:Harvester,1980.
[12][13]Michel Foucault.Dits et Ecrits.Vol.Ⅲ .Paris:Gallimard,1994.
[15]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Gallimard,1971.
[18]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78.
[19]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London:Routledge,1989.
[20]Michael Walzer.The Company of Critics:Soci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Peter Haben,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