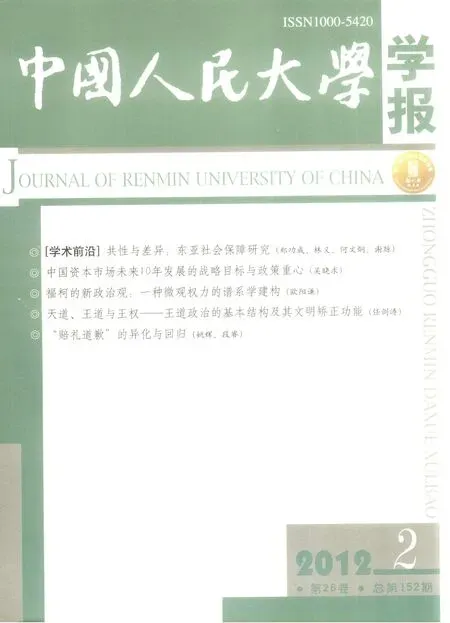“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冷成金
一种哲学的立论方式历来关涉这种哲学的性质、价值和意义。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人类所有高级的思想,正是起源于对死亡所做的沉思、冥索,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哲学与每一种科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1](P113)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共识。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道哲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审视死亡问题,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以“向死而生”的方式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与海德格尔将死亡提到本体论高度的“为死而在”的存在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未知生,焉知死”——由悬置到践行
一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鬼神有无和死亡问题悬置而不探究,立论方式是“存而不问”,其主要依据是《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下文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中国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与西方语言大不相同,索绪尔所谓能指与所指之联系既任意(自由选择)又强制(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为基础)[2](P103)的观点在此并不适用。因为《论语》的许多语言根本不是所谓的科学性语言,也并不完全是后来的形象性语言,毋宁说是具有原型隐喻——隐含着文化原型——性质的有意味的符号。对这种语言由能指求所指,有时如缘木求鱼。如果从原型隐喻的角度来看,该章恰恰隐含着对鬼神有无和生死问题的终极解决方式。
鬼神有无和死亡是并非同类却又相通的问题:鬼神可从有无的角度去考察,而死亡则是必有;但鬼神有无之不可论证与死亡之不可体验又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死亡如可经验,鬼神有无自可明辨。两个问题在《论语》同一章中一并提出,是古人对此长期思虑的自然表现。该章隐含的意思是:如果有鬼神,则必定先侍奉鬼神;如果能够了解死亡,则必定先去了解死亡。其真义是祈求为人的存在找到依据。孔子的回答则隐含着这样几层意思:(1)人生的要义乃至全部意义就在于“事人”和“知生”,不必问鬼神、死亡之事。(2)尚未做好“事人”、“知生”之事,就不必问鬼神和死亡的问题;即便做好了,也未必要问。(3)人很难做好“事人”、“知生”之事;如果真的做好了,就超越了鬼神和死亡,这个问题也就不必再问。(4)鬼神和死亡是不可靠和不可知的,不能作为人的存在依据;人只能面向鬼神和死亡,自我作祖,选择“事人”与“知生”,进入以彻底的悲情为底色的悦生乐世的开放境域。
《论语》还有很多章涉及这一问题。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篇》)这里仍然不谈鬼神的有无,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仅是对王孙贾乡愿面孔的鄙夷,更是对人与鬼神关系的宣示:人生全部和唯一的任务就是追求“仁”,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篇》)人与鬼神的关系就是人与鬼神没有任何关系,探究鬼神的有无不是人生的应有之义。死亡是否可知的问题也随之而解:“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人生的意义在于“闻道”,死亡作为一种无定的必然,对人来说并无意义,因此不必了解。
然而,孔子并没有否弃鬼神和死亡,相反,鬼神和死亡是其哲学的起点。人被毫无来由地“抛”到这个世界上,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二者互为因果),人因此陷入绝对的虚空。这造就了极富中国特色的悲剧意识——没有斗争对象乃至没有屈服对象,这是绝对意义上的悲剧意识。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那也是悲极而乐(选择乐)的文化。面对人的有限性(死亡)和人的空虚性(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孔子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在彻底的悲剧底色上,儒学选择的是生,是人自身毅然的崛立:“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至北宋张载则将此意发挥到极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死亡可以置之度外,“立命”乃是根本。人生的意义被规定为求“仁”,因此死亡可以被超越(不是被忽视)。这是儒学“向死而生”的真义。
但鬼神是可以被“利用”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篇》)祭祀导向的是心理的“诚”,有着培养人性心理的巨大作用。“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论语集注》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可“利用”而不可相信(相信则为迷信),正是实用理性(非实用主义)的态度。
鬼神和死亡的问题看似被悬置起来,实则在践行中得到了彻底解决。只是这种解决方式不是理性的认识论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存在论的,而是实用理性的。实用理性的基本特点是“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3]它在历史实践中建立起来,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阶段,关注人类总体,并以人类总体为思考一切问题的根本依据;它基于经验,重视经验,但不囿于经验,而是总结经验,并从中提升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使之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它将当下的心理看做人的目的,此心理不单纯是人的动物性心理或道德观念,而是二者有机融合并指向境界提升的情理结构。实用理性不去探讨世界和价值的本源,而是以可把握的人格境界取代之,从而斩断了探讨本源性问题与人格修养之间的联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正是在上述思维方式观照下作出的论断。在这里,孔子没有设定一个外在的本源性概念进行推导,也没有走向纯粹的人的“内感觉”,而是根据普遍的社会现实和经验,总结出对待鬼神和死亡的方法和态度,并以此作为建立人生价值的原点。
二、“朝闻道,夕死可矣”——意义与生死
孔子不仅不讳谈死亡,还刻意将死亡时时拈出,通过端正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范导人生,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丧葬之礼。“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这固然是对待别人的死亡,但这种规范建立起来以后,自己的死亡也会被如此对待,而且这也应该成为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面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而是平和地乐生顺死,一生尽礼,死而后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论语集注》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丧尽其礼”、“祭尽其诚”解得极好。丧礼是人类觉醒和自我确认的一种形式,可以培养人性心理,建立价值意识。有关丧礼的规定并不是外在的硬性的规定,而是符合人的心理情感的必然选择。谨慎地办理丧事是孝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人性心理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可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祭思敬,丧思哀”,丧礼之哀源于自然血缘基础上的人性心理,而祭祀祖先的感情则应是由诚而敬。祖先逝去已久,很难引起哀思,但人要以真诚的态度相信祖先,并起敬畏之心,从而不敢肆逞己意私欲。如果说“丧思哀”是内在建构,“祭思敬”则是外在约束。所有面对死的“慎终追远”,都是为了生的“民德归厚”,而且前者是价值建立的依据。这固然首先是群体意义上的“向死而生”,同时也是对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基本要求。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的命题将上述的“向死而生”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人生的全部意义被规定在“闻道”上,生死与价值的建立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死亡是可以被超越的。该命题隐含的深意还在于:正是因为死亡规定了人生的有限性,才给人以超越死亡的冲动,也为超越死亡提供了可能;一旦人是永生的,超越死亡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闻道”也就不会成为人生的必然选择。死亡是人生价值的起点和原点,而超越死亡是人生的根本目的。西汉刘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世不寤者也。”(《新序》卷一)唐代李翱说:“《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复性书》)人生意义与生死的关系就此被彻底定格。
《朱子语类》卷二六“朝闻道章”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基本合乎孔子的原意,可解许多疑问。兹摘数则如下:
问:“朝闻道而可夕死,莫须是知得此理之全体,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谓闻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须是知得多有个透彻处。至此,虽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谓:‘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须是实知有所得,方可。”
“‘朝闻道’,则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闻道,则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无纤毫不合道理处,则死如何不会是!”
“此闻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闻道,故虽死可也。若以听人之说为闻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谓枉死了!”
“知后须要得,得后方信得笃。‘夕死可矣’,只是说便死也不妨,非谓必死也。”
有一则需要特别拈出:“问‘朝闻道,夕死可矣。’曰:‘若是闻道,则生也得个好生,死也得个好死。’问:‘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闻而非久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犹愈于不闻。’”此人问得过于“形而下”,“犹愈于不闻”的回答却极为睿智。朱熹的意思是说,如果将孔子的话理解成闻道即死且有悔意,比不闻道更不堪。“闻道”并不必然与生构成矛盾,相反,只有生才能“闻道”,因此孔子誓言“守死善道”(《泰伯篇》);“闻道”也绝非一语之悟,而是毕生的生命实践,是内心感悟与外在实践合一的渐进过程。这与乡愿式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使那种欲陷仁者于死地的想法无隙可乘。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是“向死而生”这一理路的必然结论。既然死亡不可知,鬼神不可靠,人只有依靠自己,人是天地间最主动也最生动的因素,因此,在人与道的关系中,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也是同样的理路。人生来未必愿意“弘道”和“欲仁”,却必须“弘道”和“欲仁”。从人类社会总体来讲,这是人的必然选择,否则人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同时,因为死亡和鬼神的不可知和不可靠,“道”、“仁”等概念就失去了绝对性和超验性,被定位在实践的开放境域中,被维系在人的温暖的情怀里。这是真正的非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建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精义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讲,孔子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突破思想桎梏的作用。至于封建统治者将孔子的思想解释成政治意识形态,那是另一个问题。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论语》中对死亡与闻道的关系还多有涉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篇》)“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宪问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篇》)“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篇》)“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篇》)至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则补齐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在现实情景中所有的实践细则。
“闻道”不是为了体味死亡,而是为了达至人生的审美状态,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人生进阶。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朝闻道”一章“记”曰:“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是为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4](P107)这大概是受宋儒的影响。《论语集注》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张载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其实宋儒之学与孔门儒学相去甚远,多掺杂了佛家思想。孔门儒学“深情感慨”有之,但“生烦死畏”不多,更不“顺事安宁”,而是执著现实,勉力践行,深情追询,超越死亡。
三、“不怨天,不尤人”——人的自足性
人的自足性是指价值完全依靠自己而建立,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孔门儒学不信仰鬼神,人无原罪亦无原善,一切都是面对死亡——人生有限性——的自我设立,因此人具有最彻底的自足性。
与孟子具有先验色彩的性善论不同,孔子并未将人性规定为任何东西,而是把人性看做是在实践中养成的过程。从《论语》可以清楚地发现,孔子是将人性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的社会性,一是人的动物性。“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好德”是人的社会性,而“好色”则是人的动物性。人只有不断地克制自己的动物性,才能提升其社会性,才能达至“仁”。当然,动物性与社会性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动物性是基础,社会性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性心理培养而不断生成的。但是,“好德”的动力在哪里?鬼神既不可信,人性善恶就无依据。问题还在于,何谓善恶?从人类总体的角度讲,一个人的贡献多于索取,谓之善,反之则是恶。因为只有贡献多于索取,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反之则是倒退和灭亡。因此,人生来未必是“好德”、“性善”的,却必须是“好德”、“性善”的。“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篇》)“性相近”不仅是说人有着相近的动物性,更是说人有自己必须和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使人性相近;“习相远”是说在后来的生命实践中未必能坚持同样的选择,即使有同样的选择,实现的成就和达到的境界差别也很大。“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篇》)是说只有正道直行才是人生的本分,但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灾祸罢了。这其实是说性善才是本分。人性之善是应然的,是人在无外在依傍背景下的彻底的自足性的选择。
于鬼神无所待,于人是否可待?“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不怨天,不尤人”是说不去、不应该也无法怨天尤人,这是对上天(鬼神)和人(他人、社会)的绝待,是对外在因素的剪除,是对人之自足性的确认;“下学而上达”是进德的方式,是从践履到超越的路径;而“知我者其天乎”则是人格的最终归宿,是“上达”之所。这里的“天”是虚灵的(此“虚灵”出自朱熹《大学集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具有“客观社会性”的合理性,是李泽厚先生倡言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历史”。
绝待之时,便是境界的开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篇》)既然生与死、贵贱与穷达是人所左右不了的,那就把它交给命运和上天。在理性的极限处,孔子的儒学止步了。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孔子没有勉强,而是将其交给“命”和“天”——纯粹中国式的自然而然。这种自然而然与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努力无关,于是,一切有待都被否弃,在绝待中,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那些不能用道德境界观照的“命”、“天”与人无关,可以也应该悬置不顾,可用道德境界观照的“命”、“天”则化为建构道德境界的精神资源,人生的境界因此豁然打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境界的打开绝不意味着对“死生”、“富贵”之类现实问题的否弃,而是在执著中实现了超越,指向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理想。
在具体的现实情景中,人的自足性有着各种表现形态。“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篇》)“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可贵,但那仅仅是人的志气和修养,是在某个问题上的特定表现,还不是做人的根本。按照古汉语互文的修辞手法,“贫而乐,富而好礼”可理解为无论贫富皆乐道好礼。这说的是人的应然的常态,是做人的根本。之所以后者高于前者,是因为从前者不一定能推出后者,但从后者一定能推出前者。乐道好礼是不受贫富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的,因而是人的自足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说的也是此意。
内省在孔门儒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人在绝待的自足状态中,只有依靠自觉的内省,才能提高道德境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内省是儒家文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培养和建构人性心理的基本路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篇》)中国人无宗教性的原罪感,所以无内心之忧惧。有所忧者,乃道之不行(此为“客观之忧”,与对宗教原罪的“主观之忧”不同);有所惧者,乃德之亏欠。因此,知命不忧,足德不惧,内省不疚。这不仅充分展现了道德修养的自律性、自觉性和自足性原则,也充分显示了人独立于天地之间的精神。至于孟子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更显英雄气概。
四、“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向死而生”的转向
在前文,我们讨论了孔子思想对鬼神和死亡的绝待,把人的价值、意义归结到“仁”。但“仁”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建构,对于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讲,它还须有一个终极的着落处,那便是“天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篇》)“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篇》)“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何为“天命”?“天”最初有其超验性,在《尚书》中有充分表现,如超验的善、超验的正义、超验的监督与惩罚等。但这样的“天”在《诗经》中受到了抱怨:“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大幠,予慎无辜。”(《小雅·巧言》)孔子则基本上抛弃了外在超验的“天”,将之改造成了“天命”。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典籍”,为理解孔子的“天命”提供了路径。其中《性自命出》篇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乐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诗、书、礼、乐,其始皆生于人……理其情而出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得于中者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这里提出的“道始于情”的思想和天—命—性—情—道—教的理路,非常符合中国哲学—文化的基本事实。
何谓天、命、性、情、道、教?“天”是宇宙总体,是物质与超物质、情感与超情感的总和,是物质情感化、情感物质化的统一体。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最终的物质—精神依托,它拒绝理性分析,只要情感认同,因此是绝对的;它又不是超验或先验的,不是宗教,其绝对性是由经验积淀而来的,与现实情感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因此,“天”是一种“社会客观性”。
“命”具有个体意义上的无定的偶然性,但因“自天降”,必然具有超越偶然的品格。因此,人类总体的必然谓之“天命”,了解并奉行这种必然叫做“知命”;如果将人类总体的必然机械地照搬到个人命运上,则谓之“宿命”(如就总体或长远来讲是善有善报,但对具体的个体来讲未必如此)。君子知命是指对人类总体的光明前途与个人为实现这种光明前途而必然遭遇的命运坎坷有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孔子的“天命”与“知命”的意义。
“喜怒哀乐之气,性也”,此“性”具有很强的动物性色彩,即人的自然性,它需要在“命”的指导下将“喜怒哀乐”的内容人化,明辨是非善恶,充分培养人性心理。此种人性心理的显现便是“情”,“道始于情”,由这种情而产生的社会规则便是“道”。宣传此道并培养人的遵道之心谓之“教”。
这一理路在现实中的顺序是:由教而遵道,因道而生情,因情而定性,因性而知命,因命而依天。《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是此意,但少了核心因素:情。在天、命、性、情、道、教的逻辑链条中,情是基础与核心,无此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情,一切将归于虚无。为使此情有所着落,建立起天、命;为使此情得以培养,建立起道、教。这是一个以情为核心,由现实践行到形而上超越,以形而上超越观照现实践行的完备的哲学—文化体系。它是人的归依,也最终落实到人。人完全可以在其中得到永恒,但它始终不涉及鬼神和死亡这一人类不能回避和人情不能逃避的问题。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独不畏鬼神和死亡,这正是面向鬼神和死亡的生(以人情为本)的转向。这种转向从《尚书》中对超验之天的信仰,到《诗经》中的怀疑,再到孔子的否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哲学突破”时期,孔门儒学终于以“向死而生”的方式建构起这样一个体系。
“子畏于匡”等事是“向死而生”转向的生动体现。《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可见当时情势之危急。其中孔子的话见《子罕篇》,《论语集注》在该章下注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后死者。言天若欲丧此文,则必不使我得与于此文;今我既得与于此文,则是天未欲丧此文也。天既未欲丧此文,则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孔子世家》又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今天看来,孔子循环论证“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的方式很滑稽:他好像把上天看做是具有无限能力的人格神,又把自己掌握了礼乐文化看做是上天不想消灭礼乐文化的证据,因此得出了匡人、桓魋不可能伤害他的结论。其实,无论是孔子还是颜回,他们所表现出的巨大自信,不是基于相信人格神意义上的上天,也不是虚幻的自我安慰,而是基于与天命(社会客观性)相通的人格境界。这正是超越鬼神和死亡,将人生最终着落到“天命”的“向死而生”转向的极致体现。
五、“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面对有限性的审美人生
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相比,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在“向死而生”的转向上没有那么多准宗教的意味,更多的是审美超越的色彩。
没有人像庄子那样对人的有限性给予了那样多的关注。首先,庄子对死亡的认识是“唯物”的、方法是“辩证”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这是说生死是物质性的、连续的、互为始终的,既然如此,就应当齐一生死。其次,庄子多次谈到死亡的必然性,认为死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庄子·盗跖》)“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对此的态度当然是“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第三,时空的无限性强化了人的有限性。在庄子看来,宇宙空间是无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庄子·应帝王》)“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庄子·逍遥游》)“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庄子·秋水》)时间也是无限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齐物论》)“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庄子·则阳》)庄子对宇宙无限性的感悟是深刻的,面对无限的时空,他感叹道:“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庄子·知北游》)“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在《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一段中,庄子更以悲凉孤独的笔调表现了人在宇宙中的渺小。第四,宇宙的合目的性彰显出人的无目的性。“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庄子·秋水》)万物没有单一的目的性,但其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性,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齐物论》)正是这个意思。然而,人的目的性在哪里?合法性又在哪里?
庄子对人的有限性的考察十分深刻,是先秦时期人的理性觉醒的产物,所提出的问题也是人所无法回避的,至今仍然不能得到圆满的回答。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给出上面的罗列,就是为了说明庄子哲学的起点是在人的有限性上。而对人之有限性的理性考察,是人类文明史上“哲学突破”时期的共同特点,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样,只是庄子在先秦诸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在“哲学突破”同时也是哲学转向的历史过程中,以理性考察始,但未必都沿着理性的思路前行。庄子在面对理性无法超越的人之有限性时,“向死而生”,转身建立起“美”的人生哲学。庄子的方法很简单:人的有限性是“有待”的,只要“无待”,人就能超越,就能获得自由。“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这是最典型的“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紧接着的结论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就是无待的意思。在《庄子》中,“无待”、“自然”、“齐一”、“逍遥”、“物化”等都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如:“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这是无待的超越、自由、审美的状态。
“无待”与物性的自足是一体两面。分析《逍遥游》一篇可以看到,不是大鹏、蜩、学鸠、大年、小年等没有意义,而是相互比较没有意义;它们的意义不在于进行有参照物的比较,而在于“无待”的“逍遥游”,这就是事物的自足性。“逍遥游”就是对其“自性”最充分的尊重,也是其“自性”最充分的显现。事物的“自性”则是在具体历史情景中最合理和开放的内在因素的集合。《庄子》反异化的思想就在于此,其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原动力也在于此。“逍遥”的态度,正是对一切有限性——最根本的是死亡——的审美超越。
以理性考察始,以实用理性解答终,这是庄子哲学的理路。庄子哲学不是逃避现实的哲学,相反,是突破束缚、反对异化的哲学。但在现实中,则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以“坐忘”来消解烦恼,消弭斗志,则庄子哲学是消极的;以“逍遥”来睥睨尘俗,建构高洁的人格,则庄子哲学是积极的。然而,庄子哲学的意义远不止此。
“无待”的哲学不是虚无的哲学,它为我们提供的“逍遥”境界仍然立足于现实,是在现实条件下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状态;它把人置于一个开放的境域中,为人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和生存动力。但这种哲学同时又时刻提示着人的有限性,时刻提示着死亡的来临,时刻提示着精神家园的不确定性。“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庄子·齐物论》),正是因为对生与死、可与不可等看得那样“不齐”,才有了“齐物论”。所以,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将“愤世嫉俗”乃至对人之有限性的愤慨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它不仅始终充溢着生命的悲情,更是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底色,在本来无情的宇宙自然面前,“自作多情”地欢然自立。
很多论者认为中国哲学不去探讨死亡问题。其实,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文史哲一体,对死亡问题的“理性”讨论在所谓哲学著作中的确不多见,但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中是极为丰富的。在中国人看来,死亡问题、人的有限性问题既然不能用理性解决,也就不必探讨,却可以在艺术中表现和感受。艺术感受也许比理性探讨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存在人格分裂的弊端,而且可以在培养人性心理方面起到更为直接和积极的作用。
六、“向死而生”与“为死而在”——人生动力与价值取向
海德格尔重续古希腊的存在哲学传统,在《存在与时间》第二篇讨论时间性时专辟一章来讨论死亡,将死亡提到本体论的高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死而在”在海氏的死亡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基本方法是“先行到死中去”。“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5](P301)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此在”在现实生活中被各种关系所左右,被“常人”所淹没,为“闲言”所遮蔽,丧失了自我,成为“非本真存在”。只有“先行到死中去”,时刻体味死亡的过程(而非经历“亡故”事件),才能以倒叙的方式从终结的死亡看人生的意义,以整个存在都看得见的可能性来把握存在,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达至“本真存在”。但是,“先行到死中去”仅是“此在”领悟到“本真存在”的可能性途径,只有“良心的呼唤”才是实现这种可能性的选择和手段。但问题是,这里的“良心”是空洞的,“良心的呼唤”实质上是死亡的呼唤。只有时刻感受死亡,人才能够达至“本真存在”。因此,人生的目的不在别处,而在于时刻体味死亡。人是为了体味死亡而存在,这毋宁说人是“为死而在”。据说只有“为死而在”,人才能去感悟世界,领悟人生的本质,积极谋划选择,承担责任,开出无限的可能性,创造自己自由而多彩的人生。
海德格尔通过沉思庄严地向人们提示着死亡的不可替代、不可逃避的绝对性,实际上把死亡当做令人畏惧服从的“绝对命令”。在这一“绝对命令”面前,“诸神退位”,人的自由存在成为唯一的本体。这固然可以反对异化,甚至可以走向海氏晚年深情拥抱的“诗意的栖居”,却也容易走向神秘与抽象。死亡的“绝对命令”直接为人提供了存在的动力,但因为缺乏中间环节的过滤、消解、缓冲和规范,这种动力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生物意志,而生物性的生存本能在人的巨大能力的推动下,又容易变为强力意志。先秦儒道哲学的基本立论方式是把死亡当做起点和原点,却并没有像海氏那样沿着理性的思路无限地推究死亡、体味死亡,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人的有限性所提供的彻底的悲剧意识上。这种悲剧意识,既有孔子“逝者如斯”式的深情,也有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式的愤慨,是深情与愤慨的融合体。在这种历史的境域中,“闻道”、“成仁”成为人的动力之源。中国文化因为在死亡和生存之间有了悲剧意识这个中间环节,成为真正的“向死而生”,与海氏的“为死而在”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海氏从为消除“共在”的烦、畏而“先行到死中去”,反而更加烦、畏,可谓从畏到畏。不过后一种畏是本体性的,可以因畏极而去畏,亦即对死亡的超越。具体的做法在“物性”时间的无数节点上都提前“死”,就是说,心理上的“死”总是赶在“物性”时间节点之前,因此,当这个时间节点来临时,人就不会再“死”。这仍是“为死而在”。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信”看成高于死亡的社会规则,至于“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更是将死亡与意义建立判为互不相关的两截,从而超越了死亡。庄子顺生乐死,倡言“逍遥”,孔门仁学强调人的自足性,也从不需要时刻感受死亡。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篇》),更是面对人之有限性建立起来的活泼泼的审美人格。
海氏的“本真存在”与《中庸》的“诚”有一定的对应之处。“本真存在”是死亡赋予所有人的可能性,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完全个性化的命运。它摒除了一切非本真的世俗,与死亡同在,由此达至人的自由和独创。《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本是来自原始巫术活动中的要求和心理感受,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提升为宇宙的本质和人生追求的根本目标。因此,“诚”是一种设定,这种设定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来自人的理性的凝聚,即必然的道德伦理要求。在后来的文化观念中,开放性的“诚”是一定历史情景中各种因素博弈以后沉淀下来的最具合理性与开放性因素的总和。“天”依据这些因素存在和运行,人应该力求对这些因素进行体认。“本真存在”与“诚”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要求内心最本真的感受;不同之处在于“本真存在”是“先行到死亡中去”的感受,“诚”是对最合理的社会—文化因素的感受,而这种因素由“历史建理性”而来,不是“本真存在”意义上的。
海氏对死亡的“畏”与先秦儒道思想中对死亡的“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死亡之畏的确可以产生“为死而在”的奋进的自由,死亡因此成为人生的推动力,但这种推动力沿着理性的进路进展,终究无法解决死亡的问题,反而带来了极度的焦虑,焦虑则易使人狂躁。实际上,在“先行到死中去”的过程中,人往往被激发出强烈的反理性冲动,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存在哲学虽不能完全被看做“士兵的哲学”,但自由与荒诞并存则是不争的事实。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不是为了体验死,而是为了体验生,并以此超越生死,心态平和而温润。这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消极而懦弱,但实际上是面对死亡泰然而淡然,面对生则做应然之事。至于儒家,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所惧者不是死亡,乃是无所贞立。人生动力的不同,导致人生的价值取向也不同。
后期海德格尔回归自然,希望在自由中倾心悦乐,因此而获得“敞开”和“无蔽”,试图把沉沦于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唤回到与天地神人共在的一体之中。然而,这种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对死亡的焦虑可能会使一切诗意化为乌有。希特勒的高级官员大都有很好的艺术素养,有的还是顶尖的艺术鉴赏家和当时最大的艺术品收藏家,但他们一边在内心里酝酿诗意,一边疯狂地发动战争,甚至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这种人格的分裂未知从何而来。
哲学起于沉思,更起于实践,而死亡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实践的问题,它可以被沉思,更不排斥沉思,但不能仅仅限于沉思,死亡的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解决。“向死而生”与“由命运而境界”一样,成为人类文化“哲学突破”时期中国先秦儒道思想和哲学的基本命题,但前者将问题提得更加直接、显豁和彻底。对于死亡这一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实用理性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和答案。当我们守望这种哲学的时候,也许会感受到真正的“良心的呼唤”。
[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台北,华新出版有限公司,1976。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