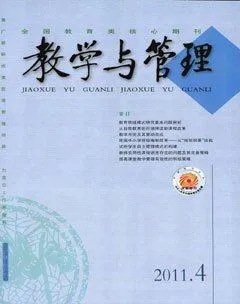从自我教育的内涵释读新课程改革
新课程改革说到底就是中国面向新世纪预设的,应变未来各种挑战的一种文化构建。这一构建指向的目标就是“智慧”,在学生身上,生成一种基于他个人的生存智慧,在国家、民族层次,生成一种自主创新的复兴大智慧。但“真正的智慧是不可能被教会的”,它不仅要“以道观之”,还必须“以我观之”,无“我”则无智慧。a以此观照过去几年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会发现一些教师并没有深深吃透新课程改革的本义,因而在相关教育教学环境越来越多弥漫的是“应景”式的技术、技能、技艺的复制、表演和转借,于是导致学习者的学习,更多脱离了他们最深层的有血有肉的人性,而建构在人为的、强制的、外控的布景上,致使“伪智慧”层出不穷。毫无疑问,决定这次课程改革成败的就是第一线的教师,他们的观念、灵感、激情、乃至最深层的有血有肉的人性,能被他们主动地、自主地、独立地挖掘出来几分,学生的创造性、主体性、批判性就能达到几分。换句话说,教师的自我教育能达到什么程度和广度,学生的自我教育就能达到什么程度和广度,与此同时,新课程改革就能成功到什么程度和广度。这里的自我教育不仅指学校环境中围绕着学科文化的“狭义自我教育”,更包括在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承载着无限丰富的文化传承的“广义自我教育”。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通过把自我作为对象所进行的一切教育过程,反映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学习模式”。这些模式的进行大多数并不像在学校教育中那么目的明确、计划周密、控制有致,相反是在极端纷繁复杂的家庭、社区、单位、偶然社会环境等等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展开的。在其中,每个人时时刻刻身浸体感在周围生存环境、情境、情景的价值和意义的运动变化中,在对这些环境、情境的价值和意义的审视、认识、理解、判断中,在对特定(职业、学业等)生存环境认识和行为方式的融通与超越中,从而显现出了每个人对知识主动的“深”加工,独立的“精致”加工,自觉的“超越性”加工中“转识成智”的一条条通途。
一、课程资源挖掘中的自我教育
如果把这样一个自我教育界定投入到新课程改革中,则教师的生涯发展未免显得苛责和悲壮。一些研究者曾把全国特级教师孙维刚,还有像李吉林、刘可钦等的教学过程进行了总结,得出了一整套的教学方法模式,意图向全国推广。笔者大胆猜想推广的结果,大多数都是东施效颦,因为总结出来的都是这些特级教师表面化的皮毛特征。翻看他们的教学历程会发现,他们的所言所行是其他任何教师都可以做得到,之所以后者没有做到,是因为后者缺乏一种自觉的主体智慧。居于这种智慧核心的就是一个词——学生,在这些最优秀教师的血肉、骨髓乃至灵魂深处,这个词是最神圣的,也因此孙维刚上了八次手术台,第八次终于没有下来,李吉林几种疾病缠身,无怨无悔,应该说,这种状况就是他们生命能量全部“超越性”地投入到课程资源挖掘中的结果。
2006年教育部委托几所师范院校对新课程改革数年来的实施,做一追踪调研发现,课程资源的匮乏已严重影响了新课程的顺利实施,突出表现是:尽管经过大规模教师培训,教师对新课程理念及基础教育的现实问题有了了解,但是怎样把这些理念在教学中呈现出来却有很大的难度与差异度,因为“找不到和教材有关的资料”。是真找不到吗?《纲要》及其《解读》明确表达了本次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深入地投入到学生的生存环境中,去挖掘和建构围绕着他们生活兴趣、体验和情意的一个感受、感知和感应系统,以使静态的认知过程活化、灵化和自由化,从而极大地推动学生最底层身心状态的全面开放。从中可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是教师取之不竭、展开新课程改革的资源宝库。
关键在于教师的精神世界有没有一个自主建构起来的,随时随地、临场即时的“心向”,它表现为大脑皮层一组活跃的“兴奋灶”,里面的内容包括三类:一是有关学生的包罗万象的人格特点;二是种种课程的认知点;三是如何把前两者结合起来的种种“?”。其中的第三点几乎构成了教师全部生活的“当下意识”,内隐的暗示性语言经常是:“这个现象(生活中碰到的)会不会有助于学生理解‘惯性’”、“这个镜头(电视中看到的)我是不是可以让学生看看,他们看到了会怎么想,和我想的一样吗,社会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我应该怎样尊重性地启发、引导他们”、“这个事件(来自媒体、网络甚至偶然聊天)应该拿到班里让学生讨论一下,肯定比教材的效果更好”、“这种情况要是王小明白,一定会更加清晰地知道什么是新陈代谢”等等等等,整个过程折射着全身心投入的敏感性、敏锐性甚至过敏性的教育使命意识,其推动着教师的自我系统总是在生成假设、解释、预测及信息的加工组织中,持续地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应和自我强化,以最广泛地洞察、搜寻、捕捉到那些切合于教育教学的复杂又微妙的课程资源。李吉林选择与教学相关的最佳情境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赶在学生前面去观察日出,夜不能寐,困顿中梦见太阳在黑云里翻腾,好久也跳不出来,一下子就急醒了,马上翻身起床,立即出发。在黎明前的黑夜里,她独自骑着车,飞奔在乡间小路上。刘可钦始终认为“她自己”就是一个课程资源库,一笑一颦,一促一急,无不牵引着学生们心绪、情感、想象的流离波澜。因此,在每学期开学前的整个晚上,她都在对着镜子练习一句话:“孩子们,你们好。”这句话已无数次在她脑海里涌动,但是她认为问题不在于这句话本身,而在于将用怎样的语气、怎样的表情说这句话。在练习中,她总是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有时太严肃、死板,有时声音太高,故意做作,有时在仓促中应付了事。直至第二天在去学校的路上,在路人惊诧的目光中,她还在练习和倾听着这句话。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这样一句温情又自然的问候中,让学生们在整个学期,成为一个完全乐于接受教育的、满足和幸福的人[1]。
范梅南建议基础教育的教师们,要深切“同情”学生,这种同情与其说是教师设身处地地生活在学生的世界中,还不如说是学生已经生活在教师的内心世界中[2]。后者凸显着教师的自我系统持续不断地运转着“毋我”、“毋固”、“毋必”的专业化解放之路,这不啻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被改造之感,因为他将以谦恭的心态、甘当配角的“屈己力”及天文学家那样精细的洞察力,去沉浸在对学生着迷般的极大兴趣中,从而在精神世界衍生出一个如影随行的“教育心向”,于是,周围的社会环境自然而然成了他取之不竭的课程资源宝库。
二、课程事件展开中的自我教育
课程事件观认为,课程是指在某种具体情境下,让学生作为主要参与者对人类生活进行的某种“复演”、表演。现行的语言体系对课程事件有三种理解:宏观、中观、微观,本文更多地着眼于微观课程事件的展开,即课堂上浓缩的人类历程的变化及其存在的情境,通俗讲就是各学科的课堂教学。
新课程改革用一个“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概括了它要追求的课堂“生命活力”。应该说“情感态度”是其中居支撑地位的枢轴,诸如,物理学中对事物运行法则的内在景仰,数学中对数字变幻莫测的神奇膜拜,语言学中对奇巧精文的“如尝甘饴”等等,归为一句话,就是养成对科学、对人类的人文学科一种崇尚理性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表现为好奇、怀疑、不轻信,不盲从,崇尚真理,人格独立,多元价值兼容等,实质就是批判性思维的生成,它与创新性作为一对孪生兄弟一起成为了学生智慧的首要表征,其典型行为就是层出不穷地提出问题,惯于四处寻找答案,常常自主地猜想、反思和得意于一些“异想天开”的主意中……但是有这样行为的中国学生比例非常低。杨振宁不断地说起“外国学生知道一些皮毛的问题,中国学生可能做过成千上百遍了,但中国学生胆子小,教师没讲过的不敢想,老师没教过的不敢做”。问题是,中国学生为什么胆子小?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创新性往往是一个人最深层精神能量的外化,伴随这一过程的更多是紧张、焦虑、惶恐甚至极大的不安,这时学生特别需要教师给予一个强大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如范梅南所讲的,并不仅仅是“作为教师角色的社会支持,而是像父母样的深切体怀性支持”[3],只有这样,学生的最深层精神能量才能“肆无忌惮”地激情四射。刘可钦上课时要是有学生迟到,她会深情问:“你可来了,我们正为你担心呢!”在她巡视学生做练习时,发现小飞写错了一个字,于是站在身后“小心地屏住气说:‘这个字能不能再检查一遍’”,这时见小飞惊恐地回头瞥了她一眼,赶忙拿起了橡皮……这一瞥曾使刘可钦久久不能忘怀,她想自己已经是非常小心地注意了讲话的语气,学生都这么惊恐,那么平时他们是带着多么大的紧张、慌恐和防卫感在接受教育。她进一步思考,要打消他们的慌恐和防卫感,不是要尊重他们,而是要极大地尊重他们。第一步就是无条件地把他们当成一个个非常独特的个体,要经常把这样的问题挂在嘴边:“小明的学习风格是什么样的”,“小红对什么有兴趣”,“小丽遇到的障碍在哪里”,“小华学习四则运算的敏感点是什么”。一次,刘可钦要学生们举手回答一个问题,发现小青的手欲举又放,犹豫不决,于是课间她问小青:“你是不是很想回答问题,但又没有想好?”“就是”“那么咱们约定,你对问题很有把握时,就高高举左手,还没有想好时,就举右手,怎么样?”在师生间的这种心灵默契中,小青坚定又自信地举左手的次数越来越多。全国特级教师斯霞一次讲“笑嘻嘻”这个词,她让学生看她脸上的表情。学生们见斯霞咧着嘴,咪着眼(显得夸张、搞笑),都说老师的脸上笑嘻嘻的。可以认为,这些最优秀的教师正在将来自成人世界的自尊感、自贵感、尊严感自觉地降到最低、最低,以充分地暴露、表达出自己最深层精神能量中稚气、率真,甚至脆弱的一面,去精细地辨别学生的声音、眼神、动作和神态的细微差异,配之以聆听、扬眉、点头、深情的注视、期待的凝望,以求得一个与学生共同在场的、共同遭遇的、共同开拓的互动、灵动、触动、序动、跳动的课堂情境,进而换得学生最深层精神能量的大胆迸发,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像教师的“教师”。
苏霍姆林斯基始终认为,任何使学生没有感觉到教育的教师,肯定是最好的教师。因为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会油然诞生在学生的心灵中,推动着他们生出一种社会主体间交往的美感来,这种美感会极大地激励他们相信自己内在需要的真理性。于是敢于对自己负起责任,敢于与众不同,敢于表现真实的自己,敢于欣赏自己的所作所为,敢于最充分地、生动地体验社会生活的每个时刻。也就在这时,他们成了自己最好的教育者,从此,“学生式的教师教出了教师式的学生”,教师外部教育行为的终结点,成了学生自我教育行为的起始点,这是教学艺术最可贵的体现。这个起始点最显著的表征就是,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充满了问题欲的“问题库”,其中的问题就像是陶行知的八位好朋友,它们都姓“何”:“何事、何故、何人、何时、何如、何地、何去,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
三、社会化成长中的自我教育
法布尔曾做过一个试验,将一些蜜蜂和苍蝇放入瓶中,瓶底朝向有阳光的窗户,瓶口朝向屋子较黑的地方,一会儿发现所有蜜蜂都朝着有阳光的瓶底冲去,连绵不绝,矢志不渝,直到最后全部累死,没有一只知道转一个方向就安全脱险。而苍蝇刚开始向有阳光的窗户冲了几次之后,马上转身向较黑的瓶口冲去。社会生活远比学校科学知识描述的复杂得多,科学知识只是给学生了一些普遍性的准备,更多地需要学生面对各种最具体的社会情境,自己迸发出“苍蝇式的智慧与勇气”——冒险、即兴发挥、迂回前进、混乱、随机应变、非理性直觉、生命化体悟及边缘化旁门左道等等,这些属于学生的“个人知识”可以说是他们社会化真正的主导力。但是孙维刚不赞同“苍蝇式的个人智慧”。他的学生是社区、学校图书馆以至区教育局最受欢迎的学生,因为请他的学生来帮忙劳动,干活干到了精细的程度,认真负责到了让人感动的程度。在他的教室里赫然挂着“诚实,正派,正直;树立远大理想,为人民多作贡献;做有丰富感情的人,是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一系列条幅,更甚者,他规定了:不许留长头发,不许穿皮鞋,不许唱庸俗的流行歌曲,男女生不许轻浮地说笑,不开生日晚会,不寄贺年卡等这样一系列“恍若隔世”的班规。没有一个学生有异议,相反全部主动、自律、自觉、自愿地遵守,任何一个新来者不用一天就会自主地融入到这些班规里。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孙老师也是认真地这么做的。
“苍蝇式的个人智慧”离开了生命最底层厚重的“利他”力量,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能是危险的,这正是孙维刚忧虑之所在。他说:“外面的风气我管不了,我能管的就是我自己和每天触及的那片小天地。”正是融入着最深层的体验、激情、灵性,投入到这片小天地的“去存在”、“去生成”的自然显现、自我澄明、自身彰现的过程,凝结出了教师一系列教育教学最本真的理解——非判断性理解、发展性理解、分析性理解及形成性理解。也正是这些理解一步步地唤起、推动、养成、构建、铸造出了学生未来发展中,适应、完善、改革、超越社会的种种类型各异的自我教育系统,使他们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民族恒久瞬息的长河中,获得了自身生涯发展最节省能源的方法,那就是用自己心灵深处的能源,来照亮自己的精神世界。
有研究者认为,本次新课程改革已经走向了“泛人本化”,不是在释放张扬学生的个性,而是在迁就放纵他们的劣性。笔者很不赞同这种看法,这不啻是教育者对过去以“他”为中心的单一、刻板、权威教育生活留恋心态的折射,学生的“无忌”、“坦言”、“锋芒”甚至“放肆”,无疑开始深深触及教育者多少年来固结下来的“教师尊严”。应该说,在当代面对这种“触及”,教师所能做就是迎头赶上,静下心来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沉思、自思、反思,像刘可钦、孙维刚们那样对多少年来固结下来的“自我系统”,进行大纵深的重组、破立、阵痛、致思、颠覆甚至革命,于是成百上千个刘可钦、孙维刚就会涌现出来,进而教育的本质“让学”就会变得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细、精致、精妙绝伦,自然而然,新课程改革也就瓜熟蒂落。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刘可钦与主体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加拿大]马克斯·范梅.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 胡东方.教育新思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容中逵,刘要悟.论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现代教育论丛,2004(5).
(责任编辑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