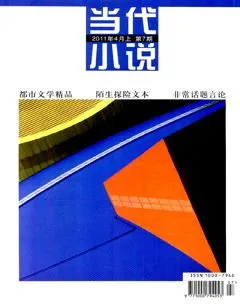康德与张家界
一直以来,命运的列车总是由父母的目光在驱动,当他们终于以老迈双眸黯淡之际,我的列车便在张家界这里作了停留。于是,十年负笈的星星点点在绝美山水间驻足,这种机遇同时给我提出了一个巨大的人生和学术命题:我所信仰者与坚持者,到底与这山水何关?由于工作需要,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室,我曾经很费心思、找了很多资料为这个办公室定位,安排工作任务,自认为已是齐备,于是在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进行讨论。良久,一位同事提出补充,他是从“办公室”这个概念下手,认为既然叫做办公室,就当有如何如何的职能,因此,提出诸下补充意见云云。
会后,我即出差,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与他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之间的关系。飞机在白云上翱翔,不带一丝尘滓。我突然想起了康德对于柏拉图的指责:在没有空气的环境,鸽子无论如何扇动翅膀也是飞不起来的。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似乎有所得。在我所认真读过的康德作品里,似乎提到过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知性的方式,通过经验与直观的结合而产生知识,一种是理性的方式,仅凭概念就可以得出知识。据此,我似乎可以明白我与那位同事之间的不同了。大家在从不同的向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似乎他的工作方法要高我一筹。
我一味在从经验层面去设想工作的种种,但是从归纳法的命运可知,完全的归纳是不可能的,因此,经验也是无法穷尽的,真正要达到一种完备的程度须得靠概念的统合才成。但理论上说,概念具有一种先天的脱离经验的倾向,但那位同事所依据的概念当然是有着多年的工作基础为其经验的。因此,他的方法事实上是结合了经验的概念,因而通过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检测程序,当是优于我所采取的工作方法。
我读过一些年的哲学著作,深为先贤们所创造的智慧形式所折服,但一直对于它的实际功用感到疑惑,因为在那些深奥的著作里明确写着,这些东西除了训练思维以外是无用的。也许我应当相信它有改变实际生活的作用才对,随着年岁的轮转和生活面的拓广,我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日常生活里发现康德、海德格尔这些人的年轻身影,他们似乎用自己那些曾经被无数次翻译的语言告诉我:我来了,就在日用寻常中,与孔夫子和佛陀一起来到了你们的生活中。
看着五个月大的小儿在床上踢脚摆手,口中咿咿呀呀,有时会咬住衣角当吃的,眼神定在我面前的时候无比清澈。我跟妻子说,也许他现在这种状态才是通向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之原初状态的惟一的路,这也应当是最原初的智慧所在。
于康德而言,小儿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物自体”,没有人能从他目前的表现里洞察其以后的诸种可能性,只有切切地等待他自身不断的显现。而熊十力则告诉我们不要为他的任何未来之事担心,因为“体用不二”,他未来所展现出来的,正是他此时所具有而未曾为我们识知的一切。
我们夫妻围坐在他的身周,一个个先哲前贤的警语在这个名叫慧海的小子周身转悠,他睁大一双眼睛看着我们,似乎这些智慧的话语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并使他有力量去止住哭声。我得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在他这个阶段,似无需知道太多的哲学话语,我要告诉他,没有相当深厚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哲学的玄谈只会空虚无着。
也许,我是得给书柜里再添一些科学书籍了,在我读康德传记的时候,早期的他却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出现,而且在其著作全集的头几本里都是科学著作为主。
我现在坐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大道上的旅游大巴在进进出出,也可以看到那曾经被飞机穿越的天门洞,是否它们也曾以各种方式在阐释着为常人所不知的哲学道理呢?或者,所有的哲学都只能被作为灵长类的人所阐释?
朱熹似乎有说过“绝知此事要躬行”,我知道,生活的审美化要实现,需要有思想的力量,日常生活总是每天如此,只有挥起思想的巨锤,方能在平淡的生活里碾轧出美的元素。也许,康德就能提供这么一柄大锤。只不过提起它也需要勇气,但一旦我们能挥之而起,则会发现,原来费力的事情也是那么的美妙。
我曾如此惊叹于张家界景区的美丽,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我曾读到过优美和壮美的井然有判的区分,当无数的群峰展现在我面前时,我已经失却了如何去判别这两种美的能力,事后我曾无数次在冥想中去回味当初的情态,可我还是不能区分那种感觉究竟是优美还是壮美,也许,审美的经验能修正我们的概念。后来有着多次的机会,我到现场去体会,结果我发现,原来不是康德错了,而是我有误,也许,那种情态根本就无需区分,我只需名之为“美本身”即可。
我不知道,类似于康德这样的人还要给我上多少课,只是在张家界的这些日子里,已经有许多课了。是否,如果我不是身处此地,而另在他地,也会有如此感受呢?在我,当把这作为一个问题采用如胡塞尔般的“悬置”态度,因为毕竟,哲学是太深奥的东西,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幸福,不要那么多“如果”,要“现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