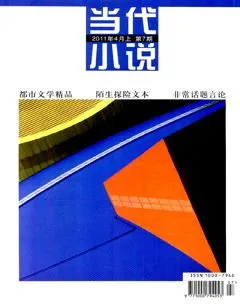心祭
依克拉姆大娘归真的那天,达乌德在万里之外的西藏日喀则就把消息知道了。是大娘的三儿子海顺在电话里告诉他的。
那天,达乌德晕倒在昂仁县抗震救灾的指挥岗位上,几个藏族汉子强拉硬拽才把他塞进汽车。刚刚送进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他就接到了海顺的电话。
达乌德和海顺兄弟三十年前是交换过口换的。那口换是只要大娘健在,他每年回老家时都要看望老人。一日老人身子不行了,不管达乌德在哪里,都必须告诉他。
大娘对达乌德有恩。
那恩,是一颗心,是一个人的一条命,也是一个人一生的一条路。
如今,大娘走了,是达乌德兑现承诺、应承口换的时刻了。他却远在万里之外的西藏。
奔土如奔金。入土为安。这是等不得外地亲人的回归的。达乌德掐着指头算了又算,就是能买上当天的机票,也赶不上大娘的葬礼呀。
海顺在电话的那头说,达乌德哥哥,这些年你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俺娘,每年探家都来俺家,你也替俺们兄弟尽孝了呢。再说你现在担负的是国家的差事,一个省的援藏总带队,由不得自己呀。
也是。达乌德沉思了一会儿。脑子里关于依克拉姆大娘记忆的沉淀就迅速地激活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娘的一饭之恩。
1961年春上。青黄不接的时令。
被秋旱、冬旱又接上春旱折磨了半年多的鲁北平原,失去了它本应姹紫嫣红的春天本色,裸露在人们眼前的,除了白花花的盐碱,就是漫天黄沙。干热风出奇得大,仿佛要和这片本来就贫瘠的土地较劲。小麦刚返青那会儿,原野上还能看出一点生命的迹象,及至清明节过后,那本来就有气无力的小苗也慢慢地缩回去了,沙窝窝里能看得见的,也只有被埋在下面的麦苗那干枯的叶子。至于本应苍翠鲜亮的杨柳树,早就被人们捋光了叶子,和野菜一起煮着吃了。最倒霉的榆树们,榆钱刚打苞,被人们疯抢一遍,叶子出来,又疯抢一遍。榆钱和嫩叶都吃光了,人们又开始剥树皮。榆树们真可怜。远远望去,那被剥光了树皮的榆树们,像被剔光了血肉的人体架子,以其特有的白而赤裸,述说着天灾人祸强加给大自然的磔刑及其无道。
与大自然的萧条相呼应的,是人类的饥饿。
断粮,威胁着所有的生命。
从春节到清明,村子里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无心计算。但是,最近去世的几个,已经很难找到人往坟上抬。都是亲门近支为亡人做了祈祷之后,送到坟上草草地埋掉。甚至有的人在送亡人入土后回来的路上,眼一花,头一晕,栽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死神一旦瞅准谁家,总有人在亲人们的哀叹声中无奈地上路。
达乌德也没有逃过这场灾难。那一天,他和小他两岁的妹妹索非亚像是约好了去赴一场灾难,一起躺在土炕上吐血。爹和娘眼看着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一个七岁的姑娘已经昏迷不醒,把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实在找不到能让孩子活下去的门路了。两个老人嗓子都哭哑了。一会儿抱起这个亲亲,一会儿又抱起那个亲亲,虽然孩子瘦得皮包着骨头,可总是爹娘的连心肉呀。两口子瞪着红肿的眼对视良久,最后也只能是哀叹一声:咳,怕是留不住了,快去买克凡布①吧,省得孩子断了气来不及……
“那就快去扯布吧。”爹迈不动两条灌满了铅似的腿,瞪着绝望的眼对娘说。
娘眼睛里立刻浸满了泪水。那一刻,她本来就黄得吓人的脸,像是突然间又覆了一层黄表,慌汗珠子和浑浊的眼泪搅在一起,从她难堪的脸上滚落下来。
她知道,买白布对她意味着什么。作孽呀,我这不是替地狱里的小鬼拉纤么?走在去供销社的路上,她紧紧地咬着牙关,强撑着一步三晃的身子,像一个心无所依的孤魂。
这一切,被迎面走来的依克拉姆看在眼里。
妹子,看样子遇上过不去的坎子了?
娘就照实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唉,这年头要是七老八十的大人遇上这种情况也就算了,孩子还小啊,他们是岁月的芽,是日子的根,咋能说埋就埋了呢。妹子,你先回去,让我思谋思谋,想个把孩子留住的办法。
像满天乌云突然裂开一道缝,火石般的毫光立马激活了娘那颗绝望的心。
一盏茶工夫,依克拉姆大娘真的来了。进门把个背在肩上的口袋朝墙角一放:“他婶子,家里也没有什么好的,都是早些年开磨坊剩下的谷糠,赶紧给孩子兑活着弄点吃的,说不定这里面还能有点救命的东西呢。”说完,就一撅一撅地走了。
娘立刻把那口袋里的谷糠朝笸箩里一倒:呀,谷糠里居然还有两个小米面饼子!
救命的仙丹呀!
爹顺手抄起一个饼子在两个孩子眼前一晃,那混浊的眼睛像突然开启的电源,同时发出了光芒。接下来的狼吞虎咽,如果有如今的记录手段,那肯定是动物界人类这个分支求生欲望的最完美、最真实的体现。
半个小时前还是冥界备选的两个孩子,一转眼脸上就有了光泽,有了笑容。达乌德和索菲亚不约而同地看看爹,看看娘,两个老人却不约而同地哭了。
天不灭曹。就在那天夜里,上天落下了八个月来的第一场透地雨。那场雨下得不风不火,不紧不慢,像一只温柔的手,用多情的按摩把干透了的平原重新又给浸润了。
这场雨为所有的生命注入了新的律动。短短几天,草绿了,鸟鸣了,青青菜、土露酸、苦苦菜、蒲公英……全都呼呼地旺长了。
达乌德和索菲亚又能到地里去挖野菜了。那天下午,达乌德早早地背回一大筐又鲜又嫩的野菜,高兴地对娘说:地里的青棵棵长得真快呀。
娘说:小草和孩子一样,有吃有喝就长得快。你能活过来,还不亏得你大娘给你送来的救命饭?记住,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大娘的这顿饭。
娘的话,达乌德真的记住了。几十年来,他念书升学,当兵提干,直到当了县委书记,当了副厅长,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那顿饭,更没有忘记给他那顿救命饭的依克拉姆大娘。每年回乡,他都去大娘家里坐坐。和大娘的亲儿子一样,唠些居家过日子的大事小情。大娘知道这孩子厚道,很少提起当年的那两个饼子。只是有次论道起歉年度荒的话题,达乌德才知道了当年那两个小米面饼子,是大娘用两簸箕谷糠从别人家换来的。说起这些,大娘心情很平静。她说她见不得娃娃们受罪,如果能救活孩子的命,从她腚上拉块肉都行。人活在世上,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德行不能损。
这些话达乌德也记住了。
十五年前他在清和县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散步,见一伙人在体育场附近的万松园门口比划着说什么。原来大家正在议论三官庙村一对农民夫妇因意外事故闪下两个孩子撒手人寰的事。他凑上去弄清了原委以后,问:这件事情村里的干部没有报告吗?就是那天晚上,他去了三官庙。在那里,他和村支部书记每人领养了一个孤儿。如今,那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达乌德领养的那个男孩已经成家立业了。孩子参加工作以后,第一个月就把工资交给了他。不知为什么,达乌德没有要孩子的工资,自己的眼睛却湿润了。
今天,在海顺打来的电话里,听到依克拉姆大娘归真的消息,达乌德心里先是一震,接着对海顺说了些安慰的话,自己却一时间六神无主了。他的确想赶回去送大娘最后一程,他忘不了这个曾经救过自己生命的老人。多么好的一个老人,善良、慈祥,虽说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在庄稼地里苦累苦熬了一辈子,可她那金子般的心却远在许多达官贵人之上。该去送老人一程呀,哪怕只是见上一面,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慰藉。他掐着指头算来算去,除了眼前援藏工作正在抗震救灾的火候上,他怎么安排都赶不上老人的葬礼。西藏这地方离内地太远飞机又不能直航。咳!
按照当年的口换,他是应当回去的。凭着他对老人的那份敬仰与思念,他不能亲自去送葬,至少也要大放悲声地痛哭一场。
他没有那么做。
他简单地清理了一下办公桌上文件,然后一个人心无所依地走进办公楼电梯,下意识地摁下了顶层的号码。
到达顶层以后,他又一个人去了楼顶。
楼顶上摆放着一些机关干部业余时间养的花和盆景。在日喀则这个地方,能在楼顶上养花的日子不是很多。难得的季节啊。
达乌德站在一览无余的楼顶。
目能所及,除了藏民的房子、藏传佛教的寺庙、拴着哈达和彩带的敖包,就是斑斑驳驳的高原。那高原逶迤着伸向远方,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连成一体,蓝天白云之下,巍峨的西马拉雅山雪峰,洁白无语而又肃穆庄严,怎么看都像一位横卧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老人,那老人慈祥善良敦厚豁达包容刚强,像无数中国母亲集体化身。那其中,谁敢断定没有依克拉姆老人的身影呢?
达乌德想着想着,脑海里的视像突然迅速地切换成故乡一支充满着人生终极关怀和哀婉情调的送葬队伍。身着孝服的依克拉姆老人的亲人们,哭着,走着,不时跪倒在地向前来送葬的人们叩头谢孝……
突然,达乌德猛一转身,从一盆正在盛开的菊花丛中,摘下一朵又大又白的菊花,朝着故乡的方向,朝着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大阪,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又深深地跪下了。那一时刻,他觉得自己踏上了故乡的黄土地,他融进了滚滚的雅鲁藏布江,融进了用最纯洁的母爱凝注起来的巍巍雪峰,融进了西藏雪顿节的愉悦……
就在那一天,那一天的下午,达乌德带着身边的两个工作人员,又一次返回遭受地震灾害的昂仁县。
行前,他让秘书把他刚发的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带上。他说,那里有他的爹娘,有他的亲人,还有他的依克拉姆大娘。他说,他要去交纳一份随心的“乜贴②”。
注释:
①可凡布:回族人死后用于裹尸体的布叫可凡布。
②乜贴:以非纳税方式周济遭受灾难的人们所捐出的资金。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