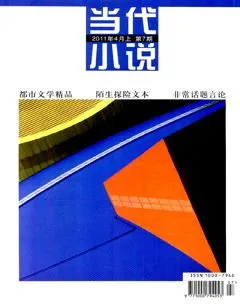乍暖还寒中春风的微笑
·春
春季主持:房伟
补评:张艳梅
嘉宾主持:张丽军 赵月斌 马兵 肖涛
主持人:房伟 文学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讨论者:盖永爽 张琳 郭帅
房伟:大家好!去年,《当代小说》四季评这个栏目在文学圈和读者中产生了一些反响,这也说明大家还都在关注着文学。今年,我们的形式可能会变化一些,这一期就主要由几个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谈对作品的看法和认识,他们更年轻,更敏锐,也更有热情,也是文学刊物最为新锐的研究者和阅读者,我想,他们的评析,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青春气息和新的思考。
盖永爽:女性小说,还是这个春天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女作家阿袁发表在《十月》2011年的中篇小说《子在川上》。阿袁擅长用后现代的思考方式,密切地关注高校“儒林”里芸芸众生们的情状秘闻。阿袁近期的几部中篇都是取材于学院里的“八卦”和“内幕”,她以描写“中文系”里的教授、博士之流的言行举止为故事的引子,巧妙地点出这群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们,那五花八门的生活情状、暗潮汹涌的心理态势、不为外人所知的精神困惑。《子在川上》,情节脉络依旧是在写学院故事以及相关人事纷争。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位是师大手握实权、老奸巨猾的系主任陈季子,一位是早年毕业北大、有名士作风的资深教授苏不渔。两个人在师大中文系的明争暗斗、相互轻视,看似来源于两种生活方式、工作态度的差异,实际则是两类学院哲学的迥异。苏不渔生活洒脱,不拘小节,他认为论文是思想的精华,他对一年发表“几麻袋”论文的陈季子充满鄙视,苏不渔的“述而不著”其实也是对现行学术体制傲然反叛。他最后愤然而书的《告全校师生书》,也是作者阿袁对当前学术界处以某种紊乱无序状态的批判。苏不渔最终因得罪师大的杜校长被“发配”到资料室,成了一位普通的系资料员。小说中,阿袁的情感态度显得暧昧飘忽,她用看似超然轻松的语言,叙述着一幕幕学院内隐秘故事,波澜不惊,从容而笃定。但同时,她也以几乎调侃的话语姿态,暗暗勾勒了现行学术机制之于高校教师的生存窘境和学术压力。
房伟:的确,这个春天的小说创作,很多女作家不约而同地从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等视角来关注时代潮流转变下的人性蜕变、底层生活、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
张琳:同样是女作家,叶弥的小说同样也值得关注。叶弥的短篇小说《到客船》(《钟山》2011年第1期)理性而深沉,有着深刻的沉重感,内容深厚而内蕴丰富,叶弥用其强烈的现实关注力和犀利的社会批判能力表达了她对现代社会生活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叶弥在《到客船》中用穿云裂石般的力度来揭示了所谓“物质文明”和“城市文明”对人性的吞噬和异化。一只漂泊的小船载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顶着河流来到了青山绿水的小钟村,而这个表面上看似平静的村子的真实状态却让人心生恐惧。村民们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用出卖土地的钱财赌博、嫖娼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司空见惯,整个村子乌烟瘴气。而村民却把自身的堕落、村子风气的败坏赖在外来的女人和婊子身上。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千万别墅,这种显著的贫富差距对村民们来说是一种无声的巨大刺激,道德的沦丧,价值观的混乱,“理想”与“希望”的消失,贫富的差距都使人更加的堕落,亲情也被金钱与欲望消解。村里的人精神都呈现出不正常的病态。而与之相反,绿杨和汤婆子做的是见不得光的生意,在道德层面上本来应当受到谴责的绿杨和汤婆子却与那些村子里道貌岸然、自命清高的所谓“正人君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身上甚至闪耀着村民已经消亡的人性光芒,心中还存留着一丝的良善。在物质金钱的冲击下,传统意义上的淳朴村民对物质力量的推崇使自己成为吃喝嫖赌的道德上的堕落者,而一直为人们所不耻的妓女却成了小说中最像“人”的人,这种对比和差异有着耐人寻味的反讽意味。
房伟:现在文坛上,女作家的创作是主力军呀。在2011年春季的小说界,还有哪些女作家的作品引起了你们的注意?
张琳:女性生存困境,应该是这些女作家的兴奋点吧,她们总是在婚恋题材和日常生活的领域,找到文学的突破口。王雪梅的中篇小说《小满》(《北京文学》2011年第1期)讲述了一个出生在小满那天名叫小满的女孩的悲惨命运,小说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和转换,她逢七的七岁、十四岁和二十一岁的生日是她生命中关键的节点。作者曾经参与过多部影视作品的制作运营,小说的这三个生日发生的故事就像是电影的三个重要场面为我们呈现了小满的命运。母亲出走,父亲车祸去世,本应是幸福的生日,却几乎没有给小满留下任何幸福的记忆,年仅二十一岁的小满历尽了生活的沧桑,懵懂无知的初恋、与街头小混混没有结果的恋爱,现实中爱情愿望的破灭使小满沉浸在虚拟的网络爱恋中,并深深陷入和迷失在这种虚无、不怀好意的所谓“爱情”之中,无法释手。她渴望关怀,渴望着爱情,但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她爱的人都没有给她幸福,相反,她每次都被爱情伤得头破血流,带给她无限的痛苦,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终小满被刘博拐卖到偏僻的山村,过着麻木的似行尸走肉的生活。小满是单纯的,她没有实现真正的精神成长,始终停留在单纯幼稚的阶段,她天真善良,对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但也就是因她单纯,所以她爱的时候爱得投入,恨的时候恨得彻骨,刘博欺骗了她,她最终亲手杀死了刘博,将心中的恨发泄,这不仅是对刘博的报复,也是对自己命运的发泄和报复。
盖永爽:你的观点还是有些偏狭,其实很多女作家对文化和人生的关注,视野也是非常开阔的。相比于孙频充满华丽质感的文学才华,常芳的《请让我高兴》虽然也有观察生活的独特体味和深沉思考,但过分沉湎概念化的人生哲理,反而使其小说显得不太真实,没有应有的文学深度和艺术敏感。常芳在《请让我高兴》里,依旧是写关于济南市民的生活波澜和生存感悟,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平凡的底层小民,而是换成了中产白领。主人公唐娜是一个高级的股票分析师,老公肖建国是部队高干之后。然而,优越的家庭环境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婚姻一定会美满,也不代表着生活的彻底幸福。小说中肖建国酷嗜砚台,平日里对他妻子唐娜却不管不顾。作者似乎是急于把什么是人生幸福之类的大道理强加给读者,从而让小说的结构有着明显的概念化之弊端,也使小说失去了应有的文学魅力。在小说的结尾处,唐娜似乎恍悟出了人生要如何度过的生命哲学,突兀的情节设置不仅削弱了故事的连续性,而且也让小说本身的艺术探索显得平庸和浅显。
与常芳表现城市白领的婚姻危机、幸福危机不同,迟子建发表于《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七十年代的四季歌》,则聚焦自己身边平凡而普通的亲人,着力展现在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存在个体与生存境遇的互动关系。作者把外祖母、祖父、母亲、父亲在七十年代或坎坷多艰、或平淡无奇、或悲欣交集、或无可奈何的生活遭际,与春夏秋冬一一对应的同时,也暗示着七十年代生活本真情状的苦辣酸甜。迟子建用诗性般的怅然回忆,注视着这些逝去已久的少年记忆,悠然地摩挲着那一代人的歌哭和悲欢。伴随着精致细腻的娓娓诉说,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别样的、失去已久、又历历在目的社会风景。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边地一隅,同样也蕴藏着一个个饱含生命体温的情感故事。贤惠知礼的外祖母,勤劳能干的祖父,既才华横溢又有出世念头的父亲,辛勤操持家务的母亲,白雪皑皑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地,困难岁月邻里街坊相濡以沫的感人场面,都成为迟子建文学灵感的重要来源。面对着那一代人终将逝去的无奈现实,迟子建没有效仿贾平凹《秦腔》式的深情哀悼,而是用慈悲温润的心灵去介入、接纳、融入进那段悄然消失的历史记忆,从而在无意中打开了书写七十年代的另一扇文学之门。
张琳:女性作家,当然可以写更宽广的东西,但作为女性,我还是认同她们对女性生存体验的敏锐和深度,这是她们的优势,也是她们的长处。林那北的中篇小说《燕氏平衡》(《钟山》2011年第1期)主题聚焦在了一场近乎荒谬的婚姻上。身为市政府高层官员的薛定兵十三年间向余致素提出了二十五次离婚,而余致素每次都会不动声色、冷静地面对,微笑着拒绝,五十多岁的余风韵犹存,拒接得也十分高贵优雅,每次都在笔记本上画上正字来标记着自己的胜利,十三年间一直围绕着离婚进行着心理上的博弈。作者不断地暗示着余致素十一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事件,甚至使她对异性、婚姻的看法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却一直没有告诉读者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婚礼前一直到婚后的多年间,薛定兵对余致素很冷淡,只是维持着表面上的恩爱而薛定兵不断提出离婚的原因,作者也始终没有告诉读者,作者将悬念一直放置到最后才解开。余致素多年的婚姻已成为“内里已经是斑驳的破絮,就是长满了虱子与蛆虫,从外面却仍然看到绸缎的华丽质地”的华美的袍,她的婚姻表面风光却内含硬伤,坚持不离婚的余致素甚至有些执拗。林那北的这篇小说中蕴含的元素很多,如对表里不一的婚姻的慨叹、金钱权力对人的侵蚀、男性话语对女性命运所产生的决定作用和男权对女性的阴影,却未能将这些元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尤其是男性造成女性命运悲剧和金钱权力对人的侵蚀仿佛是小说两条没有交集的线,似有脱节,有种生硬僵涩之感。
房伟:林那北是成名的女作家了,但80后的女作家也成长很快,而且有些80后女作家的作品,也不仅仅关注女性,而是表现出她们宽广的艺术视野和敏锐蓬勃的艺术生命。说起来,80后的作家也都不小了,也该是他们集体发出声音的时候了,而女性作家,无疑是不能忽略的存在力量。
盖永爽:是的,我同意房老师的观点,这个春季的80后女作家的创作,也有很多值得关注。“80”后女作家孙频,用神秘朦胧、诗性内敛的审美语言、大胆超前的艺术想象,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平淡不惊的社会更迭、卑微普通的现实人生中,扎实而稳健地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2011年伊始,不到而立之年的她就在《十月》、《上海文学》这样的“大牌期刊”频频亮相,显示了不俗的文学实力和勃勃的艺术生机。孙频的文学素描尤以想象女性命运的跌宕起伏、勾连历史无常的沉重一幕为其首要特色。无论是中篇小说《碛口渡》(见《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还是《罂粟的咒》(见《十月》2011年第1期),她的叙述语言都是唯美而朦胧的,散发着朴素典雅的古典气息,氤氲出阴柔萎靡的故事内核,这些都使读者沉湎于此不能自拔。而孙频精心塑造故事、细致营建情节、巧妙镂刻人物、认真设置背景的功夫更是一流,她的小说故事总是具有独特的神秘质地和充满浓重诱惑感的文学张力,又在内敛之中饱蘸着巨大而华美的语词才具。在《罂粟的咒》里,武心惠、武心爱、武心琴三姐妹用丰腴的身体与残酷的生存现实博弈、与无可奈何的历史抗争、与那如梦魇般恐怖的罂粟咒语周旋不息。但谁能说得清到底是哪股力量让她们如此疯狂?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生活得这般沉重呢?以至于她们苦苦挣扎拼命超越,结果却总是功败垂成,无果而终?在小说《碛口渡》里,痴情女人陈佩行心比天高无奈命比纸薄,她苦恋年轻画家无果,幸嫁煤老板无后,偶遇少时情人遭诈。她的情感波折,像极了黄河古渡边上的碛石,日日被黄河水击打,却总不能与黄河水相伴一生,终老一世。她腰缠万贯返回家乡,却早已把屡受伤害的心遗失在了情感的远方。孙频把大量的审美意象融入小说中,既喻示着女性的多舛命运,也隐喻着男性世界的复杂难言和不可琢磨。如《罂粟的咒》中的长满了田野的罂粟之花,它们似“恶之花”般绽放着、张扬着、舞蹈着,也把欲望、罪恶、灾难、机遇和财富一齐洒向人间;如《碛口渡》里静谧光滑的硕大碛石,在古旧悠长的黄河涛声中,它们一边见证着岁月的无情,也一边审视着女性情感生涯的长与短、人生命运遭际的凉和炎、人类内心世界的刚及柔。如果说,孙频小说中的先锋探索精神和淡雅神秘的古典气息,使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