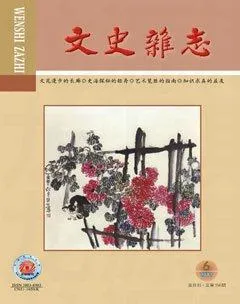汉代画像中的侍仆与奴婢
一
汉代画像(石、砖)中常见有刻画的侍仆、奴婢形象,而且数目甚多;其中尤以侍女居多。她们的姿势神态与服饰造型都显出谦卑的特点,或正面持物而立,或作侧身躬立状。这种造型上的特点显然是由她们的身份决定的。饶有趣味的是,她们所持的物体种类较多,姿势也因持物的不同而形态各异。最常见的有端盒、捧奁、提卣、执镜、持炉、捧壶、端灯(图一)、打扇(便面),或斟酒、侍奉之类,内容十分丰富,是汉代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
侍女所持者大都是当时的常用物,如卣是盛酒容器,奁是放梳妆品的盒匣;又如铜镜与博山香炉之类,皆是汉代富室或官宦人家的常用之物。古人用铜镜自照容颜,历史悠久,出土实物至少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商周以降更为流行,制作也更加精美。秦汉时期已出现专门贮放铜镜的奁、盒之类器具,《后汉书·皇后纪》就有汉明帝谒阴太后原陵“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的记载。但考古发现出土的铜镜数量颇多,镜奁镜盒则较为少见。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曾发现有竹编的镜奁,在湖南长沙一号汉墓中出土有漆奁,内放有裹在镜衣(红绢镜套)中的铜镜以及梳篦、毛刷、脂粉等物品。汉代画像刻画的所捧之奁,亦应为漆奁,既有方形又有圆形,是关于汉奁的重要图像资料。
汉代画像中的博山香炉也很珍贵。古代很早就有焚香洁室或熏衣染被的习俗,而将焚香的器具做成博山之形则是汉代的创新。根据文献资料和出土实物可知,汉代的铜制博山香炉大都由炉盖、炉身、柱柄、铜盘等几部分构成,炉盖通常雕镂成高而尖的山峦形,以象征海上仙山“博山”,有的于山峦间还雕镂有人物、鸟兽以及云气纹;炉身为圆形,于炉内焚香,烟气由盖上镂孔散出,有轻烟缭绕、山景朦胧、群兽灵动的效果;柱柄上承炉身,竖立于底座圆形铜盘的中央;有的较短,有的较高,有的炉柄还做成力士骑兽或竹节蟠龙造型。例如河北满城县西郊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与其妻窦绾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图二)与骑兽人物博山炉,陕西兴平茂陵附近1号无名冢的从葬坑内出土的竹节熏炉等。汉代刘向《熏炉铭》中描述说“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麝,朱火青烟,蔚术四塞,上连青天,雕镂万兽,离娄相加”。鲍照《拟行路难》诗说:“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斵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帏里明烛前,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由这些描述可知古人对博山香炉的制作与使用情形。上面雕镂的仙山之类与汉代方士神仙之说的盛行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博山香炉的造型即是对神仙的信奉与希冀求得长生之术观念的产物,这在汉武帝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博山香炉也正是此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汉代画像中刻画的博山香炉与文献描述及出土实物非常相似,炉盖为博山之形,柱柄较短,应是汉代熏炉中的精致之作。这不仅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对此物的喜爱,也说明了其身份等级的非同一般。
二
汉代画像中表现奴仆持“便面”者,也是汉代富有阶层生活情景中的一个真实写照。从文献记载看,扇的使用在中国起源颇早,可追溯到上古,如高承撰《事物纪原》有黄帝作五明扇之说,崔豹《古今注》卷上则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不得用”。同书又称商周有“雉尾扇”,“为王后夫人之车服”,“汉朝乘舆服之”;又有“障扇,长扇也,汉世多豪侠,象雉尾扇而制长扇也”。这些记述说明扇曾作为仪仗或乘舆装饰用以障尘蔽日。此类扇主要是长柄大扇,称为扇翣,又称障扇(或掌扇),其使用常与身份有关。但扇的最主要的功能则是纳凉,有短柄轻便之扇,在汉代已广为使用。刘安《淮南子·人间》说“武王荫暍人于樾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说的就是为中暑人打扇的情形。吕望《六韬》卷二已有“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之说;《管子·四时》亦有夏行五政之三曰“禁扇去笠”之语,讲的都是扇的招凉解暑作用。此外扇在汉代还被用以障面,《汉书·张敞传》记述“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古注曰“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
汉代扇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汉成帝时的班婕妤《怨歌行》诗中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歇炎热,弃捐箧筒中,恩情中道绝”。葛洪《西京杂记》卷一称汉朝后宫有“夏设羽扇,冬设缯扇”的制度,又说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时收到其女弟昭仪送的礼物有“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云母屏扇、琉璃屏扇、五层金博山香炉、回风扇”等。由此可知汉代宫廷中扇的种类与使用情形。
从考古材料看,湖北江陵楚墓出土有短柄竹扇,扇面略呈梯形,以红黑二色漆竹篾编织,较长边固定于柄上,是典型的“偏扇”或“单门扇”。同时出土的还有长柄与短柄羽扇,扇面呈半圆形与椭圆形。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也出土有短柄竹扇,其形制也是扇面略呈梯形的单门状偏扇。有认为此类偏扇,即是《汉书》中所说之“便面”,[1]虽然解释不同,但偏扇或“便面”在汉代十分流行,为汉朝上层人士或富有阶层的常用之物,则是不争的事实。[2]
汉代画像中对此就有较多的描绘,刻画的奴婢所持之扇差不多皆为偏扇,由此也可知这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形制。河南南阳市东关李相公庄出土的“许阿瞿墓志画像”,就刻画了年甫五岁的许阿瞿端坐榻上观看舞乐百戏,一位奴仆持偏扇于身侧为其纳凉的情景。山东嘉祥地区的画像石特别是武氏祠的石刻画像中也有较多的画面刻画了奴婢手持偏扇站于主人身后为其纳凉或侍从持便面跟随于车骑之后的情形。其中后石室第五石局部还刻画了手持偏扇的羽人为伏羲、女娲打扇纳凉,显然是将人间的真实生活情景挪用到神话传说之中。在有的表现西王母的画像中,亦有侍者手持便面的情景,其手法与用意也是一样的,借用了人间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来表达对西王母的尊崇。例如山东滕县大郭村以及城里宏道院等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就对此作了生动的刻画。江苏徐州地区出土的画像石对汉代上层人士或富有阶层使用偏扇或便面的情形亦有较多的表现,还有安徽宿县禇兰镇出土的画像石上对众多男女手持便面交谈的情景更是作了详细的描绘。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等地出土的画像石刻庖厨图中还刻画了使用便面扇火烤肉串的情景,四川出土的画像砖上则有庖者执便面跪于釜前扇风添火的画面(图三),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据称如今在新疆还可以见到用这种偏扇烤肉串的景象,[3]或许就是汉代的遗俗。
三
奴婢在汉代社会属于被奴役的群体,按照恩格斯的论述,都是“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4]。从考古资料来看,汉代奴婢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越是达官显贵或是大地主与富豪阶层占有的奴婢就越多,如各地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奴婢俑就是显著的例证。它们作为奴婢的模拟物与随葬品,不仅表达了要在冥界中为死者继续过豪华生活提供服役的殉葬观念,而且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拥有奴婢的情形。古代文献对当时统治阶层拥有奴婢的情形也有较多的记载,如葛洪《西京杂记》卷一、卷三就分别记述汉高帝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霍光妻“奴婢不可胜数”;“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述将陵侯史子回之妻因嫉妒“绞杀侍婢四十余人”,可知其家中奴婢之多。蜀地临邛有许多因冶铸而发财的富人,“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 [5]。
总之,这种统治阶层与富豪们大量拥有奴婢的情形在汉代社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汉代奴婢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服侍主人和家务劳动,这在汉代画像中就有相当真实和丰富的描述。从画面表现的各种内容来看,汉代奴婢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其中绝大多数为侍从奴婢,又有伎乐奴婢、驾车奴、驭马奴、守门奴、炊厨奴婢,以及从事清洁、饲养家禽、喂养牲口、担负各种杂役的奴婢,此外还有个别为主人从事手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奴婢。汉代奴婢中亦有一定的等级,有大奴、大婢、小奴的区分。[6]汉画中刻画的侍从奴婢,穿着都比较讲究,身材容貌也秀丽可观,显然都是墓主人生前喜欢的和等级比较高的奴婢。此类奴婢在画面中有较多的描绘,其用意主要还是为了衬托墓主人的身份和表现墓主人曾经享有的豪华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各地的奴婢情形并不完全相同,由于官僚阶层的分布与社会经济的差异而展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汉代画像对此都有充分的揭示。汉代画像提供的图像,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对研究汉代社会结构与等级制度等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注释:
[1]参见饶泽民编著《扇苑古今——中国扇趣话》12页,农村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周到、王晓著《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第4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册第1364页词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
[3]参见饶泽民编著《扇苑古今——中国扇趣话》第205页,农村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高文编《四川汉代画像砖》图十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又见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