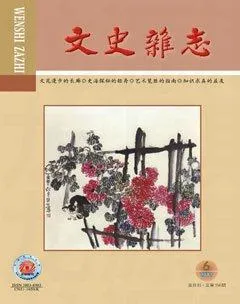明清两代在宜宾采伐“皇木”
明清时期,金沙江下游(即古之“马湖江”)两岸特别是屏山县老君山地区古木参天,覆盖着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其中不乏珍贵木材桢楠、香杉等,且驰名全国。为满足封建统治者修宫殿、陵寝、园囿的需要,从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起,到清朝嘉庆七年(1803年)止,朝廷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为时长达四百多年的采伐“皇木”的活动,谓之“木政”。
早在明朝初年,叙州府(今宜宾市)地方官便将老君山珍贵树木作为贡品向皇室进贡。现在老君山原始林区之内的桢楠,胸径2米,高二十多米,树龄在四五百年者仍为数不少。《屏山县志》明确记载,老君山桢楠为明清两代宫廷金柱(擎天柱)的御用木材。清康熙时修《叙州府志·宜宾县》(手抄本)及嘉庆《宜宾县志》均记有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都御史刘南峰曾来宜宾“办理采运皇木事宜”。明嘉靖《四川总志》则记有正德进士、江西人潘鉴,继刘南峰之后,以“钦差巡抚都御史允行粮储事宜”的名义,来宜宾办理“皇木”事宜。据明清史籍记载,故宫各大殿所用之桢楠、香杉,均大量取自宜宾地区。故宜宾名贵树木在国内知名,即起于明清两代。
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1406年),宋礼以工部尚书身份亲到四川督军民采木,马湖府(今宜宾市属屏山县及凉山州雷波县一带)地区便是重点采伐区。当时,森林大材近河者多,以至在马湖府老君山中采得围以寻尺、干逾寻丈者若干。这许多超级木材要运出山外需砍树开道,“庸万夫力乃可”。可能是遇上山洪爆发,“一夕,木忽自行达于坦途。有巨石当其冲,夜闻吼声如雷,石划自开;木由中出,无所龃龉;度越险岩,肤寸不损;所经之处,一草不掩。”于是永乐帝特封老君山为“神木山”,并命大学士胡广撰写碑文,建“神木山祠”于其地。此事,《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也有记载:“神木山,在沐川长官司西二十里,旧名黄种葛溪山,本朝永乐四年伐楠木于此山。一夕楠木不假人力移数里,遂封为神木山,岁时祭之……南现山,在沐川长官司北,永乐五年建神木山祠于其上”。今屏山县中都镇东南白塔乡,古名迎恩庄,有迎恩桥,还有嘉靖壬寅(1542年)书的“迎恩桥”三字。相传沐川长官司在此地迎接御赐“神木山碑”而得名。
嘉靖二十年(1541年),由于皇宫奉天殿遭火灾,急需珍贵木材,嘉靖帝命李宪卿为左副都御史,再到川南、滇东北金沙江下游地区采办“皇木”。李宪卿到蜀后,考察近水处已无大木可采,“乃行巴庸僰道,转荆岳,至东南川,往来督责,钩之荒裔中”,“于是万山之木稍出。”此次采木历时3年,虽“深入穷搜”,不过得丈围以上楠杉二千余根,丈四五以上楠杉117根,仍比不上永乐时建故宫三大殿所用金柱的围长。足见这种过量的开采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使金沙江下游地区楠、杉生产受到明显不利影响。正如清修《四川通志》所云:“近世以来,特重蜀之楠杉,深岩丛箐,缒幽凿险,万工举斧以入,但乐其材之足用,而弗审纲运之艰。其弊遂有不可胜言者”。
清代,“皇木”的采伐量也颇大。如康熙六年(1667年),工部议修太和殿,需要大量楠木。四川巡抚张地德奉旨,亲至马湖府一带考察,称“栋梁之材,各箐之中,大约皆可采办。”但因明代连年采伐,离溪水、河流近处容易移运的木材已伐光。“若百里之外者,山势逾峻,道路逾险,虽有大木,无可如何矣。”(《四川通志·木政》)故时仅采得珍贵楠木80根运到北京。又据《四川通志》卷七十一引清《王德元疏略》:“(乾隆)三十年,四川总督鄂尔泰进正楠木二十根,余木两根,富顺县宰、屏山巡检运送进京,送至圆明园交收。”“乾隆三十年,四川总督鄂尔泰委叙州知府、巴县知县于屏山县高竹坪等处采办大楠木三十六根运送圆明圆。”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北京重修太和殿,清廷指派户部郎中齐穑、四川巡抚抗爱、马湖府知府何源濬等人动员一千多民工,准备上老君山采伐“皇木”。经过一番踏勘之后,何源濬认为,采伐、运输困难重重,遂详陈种种理由,上奏朝廷,恳请停办此项差事。清廷采纳了何源濬的意见,遂使老君山原始林区的珍贵树木逃过一劫。但如前所述,乾隆年间,清廷又在屏山一带采伐“皇木”,只是规模已大不如前。直至嘉庆七年(1803年),清廷正式下诏,停止在金沙江下游地区的“皇木”采伐活动。这场自明朝初年开始,为时长达四百多年的“木政”活动才真正结束。
作者:宜宾县二中历史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