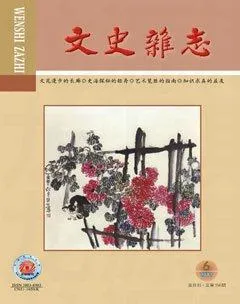韦皋镇蜀与佛教
韦皋乃中唐名臣。唐德宗因避朱泚之乱而奔奉天。此时干戈扰攘,京师横溃。韦皋以智谋瓦解了叛军对他的诱惑,而且在诛除叛逆中有大功于王室。因此,兴元元年(784年)德宗还京时,任他为左金吾卫将军,寻迁大将军。
贞元元年(785年),韦皋拜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御史大夫等要职,居蜀方面重任达21年之久。他在安定蜀中,平定西南少数民族侵扰方面功勋卓著,尤其在对吐蕃和南诏方面的用兵,取得了巨大战绩(详下)。剑南西川与云南、西藏也因此而安定下来。
韦皋在安定两川之后,对文治颇为重视。他与佛教关系颇深,在蜀中名刹——成都大慈寺的建设方面成绩突出。
辑录在《全唐文》中韦皋的文章凡九篇,其中即有四篇文章乃专就佛教及大慈寺所作,足见其与佛教结缘之深,与大慈寺关系之密切。他在《宝历寺记》中说:“宝历寺者,剑南西川节度使……所创也。臣皋以守司西蜀,向二十载,奉若睿旨,缉宁遐夷,兵休边陲,人获富庶,天宝为德,顾何力焉。”在境安民庶之际,与佛缘分深厚的封疆大吏韦皋决定用自己的俸钱建造宝历寺。文中又写道:“遂以俸钱于府之东南择胜地建仁祠,号曰‘宝历’”。如此举措,得到唐室首肯。经过勘察与周密设计、选址、构建而成之宝历寺:“增峻址,列高墉,规梵天而立制,集班倕以骋巧,邃殿耽耽以云蔚,危楼蘧蘧以虹指……锦江澄明而俯槛,雪岭晴开而入座。用能崇福广化,网罗群生,晓钟清水月之音,宵呗警昏沉之耳。”
为了弘扬佛法经义,他还“刊梵文于贞石,炳万字于云幢,所以导瞻仰之目也。禅堂究无生之义,广座喻莲花之旨。”从而实现“咸以见闻,悟于观听。孰不归于正而去其邪”的目标,净化人们的心灵。这是韦皋崇佛重法的缘由。
为此,韦皋还在戎马倥偬与政务繁剧之暇,撰写了《宝园寺传授毗尼新疏记》和《西川鹦鹉舍利塔》二文推尊佛理,阐释像教,前者赞颂大圣如来的伟大。为了弘扬佛教,规范义理,整饬戒律(毗尼),对于流传渐久,门派师说各异的紊乱情形予以澄清,以达正本清源之目标,韦皋也以自己的薪俸倩人缮写毗尼“新疏四十本,兼写法华疏三十本,命宝园(寺)大德光翌总而行之。爰集缁徒志行纯深,表仪端素二十一人,随给其疏,以成其志。”至于后者,则为旌扬灵异聪慧的鹦鹉。其能念弥陀诵经,临终之际,随磬击之音而念弥陀。它火化之后有舍利十余粒,传为神奇。僧众遂将鹦鹉舍利建塔纪念,韦皋特著文悼之。
韦皋与大慈寺的因缘是他对大慈寺的修葺扩建。《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载录其事。
文章破题,以简括中肯之笔,点明重修之由来:“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无缘,诚感必应。大慈寺普贤像,盖大照和尚传教沙门体源之所造也。”彼时造像:“仪合天表,制侔神工,莲开慈颜,月满毫相……”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未能及时修缮,以至于出现危栋泄雨,颓墉生榛,狐狸枭鹫,号啸昏昼”。这距离大慈寺之修建不足半世纪光景。大慈寺的破败荒凉已到如此地步!
于是,韦皋发出喟叹:“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达群迷,何废兴之变阴骘于冥数!昔大历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许人也,曰,斯像后十年而废,二十年而复兴……”韦皋决定再修此庙,重塑菩萨慈容。他的具体做法是将菩萨和殿堂“南迁百余步,度宏规,开正殿,因诏旨(得到皇帝的诏意,即文中所说:我今皇帝神圣纂图,诣四方蓝宇,修旧起废),谕群心。千夫唱,万夫和,奋赑屃,岑穹崇,横绳运,巨力拔”。经过努力,大圣慈寺再现辉煌雄姿,菩萨仪容:
观其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诱。安得不大其栋宇,规正神居哉!
韦皋认识到:“夫像设陵夷,去圣弥远。言教者必滞于物,遗物者亦住于空。将求乎中,宏我至教。乃择释子达真源之所归者,于以居之。皋受命方镇,十有七年,求所以赞皇猷,裨大化,尝以万民之心,不俟惩诫,靡然归善者,释氏之教宏矣。况冥祜昭报,大彰于时,崇而守之,亦同归之理也。”
这即表明,佛教于民众而言,劝善远恶,净化灵魂之意甚明,是广大信徒的精神家园,具有普世意义的灵魂归依,其意义是巨大的。
韦皋镇蜀21年,其安定社会秩序,维护民生的历史作用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对于韦皋的历史评价,新、旧《唐书》颇不一致。《旧唐书》云:“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其从事累官司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又或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故刘辟因皋故态,求不轨以求三川,厉阶之作,盖有由然。”
然而,《新唐书》对韦皋的评价与之相悖:“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擒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善抚士,至虽婚嫁皆厚资之,婿给锦衣,女给银涂衣,赐各万钱,死丧者称是。其僚掾官虽显,不使还朝,即署属州刺史,自以侈横,务盖藏之。故刘辟阶其厉,卒以叛。”
两《唐书》对韦皋的评价表面看来是截然相悖的,但细加寻绎,又可获得趋同的认识。《旧唐书》着眼于“重赋敛”致使蜀土虚竭,长年用兵必然带来的蜀中疲惫。而《新唐书》则以韦皋对吐蕃等用兵起到的靖边安民的积极价值为重,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长年用兵必然消耗人力财力,可是,如果不以兵止兵,又何谈保境安民呢?
《新唐书》的评论较为客观,韦皋善待下属,应予肯定;而自署府州刺史则不足为训。两《唐书》一致指出,这样做乃为掩盖韦皋在蜀的劣迹,所造成的恶果是刘辟之乱。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历史过错,也是韦皋无法抹去的污点。
《新唐书》载:“始,皋务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岁一复。皋没,蜀人德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镵其文尊讳之。”《新唐书》又载:“始,天宝时,李白为《蜀道难》斥严武,(陆)畅更为《蜀道易》(“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以美皋焉。看来,韦皋善抚士,厚待蜀人应属可信。
韦皋并非詩人雅士,乃一方镇大吏,然则在《全唐詩》卷三百十四中辑其詩三首,最末一首乃一绝句《忆玉箫》,隐含着一段悱恻缠绵的浪漫故事:
黄崔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
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
《云溪友议》卷中记载此詩背景颇详:“西川韦相公皋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只候侍于韦兄……玉箫年渐长,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君季父书,……发遣归觐……”韦皋依依不舍地与玉箫别离,“遂与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载,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詩一首……”可是,别后玉箫“郁念成疾死”,使这段情感留下极大的遗憾。此可见韦皋情感世界的一个侧面。
韦皋镇蜀虽有坐大一方之嫌,却无背叛朝廷之念,这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中唐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亦并非溢美。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