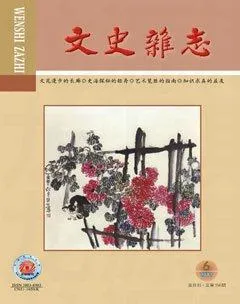浅析契丹与北宋的正统之争
正统问题是历代以来争讼不已的问题,上古时期便有中国和“四夷”的区别。谁为中国统治的正统?对于这个问题的争执在北宋和契丹之间尤为明显。
一、契丹王朝和北宋的正统之争
“契丹”以镔铁为原意,象征着很坚固的意思。契丹在公元916年由耶律阿保机建国,兼并周边民族政权,一跃成为中原北方第一大国,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而当时中原正处于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无暇顾及北边,遂使契丹坐大。北宋自立国之始,便与契丹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北宋总是负多胜少。契丹统治者在各个方面和北宋都展开争夺。契丹自辽穆宗以后,基本上放弃了用武力直接统治中原的想法,尤其是在“澶渊之盟”(1005年)以后,北宋和契丹的边境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没有爆发大的冲突。但契丹汉化的进程确实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辽圣宗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儿子辽兴宗就称赞他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有唐世文皇。”[1]兴宗是说唐王朝后面,都没有固定的正统,北宋也不算,自认契丹是正统王朝。辽国的君臣在与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一直争锋相对。契丹的统治者进一步发扬了上古时期儒家的正统观念,认为自己不属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列,应该和宋朝拥有同样的地位。纵观整个北宋的历史,契丹王朝在和北宋的交往中,一直坚持互相称南朝和北朝,以此来显示二者的对等地位。虽然北宋在内心一直不情愿,但现实无法改变。“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北宋统治者基本默认了契丹北朝的称呼,这样二者就成了手足兄弟国。北宋也就是承认了契丹,默认了契丹的正统地位。
1.契丹的政权建设 辽太宗之时(公元927-947年),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此后便加快了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步伐,但社会上仍然有很多奴隶。契丹国家的奴隶来源主要是四个方面: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奴隶可分为官奴和私奴,私奴称为驱口。[2]契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增长财政来源和增加赋役,开始抑制奴隶制。“澶渊之盟”以后,因为缺乏大量的可掠夺人口,奴隶制进一步受到约束。辽圣宗时,一些奴隶被编制成国家直属部落,称为编户。这一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提高,统和十四年(996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3]契丹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顺利过渡到封建社会。
2.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 契丹建国之初,汉人韩延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契丹确立各项制度,正君臣、定名分,加速了契丹封建化的进程。契丹人于公元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实行的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4]“定制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5]这充分显示了契丹统治者政治制度以及法律的成熟。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帝以“君臣同志,华夷之风”诗进呈皇太后。[6]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显示了契丹王朝的进步,反映了契丹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契丹自兴起之后,便给人以强悍的形象。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因拥有骁勇善战的骑兵,在与宋、西夏的战争中经常取胜(西夏就曾经臣服于契丹),在和北宋的争斗中一直处于上风。战争的胜利使得契丹在周边国家中形成了威慑力。
3.文教与礼法观念的普及 契丹自建国之时,就吸收了大量的中原人士进入统治机构,上文提到的韩延徽就是典型的例子。契丹在占领燕云十六州后,又开始大规模接受汉族文化,积极引进人才。统和七年(989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7]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8]不过在“澶渊之盟”以后,契丹却关闭了从北宋吸收儒生进入官僚机构的大门。契丹为了人才培养的需要,还推行科举制。契丹建国初期,就在上京设置国子监,燕京建有太学。学校教育普及则在道宗时期。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9]中京国子监、应州、滦州、高州、良乡县、新城县、玉田县等州县的学校都是道宗以后创办的。[10]朝廷通过普及学校教育来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大大提高了契丹人的文化素质。
契丹原本没有佛教信仰。契丹建国初期为安置移民、收揽人心,遂开始借助佛教的力量。至太宗,则将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迁往木叶山,供奉于菩萨堂,消解民族隔阂与儒家价值观中的“夷夏之防”,佛教渐成契丹信仰。随着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流播辽境四方,成为凝聚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核心思想,并对契丹人的衣着服饰、生活饮食乃至政治、国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丹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加上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文化教育有了很大的提升。国家提倡礼法治国,则对各级官员提高了要求,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这样使得整个契丹民族兴起读书热潮,许多文人雅士写出与中原人士同样好的文章,有些人还有文集传世。契丹历代统治者中,有许多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比如圣宗、兴宗、道宗。契丹能有这么高的读书热潮,与中原文献源源不断地输入有很大关系。通过边境榷场以及掠夺等其他途径,中原的许多文献都成了契丹人家中的珍宝。如宋州逸士魏野工诗,“契丹使者尝言本国得其《草堂集》半部,愿求全部,诏与之”。[11]这反映了契丹人对学习汉文化的渴望。
正是由于契丹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使得他们对天下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也是文明之邦。契丹国力雄厚,加上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周边民族臣服,使得契丹民族充满自信,认为自己才是中国的正统,并不是中原王朝所说的蛮夷。所以契丹在各个方面和北宋展开争夺,一直延续到契丹灭亡。
二、如何看待契丹王朝和北宋的正统之争
到底何为正统?简单地说,就是皇帝得来的皇位是不是名正言顺,所建立的王朝是不是顺天应人。古人用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说来解释王朝的正统性,这固然带有迷信色彩;然而,在古人心中遵守伦理道德是应当时时牢记的,没有什么比正统更具有号召力了。一旦被认定是正统,统治者就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百姓的拥护,皇位和所建立的王朝才能够稳固。
提到正统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北宋欧阳修的《正统论》。在《正统论》中,他说:“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2]从这里可以看到,欧阳修的正统论是从道德和功业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王朝的历史地位。在我看来,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一、皇位来得光明正大且统一天下。二、来路正,但没有统一天下。三、来路不正,但统一天下。由此,他认为历史上的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于来路正且统一天下类。同时,欧阳修还提出“绝统论”。“绝统”就是这一时期没有正统的王朝,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有正统也有绝统。在他看来,北魏和东晋对峙时期就没有正统王朝。与欧阳修不同的是,司马光在看待正统问题上认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不可移夺者也”,“非大公之通论也”,[13]故而他提出自己之所以编撰《资治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14]司马光很看重国家的兴衰和老百姓的生活,他以功业来评判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种观点是根据历史事实来的,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与之相比,欧阳修除了认定功业之外,还把道德枷锁安在这个问题上,很明显地带有主观意识。
欧阳修对契丹的正统地位向来是不屑一顾的。他作《新五代史》,将契丹的史事载录于书后,为“四夷附录”,这件事情使辽的统治者极为不满。寿昌二年(1096年)刘辉上书认为,欧阳修既然作书对辽朝“妄加贬斥”,辽亦应“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15]。不用说欧阳修是在极力维护宋的正统地位。但依上面提到的欧阳修的观点来看,北宋的正统地位却大有问题。欧阳修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其一,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建立的北宋来路并不正。周世宗柴荣对他委以重任,信任有加,但他却从柴荣留下的孤儿寡妇那里夺取了天下,实在是背主负恩。虽然说赵匡胤还有些军功,但他的做法在古代就是夺国篡位。可以再看一下宋太宗赵光义的皇位,虽有太后撑腰帮他取得合法继承人的位子,但他一直背负着“烛光斧影”嫌疑,有杀兄篡位之嫌。虽然这个千古之谜已经无法解开,但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二,赵宋从未统一天下。北宋的君主们不得不承认北方还有个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契丹皇帝,而且作为汉族传统区域的燕云地区也一直处于辽的统治之下,周边还有西夏和金。北宋在和他们的战争中总是负多胜少。所以翻开北宋的发展史,总感觉一股压抑的气息,给人一种积弱的感觉。正因为得国不正,北宋的君主们以及他们的南宋继承人最希望自己的臣下生活奢侈,耽于享乐;最忌讳那些一身正气,有理想的正人君子。岳飞之死的主要原因诚然是因为他违反了宋高宗求和的既定国策,但是也和他的正直清廉有很大关系。北宋在缺乏自信心的君主们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士大夫官僚大面积地制度性腐败。而宋朝的命运也和晋朝出奇地相似,只能苟延残喘,等待来自北方的民族来吞噬自己。这样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内心充满了恐惧。它的“重内轻外”、“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与其说是吸取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倒不如说是潜意识中对自己政权来路不明的焦虑在政治决策上的反映;它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与其说是政治宽容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一种制度性的政治收买。它的“相互制衡”和“祖宗之法”使得国家机器在无休止的内耗中丧失活力,最终只能接受灭亡的命运。
不过,契丹王朝自谓的正统地位也是不能成立的。契丹作为少数民族没有像后世的蒙古和满洲一样入主中原、统一全国;而它在文化上与中原文明的差距乃是全方位的,不是几十百把年的努力可以追赶上的。所以,不管是按照欧阳修的正统论还是先秦儒家的观点,契丹王朝所谓的正统地位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倘若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把辽宋对峙时期称为“绝统”才更合适。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国与国之间斗争的主体民族最后都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中,所谓正统之争也就自然宣告结束。
注释:
[1]转见张希清、田浩:《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参见李锡厚:《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5][6][7][8][9][15](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10]参见陈述:《辽金史论集》,《辽代教育史论证》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五,大中祥符四年三月甲戌。
[12][13][14]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历史文献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