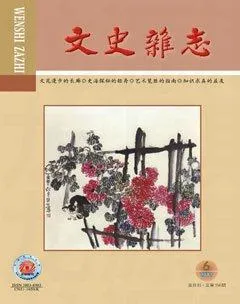对四川保路运动演进的几点思考
三
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十余日,鉴于成都一时难于攻下,经保路同志军主要首领商议,决定实行军事转移,分兵攻略州县,将反清革命烈火引向全川。秦载赓率领东路保路同志军与龙鸣剑、王天杰领导的荣县保路同志军会师后,成立东路民军总部,在一个月时间里攻占川南10余个州县。侯宝斋率领南路保路同志军与周鸿勋所率邛州巡防军反正士兵会合于新津,建立川南保路同志军总部,与清军在新津战斗半月后,转为分散作战。川西平原上其他地方的保路同志军前仆后继与清军开展争夺城镇的战斗。川东、川北各地保路同志军起义风起云涌,袭击清军,攻占城池。西昌地区彝、汉、回、藏各族群众5000余人在张耀堂带领下起义,攻进西昌城,冲进县衙,诛杀作恶多端的西昌知县章庆。川西北藏、羌族起义民军与川西保路同志军并肩作战,攻城略地,屡建奇功。川边藏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汹涌澎湃,除巴塘、甘孜、炉霍等几个孤立的据点外,广大藏区都被起义军控制。四川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气势磅礴,发展迅速,汇集成反清革命的洪流,导致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最终土崩瓦解。
1911年9月25日四川荣县独立,创辛亥年间革命独立之先河,引动着四川全省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滚滚独立潮。四川的革命独立,先在州县兴起,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推动着四川中心城市重庆、成都实现独立;然后,又推动全省未独立的州县实现独立,再建立全省统一的革命政权,光复全省,从而展现出四川革命独立的特有运行轨迹。这不像有的省份那样,在省城发动起义独立,然后传檄而定,全省光复。
通观保路同志军兴起、发展的历程,有关保路同志军的性质、群众基础是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1.关于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性质。
保路同志军是四川人民进行反清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同盟会会员、四川保路运动参加者、保路同志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曹叔实曾说:“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兴之始,促亡满虏,不可谓无功。”又说:“该军(保路同志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28]保路同志军是在同盟会组织下建立起的一支反清革命的武装部队。就整体而言,领导保路同志军起义的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保路同志军则是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四川保路同志军以同盟会政治纲领为指导,擎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东路民军总部“以三万余人,占领四县。而各军皆树旗四面,文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29]向来以“排满兴汉”为固定不移宗旨的哥老参加了保路同志军,“对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非常拥护。”[30]同盟会会员、哥老会首领罗子舟于1911年9月17日率领保路同志军围攻雅安城发出布告,以“撞自由钟,竖独立旗”为号召。[31]与云南盐津县毗邻的四川宜宾县大关河地区的民众,在保路运动中接受了爱国教育和革命宣传,认识到广大群众对清王朝的愤怒,“一旦爆发,萃为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势如烈火燎原。”当李乐伦等人接到成都发的“水电报”时,立即联络,由川、滇两省群众组成大关河同志军进行起义,提出“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周善培),上成都”的战斗口号。[32]大竹保路同志军起义发布檄文,“声讨清朝种种罪恶,说明起义的目的:驱除鞑虏,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号召各地人民共同起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33]周鸿勋率领驻邛州巡防军起义以后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名山县宣布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于士兵肩章上写:‘中华国民军’,周则用中华国民军武字营统领头衔。”[34]1911年11月19日,同盟会会员凌阗在江油起义。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反清起义,早在1908年11月,凌阗与另一位同盟会会员刘绳初就以“大汉革命排满光复军司令官”的名义,写好讨清檄文,秘密传播。他们在檄文中明确宣布:“今日揭竿义旗,继孙逸仙、黄克强排满兴师”,以达到“驱逐满奴,勘定中原,共和告成”的目的。[35]
上述事实表明,保路同志军高标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以同盟会政治纲领为保路同志军的指导思想,以及为实现同盟会政治纲领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发出的号召,提出的战斗口号等,已在当时保路同志军中乃至社会上快速流行而独步一时。虽然在保路同志军兴起之初,有的保路同志军对起义的任务、目标不明确,停留在单纯追求保路权,救蒲、罗的层面上;但是,由于时代潮流的推动和整个革命形势的影响,他们很快就融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潮中,接受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使其行动转变为推翻清王朝、实现革命独立的起义。
保路同志军遵循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实现革命独立为奋斗目标,战斗在巴蜀大地上。保路同志军群众基础广泛,发动迅猛,手执窳劣武器,英勇奋战,到处出击,打得清军“防内攻外,东驱西击,刻无暇晷。”[36]清军如蹈入汪洋大海中。各地保路同志军一次又一次地连续作战,历经近半年的武装反清斗争,终于埋葬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迎来了四川全省整体性的革命独立。
回溯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可以证实四川保路运动与保路同志军起义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发展整体,两者紧密联系构成辛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辛亥年间四川革命的实情,可简明地称之为四川的辛亥革命,这也是符合历史本义的。
2.关于保路同志军的群众基础。
保路同志军起义是具有群众性的反清武装起义。群众积极参加保路同志军,群众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保路同志军,是保路同志军一大优势和显著特点。
保路同志军兴,群众踊跃参军。在保路同志军初起义时,有的起义队伍达万人,有的几千人、数百人,或百余人不等。如秦载赓于1911年9月7日晚率华阳保路同志军千人向成都挺进与清军作战,同时派人四出号召群众参加保路同志军;到9月10日“四方应召者万余人。”[37]同盟会会员向迪璋在双流起义,杀知县汪橡圃,“不一二日同志军达双流者逾六千人,环邻八县皆景从。”[38]同盟会会员、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在大竹县大寨坪率众举义,参加起义的群众达数千人。当革命党人张达三、张捷先在郫县新场筹组西路保路同志军时,成都及邻县各学堂学生出于爱国热忱和受同盟会宣传的鼓舞,先后有五百余人奔赴新场要求参加保路同志军。经张达三等人研究,决定在西路保路同志军中建立一支学生大队。当时,也有四川陆军小学堂学生离校回乡参加保路同志军。在广阔的巴蜀大地上,人民群众参加保路同志军者络绎不绝。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纷纷加入保路同志军的反清武装斗争。例如,川西北汶川瓦寺土司索代赓在保路同志军兴起时,率领由藏、羌族群众组成的一支三百余人的民军队伍到灌县,协同灌县保路同志军作战;接着与川西保路同志军一道,转战于成都西郊和郫县、崇宁一带,直到四川完全独立才回故里。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还得到云南盐津、绥江和贵州仁怀等地群众的响应与支持。他们组织武装力量与四川保路同志军并肩作战。四川保路同志军由于有群众踊跃参军,其规模之大,气势之猛烈,在辛亥革命中是仅见的,令世人瞩目。
保路同志军是以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反清革命队伍。在保路同志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援。“人民箪食壶浆来迎。”[39]他们见到保路同志军“则助粮助饷,见兵则视同仇雠,甚至求水火而不与。”[40]广大群众热情沸腾,人多胆壮。当保路同志军作战时,妇女亦争先恐后作侦探,或在保路同志军设伏地区协助保路同志军点燃地雷引线以打击敌人。在郫县,人民群众欢送学生军出征的情景非常感人。学生军行进至八里桥已时至中午,当地乡亲们安排学生们吃饭,“无论男女老少都像待客似的,满脸带笑劝大家吃饱”;还满怀感激之情地说:“你们这些读洋学堂的先生伙,也替我们去吆赵屠户,我们啷个不感激你们!狗日的赵屠户,自从他两兄弟做了制台以来,把我们四川百姓也算整够了!”吃了饭,学生军在群众欢呼相送声中沿着逶迤在稻海中间的泥路向东进发。学生军大队长蒋淳风感慨地说:“有这样的民心,还怕把赵尔丰撵不动么!”[41]从酝酿、筹组保路同志军到保路同志军起义的全过程来看,保路同志军是在同盟会厚积群众力量的基础上所组成的一支反清革命武装队伍。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保路同志军赢得反清革命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2]四川革命党人吸取了以往起义无人民响应而挫败的教训,因而在组织和领导保路同志军武装反清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重视发动群众,凝聚革命力量,将革命植根于民众之中。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才能使保路同志军的武装反清革命斗争迅猛发展起来,并集聚足以致清王朝于死命的革命力量,从而取得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的伟大胜利。
四
四川的辛亥革命以四川保路运动的狂飙和四川保路同志军的壮举而彪炳于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加速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对武昌起义爆发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评论四川的辛亥革命时曾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43]孙中山先生的评论客观公允,反映了辛亥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自辛亥广州起义以后,我国的革命运动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形成“以武昌为中枢”的长江流域革命战略的格局。武汉则成为大多数革命党人心目中选定的发难地点。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之际,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趋势,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为大举起义期。[44]但当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宋教仁审时度势,遂改定在辛亥年(1911年)八、九月间“乘机大举”起义。[45]这比同盟会中部总会原拟定大举起义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年。在湖北,因“四川路潮扩大,湖北中部同盟会汲汲欲动。”[46]在湖北武汉,“自蜀发难,武汉各镇翕然响风。”[47]1911年9月下旬,早已在湖北新军、会党和青年学生中发展组织,积蓄了革命力量的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鉴于四川保路运动已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感到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策动下,联合组织成起义的领导机关,积极准备在武昌发动起义。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由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同时,由于清廷令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四川爱国革命运动,使武汉防务削弱,给武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绝好机会。“武汉为四战之地,而非深根固蒂之区,必后路有堂奥之可凭,而后可以收进战退守之势。”[48]而地处长江上游与湖北接壤的四川自古为用兵者所必争之地。在武昌起义之初,四川保路同志军正与清军在巴蜀大地激烈战斗,使得清军不能从四川沿长江东下攻打武汉,从而减轻了武昌起义的军事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武昌革命军的西顾之忧。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迎来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四川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起义则是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爆发最重要的因素和原动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革命党人、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孙武密函通知入川鄂军中的革命党人杀端方,以助四川独立。12月27日凌晨,鄂军中革命党人在四川资州发动起义,诛杀镇压四川爱国革命运动的端方,除掉了四川革命独立的一大障碍,有力地支持了四川人民的反清革命斗争,受到四川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蜀军政府还专门发布告示,表彰入川鄂军起义杀端方对四川革命建立的功绩。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浴血奋战的四川人民,有力地推动着四川革命独立达到高潮,形成如川江那样奔腾激荡的独立浪潮,直到重庆的蜀军政府与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合并,全川统一,实现了四川整体性的全面独立。四川保路运动和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与武昌起义相互推动向前发展,体现了辛亥革命内在的规律性,这是辛亥革命一大特点。
注释:
[28][29]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相》,《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页,369页。
[30]政协綦江县委员会:《綦江县辛亥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80页。
[31][34]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199页,199页。
[32]李乐伦:《大关河保路同志会的武装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313、315页。
[33]政协大竹县委员会:《李绍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96页。
[35]檄文影印件藏四川博物院。
[36][40]《赵季和电稿》第4卷“致内阁”,第4卷“致内阁”。
[37]《蜀中先烈备征录》第5卷第13页。
[38]熊克武:《蜀党史稿》。
[39]郭孝成:《四川光复记》,中国近代史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41]《李劼人选集》第2卷中册第621、622页。
[42]《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01页。
[4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页。
[44]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
[45]徐血儿:《宋先生教仁传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44页。
[46]罗永绍:《谭石屏先生事略》,《谭人凤集》第436页。
[47]邹鲁:《彭义烈传略》,《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483页。
[48]《论川鄂有连合之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页。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