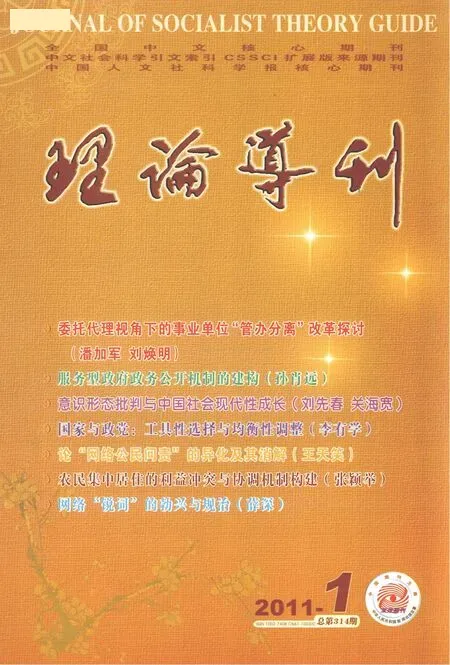国家与政党:工具性选择与均衡性调整
李有学
(河南大学地方政府与社区治理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4)
国家与政党:工具性选择与均衡性调整
李有学
(河南大学地方政府与社区治理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4)
国家和政党都是源生于社会的政治性组织。两者基于共同的社会基础而相互选择形成契合关系,但这种选择的互为工具性性质和目的性的不同导致这种契合关系的不对称。本文分析了国家和政党的不对称的工具性选择关系及其带来的多方面后果,并提出国家与政党改变这种不对称关系的均衡性调整方式。
国家;政党;工具性选择;不对称关系;均衡性调整
现代社会,政党在几乎所有国家普遍存在,而且“政党政治”成为现代民主国家普遍的制度模式,政党也因此在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有了不容置疑的基础性地位。政党成为民众与国家的媒介,将民众的意愿集中并通过体制渠道上升为国家决策,因此“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的主要区别标志之一,政党创造了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1]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政党政治”所导致的种种消极现象,比如: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冷漠,严重的政党腐败等等,可以说政党带来福音的同时又产生了危机和困境。如何理解这种现象成为现代政党研究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党和国家的工具性选择关系的分析解释这一现象,并对现代政党和国家关系的调整方式进行分析。
一、国家和政党的工具性选择
国家和政党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两者的相互契合,两者的契合是基于彼此的“有用性”和“有利性”基础上的互为手段的选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家选择政党——一种当然的选择。国家作为公意的集合体,其公共权力来源于民众的同意和权利让渡,其目的在于行使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可见国家是源生于社会的政治实体,其所代表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受到社会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制约并为其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民众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做的一种妥协、一种工具。但是国家一旦产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实体就会形成自身的利益要求而独立于社会。因此不管从社会工具性质的角度还是国家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国家作为一种权力主体都不只是一个抽象存在,它的意志必须能够被表达与执行。国家运转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家的政治表达和行政执行的协调,它的权力最终要落实到某个人或个人组织的集体上才有意义,因此“要使政府协调的运转,就必须找到某种使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协调一致的办法……这种办法在政府体制内部不能找到。事实上,可以在政党中找到它。”[2]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3]政党是社会内生性的政治组织,国家之所以会选择政党,主要在于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党有无比优越的特性和作用。首先,政党具有超强的聚合性力量。作为一个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实体,政党有着严密而坚固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纪律以及汇聚着强有力的政治精英群体,这使得政党在力量基础、战斗力保证和领导核心力等方面形成体系化集束力量,这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其次,在于政党的媒介性功能。在“国家——社会”的二元存在中,社会民众的利益要求以原子化状态存在,不可能直接传输到国家政治系统,而只能通过一定的中介加以转化。而具有明确政治取向的政党可以作为利益输入的媒介,而且这种输入并不是个人利益简单的集合。政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将原子化利益集束化并整合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并形成国家的政策。尽管这种媒介功能对于政党而言也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但是政党自身的强大力量和媒介功能却可以完成国家政治表达和行政执行协调的双重要求,所以比较而言政党就成为国家当然的选择。
2.政党选择国家——一种必然的选择。利益准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对利益的追求是各个行为体的基本出发点,霍布斯曾说:“在所有的推论中,把行为者的情形说明的最清楚的莫过于行为的利益。”[4]国家是一种获取公共利益的集合,政党同样是一种共同利益的集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政党的目的在于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基于此,政党首先必然也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找到一个能使之利益实现和最大化的实现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满足“可以”和“可行”两个条件,而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国家政权。首先,国家具有最广泛范围内的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是指“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5]国家的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使之统治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并因此获得持续存在的权威。如果政党可以执掌国家政权,那么政党的利益追求就可以在社会范围内具有至少是形式上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国家掌握并重新分配社会资源、财富、价值和权力,使之向符合自身的愿望和利益的方向发展。其次,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能量。政治权力作为“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6]2它的公共性、工具性、强制性和持久性为国家政策的实现提供了保证,而如果政党拥有了国家政治权力,那么政党就有了实现阶级利益的基础性手段,政党权力就由一种参与资格转化为制约性力量即政治权力,政党权力也相应扩大了其发生效力的范围并以政治权力的名义在国家政权体系内部发生效力,因此政治权力就可能成为政党“获取其它价值的工具”。国家作为民众认可的终极权威,其巨大魅力和能量对政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政党为实现其目的必然会选择以国家为手段,而事实上,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无不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国家对于政党如同政党对于国家一样都具有工具性质。政党和国家都是社会为解决自身的困境而内生的政治性实体。尽管两者又彼此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但是二者共同的社会基础使之相互契合成为可能,而同时二者都具有的工具性质使之为了彼此的目的而以彼此为手段相互选择成为可行。因此在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政治”间接实现民众利益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位置的。在“政党政治”作为协调机制在多数国家获得合法性支持而成为普遍现象的过程中,政党和国家两个政治组织实体也实现了彼此的工具性契合。
二、国家与政党互为选择的不对称与差异性目的
尽管国家和政党可以实现相互的契合,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国家和政党彼此间的契合选择是不对称的。国家对政党的当然选择隐含的是一种必须和无奈的情绪,因为只有政党比较符合国家运转的要件。而政党对国家的必然选择则是一种唯一的指向,因为有且只有国家能够使政党达到其追求的目标。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国家和政党两者契合的“政治边缘”,突出表现在国家的目标可能不会完全实现,因此国家和政党的契合实质上是不对称的相互选择。在国家与政党的政治跷跷板上,国家试图以大制小而政党则希望以小搏大,突出表现为两者彼此选择的目的存在巨大差异性。如果用“利益——价值”机制分析这种不对称与差异性,则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党两者在利益导向和价值取向两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
首先,表现为两者的利益导向差异。利益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国家和政党源生于社会,也必然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国家是人们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建立的,以实现个体利益为最终目标。国家以政治共同体的形式将个体利益统一纳入到公共利益的范畴。国家存在和运行的目标就成为实现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的实现带有普遍性意义。相对而言,尽管几乎所有政党都宣称其是大众性政党,代表全民的利益,但是政党的阶级本质表明政党追求的是本阶级的利益,是基于共同意识上的“准”公共利益,这种“准”公共利益是特定的集体利益,只具有特殊性意义。因此政党视野中的特殊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只是国家视野中的普遍意义上的“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利益可以更大限度的接近整体利益,但是却将两者利益追求方面的差异表露无遗。
其次,在于两者的价值取向差异。价值是“思维沉淀的产物;亦是一种思维定势,它表现为一定的主体之于客观世界的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看法或观感”,[7]价值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人们的信念以及行为方式。在社会范围内,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尽管国家具有独立政治人格,并有一定的独立利益,但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在于“民众同意”的合法性基础,而实现“民众同意”就必须满足“民众需求”,因此国家的价值目标定位于实现国家辖域范围内的“社会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善”的实现。政党是通过将阶级内部的个体资源整合为集体资源从而获得行动能量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基于特定阶级或阶层的“阶级意愿”,因此政党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本阶级的意志和期望以获取持续的动力支持。通过选举、革命等手段执掌国家政权以此将政党的纲领、政策以及意识形态合法化上升为国家意志表达,最终实现的是政党范围内的特殊的“阶级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追求的价值取向是“优”的实现。尽管政党追求的“阶级幸福”可以是国家范围内一部分公民的意愿与期望,但是这种片面的“优”的价值追求与全面的“善”的价值追求在整体意义上还是体现出国家与政党的价值差异。
从以上分析可知国家与政党的契合是互为手段而目的相异的不对称的契合,这种不对称的契合最明显地表现在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上。一般而言,“权力或权威有三个特性:广延性是指遵从掌权者命令的B(权力对象)数量很多;综合性是指A(掌权者)能够调动B所采取得各种行动很多;最后,强度是指A的命令能够维持很远而不影响遵从。”[6]15从这三个特征方面比较可以看出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在广延性、综合性、强度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政党权力作为部分力量的综合,在这三个特征上都要弱于全体力量的综合——国家权力。也因此国家和政党的契合关系使得国家权力得以运行的同时,契合的不对称却使政党权力有机会向国家权力延伸并表现出消融甚至替代国家权力的趋向。权力本质上作为一种工具有自我膨胀和不断扩张的趋势。“它总是有着一种越出自己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倾向于增加权力”。[8]国家权力过分扩张并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导致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政党权力的过分扩张并渗透到国家政治体系内部,导致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党。因此国家政治权力的所有和行使出现分离的趋向,而这在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就可能“引起政治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其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运行,以致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的所有者或偏袒部分所有者。”[9]这也是国家选择政党的无奈之下的隐含风险,而寄希望于政党良好的道德自律又是不现实的政党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可能使国家权力背离公共利益的目标而成为为个人或集团谋利益的工具,现实中常常出现的政党腐败为此做了很好的佐证。因此,如何消除或至少将不对称契合与差异性目的造成的恶劣后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成为各个国家必须解决的难题。
三、国家与政党的均衡性调整
国家和政党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权力完全回归社会是不现实的,而且国家和政党的存在和契合也在事实上减少了社会交易成本,因此只能采取调适这种策略性选择,加强国家与政党彼此之间的组织性均衡。均势理论认为达到双方力量均衡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设法减少较强一方的力量,二是增强较弱一方的力量。因此调适可以从国家和政党两个层面进行,此外,两者间的契合机制的调适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首先,国家层面的调适。国家层面的调适是国家采取的被动性策略,目的在于划分权力边界,确定行为范围,以此减少不对称与差异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整:第一,体制外的调适。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局面,扩增社会权力空间,增强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同时,减弱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支配,减少政府的权力空间和可支配资源。大量的经济组织、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性组织形成的群体联盟可以抗拒国家的自我膨胀,借以限制政党利用国家权力侵占社会权力与权利的空间。第二,体制内的调适。“政治——行政”二分使国家行政权力独立运行,不受党派争权的影响,政党则只被限制在“国家政治权力市场”进行角逐。这使得两者的不对称与差异性只会在有限范围发生作用,而不会影响国家的整体运行。
其次,政党层面的调适。政党层面的调适是政党采取的主动性策略,目的在于扩大利益表达范围,借以拓宽与国家对接的边界,以此至少在形式上增加选择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调适:第一,党内调整,扩大自身阶级基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导致的利益的分化和需求的多样化这种现实对于源生于社会的政党而言,意味着政党的发展壮大需要动员和组织更多的民众进入政党体系,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整合更多的利益诉求并代表之。以至于政党不惜更改自身的阶级思想、阶级政纲乃至阶级性质,其目的在于增强政党的包容性、回应性、代表性和适应性,使之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与国家实现整合以获取和加强主导政权的合法性地位。第二,党外调整,结成政党联盟。尽管这种党外调适的方式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却可以由此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取得某种至少是数量上的优势,这样的联盟由于获得了更广范围的利益代表,所以使得政党与国家契合的广度和强度增加,因此也不失为政党主动调适的策略选择。
最后,契合机制的调适。契合机制是指关于政党获取国家政权的体制渠道的制度性、程序性安排。在社会范围内,国家是唯一的,而政党基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则可能不是唯一的,契合机制的调适就在于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构建契合过程中的政党之间的竞争性政治生态,其目的在于实现党派间的竞争和制衡,致使任何执政的政党都不能不顾及阶级之外的利益诉求而表现为权力任意。反对党和在野党或者是采用“阶级合作”的合作党派会以自身力量监督执政党的权力行使,尽管这种监督行为主观上是为其自身利益着想,而且这种制衡可能造成公共管理效率上的风险,但是却能够在客观上使国家权力增强政治回应性,能够代表和实现更广范围的社会利益。此外,“一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保护其国家不受公民不满引起的破坏:抱怨和攻击针对的使那批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官员,而不是整个制度”,[10]这也使国家及其权力行使能获得稳定性制度基础。当然,如果能够创设一种合作机制,使执政党与其他党派能够实现政治体系内的协商合作,则既可以避免政治竞争的高成本,又可以实现均衡状态,则更是一种政治创新。
综上,国家与政党作为两个政治性组织,在现代政治背景下,事实上表现为工具性的相互选择。在和国家的契合过程中,政党客观上起到了利益表达、媒介传输、力量支持等正面效应,但是这种工具性选择本质上的不对称与差异性又导致政党可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必须在“社会——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对国家和政党的不对称与差异性进行均衡性调适,以尽可能减少不对称与差异性造成的不良后果,增加尽可能多的正面效用,以获得社会、国家、政党三方面共赢的效果。
[1]E·E ·Schattschnieder.Party Government[M].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42:1.
[2]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
[3]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479.
[4]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57-558.
[5]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10.
[6]丹尼斯·朗.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8.
[8]马里旦.人和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0.
[9]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04-305.
[10]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8.
D05
A
1002-7408(2011)01-0026-03
李有学(1979-)男,河南安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地方政府与社区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地方政府与政治研究。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