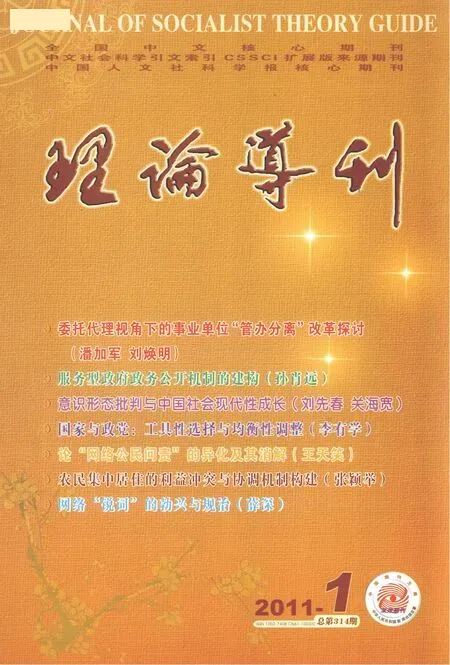唐玄宗晚年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缺失及其恶果
——以安史之乱爆发为例
金荣洲
(1.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062;2.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郑州450053)
唐玄宗晚年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缺失及其恶果
——以安史之乱爆发为例
金荣洲1,2
(1.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062;2.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郑州450053)
古代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爆发,实质上是唐王朝危机管理体制削弱和唐玄宗危机意识缺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为后世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危机管理案例。
安史之乱;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
唐玄宗李隆基在即位前期,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但是在其晚年,由于意志衰退,贪图享乐,委政于权臣,给朝政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尤其在处理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大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学术界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是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至今尚未见到相关成果问世。其实唐王朝曾经建立起一套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只是由于唐玄宗未能很好坚持执行这一制度,因而不能制约分裂势力的壮大,终于导致了这次公共危机的发生。可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缺失所导致的恶果。本文着重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例进行分析。
一、唐王朝危机预防制度的设计
经历隋末战乱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总结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制度设计上,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了革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防范机制。
首先,在宰相制度上,群相分权,互相制衡,集体议事,权归皇帝。唐前期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为宰相,虽然后来又出现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名号,但在宰相人数的设置方面,仍然保持了较多的职数,以便互相制约。宰相既然人数众多,为了便于对军国大事的讨论与决策,便必须有一个专门的场所,这就是政事堂,宰相权力更多地体现在政事堂会议上。为了便于议事,政事堂召开会议时必须要有一个主持者,这就是秉笔宰相,他具有首席宰相的地位。为了防止秉笔宰相专权,唐初规定由三省长官轮流秉笔,每十天一换,后来又改为每日轮换秉笔,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宰相专权擅政。
其次,部门之间权力的限制与制约。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省为制令机关,即皇帝的诏敕由其起草;门下省是审议机关,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必须经过其审议,否则不能颁布执行;尚书省是政务机关,皇帝的诏敕由其颁布执行。三省处于鼎立状态,也就是说其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一省也不得凌驾于其它省之上,从而比较有效地保持了这些重要部门之间权力的平衡,达到了相互制约的目的。六部隶属于尚书省,它们分别掌管全国的各类政务工作,相关政令都是由其制定并颁布,但是六部却不能直接掌管事务性工作,具体事务性工作是由九寺五监等部门掌管的,它们遵照六部的政令进行工作,自身并无制定政令的权力。比如工部掌管工程方面的政令,在工程立项、工程设计、工程预算等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具体工程建设的实施却由将作监等部门负责,工部并不能干预,这样就比较有效地预防了贪污与贿赂之事的发生。
再次,加强监督与检查。唐朝的最高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下设三院御史,即台院之侍御史,殿院之殿中侍御史和察院之监察御史。台院负责对在京百官的监察和奏弹,殿院负责殿廷供奉之仪式的监察,并与台院共同负责巡察两京地区(长安、洛阳),包括对两京各中央部门和郊区的日常巡察;察院则负责地方的监察,监察御史每年都要分赴全国各地巡察,发现不法之事,大事奏裁,小事立决,权力极大。唐代监察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加强了日常的监察工作,比如尚书省召开政务方面的会议,其有权参与,以便随时监察,在京各部门包括禁军驻地亦有权随时巡察。重要物资和资金出纳,御史台都要派人到场监察,并不是发生问题后,再事后查处。此外,唐朝的中央与地方各部门内部还设置有专门的审计与监察官员,并且规定本部门处理的公文必须有这类官员的署名签字,接受的上级公文和下发的公文,都由其登记接收和处理完毕的日期,以便随时监督,避免延误工作,拖拉扯皮。
在唐前期100多年里,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既避免了权臣专权,又比较有效地维持了各机构的正常运转,同时也有效保证了皇权的稳固和国家权力格局的相对稳定,具有十分明显的权力制衡的作用。
最后,在军事方面,形成了“内重外轻”军事格局,内外制衡,相互制约。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同时还有北衙禁军。太宗时,整顿府兵制度,把军府更名为折冲府。全国折冲府最多时有633(或634)个,其中关内道有261个。因为关内道是京畿所在之地,是军事防御的重点地区,故其军府占全国总数40%以上,兵力最为雄厚。如果关内道发生问题,举全国之兵力足可以进行讨伐;如果某一地区发生问题,仅依靠关内道之兵就可以轻易地讨平。
全国的军府分别由中央十二卫管辖,每卫各辖数十个军府,十二卫之间互不存在统辖关系,从而达到军权分散之目的。十二卫虽然有握兵之要,但却无调兵之权;兵部有调兵之权,却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唐朝规定除紧急军情之外,凡调发十人、十马以上,都要有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的符、契为凭,才可以调动军队。“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1]至于领兵的边将,“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2]皇帝通过兵部和诸卫(率)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常备军队。诸卫与兵部之间互相牵制,共同对皇帝负责。这种纵横交织的军事控制机制,有效保证了皇帝对军权的控制。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战略部署,形成了军事上居重驭轻的局面。在京城驻扎的禁军,分为北衙禁军与南衙卫军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互不统辖,其中北衙禁军归宦官掌管,南衙卫军由宰相统率,从而达到了相互制约之目的,在京畿形成了一种军事平衡,从而确保中央政权的稳固。
二、危机预防制度的破坏
唐前期在政治、军事上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唐帝国的稳定发展。但是到玄宗开元年间,这些有效的制度遭到人为破坏,制度上防范危机的功能逐渐丧失。
首先,宰相分权制度遭到破坏。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五房于其后:一日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3]由此政事堂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宰相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就是宰相的数量减少了,“开元以来,常以二人为限,或多则三人”。[4]秉笔宰相轮换制也遭到破坏,长期以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以中书令的身份任秉笔宰相,破坏了原来群相分权、集体议事之制,变相恢复了专职宰相制。在这一时期使职差遣制大为流行,出现了“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局面,[5]有的宰相身兼数十职,如杨国忠便是如此。他甚至在家中办公,决定官员的任免,而皇帝不加过问。
其次,内外军事制衡局面发生逆转。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府兵制至此遭到了破坏,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6]这道敕书的颁布,标志着府兵制的彻底终结。募兵制推广到全国,并允许节度使自行募兵,使节度使的权势顿时大增。自高宗中叶起,为增强边防力量,唐帝国主要是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广置烽戍,增加驻军,”至睿宗时,则开始在边境重要军区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年,节度使(经略使)陆续增加到十个:即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朔方、河东、范阳、平卢等节度使以及岭南五府经略使。这些节度使拥有强大的兵力和财力,而且全部分布在沿边地区,内地包括京师的兵力非常虚弱,从而使内外制衡的军事体制遭到了破坏。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共有兵士57.4万人,而边境上就有49万多人,竟比中央和内地多了五倍,其中安禄山的部队最多,拥兵20万,战斗力也最强。中央的警卫部队,因“天子(玄宗)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7]所以军事训练逐步废弛。南衙卫兵早已不复存在,而北衙禁军,养尊处优,以致徒有虚名。唐初以来的内重外轻的军事制衡局面此时却颠倒过来,变成内轻外重了。
再次,地方军镇主官定期换防形同虚设。在权力制衡、防范领军大将尾大不掉方面,唐朝政府已有制度化的规定:“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8]且唐代的各级官吏,上至刺史,下至参军等,均由中央直接任免与调动。由此可知,唐王朝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数年一任。仅仅如此还不够,在用人方面也有规定:“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9]6888-6889但是安禄山自天宝元年担任平卢节度使,天宝四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兼任河东节度使,到其造反时,长达十多年没有换地方,从而为其培育私人势力创造了条件。
玄宗从开元末以来,由于年事渐高,施政力求稳定,希望有一个能力强且忠于自己的人才来维护边境安定,这是他选择安禄山的根本原因,而缺乏应有的危机管理意识。唐玄宗对危机预防体制的改进,仅仅就是在开元后期设置了监军使,尽管这种做法在对其他领兵将帅的监督和牵制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然监军使最终也没有能阻止军权下移、领兵将帅势力膨胀的趋势,更何况他根本就没有向安禄山派遣监军使,可见其危机管理意识已经薄弱到何种程度。这说明从制度上防范边帅坐大才是治本之策,舍此别无他途。
高力士于开元二十三年、天宝十年、十三年三次曾向玄宗反映,[10]其中有两次涉及边帅拥兵自重问题,高力士明确提醒玄宗:“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玄宗只是说“朕徐思之”[8]6927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使帝国政府的危机预防制度出现了重大安全漏洞,最终酿成难以收拾的悲剧。
三、安史之乱的爆发及其思考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造反。由于内地长期以来缺乏防范突发事件的准备,叛军很快席卷河北、河南等地,并攻下了唐朝的两京,即洛阳和长安,迫使唐玄宗逃到成都避难。后来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战争,虽然平定了叛乱,然社会经济已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大唐帝国从盛世走向了衰落。
这一危机的爆发,乃是由于玄宗在危机管理上没有严格执行防范制度,危机管理意识缺失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宰相杨国忠因“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于是总在玄宗面前挑拨,“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8]杨国忠因个人恩怨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为了逼迫安禄山造反,先是指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第宅,逮捕安禄山的亲信多人,并秘密处死。借口韦陟贿赂御史中丞吉温,求救于安禄山的事件,又将安禄山在京亲信吉温贬为外官。[9]6929作为皇帝的唐玄宗仍未感到事态严重,反而欲通过加授安禄山为宰相的办法来安抚他,结果由于杨国忠的反对而作罢,只是“加禄山左仆射,赐一子三品、一子四品”。[9]6923至此,玄宗仍没有任何警惕心理。天宝十三载安禄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壬戌,兼知总监事。”[9]6923-6924“闲厩使”与总监都是专门负责战马牧养、管理和供给的官职。玄宗此举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安禄山的实力,致使安禄山在叛乱前夕利用这种权力给自己调拨了大批战马。
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开始做反抗中央的准备。尽管宰相杨国忠和韦见素表示反对,但是玄宗却信心十足,“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同意了安的请求。后来在与大臣召开的殿前会议上,答应考虑杨国忠提出的“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11]6930以分安禄山大权、防范其可能造反的危机解决方案。但是玄宗并没有把任命诏书发出去,而是“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结果辅璆琳接受厚赂,“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11]6930而“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六月,玄宗因“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七月,安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达奚珣疑有变,奏请‘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夫,无烦本军。’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会辅璆琳受赂事亦泄,上托以他事扑杀之。”后来玄宗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谕禄山“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更不敢来了。至此,玄宗仍没意识到将会爆发空前大危机,也没有做任何政治、军事准备。[11]693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唐玄宗在危机面前不仅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安禄山的气焰,增强了其实力。可见危机管理意识的缺失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任何个人恩惠及帝王权术都是无济于事的。
唐玄宗作为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其统治前期,在应对国内自然灾难、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冲突、防范宰相权力过大、西北将领坐大方面,他的危机管理意识很强。比如对曾担任过朔方、河东、河西、陇右等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和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等处置,干净利落,毫不手软。[12]6882-6883、6912对于一些比较强势的宰相,如名相姚崇、宋璟,尽管他们辅佐玄宗,促成开元盛世,贡献甚大,出于防范宰相权重的需要,仍然不让他们久任宰相。在对待宰相张说、张九龄的问题上,玄宗同样也是如此。但是在其晚年,这种防范意识逐渐淡漠了,致使李林甫、杨国忠长期专权,从而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盲目发动的对吐蕃、南诏的战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使当时的社会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了。对这些矛盾唐玄宗视而不见,对迫在眉睫的安禄山问题,他出于个人的情感偏爱,没有任何警惕心理,自然也不会启动危机管理体制。
当危机爆发后,玄宗在好几天后才收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而且一开始还不大相信。等到确认下来,采取的措施中又有一部分失当,没有注意整合一切可以化解这场危机的资源和力量,缺乏全局意识、风险意识,认识不到这场危机的危险程度、破坏程度,而是急急忙忙杀掉安禄山的儿子(本可以做人质),在军事力量没有集中、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催促哥舒翰与安禄山灵宝决战(本可以固守待援),导致潼关失守,致使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司马光就曾批评晚年的玄宗危机防范意识淡薄,他说“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13]6994安史之乱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危机管理案例,为后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从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很多的。
[1]欧阳修.新唐书(卷五〇)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后晋]刘眗.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杜佑.通典(卷二一)[M].中华书局,1984.
[5]李肇.唐国史补(卷下)[M].
[6]李林甫.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M].中华书局,1992.
[7][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M].中华书局,1955.
[8]欧阳修.新唐书(卷二〇六)杨国忠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条[M].中华书局,2007.
[10]郭提.高力士外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四载条[M].中华书局,2007.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二一六天宝五载、十一载条[M].中华书局,2007.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天宝十五载条[M].中华书局, 2007.
K242
A
1002-7408(2011)01-0110-03
金荣洲(1969-),男,河南商城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