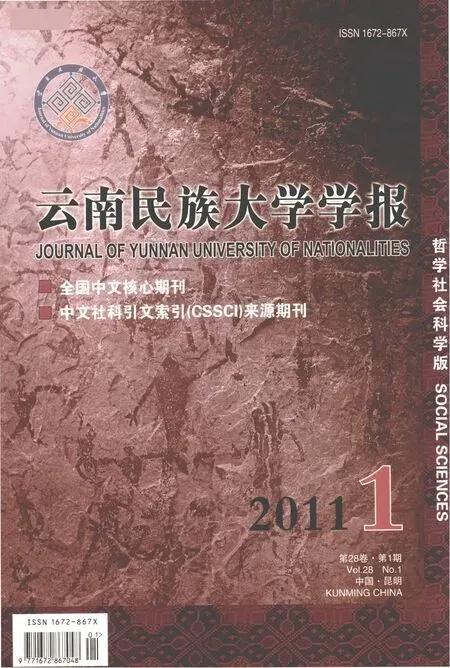怒族多元文化互动与性别承载
宋建峰
(昆明学院昆明科学发展滇池泛亚合作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怒族多元文化互动与性别承载
宋建峰
(昆明学院昆明科学发展滇池泛亚合作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怒族是云南特有的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较少的民族。怒族社会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文化共生特征,其中既有历史积淀的因素使然,也有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影响。怒族社会在交流与碰撞、融合与排斥、重构与再生的多元嬗变过程中,呈现族群性别的平等与尊重、圆融与发展,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独特因素。多元文化中的怒族性别承载主要体现在怒族服饰、日常用品、居住、节庆、饮食等方面,分别其性别配置理念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形式、途径、手段和机制,探索怒族女性在民族文化传承、男性参与保护怒族传统森林文化,复兴本民族生态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发展怒族社会区域经济,建构怒族两性合力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和谐生态系统,怒族人民才能在认识自然、继承祖先生态生存经验的总结中获得发展的良性启迪,并在不断了解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对其他民族文化占有、甄别、挑选、为我所用,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族群发展的文化。
多元文化;性别;承载;共生
怒族自称“怒苏”、 “阿怒”和“若柔”,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贡山、兰坪及泸水各县,是云南怒江居住较早的特有少数民族。其中“怒苏”、 “阿怒”主要分布在泸水、福贡、兰坪三县,“阿怒”主要分布在贡山县。根据2007年《怒江统计年鉴》统计,怒族人口总计有29979人,其中男性15426人,女性14553人,男女性别比为106∶100[1],他们大多居住在怒江两岸海拔1500米至2000米的山腰台地上。由于怒族族源形成历史千差万别,加之居住地区山川阻隔,怒族各支系之间的语言差别很大,即没有本民族文字,彼此也不能通话,“一体多元”特征历史上就已经初露端倪。20世纪50年代前,怒族生产生活水平很低,主要以农业为主,狩猎次之,原始公社制较为显著,属于从原始社会末期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较少民族。近60年来,怒族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居住、生产生活、日常用品均较过去有很大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怒族社会传统与现代碰撞尤为显著,裂变、融合新态势,构筑了当代怒族社会多种宗教、多元文化、两性容纳共生的和谐生态系统。
当代怒族社会多元文化域境下的性别承载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表征的两性调适
文化表征是民族文化的显性特征,是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存续的根本保证。它集中表现在怒族男女两性共同构建、保留、延续的服饰、传统日用品、居住、节庆仪式等活动中。它是可持续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神纽带,同时它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保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文化的基础。
(一)服饰文化与日常用品传承中的性别分工
关于怒族服饰历史的状况,早在清代,余清远在《维西见闻录》里曾这样描述:“男女披发,面刺青,首勒红藤,麻布短衣,男着裤,女以裙,俱跣。”[2](P16)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怒族衣着简单,男的穿麻布长衫、短裤,蓄发,有的结发辫,有的披发;成年男子还喜欢在腰间佩挂砍刀,肩背弩弓和兽皮箭包。女的穿麻布衣裙,赤足,没有穿草鞋的习惯,而且各地怒族女性都喜欢用细藤环绕头部、腰部及脚踝部分。[3]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怒族服饰无论是服饰的材质,还是装饰上都较过去讲究,棉、绒等现代材质受到普遍的接受,式样和图案更加丰富多彩,跣足已被布鞋、胶鞋、皮鞋取代,但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在怒族村寨,赤足的情况还比较明显,男女悉然,尤其是不外出赶集、干活时。值得注意的是,透气、耐用的传统麻布制品在今天仍然受到怒族男女的青睐,尤其是男性的青睐。对传统麻布的热爱与敬意促使怒族男女至今都喜欢穿戴麻布制成的服装,由于生态透支问题突出,由男性负责实施的麻布原材料难寻、女性承担的麻布服饰制作程序复杂、成本高,作为日常服饰穿戴已不常见,所以目前日常生活中的怒族男子,无论老幼,着装均与汉族一致,区别仅在于出门身背怒包或佩挂砍刀,然而今天的怒族成年男子仍然在腰间佩戴砍刀、身背怒包,主要是出于季节劳作和实用的需要,勤劳勇敢的怒族男性文化表征在装饰上已被弱化。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怒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频率提高,怒族女性的服饰开始有新的变化,多元融合突出,尤其是怒族青年外出打工或者怒族女性外嫁汉族,怒族服饰文化消失。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怒族在服饰文化的生成上,没有过去那种被迫趋向于汉族的情况,更多的是对汉族服饰的包容、欣赏、趋同,民族自信心增强这是迥异于过去怒族历史的。
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怒族男女老少基本不与外界交流、接触,不会听说汉话,怒族传统民族服装的男女日常衣着率高,普遍性较强,传统日常用品也主要是竹篾器、木器。并且,制作日用竹木器、打铁、酿酒等是传统怒族男性的社会职责,是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承担的事务,是族群对男性社会价值的重要衡量标准。其精致的竹木制品制作有外地人“不远千里往购之”的历史记载。[4](P19)纺织则由女性担任,织麻、织布、制衣以自给,性别分工明确。近年来,由于怒江公路修通,怒族男女与外界的交流与接触日渐增多,男性承担了家中更多的对外交流活动[5],他们更多的人会听讲汉话,他们的商品买卖意识、赚钱意识略强于女性,如打工、出售弓弩、草药、柴禾等,甚至女性加工怒毯的活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男性参与完成的。然而,怒江州乡镇集市的发展却使怒族传统服饰文化和传统编制技艺很快被廉价的日用器具和成品服装取代,再加上各类组织的衣物救助,怒族村寨中90%以上的男女着装均与汉族一致,仅60岁以上的女性老人普遍还保留着怒族传统服饰的样貌,如用藤辫环绕头部、着裙装、系条纹围裙。①2010年1-2月本人在怒江贡山县丙中洛乡调查所获资料。目前,在怒族村寨,除了女性还照常制作怒毯外 (传统制作技术仅限于35岁以上的女性),男性鲜少或已经不再制作竹篾器、木碗、木勺等日常用品,对男性日常生活技艺方面的审美价值追求已经淡化甚至消失,怒族生产生活用具已经被塑料、搪瓷等现代材料所取代。如我们在贡山县丙中洛乡茶腊怒族聚居村调查时,当问及中年以下男女为何鲜少着怒族服饰时,村民说:“怒族服饰制作麻烦、穿戴麻烦,而且女性穿裙子干活不方便,汉族服饰则简单得多,不用自己制作,镇上买就是。”当问及是否喜欢传统怒族服饰时,男性回答: “无所谓”。女性回答: “喜欢,但穿着不方便,佩饰太多。”男性普遍对自己本民族的服饰文化持可有可无的态度,热情不高;女性虽然喜欢,但也觉得穿着起来麻烦,不方便劳作。该年龄段的男女对怒族传统服饰的热情都较为淡薄,男性较女性明显。一个比较突出的事实是,该村中年以上的女性大多都衣着怒族传统服饰,着裙装干活,但问她们以上问题时,她们均回答:“怒族传统服饰舒适、漂亮,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当问中年以上的男性是否喜欢着传统服装时,他们说: “喜欢,但现在很少有人制作。女性服饰更漂亮。”由此可见,中年以下的怒族男女,简单、方便、与汉族一致的着装理念较强,对传统特色文化的自豪感较弱,但方便、快捷的现代感较突出。再如,查腊怒族自然村一社和二社共有村民353人,男性184人,女性169人 (根据2010年1月“双拉村委会人口统计表”统计)。该村怒族女性传统服饰制作的时间以一年12个月365天计,怒族女性在家织布、织怒毯,制作怒族服饰的时间约60天,而且主要集中于8月、9月雨季和冬季农闲时,[6]这四个月织布、织怒毯、制作怒包、怒衣的女性平均每天约4人/次,而且制作本民族传统怒毯的女性人数也较为固定,占全村女性人数的7%,35岁以上女性居多。该村怒族女性制作怒毯 (怒包、怒服较少制作)50%自用,50%出售,商品买卖意识在女性中开始呈现。男性则无编制怒族传统竹木器具的人,即使自用或出售。该村外出务过工或外嫁又回到村中居住的女性,她们赚钱的意识明显高于从未到过县城或仅到过县城的女性,但女性自觉自主制作怒毯并进行商品买卖的氛围至今还没有形成,怒毯的制作大多是被动地帮助商户或旅游部门加工,赚取手工费,但从客观上也催生了怒族传统纺织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二)居住文化表征的两性演绎
居住文化是怒族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外在表征之一,目前在怒族地区,虽然少量的竹篾房和木板石片房仍然在怒族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男女两性在居住文化表征上呈现出传统与当代交织的多元状态。如贡山县丙中洛乡双拉村查腊村民小组是一个以木板石片房为主要居住样式的怒族聚居村,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120份调查问卷显示,60岁以上的怒族群众喜欢现代水泥空心砖房的占68%,19岁至59岁喜欢现代水泥空心砖房的占65%,女性多于男性。①2010年7-8月在怒江贡山县丙中洛乡做入户调查及问卷所获资料。年纪越大对现代水泥空心砖房的期望值越高,从心理上他们更加愿意改变现有居住样式,获得与外界一致的发展步伐,这一点女性比男性表现得显著;而35%和32%的村民则认为,传统的木板房不仅适合当地的环境,冬天温暖,舒适感强,而且村社凝聚力在建房时体现得最为充分,历史的团结互助精神符合他们的精神期许,是他们族群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繁衍的根本保证,所以他们更喜欢木板石片房,这一点则男性比女性表现得强烈。通过访谈,60岁以上的老人喜欢空心砖房的比例明显高于59岁以下成年人的原因是: “空心砖房比木板房更方便打扫卫生,能够保持室内外清洁舒适,赶上外界发展速度。”60岁以上老人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冀望,对族群发展的要求明显比较强烈,对自己族群的传统居住样式希望改变的心理明显强于年轻人。而年轻人则认为,在怒族社会,一人有难,全村相帮的习俗仍然是怒族社会面对险恶生存环境的保证,原始互助遗风仍然是族群凝聚力的主要表现形式。[4]现代空心砖房的建设明显不需要全村人都来帮忙,也无法帮忙,对族群人际的疏离,对自我的肯定必然带来族群对传统文化的失落感,这是这个“直过民族”年轻群体对现代空心砖房希望不如老年人强烈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建房筑屋的原始互助理念是怒族村社凝聚力的有力保证,它集中地反映了怒族族群在险恶的地域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怒族族群幸福生活的精神期望和心理保证。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供资金、原料,资助怒族民众改造旧房、危房,消灭茅草房。于是,传统的竹篾房、木板房也加快了消失的步伐,代之以石棉瓦、石片屋顶的土墙房、砖瓦房,两三层小楼房,发展的要求和希望使得怒族建房筑屋已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但是互助的风尚仍然盛行,村民男女老少自愿帮忙的习俗仍盛,如查腊村,修房盖屋的互助习惯至今犹存,稍许不同的是以经常相互帮助的人群为主体,过去那种全村人都来帮忙建房的习俗变为部分村民帮忙的形式。男性主要帮助锯木头、扛木头、竖桩柱,女性主要帮助培土、填土、割茅草、做饭、斟酒。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女性的建房禁忌,尤其在庆祝建房的祈福仪式中烟酒、歌舞、娱乐均没有男女老少之分,都可随性参与,比较自由,无任何约束限制,有高度的平等理念,村社凝聚力比较强。
在查腊村访谈和参与性观察中我们发现,该村女性在居住样式上接受新事物、改变目前生活环境方面呈现出比男性积极、快速、宽厚的态势,她们较之男性较少受传统习惯、成规、理念的影响,更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获得与外界一致的居住环境。这是交通改善后、现代科技进入怒族村寨,怒族群众与外界频繁交流所致。毋庸置疑的事实却是怒族传统居住文化面临消失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
(三)节庆仪式的多元性与两性合力
怒族传统节庆仪式的多元演绎是传统与当代文明接轨的显性直观。怒族男女两性群体对节庆文化的开放性接纳是这个民族在接触外来文化时与外来文化沟通的普遍方式,它已经熔铸为这个民族的血液元素,成为男女两性的共同的行为理念。近20年来,怒族传统的节日除了“鲜花节”(仙女节)在族群中影响范围比较广泛外,其余怒族传统节日如“年节”、 “汝为节”、祭祀节、新米节等,[4](P102)即使是怒族群众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鲜花节”(仙女节)也仅限于非天主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男女参加。
在贡山丙中洛,非基督徒和非天主教徒男女每年照常过“鲜花节”,但主要以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作为民族节日的助推器,传统民间形式的节日祭祀活动让位于政府组织的拔河、篮球比赛、民族歌舞表演,具有与现代科学理念接轨的意识,但怒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在民间主体中的自觉意识不是很突出。目前,怒族群众更多的是热衷于各种各样宗教的、汉族的和国家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如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村怒族群众 (该村藏传佛教徒占多数)不仅过仙女节,而且也过圣诞节、复活节、春节、三八节、五一节、中秋节、国庆节、元旦节,每次节日不仅村里有各种活动,而且非基督徒男女饮酒、唱歌、跳舞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群众则杀猪杀鸡、家庭聚餐,满足感、幸福感较为显著,各种节庆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本民族传统节日。[2]然而,对国家、主体民族、宗教节日的热衷,一方面是形成怒族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是促进怒族社会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桥梁,另一方面也是对本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消融与异化,它消泯了怒族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注意和积极部分的坚守,这也是怒族文化特色逐渐消失的原因之一。如茶腊村,过仙女节的时候,乡村民间文艺宣传队需到乡政府参加表演,但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群众不会去参加仙女节活动,本该由女性为主体的仙女节也仅限于藏传佛教徒参加。再者,由于近年信仰基督教的怒族人数已超过了50%,仙女节在民间的活动愈来愈式微,男性参与面更小。宗教节日或是国家法定假日,则男女老幼积极性都很高。[6]目前在查腊村,一年四季节日较多且节日氛围比较浓厚,饮酒、唱歌、跳舞是节日常态,但是在节日里是否衣着怒族传统服饰、歌咏怒族传统歌谣也表现出多元的状态。通常情况下,乡村民间文艺宣传队的男女成员会衣着怒族传统服饰进行歌舞表演,其他人群除了饮酒、弹吉他、跳传统怒族舞蹈、现代舞蹈外,基本不专门进行各种节日的怒族传统文化装饰和仪式。乡村民间艺人也会在表演的时候演唱、叙说怒族古代神话、传说等,但也仅只是在公共表演的场合,村中建房、婚丧、节庆已经很少进行此类以民间为主体的文化传承活动。村中会演唱、叙说怒族古老歌谣、神话、传说的老人已经不多,仅5人左右,男性民间艺人多于女性民间艺人,其他怒族村寨亦然。当我们对怒族30岁以下的青年男女进行“怒族民间文艺在民间”活动可能性调查时,30岁以下的非基督徒青年说:“如果有人组织的话,我们很愿意成为怒族传统民间文艺的传承者,方式可以是每家轮流做东,政府扶持一点酒水费,专门请村中民间老艺人进行传授。”但是响应者不多,积极性总体上不高,女性亦然。应该说,历史上多种宗教存在现状、多种文化因素碰撞,大开放、大融汇是怒族男女两性合力构成多元文化性状的基础。[7]应该肯定的是,近年来,国家及政府各级各类组织均十分关注人口较少的、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对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卫生条件、居住环境、交通医疗条件的改善等均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如青黄不接的时候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发放水泥、石棉瓦等材料帮助怒族群众修房建屋,消灭茅草房、竹篾房;组织群众对贫困户进行帮助等,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扶持确实使怒族群众深切体会到国家的惠民政策是族群生活得以改善的基础。由此,一方面基于对国家和政府的由衷感激,节日趋于与国家一致;一方面则因为交流的扩大、视野的宽泛,对发展速度较高的主体民族较为趋奉,再加上基督教的因素,所以,他们更多地以自己的固有文化来完成自己民族文化的体认。这是怒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注意的。否则,民族文化消失得越快,仅仅保留族称作为结束的特有民族成为历史记忆也就不可避免。
二、多元文化中的酒与两性容纳
在怒族历史上,酒是怒族民众人际交往、沟通思想的媒介,怒族男女老少皆能豪饮,历史上常因煮酒耗粮太多而借债、逃亡。目前,虽然不会因酒致使逃亡的事发生,但是煮酒耗粮太多致使农忙时节断粮的情况仍然频繁,甚至在对外交流中以酒代茶接待男女老幼客人、饮食中以酒做菜并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特色饮食等贯穿在族群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劳作、节日、婚礼、丧礼等均离不开酒的濡染,无论男女老幼,酒文化的养生功能不突出,嗜酒的现象比较明显,其中又以信仰作为分界线。虔诚的基督徒滴酒不沾,天主教徒和藏传佛教徒嗜酒的现象较为显著,尤其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人群。
如查腊村是一个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多种信仰并存的怒族聚居村,其中藏传佛教徒人数最多,天主教次之,基督教和原始宗教人数最少。该村怒族村民种植、收割两季均有共耕共收的互助形式,主人无需付酬劳,只需提供食物即可,但虾辣 (以酒和肉为主要制作材料)是必备食物 (基督徒不食用),对酒的需求量较大。据统计,查腊怒族自然村除了信奉基督的几户人家、20多人以外,酿酒、喝酒、喝虾辣的天数为365天/年,男女老少悉然,尤以节日为盛。稍许有变化的是,劳动时,中午有的人家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不喝酒、虾辣外,每天晚饭必喝酒,晚上有的还要喝虾辣,男女悉然,所以因醉酒滋事、死亡的村民时有人在。在查腊自然村,酿酒、熬酒、买酒、卖酒、喝酒是村民男女老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酒的养生功能和嗜酒习俗贯穿于他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呈现出嗜酒习俗胜于养生的情况。正因为对酒的需求量过大,对粮食的损耗量也大,因此,每年7、8、9这三个月,一些村民往往需要政府的粮食救助才能度过缺粮季节。[8]所以在查腊村,一些初中学历、进城务过工的青年或者已经外嫁的女性回到村中,他们对这种习俗积弊也是深恶痛绝的,已经呼吁改革旧俗,只是积习难改,至今效果不佳。所以,目前怒族社会50%以上的人疏离原始宗教、藏传佛教,亲奉基督教,与基督教提倡禁绝烟酒有很大的关系,只是在查腊自然村,这种情况并不明显。在查腊村,无论事务大小,酒是男女村民非基督徒日常交往必不可少的最好的礼物,酒的养生功能和嗜酒的习俗并存于非基督徒不同信仰群体男女中,健康文明生活习惯的确立还需要族群自身不断的努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无论怒族选择哪一种信仰,哪一种生活方式,其生存法则、行事理念在怒族社群中均得能得到充分尊重,相互独立和平等,在饮酒、嗜酒的日常生活习俗方面亦然,其结果就是酒文化呈无性别无老幼的无序蔓延和滋生,醉酒男女成了常态。应该说,男女老少高度平等的性别观念一方面是这个族群幸福指数的根本保证,是这个族群自适、自如生活的依托,另一方面则又是这个族群在酒文化上缺失有序节制的温床。如贡山县的怒族在对待男女性别上没有尊卑之分,生育孩子极少性别偏好,入赘男子与出嫁女子受到同等的对待 (近年来怒族与汉族交往频繁,怒族与汉族结婚增多,汉族重男轻女的观念和意识才逐渐在怒江峡谷的怒族非基督教天主教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市场);[2]怒族男子也不忌讳讲自己是入赘女婿,他们认为无论是出嫁还是入赘均很正常;怒族如果分家,无论男女均可从父母那里获得他或她应得的平均份额;男性村民也不忌讳用妻子的名字作为一家之主进行各种交往活动;酿酒、煮酒、卖酒、砍柴没有性别的统一要求,男女皆可;女性织怒毯,男性帮助绕线;围绕中柱庆贺建房的仪式成年男女均可身背孩子纵情歌舞;饮酒、抽烟也无性别老幼之分,具备男女高度平等、社群一致的理念。这是同一屋檐下多种宗教信仰、多元文化共存的平等、和谐社群样态在怒族社群的典型存在现状。
因此,以嗜酒积习为契机,怒族一半以上人数疏离自己民传统特色文化,亲奉基督教就成了必然的现实选择,基督教在怒族男女群体中成了抑制酒文化无序蔓延和滋生的有效武器。可见改变酒文化积弊,积极树立良好生活习惯对族群发展、文明、进步是多么的重要。
三、两性文化中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
应该说,怒族社会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的社群存在模式,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怒族社群对世界认知的方式所致。这种大开放和大容纳是这个“直过民族”在发展中自主选择的结果。因为在怒族社会中不同宗教信仰被其视为一些形式有异、能力有别、相互间却无本质区别的生存工具,而人则不过是这种生存工具的承载系统,人的平等与尊重铸就了他们在接收和吸纳其他文化的时候更多是以两性集体性、统一性出现的。[2]因此他们对生存方式、生活理念的选择就自由得多,有自我选择、调适性别理念的因素,只要是和谐、和睦、自适的就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合理性自然存在,都是值得肯定、值得尊重的。所以在怒族日常生活中,无人为的性别观念和要求,男女两性共同构成怒族多元文化的共生现状,传统与当代相互激荡,不断冲击着怒族既有的理念和思维,推动这个“直过民族”对未来的选择。
然而,怒族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存方式,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他们的本民族的文化正逐渐被削弱甚至消失,加之这个“直过民族”走的是一条跨越式的发展路径,对外来文化呈现为一种自觉和非自觉的全面接收状态,在整体开放中接触外来文化,这种状态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对自己文化积极部分的疏远,他们不但疏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在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时候缺失审视本民族历史悠久、特色明显的视角,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消极的部分缺乏有效拒斥的理念,[9]构筑文化多元性的同时也消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然而,怒族女性独特的族群生存空间和社群地位,使得怒族女性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进行了诸多男性无法企及的有益的尝试,如坚守部分平等互助民族传统、生态平衡观、积极传承本民族纺织文化、热衷于本民族歌舞表演等,虽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族群男女同一性、团体性的视野之上的,但却从另外一个方面借助族群性别高度平等理念拓展了女性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容留并催发了女性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积极坚守与传承。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怒族女性积极为旅游部门加工怒毯的时候,男性不仅支持率高,而且是通常意义上的沟通者,男性对女性外出务工、就学、从政的支持率也较高,某种程度上使女性发展空间增大,发展阻力减小。我们对查腊怒族自然村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怒族男女对“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外出打工、自主创业”的支持率平均为90%以上,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显现。这种平权的性别配置理念已经成为怒族文化血脉的组成部分。
所以,探索怒族性别配置理念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形式、途径、手段和机制;积极支持和辅助怒族女性在民族文化传承上的努力;引导怒族男性整体参与保护怒族传统生态文化,复兴本民族生态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发展怒族区域经济,建构怒族两性合力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和谐生态系统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怒族社群才能在热爱自然、热爱祖先生存经验的总结中获得发展的良性启迪,并在不断了解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对其他民族文化占有、甑别、挑选、为我所用,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族群发展的部分,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1]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统计局.怒江年鉴 [Z].内部资料,2008.
[2]何林.阿怒人——同一屋檐下的不同宗教信仰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1).
[3]赵伯乐.新编怒江风物志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
[4]怒族简史编写组.怒族简史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
[5]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参与性发展中的社会性别足迹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
[6]何明,赵美.流动的信仰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7]李道生,袁绍坤.民族风物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1).
[8]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怒族社会历史调查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
[9]云南省社会性别小组.边缘的突破:云南社会性别探索与实践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
Abstract:The Nu nationality is a minority group in China that directly entered socialism from the late primitive society.The Nu society has the clear features of multi-cultural symbiosis which is related to its history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flicts,the Nu society has reconstructed itself with the featur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its tradition with modern civilization.The gender embodiment of the Nu nationality finds expression in many aspects like clothes,ornaments,daily articles,houses,festivals,foods and others.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and means of the Nu nationality reflect their lifestyle and attitudes towards other culture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 with Nature,an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ir acculturation and socialization process will help the healthy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Nu nationality.
Key words:multi-culture;gender;embody;symbiosis
(责任编辑 杨国才)
The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Gender Embodiment of the Nu Nationality
SONG Jian-feng
(Kunming Institute of DCOA,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 650214,China)
C95-93
A
1672-867X(2011)01-0065-06
2010-10-22
宋建峰 (1966-),女,昆明学院昆明科学发展滇池泛亚合作研究院副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女性信仰变迁与民族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9XMZ029)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