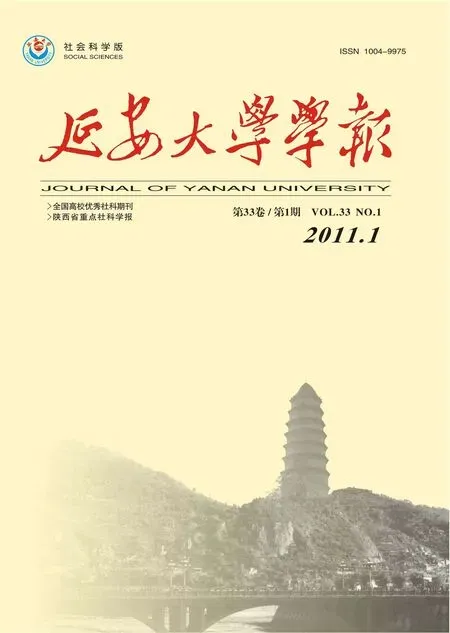论陈去病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政论文创作特点
赵 霞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论陈去病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政论文创作特点
赵 霞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作为一位集政治家与文人于一身的民国要人,陈去病的政论文创作值得重视。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是其政论文创作的高峰期,在这段时期,陈氏有着始终关注的对象,创作心态上也有逐渐的转变,从题材选取到精神内涵都既有传承,又有变化。陈去病这一时期政论文创作上体现出的特点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文人政治家的心态转变及其他社会问题。
陈去病;政论文;传承;变化;特点
陈去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文人,身份的复杂性使他具有非同一般文人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入的洞察力,而政论文无疑是融合政治观点和个人创作的绝好表现形式,因此陈去病的政论文创作值得重视。他在这一时期作品数量较大,且绝大多数集中创作于1906—1915年间,即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共有七十余篇,文章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但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在经历了这场颠覆性的革命之后,陈去病的政论文作品中仍然有始终关注的内容,在抨击对象、创作心态方面却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极具代表性。对这十年间陈氏政论文创作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了解处于特定时期文人政治家的心态转变,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问题,现从不同方面分别论述:
一、选取内容的一脉相承
陈去病始终对于政治区划,特别是边疆治理等问题极为关注,这也成为他政论文选取题材中一成不变的部分。早在190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陈去病便有《漠南北建置行省议》一文,文中详细阐述了漠南漠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指出现存的行政区划存在的严重不合理之处,沙俄也正是抓住这一漏洞才有机可趁。尤为可贵的是,陈氏并未一味提出问题,而是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包括官吏设置、大量移民等多种举措来应对,在文末更有一张《漠南北新建置总表》,可见他在相关问题上所费时间甚久,绝非一日之功。
至1908年,此类选题的政论文开始大量出现,仅当年便有《升上海为直隶州议》、《南粤分疆设治议》、《论筹防天山南路》等三篇文章出现,且依然按照“关注核心区域”和“边疆治理”的原则筛选论述对象,尤其是建议将上海升为直隶州一文,可谓极具前瞻性。陈氏已经看到了上海存在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然而租界的存在使上海管理混乱,陈氏遂建议将周边地区划归上海并升为直隶州,语言中肯,论证资料详实,理由充分。后两篇则分别针对两广海南地区及新疆地区提出一己之见,尤其在《南粤分疆设治议》一文的后记中,陈氏特别表示民国之后,自己的这一建议与孙中山的提议不谋而合,这种肯定使他相当兴奋,“爰重为删润,备当局者参考”[1]456,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关注此类问题的信心。
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陈去病始终没有放松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关注,于1912—1914年间又先后作有《西藏改建行省议》、《淮北增置行省议》和《说边关三省》等作品,由此,陈氏的创作内容范围已经囊括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边疆地区更是全部包括在内,此时陈去病已经抱着为国家献计献策的态度,积极投入到建设新国家的浪潮之中。在《说边关三省》一文中,陈氏详细地考察了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的历史沿革、出产矿产及农产品等,在文末不由感叹早年即作文认为漠南北宜改行省,却未能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使得如今北方地区面临唇亡齿寒的命运,而行文至此,更多的只是一份无奈。
作为一位有着政治理想的文人,陈去病的关注对象庞杂,除去他对于领土治理的看法,当局的一举一动、陈旧的社会陋习、相似的历史情景都可以为他所用,选取恰当的角度成文,陈氏敏锐的观察力可见一斑。然而在他的观点中,也常出现知识分子的天真,以作于1911年的《借外债与购德械》为例,陈去病意识到德国向清廷兜售枪械是欲瓜分中国之阴谋,因此汉族同胞要粉碎此计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向德国购买枪械杀清廷,可谓一石二鸟,至于费用如何解决,陈去病提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决方法:借外债,使清廷无钱可借而失去翻身的机会,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陈氏的想法显然太简单了。清廷是以附带不平等的政治条件为代价举外债的,各国岂会在看不到任何利益的情况下盲目借贷呢?陈去病的提议显然不具备可行性。尽管如此,他极强的责任心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仍然值得肯定。
二、民族情绪的日益高涨
陈去病是以民族主义为利器,激发国民斗志,推翻满清统治,以求实现民主共和,陈氏的民族立场异常坚定,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贯彻到底,甚至因此被人称为“一民主义者”。事实上,在近代,民族主义对于革命先行者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唯有具备民族与民主两重性质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而“民族革命乃是有着共同的情感传统的一群人争取解放与自治的运动,因之,革命的结果必须是该民族的全体(至少绝大多数)人民普遍地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幸福”[2]。在被满族统治的时期,倡导民族主义无疑能加强国民凝聚力,同仇敌忾,陈去病正是抓住这一心理,以民族主义为工具,煽动民族情绪,犀利的语言与无所顾忌的指斥在他的政论文中比比皆是,且在这十年间呈现日益高涨的趋势。
早在1904年,陈去病在《论中国不与俄战之危险》一文中就曾表达过对清廷充当看客的强烈不满,虽然当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尚不完善,但利用民族情绪则已然可见端倪。辛亥革命之前,陈氏政论文中多是拒绝与清廷颁布的旨令合作,如创作于1908年的《论满汉通婚之难订》,针对清政府下令允许满汉通婚,陈去病却表示:“国家之所由立,民族之所有存,皆人伦为之基也。人伦一丧,则民族之主义消而国家之基础亦因以不固”[1]440,不合作态度鲜明,且对清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意将民族主义化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在1908年8月陈去病赴汕头主《中华新报》后进一步升级,陈氏借助媒体为平台,报章体这种“短平快”的形式,对清廷大肆口诛笔伐,讥讽嘲笑。作于1908年的短文《开国之摄政王耶》对载沣封摄政王一事大加嘲讽,据此认为清廷不过是末日黄花,而“对大阿哥及摄政事的批评指斥,颇为当朝所忌”[1]117。陈氏并未因此对大胆的言论稍加约束,相反,《若要俏须带三分孝》语言更加辛辣,针对慈禧与光绪帝去世一事,陈氏认为国民须改变孝服颜色使之更加美观,字里行间不免调侃,表现出自己对此事的极度不关心。
另一方面,陈去病却不时创作怀念性文章来祭奠民族精神。如在1908年先后创作的两篇短文《八月二十七日的大纪念节》和《今日的纪念》,分别纪念南明小朝廷在东南失守及陈子龙殉国之日,语气沉重,形式正式,一改往日多变的风格,在后一篇中,陈氏言:“盖今日者,固我中国之大文豪、大党魁、大志士陈卧子先生子龙流血之纪念日也,亦即我中国先朝末运之纪念日也。”[1]487极大地抬高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地位,也是陈去病宣扬民族精神的一种方法。
尽管清廷已呈苟延残喘之势,但对于社会舆论仍然存在一定的控制力,因此陈去病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创作中也仅限于嘲讽与不合作的态度,真正的民族情绪大爆发始于1911年,在《〈江苏大汉报〉发刊词》中,陈氏不由破口大骂,从清兵入关到溥仪登基,语言一气呵成,酣畅淋漓,末段更有“报亡明之宿耻,还大汉之山河,洗胡虏之腥膻,复中华之民国。革命哉!”[1]513大声疾呼式的内容使其变成了一篇名副其实的战斗檄文。同年,他又创作了《满虏今昔之比较》,从天道循环、定数等方面论及清初及清末,涉及到一系列宫廷丑闻、传闻,语气慷慨,语言辛辣,揭示清廷种种窃国、杀戮等罪恶行径,用宿命论解释清廷的必然灭亡,做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准备工作,具有民族情绪煽动性的政论文创作也在当年达到了顶峰。
陈去病显然是以民族主义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这一点集中体现于这十年间的政论文创作中,在辛亥革命之前,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的作品层出不穷,且程度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而清廷被推翻后,此类作品数量锐减,足以说明问题。
三、抨击对象的逐渐转变
这一点紧承其上,更加充分地证明陈去病是以政治理想为第一要务,辛亥革命之前,实现民主共和的路上最大的障碍便是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推翻清廷是当务之急,陈氏于是寻找到了极好的突破口和理论武器:民族主义,它可以激发国民斗志。陈氏在创作中,不时以明末志士精神鼓励民众,以清初屠戮暴行刺激民众,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在推翻帝制之前,异族统治和当朝昏聩是陈氏政论文创作中一成不变的抨击对象,且随着清廷的舆论压制能力越来越弱而愈发地大胆、犀利。
辛亥革命之后,这一现象却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帝制已经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去病及一众革命先行者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此时再对已毫无还手之力的清朝统治者口诛笔伐、大肆声讨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抨击对象逐渐转变的最根本原因,便是实现共和之路上出现了新的障碍——袁氏专政。辛亥革命落在身上的硝烟还未散去,孙中山就任总统短短三个月之后,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便拱手让人,更让人气愤的是,袁世凯上台之后毫不关注民意,却对自己的利益患得患失,在引发了国民一致漫骂的同时,又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舆论讨伐,而这一过程也忠实地反映在了陈氏的政论文创作中。
作为一位政治家,陈去病有着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极强的思辨能力,可以先于众人觉察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早在1911年,他便预感到袁世凯将会成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而此时国内情况更是一片混乱,陈氏于是在《对于内讧者之悲感》一文中大声疾呼,希望在革命伊始之际,不要有同室操戈之举,让袁氏有可乘之机,虽然袁世凯受到自身能力限制,目前还不敢有更大举动,但如果再像现在一般各自为政,袁世凯则很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现象如此,胜负之数,昭昭然已”[1]532。
虽然当时有如陈氏这般认清形势之人,但革命派仍然难阻大势已去的命运,黯然退至幕后。袁世凯的专政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抗议之声,面临内患的中国同时也处在帝国虎视眈眈的目光中,极度失望的陈去病再次把矛头对准了袁世凯,作于1912年的《呜呼!边陲之风云急矣!》一文中,对新疆的民族矛盾,西藏的试图独立,满蒙的岌岌可危无不痛心疾首,话锋一转,直指袁氏:“然则政府诸君,能诿其责而不自疚乎?即袁总统所谓‘当世凯任内绝不使中华失片土者’,其言岂能实践乎……袁大总统!毋空言徒托,而忍弃我辛苦血汗再造之河山!”[1]536可谓字字血泪,言及随时可能成为他人囊中之物的国土时,不由愤怒心焦至极点,用哀婉的口吻控诉袁世凯的不作为。随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接踵而至,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陈氏的政论文中也不再有格外鲜明的抨击对象,现实远比想象的残酷,清廷推翻之后并非理想中的一片歌舞升平,陈氏此时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一份反思与无奈。
四、创作心态的自然过渡
无论是选取内容、民族情绪还是抨击对象,都是陈去病依据时代的不同和民众的需求作出的调整,唯有创作心态的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虽然陈氏对于清廷不屑一顾,采取不合作态度,但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创作中,他仍然不由自主的以普通民众参与议论的心态为自身定位,不论是关心地域区划还是官吏设置,陈氏更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使当权者有所察,使真正掌握话语权者可以有所作为,实际上仍未摆脱传统知识分子“下察民情,上达天听”的模式,只不过陈氏在其中表现出更多的不满和反叛情绪。
从辛亥革命开始,陈去病的创作心态逐渐从民众参与过渡到了主人翁立场,这与他和领导革命者关系密切,本身便是先行者之一的身份有关,同时也是陈氏心态上的转变。努力推翻帝制之后,有着开国者的自豪和百废待兴的责任感,这一点则直接促成了其创作心态上的转变。如1912年创作的《迁都篇》,便是针对着革命刚成的局面提出的关于迁都的建议,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成,诸如与孙中山意见相左、北京皇族的安置问题等一一作出解释,这种以主人翁立场为建设新国家献计献策的热情已经初见端倪,至1915年所作《论建立国会之非易事》,在其中陈氏对民国建立议会是否可以真正使整个国家运转正常表现出担忧,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新制度的忧心忡忡和对国家何去何从的深切思考,此时的陈去病也已经完成了创作心态的彻底过渡。
以陈去病这十年间的政论文创作特点为切入点,看到的不仅是以陈氏为代表的一批有政治抱负的文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思想,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些当时独特的社会问题。比如在陈去病创作完成了檄文《〈江苏大汉报〉发刊词》之后短短三个月,他便又执笔《〈江苏大汉报〉停刊宣言》,而这份由军方出资刻印的报纸由于形势动荡,资金不足,未满百日即遭夭折,也可看到当时报纸期刊等出版物发行的混乱情况。综上,通过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个案研究,有利于把握文人政治家的思想活动和心态转变,因此具有典型意义。
[1]张夷.陈去病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余英时.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85.
I05
A
1004—9975(2011)01—0082—03
2010-10-25
赵霞(1983—),女,满族,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