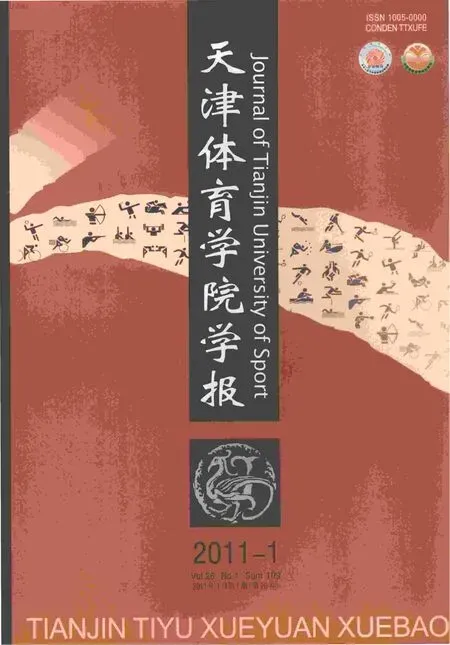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的人类学阐释
——来自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民族志报告
涂传飞
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的人类学阐释
——来自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民族志报告
涂传飞
以一个村落舞龙活动为例,从人类学的视角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进行阐述。研究表明,民俗体育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由此当地社会得以建构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对民俗体育的已有认识和发展实践进行检验。最后,认为发展民俗体育能够促进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为民俗体育的保护、传承确立实现途径。这种路径就是民俗体育走综合化的发展路径,即在依托于其民俗文化母体的前提下,保留民俗体育核心形式和核心功能,并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民俗体育中不合时宜的作用和功能进行调整和转换。
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社会再生产机制;舞龙
我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体育资源,它们在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民俗体育日益衰微的今天,研究者纷纷强调民俗体育的历史作用及其独特价值。但从已有研究来看,研究者大多把民俗体育局限于体育的范畴和框架中来解释它的历史价值,忽视了民俗体育与其社会背景的联系[1-2]。这就很可能歪曲它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而成为研究者笔下“想象的异邦”。因此,本研究选取涂村的舞龙活动为个案,将其置于解放前该村落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关联中去考察,并运用相关人类学理论对其历史作用进行阐释,以思考我们已有的对民俗体育的认识和民俗体育发展实践。
涂村位于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在每年的正月十三至十五开展舞龙活动。在舞龙表演开始前的正月十三,村民们要去村庙祭祀涂村供奉的村神,在舞龙表演期间,一方面,舞龙队伍要到各个庙宇去敬香还愿;另一方面,在正月十三到十五期间每个家庭也要在自家祭拜自己的祖先和神灵;而在舞龙结束的第二天(正月十六)早上村民们也要去村庙拜祭神灵,以感谢神灵的庇佑或希望能够得到神灵更多的保佑。
1 涂村舞龙: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指出,库拉交易是一种大范围的、具有跨部落性质的交换形式。它施行于居住在一大圈岛屿上的居民群体之间,这些岛屿正好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沿着这条路线,有两种且只有这两种物品在不断地相向流动。顺时针流动的是长长的红贝壳项圈,相反方向流动的是一种白贝壳臂镯。这两种物品在各自行进的方向中彼此相遇、不断交换。它们按大小、颜色、打磨的精致程度,以及特有的历史分出等级,正是这两种物品的相互交换构成了库拉的主要行为。此外,就地域性而言,库拉交易包括两种活动,首先是库拉社区或几个邻近社区的内部交易,其次是大规模的远航,同海外社区进行交易[3]。库拉交易不是简单的经济活动,它与巫术、宗教、神话、传说等交织在一起,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莫斯更明确地指出,库拉现象“涉及大量的、本身极其复杂的事实。而所有这些事实又交融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先于我们的社会,乃至原古社会的社会生活。这些总体的社会现象能够同时绽然展现出全部各种制度宗教、法律、道德和经济[4]”。涂村舞龙也类似于库拉交易,它是与村落整体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诸如宗教仪式、经济、社会心理等。如借用莫斯的说法,涂村舞龙表演可以称之为一种“礼物”,这种礼物的流动中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也是一种“总体呈献体系”,或是“总体的社会现象”。涂村舞龙作为一种“总体呈献体系”,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正是这种社会再生产机制,当地社会得以建构和发展。
1.1 一种社会经济再生产机制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由于库拉涉及财富和用品的交换,因而是一种经济制度[3]。莫斯进一步指出,这种经济制度“确立了特定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或者毋宁说确立了特殊的呈献方式与分配方式[4]”。Vijayendra Rao在对印度3个村落的节庆表演中涉及的经济行为的个案研究表明,公共性的事件,如集体仪式、节庆表演等可以在群体内外部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经济联系,并通过交流和增长经济生产知识、降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经济成本等方式再造一种有形的经济资本[5]。以上研究也有助于说明涂村舞龙活动中所蕴含的经济功能。涂村舞龙表演期间,也涉及到财富和用品的交换,主要有涂村舞龙献祭表演与神灵和祖先庇佑之间的交换、涂村舞龙到邻村赵村表演与赵村回礼(鞭炮、蜡烛、红包等)之间的交换、村民设宴款待姻亲来涂村观看舞龙表演与姻亲们回赠的拜年礼品之间的交换以及舞龙表演所获得的礼物和添丁家庭上交的谱饼在村内以家庭为单位平均分配等。
所以,作为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涂村舞龙活动也是一种经济再生产机制。这体现在涂村舞龙所具有的隐喻和显性的经济功能上。涂村舞龙具有隐喻的经济功能:其一,涂村舞龙展演是村民献祭给他们所信奉的神灵和祖先的“礼物”,作为“礼物”的交换和回赠,村神和祖先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一定的象征性的保障,乃至对整个村落社区的庇佑;其二,涂村舞龙既到与本村“共社火”(一种通过民间表演活动祭拜不同村落共同信奉的神灵的基础上形成的村落之间的结盟组织)的赵村表演,每个家庭又邀请与自家有着密切来往的姻亲来观看舞龙表演,这就为涂村与赵村、涂村村民与姻亲加强日后在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互助合作提供平台;其三,涂村舞龙活动是这些参与者的一次聚会,它为涂村内部各家庭之间、涂村与赵村村民、涂村村民与姻亲之间提供了一次互通农业生产信息、交流农业生产经验的机会,这也直接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外,涂村舞龙还具有显性的经济功能:一方面,舞龙为涂村社区内部提供了一种社区公共产品的再分配机制,舞龙的经费基本上是由涂村共有地产的收入来开支的,这其实是一种社区公共资源在社区内部再分配形式;另一方面,舞龙期间,该年添丁的家庭会上交一定数额的谱饼以及舞龙表演所得到的礼物都要在社区内部以家户为单位平均分配,这种再分配方式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不但是一种互惠,而且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认为这种再分配方式也是社会再生产的环节之一[6]。
1.2 一种社会教育再生产机制
本尼迪克特认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7]。传统节日以习俗的力量让民众自动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一个共同的社会就这么让人们高兴地延续下来。这就是传统节日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文化再生产功能[8]。涂村舞龙活动作为涂村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俗活动,能够自发地建构和再生产“共同体道德”,体现的是当地民众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并为他们所自觉地遵守和世代延传。因此,在这种教育再生产的过程中,其区域性的地方伦理道德也同时实现了其自身的再生产。盖尔纳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教育(人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是通过传统社区教育来实现的[9]。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教育基本上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社区的仪式和民俗传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涂村村民也是如此,社区的民俗传统是村民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涂村舞龙作为涂村的一个标识性的民俗活动,必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功能。在涂村舞龙活动中,具有一套自己严格的规定和固定的仪式,村民们通过参与到舞龙活动中,学习和践行这些规则、仪式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道德原则,这其实就是他们接受社区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在1911年进入民族国家时期,根据盖尔纳的观点,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国家力量的全面渗透,标准化的大众文化取代传统的社区文化,现代教育体制取代传统的社区训练,使注重标准化知识的新型“雅文化”侵入社区,排挤传统社区文化[10]。民国成立后,出于对现代化的诉求,新的公学制度被引进中国,用于取代传统的社区训练和教育。但是,由于当时客观原因,新的公学制度并没有渗透到涂村及涂村所在的乡镇。据涂村70岁以上的老人们回忆,解放前,涂村只有一人接受了这种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由于南昌县城没有这种新式学校,只能到南昌市的学校(南昌一中)接受这种新式教育。可以说,在明清至解放前,涂村村民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社区内部的教育和言传身教,而舞龙就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1.3 一种社会心理再生产机制
在中国,民间舞龙往往是男性的狂欢活动,是村落实力的展示。解放前,涂村与邻村邓村为争夺两村接壤的湖而经常发生斗殴。而涂村舞龙表演可以向邓村显示涂村的人丁兴旺,村落内部的精诚团结。莫斯在论及古代社会礼物交换的意义时指出,“这些被交换的事物的持久影响作为社会生活的象征,则是直接转达了使古代社会中的那些次群体凝聚起来的方式[4]”。涂村舞龙作为村民献祭给涂村村神和祖先的“礼物”,蕴含了村民对共同信奉的神灵和共同祖先崇拜的象征意义,它可以把平时分立的家户和村民联合起来,加强村民对“信仰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公共认同,造成一种村落共同体的意识。涂村舞龙也是一种献给友好村落赵村和通婚地域的姻亲的“礼物”,通过这种礼物的流动和交换,加强了涂村与赵村、涂村村民与姻亲之间的“地域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在心理学层面,通过舞龙表演这一礼物的流动,使每个个体、群体感受到礼物流动和互相赠予时的快乐与荣誉,既是他们之间心灵的握手,又是造就社会团结的道德箴言。从这个角度而言,涂村舞龙中所涉及的社会心理再生的功能也进一步证实了节庆和民俗表演具有情感和认识两个维度的心理建构功能的观点[11]。
特纳认为仪式是一种“社会戏剧”,过程包括结构——反结构——结构三个阶段。仪式刚开始总是将参与者按照日常生活中社会结构中的分层关系加以严格的安排,使之符合“结构”的基本规范的价值观。发展到仪式中心期,参与者的社会角色便消失了,他们之间的差异被暂时地排除,成为一个共同的社区。到了结束阶段,参与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得以再次肯定,恢复日常生活的角色[12]。解放前,涂村村民基本上处于社会底层,因此,舞龙对于涂村村民的心理慰藉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村落社区,以至每个家庭、每个个体排除灾难、解除罪恶的宗教式的保护性举措,表达了人们对动荡的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感。正如Mikhail Bakhtin的研究所指出的:“嘉年华以及节庆表演等可以将参与者从他们现有的社会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而临时给他们自己造就了超越正常的‘反常生活世界[13]’。”所以,在涂村舞龙这一仪式性的活动中,涂村村民在内部与本村的地主等剥削阶层是平等的,在村外,与其他上层阶级也是平等的,这与他们现实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经由这种方式,涂村村民在这种反结构的阈限状态下进入了他们自己编织的一个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式的境界中[13]。
1.4 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
正如库拉交换近可交友、远可结盟,在此基础上,土著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换关系网络,涂村舞龙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机制。它为村民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络的基本方式,强化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涂村是一个宗族村落,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平时村民忙于生计,很少有机会可以将分散的家庭组织起来。涂村舞龙作为一个祭拜共同的神灵和先祖的象征符号体系,可以将这些分立的家庭组织起来,加强了村落内部各个家庭之间的联系;村民将舞龙这一礼物献祭给神灵和祖先,无形中维系并强化了村民与神灵和祖先之间的关系,使村民获得一种神秘的支持力量和社会资本。涂村舞龙还要去与本村有着“共社火”关系的友好邻村赵村表演,同时每个家庭都会邀请在生产生活中平时与自家有着密切往来的姻亲来本村观看舞龙表演,这又可以加强涂村村民与邻村村民和通婚地域的姻亲的联系。此外,舞龙期间,涂村每户添丁的家庭也会将一定数额的谱饼交给该年舞龙的头家,由头家以家庭为单位在村内进行平均分配。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谱饼乍看起来既不起眼也不浪漫,但是涂村舞龙的这个配套活动恰恰也是维系和建设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之一。涂村舞龙表演为村民培育和扩展了社会关系,关系可以创造资本,关系资本再生产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以便村民在日后生产生活中遇到难以预期的困难时渡过难关,最终使得社会运行更为有效。
涂村舞龙不仅培育和再生产了涂村内外部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它也维持、强化了竞争、对抗的社会关系。涂村所在区域是以种植稻作经济为主,而稻作经济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自古以来,涂村和村北面的邓村为了争夺两村接壤的两个湖而经常发生宗族斗殴,所以,这两个村落也就一直都是处于紧张和敌对的关系中。自然,涂村舞龙不会去邓村表演,更不用说彼此之间有通婚关系。涂村舞龙期间,村民按照祖上的规矩去这两个湖边进行舞龙展演,既是向邓村表明涂村对这两个湖的所有权,也向邓村展示涂村的人丁兴旺和精诚团结,这又无形之中又强化了两村的紧张和敌对的关系。
1.5 一种社会等级再生产机制
历史以文化的形式活在当代,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支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动、心理取向和文化价值判断。在中国漫长的等级社会发展中,长期的生活实践形成了论证不平等社会“合法性”的配套文化。正如莱博诺指出,“每个文化都提供一种机制,这个机制能将由均衡与不均衡间相互制约而产生的社会紧张限制在一个界限之内[14]”。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俗体育作为一种仪式化的文化表现形式,其中往往脱离不开等级制度,在民俗体育表演过程中,等级得到诠释,使得社会等级不断处于型塑过程中,就整体社会结构而言,固有的等级结构不但没有被消除、打破,反而更加强化了。
涂村舞龙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首先是一种经济再生产机制。村里的地主阶层对舞龙活动在经费上的支助,体现了馈赠者(地主)的富裕,从而加强和巩固了自己在村里的社会地位。由此,涂村内部的地主与农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也得到强化和认可。涂村舞龙所具有的教育和教化功能,其本质是以封建儒家意识形态规训为主,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因而就涂村的外部关系来讲,是封建制度的凯旋。在涂村舞龙所承载的对村民教化的过程中,封建等级制度也更加合理化和强化。涂村舞龙是与村民的民间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涂村舞龙表演是献祭给神灵和祖先的礼物。Wolf指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天神、村神、祖先)象征着一种等级:天神是皇帝和诸侯,村神是地方官员,祖先是本地的族人[15]。在涂村,舞龙祭拜献祭给这些神灵是村民与神交流的手段,其中所隐喻的社会等级也得到强化。在涂村舞龙活动中,不仅舞龙活动本身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舞龙的表演过程也是一种严格的仪式。通过舞龙活动这种礼物的流动,既表现了社区内外部的互助合作,也对维持社区内外的地位级序起关键作用。涂村舞龙为村民提供了一种反结构的阈限状态,在这种反结构状态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涂村村民通过舞龙来缓解和发泄其心中的苦闷和压抑,表面上,社会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事实上,社会固有的等级制度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1.6 一种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
在法律和契约制度不太完善的古代社会,为什么它大体上是处于总体稳定和有序的状态?社会秩序又何以可能实现?莫斯在《礼物》一书中从头到尾都在追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最后莫斯发现,象征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纽带,象征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原因。作为象征符号的礼物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实现。莫斯指出,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是把联盟、赠礼和贸易取代了战争、隔绝与萧条。而且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及至社会中的个体的关系稳定就在于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这样社会才会进步。礼物既是社会实在的秩序,又是社会团结的道德箴言[4]。
作为一种教育再生产机制的涂村舞龙,是涂村社区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舞龙的整个文化体系中,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同舟共济、孝悌为先等价值观是其主要推崇的道德标尺,这对促进社区内外部的和谐有序具有重要作用。涂村舞龙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再生产机制,具有心理慰藉的功能。在舞龙活动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村民们可以缓解和宣泄个人的心理紧张情感,也可以调和社区内外部潜在冲突,使得当地社会秩序得以和谐稳定。涂村舞龙表演是一种礼物的流动,是涂村村民献给神灵、祖先、本村和邻村赵村村民、通婚地域姻亲的礼物。涂村村民通过舞龙表演所带来在涂村内部、涂村与邻村赵村以及与通婚地域的姻亲之间的互惠交往不仅维持和再生产了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通过对相互间权力、义务、地位、身份的再确认,维系和加强了社会的秩序,使得当地的社会秩序运行更为有效,以达到社会稳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对诸如涂村舞龙这样的村落宗族文化采取默许甚至是支持的态度[16]。
2 对已有民俗体育认识的检视
2.1 民俗体育的本质属性
如前所述,涂村舞龙活动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和库拉一样,涂村舞龙活动中涵盖了社会生活中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法律的方方面面。如果仅仅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个体育活动,那么我们就完全误解它了。涂村舞龙活动对我们思考民俗体育的本质属性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而国内已有研究对民俗体育本质属性的认识不够全面和准确。大多数研究者局限于从体育的视角来把握民俗体育的本质属性,认为它们根本上也是属于一种体育活动方式或是体育项目形式[17]。正因为对民俗体育本质属性认识上的偏差,所以才会出现对民俗体育、民间体育、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等的概念及其相互间关系的争论和分歧[18]。涂村舞龙的个案表明,民俗体育是依附于一定的民俗文化母体中,并是这个民俗文化母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涂村舞龙活动是一种“总体呈献体系”,同样,民俗体育的本质属性也在于它们是一种“总体呈献体系”,它们反映了方方面面。所以,民俗体育的存在范式也是应该一个文化体,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项目。
2.2 民俗体育的功能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民俗体育的功能(作用、价值)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大多数研究把它从其原来的文化背景中割裂出来进行解释,忽视了民俗体育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相关背景的联系,这就很可能歪曲它在原来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意义。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民俗体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其娱乐健身功能,如有研究指出,民间体育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娱乐健身,但娱乐健身作为其主导价值取向是不能否认的[19]。在论及民俗体育的经济功能时,大多数研究只是片面地认识到民俗体育可以通过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就忽视了民俗体育本身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隐喻或显性的经济功能。而本文的个案表明,民俗体育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就有明显的经济功能。
涂村舞龙的个案表明,民俗体育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其中,无论是社会经济、社会教育、社会心理、社会关系抑或是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机制,最终都是服务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由此,当地和谐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社会得以在此基础上发展。这就从另一角度解释了古代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命题,这并非人的理性,更并非社会契约所致,而是诸如民俗体育的这类“总体呈献体系”使然。因此,在民俗体育的历史作用和功能中,建构和谐的社会秩序是其最核心和最根本的功能。
3 对民俗体育发展实践思考
3.1 对已有民俗体育发展工作的思考
鉴于我国民俗体育日渐衰微的事实,学者们纷纷提出民俗体育发展的对策。但是,由于我们对民俗体育的本质属性和功能的认识存在偏差,所以大多数研究也只能提出一些适合少部分民俗体育发展的局部性对策,这反映在发展民俗体育的具体实践中,就出现一些简单化的倾向。我们往往将民俗体育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中剥离出来,而把它作为一个体育项目来开发和利用,也即民俗体育走项目化的发展路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民俗体育走产业化的道路,如在一些旅游景点出现的民俗体育表演项目;其二、民俗体育走现代竞技体育的道路,如将传统龙舟改造为现代竞技龙舟的例子;其三、民俗体育走健身娱乐的道路,如在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中引入民俗体育资源。
确实,有些民俗体育由于自身的特点和资源禀赋的优势可以选择这种发展路径。就涂村舞龙活动而言,涂村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村落,没有区位和资源的优势,显然,它不适合走产业化道路;至于涂村舞龙走健身娱乐的道路,似乎也不太适合涂村舞龙的文化主体,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忙于生计,改善生活,这也可以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得到解释。但是,民俗体育的本质属性是一种依附于一定民俗文化母体而存在的“总体呈献体系”;民俗体育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健身娱乐,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这体现在它是一种教育、经济、心理、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再生产机制,最终,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和再生产。这说明在民俗体育发展实践中,项目化的发展路径只是适合少部分民俗体育的发展,绝不是民俗体育的主要发展路径。但在当前我国民俗体育发展实践中,项目化的发展路径则成为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主要路径。正如路径依赖理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将项目化的路径作为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主要选择,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得到强化,即使认识到这种路径是不对的,我们仍然会坚持锁定这种发展路径。
3.2 对今后发展民俗体育的思考
如前文所论述,涂村舞龙之所以能够在数百年中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是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而存在的,并且,这种社会再生产机制中所蕴含的上述功能基本上契合了当时民众的需求。20世纪末开始,涂村舞龙开始逐渐衰微,并最终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退却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涂村舞龙所承载的上述这些功能已经基本上不能够满足新时期村民们的需要,尽管它仍然还是作为一种“总体呈献体系”的社会再生产机制而存在。也即,涂村舞龙没有在新时期实现对其自身功能的及时转化,仍然是以解放前所具有的这些功能为主,那么,涂村舞龙的衰落和退却也应是迟早的事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三农问题和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仍存在着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就在这些地区。正如莫斯主张美好社会的建构应该回到礼物这种“总体呈献体系”的建构上,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应充分利用这些地区丰富的民俗体育资源,发展民俗体育与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既是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民俗体育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应充分利用这些地区丰富的民俗体育资源,也应回到诸如民俗体育的这类“总体呈献体系”的建构上。这就启示我们,今后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主要路径是走综合化的路径。所谓综合化的发展路径,就是在依托当地民俗节庆文化母体的背景下,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进行合理的调整,使我国民俗体育成为以民俗文化母体为其个性标志的具有独特风采的高度综合性文化活动[20],像古代社会的民俗体育一样成为一种涵盖经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理念的“总体性”民俗体育文化的构建,这其实也就是莫斯所主张的“总体呈献体系”的建构。
就其具体运作来说,在形式上,必须保留民俗体育的核心项目形式,如果某一民俗体育的核心项目形式不能够保留,那就意味着该民俗体育的消亡。在功能上,保留民俗体育的最核心的功能和意义(即保留民俗体育建构和谐社会秩序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和社会要求,移除或转换民俗体育的部分功能。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21]。”当然,进行了功能转化后的民俗体育文化能够可以运作、能够发挥预定的功能,否则我们无论赋予其多么美好的功能都只是一厢情愿。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构我们民俗体育文化,我国民俗体育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涂村舞龙而言,如果涂村舞龙能够在保留其核心形式(舞龙)和继续依托于其民俗文化母体(元宵)的基础上,成功地对其功能进行适时的调整,使之能够与村民的需求协调、契合,那么涂村舞龙也许会迅速恢复并重现繁荣景象。此外,在明确了今后我国民俗体育的主要发展路径是重建民俗体育文化的“总体呈献体系”,走综合化的路径后,我们还不应忽视有一部分民俗体育文化可以选择走项目化的发展路径,只是应该给予区别对待,分类发展。
4 结语
涂村舞龙活动的个案表明,民俗体育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它是一种“总体呈献体系”,它在社会历史进程的主要作用在于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最终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得以建构。民俗体育的这种历史作用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相契合,因此,开发利用民俗体育资源,促进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不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同时也为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确立了实现途径。这种路径就是民俗体育走综合化的发展路径,即在依托于其民俗文化母体的前提下,保留民俗体育核心形式和核心作用,并对民俗体育中一些不合时宜的作用和功能进行调整和转换。
[1]王俊奇.江西客家民俗体育历史源流及其文化特征[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1):68-71.
[2]郎勇春.城镇化变迁中的孝桥镇民俗体育[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2):33-31.
[3]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Vijayendra Rao.Celebrations as Social Investments:Festival expenditures,unitpricevariationandsocialstatusinruralind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1,38,(1):71-97.
[6]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7]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8]高丙中.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J].江西社会科学,2006(2):7-11.
[9]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0]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6.
[11]Smith,Robert.The Art ofthe Festival:As exemplified bythe fiesta tothe patroness of otuzco:La virgen de la puerta[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9,81(1):170-171.
[12]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0.
[13]Mikhail Bakhtin.Rabelais and His World[M].Bloomington:Indiana Press,1993.
[14]Lebra,Takie S.Reciprocityand the Asymmetric Principle:An analytical reappraisal ofthe japanese concept ofon[J].Psychologia,1969,41(12):129-138.
[15]Arthur Wolf.“Domestic and Communal Worship in Taiwan”,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ephan Feuchwang[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74:105.
[16]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25.
[17]陈红新,刘小平.也谈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的概念及其关系——兼与涂传飞等同志商榷[J].体育学刊,2008(4):8-11.
[18]涂传飞.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概念再探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11):27-33.
[19]张基振,虞重干.论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的娱乐性[J].体育文化导刊,2005(11):75-78.
[20]郑国华.社会转型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174.
[2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2004:432.
Soci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An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 Function of Folk Sports:An Ethnographic Report from the Dragon Dance in a Village
TU Chuanfei
(School of PE,Jiangxi University of Economy and Finance,Nanchang 330013,China)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historic function of folk sports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dragon dance in a Chinese village.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folk sports reflect a soci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by this way the society could be 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Based on the findings,the paper also examined the existing recognitions and developing practices of folk sports.Finally,this article concluded that folk sports can promote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rural and ethnic areas.Meanwhile,this sets the realistic path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This is a synthetic path that preserves their core forms and functions,adjust or change some improper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of the time and the society under the premise of integrating in its folk matrix.
folk sports;historic function;soci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dragon dance
G 80-05
A
1005-0000(2011)01-0019-05
2010-09-16;
2010-12-17;录用日期:2010-12-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CTY018);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08JY15)
涂传飞(1976-),男,江西南昌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历史与文化。
江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江西南昌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