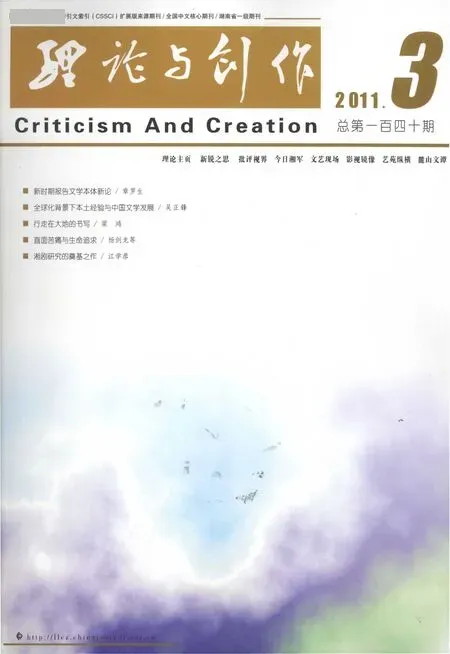生命的敞开与意义的质询——论龚鹏飞的《漂流瓶》
■龙永干
生命的敞开与意义的质询
——论龚鹏飞的《漂流瓶》
■龙永干
一味地揭露社会的腐败与黑暗,而将腐败与堕落的根由归罪于社会环境的恶劣,无休止地感喟生活的乏味与意义的虚无,而以游戏态度放纵自我,不断地唠叨欲望的泛滥与生活的无奈,而又为自我利益的获得自足……就在当下文坛演绎这种共相之时,文学审美、向善、求真的本质价值却在悄无声息中失落,其澡雪精神、疏瀹心灵的诗性被莫名地悬搁与遮蔽,文学的本体意义在晦暗不明中无法触及到生命的神圣与高贵。可以说,这种状况所引发的不仅是文学的尴尬,而且是生命自身的惶惑。但当我们翻开《漂流瓶》时,久抑的审美期待在作者所营构的叙事空间中渐渐脱去了芜杂浮躁、萎靡灰暗的心灵尘垢,在一种秋雨洗尘、明月朗照的氛围中让心灵获得了一种诗意的飞翔。
一
《漂流瓶》以许上游、司马佳、杨运仁、葛燕南等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主体,在广泛展示时代变化的同时,重点考察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心理与生存状态的演变轨迹。这里有精神的裂变,也有价值的转向,有生活的堕落,也有灵魂的升华,有痛苦的反思,也有执着的坚守……但总体来看,叙事者始终以平和之心去面对生命的多方仪态,在一种涤除成见中进入敞开的生命境界。
故事的开端是1990年代初。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热力蓬勃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分化、富于变数的时代。一群拥有激情与梦想,理想与信念的青年大学生,远离了繁华热闹的城市,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而选择了“文盲和半文盲高得吓人”“危房大量存在”“师资严重不足”的偏僻边塞,期望用自己的青春与知识去改变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状况,去实现自我的意义与价值。杨溪县民族中学成了他们进入社会的第一站,也成了他们真正面对生活与社会的起点。虽然他们多是失意的结局,有的改志从政、有的弃教经商、有的无奈留守……但从叙事者的意图来看,作者并非在于批判与揭露腐败与黑暗,也不在于展示伤痕与咀嚼苦难,而是在于以一种迎接生活的“同情”,去体验属于生活的一切,去体验生活的丰富多样与复杂深沉,去接近属于生命的本真,去探询属于生命的“自由”。
当许上游、司马佳、杨运仁等人怀着改变边地落后教育状况的理想来到杨溪中学的时候,理想在现实面前只能是意向性的悬搁。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辛、待遇的低下、人事的纠葛,还有教育观念的陈旧、自我意志的脆弱与心灵的芜杂。其中给他们激情以极大阻挠的不是其他,而是陈旧且保守的教育观念。当司马佳组织全校教师讨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名言集锦》时,新与旧、科学与落后、素质提升与应试取向的矛盾展开了一次全面的冲突,让这群涉世不深的大学生首次尝试到了守旧的重压。最终是司马佳与许上游等人在群情汹涌、锋芒所指面前无从辩驳。与之相应,许上游尝试着用讨论法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课堂教学就被否定了,文学社在《州城日报》上发表的作品也成了不务正业。当他被抽调到六沟垅乡去从事扫盲工作时,他的理想主义的做法在教育办主任王明学与党委书记雷长虎那儿更是显得幼稚简单,不合时宜。为完成扫盲任务,拆屋抓人的粗暴手段派上了用场,日本人捐助的款项没有用于发展教育,而是用于发放拖欠的工资与购买吉普车。为了应付检查,多方作假而闹出了啼笑皆非的问题……与外在的矛盾与阻力不同,各个生命主体也在杨溪中学中开始了诸多的变化,许上游在教学方面遭受挫折之后并没有颓废与消极,但不得不采取了在内敛中坚守的方略。雷厉风行的司马佳在激进中逐渐圆通,有意无意地为自我权变。同去的汤亦武、杨彩霞虽未过多涉笔,但生活的琐屑已然让两人沉沦,蔡文科等人的生活就隐现出两人的将来。现世第一的杨运仁面对生活无所用心,选择了“入乡随俗”的顺应,在教学中按照刻板模式操作,在日常生活中烧电炉、钓鱼、吊儿郎当,最终在自然欲望的驱使下与女生出轨……生命的多样与丰富,命运的多变与曲折就在一种涤除成见中获得了“敞开”。
但就在文本展示着生活的多方与芜杂的时候,叙事主体并没有简单地将生活划分为是非错对的格局之中,也没有将矛盾与弊病归结为生命的异化或社会的黑暗,而是在面对生活的矛盾与弊病时,排除成见,用心去贴近生活,去体验生活的真实。从而其对生活逻辑与人性复杂的把握就极为全面与真切。杨溪中学老教师们虽守旧,但守旧中的认真、固执中的执着却让人感喟,杨运仁虽吊儿郎当,但生活逻辑的必然让其无法自持,出轨后道德的煎熬与忏悔式的放逐也可见到其不错的质地,司马佳渴望有所成功,但最终也只能事与愿违,葛燕南虽在商场大显身手,但却身心孑然,最终落得个自戕而亡……生活自身的多样生态,让每个生命都在自我的轨道上展示出其本然的变数……让生命成为一只“漂流瓶”去“打量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去体验生活的复杂与生命的敞开,去观照与审视精神与灵魂的轨迹,人物的表白也是创作主体是生命视角,也正是叙事者这样一种开放的视角与澄澈的胸怀,让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通体明朗的审美境界,一种生命的诗意敞亮,因为“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之思”①。
二
“体验也就是从自己的命运和遭遇出发来感受着生活,并力图去把握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体验需要有灵魂要求把生活的种种关系和基于这种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内在要求,是生活着的反思,或反思着的生活。因而,体验是一种指向意义的生活。”②而这种生命意义的指向在文本中则体现为人文主义的维度。
与当下众多表现生活黑暗、意义虚无的作品不同,生活差强人意之处同样也出现在《漂流瓶》中,但创作主体并没有在虚无的情境中让人物滑向解构的泥淖,而是以人文精神为基石去建构许上游的生命主体,去呵护心灵的空间。对生命意义的探询,对精神自由的渴望,成了许上游这个形象的审美价值之所在,也成了整个作品意义得以生成的基石。《漂流瓶》所构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许上游的生活界面而展开,也就在他的视界与生命体验中,我们见到了一个以人文精神为轴心而建构的直观生命的诗意栖居之所。
人文精神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内涵。文艺复兴时期,是在与宗教神权的对抗中确立人性与人权的价值与意义,在启蒙主义时代,是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与强调,19世纪则是对理性主义泛滥的反驳,20世纪以来则是力图在物化时代重新建构人的主体性③……但无论哪个时期,它都是以人的主体性的自我构建为其根本基质,在对人的尊重、理解、“同情”、认同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与生活实在同一性存在的精神的超越。这种价值取向在许上游身上获得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与司马佳、杨运仁等人相比,许上游去杨溪民族中学的决断更多的是生命主体性建构的召唤。在杨溪县,他能从琐屑的生活中抽身而出,能去领会自然之美的澡雪与疏瀹;在闭塞的环境中他并未屈服于应试教育的压力,而是引导学生在机械沉闷的课堂中去发现生活的诗意;他不满于蔡文科等人教学观念的陈旧与教学形式的呆板,但并不虚设价值的自我指向,反而同情他们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感喟他们对生活与教育的“诚”与“真”;在杨运仁最低落的时候,他不以冷眼待之,在无言中给予一种理解;聘请的雇工“三爷”携款而逃,他也认为“合情合理”;即使得知亮亮成为别人的金丝鸟后“也不责怪命运”……与一般知识分子形象与环境的格格不入不同,他与生活之间并不存在严峻的张力,也不与他人形成尖锐的矛盾,在他身上更没有飙张的个性与突兀的性情,他身上所表现的是一种柔和与恬淡的生命情怀,一种澄澈朗照的诗意人格。
当然,许上游的生活并非皎然不滓、圣洁无比,叙事者也不想标举一种虚无抽象的圣人伦理,他的不足与弱点,并不影响他对生活的探求,生活的逻辑与艺术的逻辑让其成为了一个具体真实的生命。他的世界有人性的弱点与欠缺,也有着生活本身的芜杂与多样,但他并没有陷入颓废放纵,也没有面壁虚设自足的世界,更没有在慨叹中实用性地参与,他是一个实在具体的生命,但在实在具体的生命中所贯注的是对生活有限性的超越,是灵魂要求把生活的种种关系和基于这种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内在要求,是生活着的反思,或反思着的生活,让他总能超越外在生活的限制,让灵魂将自我与生活结合起来,在一种精神的联系中去建设一种诗意人格。也就是说,在许上游身上,他并没有与生活隔离,也没有弃绝生活,因为自我的意义与价值就在生活之中,这是一种建基于经验式的体验,在这样的一种有限的存在中,无限与永恒,超越与本体才有可能获得。简单的说,就是在生活本身获得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的需求。他在抄袭教案后,能深刻地审视着自我人性的弱点;在失去亮亮后,会更为宁静地面对命运的安排;在获得财富后,“决心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葛燕南死后,捧读王阳明,想辨清“乱”与“正”;在经历如许的纷杂后渴望回到“原点”,回到“传统美德”“善良友爱”“关心他人”……“精神生活要摆脱我们的有限性所涉及的要求不可能满足,除非精神生活显示它自己不只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实在的附加物,相反,是实在本身极深刻内容的展现,实在正是在这里获得自我直观性并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意义④……也就在这样一种生命感悟中,他最终决定再次回到杨溪中学去做语文教师。可以说,这种回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歉意,也不是偶在性的忏悔冲动,而是其性情与心理的必然,更是其生活诗意一贯追求的必然,因为生活的诸多有限性“把人带离了自己的根,漫世飘飞,离开了人之为人的人性法则,才带来普遍分裂的出现。因此,在历史境遇中要寻得同一,首先就要返本探源,寻回自己的本真。”⑤只有回到精神与灵魂的“原点”,才找寻到人文之本,才能获得一种诗意的直观……
三
在当下后现代语境中,许多小说在灵魂亏空的情境中总想追求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在远离创新的境遇中反而标举“反小说”自慰,消解情节、瓦解叙事、痴迷话语碎片成了一种疯狂的“时髦”……与之相比,龚鹏飞的《漂流瓶》显得不甚时髦,但其中却有一种为当下诸多小说所缺乏却深潜于一般读者审美召唤结构中所渴望的疏朗开阔、平和冲淡、朴质自然的诗意之美。
与诸多浮躁芜杂、阴暗低沉、颓废悲观的文学世界不同,《漂流瓶》给人一种疏朗开阔,纯净自然之美。这种美来自杨溪县宁静优美的自然风景,来自寅水河畔质朴粗犷的船工号子,来自阿凤所唱的清脆淳朴的民间山歌,更来自许上游,亮亮、阿瑛、杨溪中学学生等人对于生活的感悟与歌吟的诗歌传递,它们风格或单纯稚气、或激情昂扬、或伤感忧郁、或明悟澄澈,篇幅或长或短、体式或新或旧……这种诗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许上游与瑛子的相知相恋上。两人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是起于庾信的《枯树赋》,是缘于对于生活的审美观照与诗性体验。随后两人交流中的谈诗、诵诗、作诗,灵魂的琴弦在共鸣中奏出了美妙的乐章,达到了一种“情往以赠,兴来如答”的灵之境界。
不仅各种样式诗歌的镶嵌让作品增添了一种诗意的氛围,而且小说中人物心灵深处对于诗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也让作品骨子里见出一种无法掩抑的诗性精神。许上游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自然之美的领悟,对于当下生活的超越,让其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诗性神韵。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是一种不偏持、不严峻、不俗气、不焦灼的人格魅力,是一种恬然而出、过而不留、通而不滞的禅性智慧,是一种既融于生活而又不为物累的通脱,是以儒家的醇厚为肉、道家的超然为骨的生命气象。
与作品的诗意氛围相应,小说的结构也表现出一种疏朗开阔,自然朴实的风格。结构不仅是叙事展开的一个维度,也是作品审美构成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无论结构是单线式、双线式,还是蛛网状,套盒式,都不能脱出小说内容表达的需求去作一种思辨式的抽象,也不能因着意去贴近生活的自然状态而失去其应有的组接融裁功能。《漂流瓶》正是避免了上述种种偏颇,没有故作高深之嫌,也没有散漫随意之弊,而是以许上游生活界面的拓展为线索,杨溪民族中学从教、六沟垅乡扫盲、省会商场打拼,弥勒山闲居相恋……简明自然、疏朗开阔,与整个故事内容的推进相契相融,而又毫无滞碍……
注 释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②⑤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第238页。
③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④[德]鲁道夫·奥伊肯著,万以译:《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