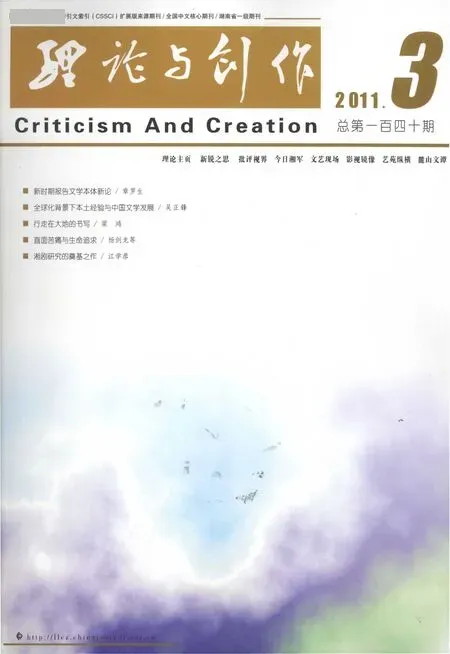在军人与诗人之间
■李美皆
在军人与诗人之间
■李美皆
有一些人会去写诗,我感到特别能理解,甚至觉得:他们活着,只能去写诗,比如李白,比如顾城。有一些人会去写诗,我感到特别不能理解,因为,他们的一切似乎都与诗毫不相干,比如,我将要写到的这个人。张同吾先生在给他的诗集《许多风景》的序言中写道:我与张蒙相识已十几年了,那时便鲜明地感觉到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严谨规范、谦虚诚恳、细致周到、睿智干练,这样的人会让战友信任、领导赏识。这段“个人鉴定”,也概括了我对张蒙的基本印象,虽然我与他相识的时间要短得多。
这样的一名军人,与我概念中的诗人实在相去甚远,我觉得他应该属于最不可能去写诗的那一类人。因此,理解“他为什么会写诗”,就成为我读他的诗的原动力。
《干事》这首诗,透示着一名干事出身的军人的精神密码,是内心的偶露峥嵘,惊鸿一瞥,如闪电撕开夜幕的一角:“一些颗粒 反复练习溶解/在一种叫做单位的液体里/被日夜搅拌/从一个容器倒进另一个容器/摇匀/博士硕士学士战士 混合后/都成为干事”。干事,就是一些在“单位”的液体里练习溶解的颗粒,这个定位很深刻,也许还有点沉郁。“大大小小的颗粒/形态各异的颗粒/他们抱紧自己的内心/飘飘荡荡/他们已经表层溶化/他们渐渐异彩纷呈/他们在无色无味 而又/五味俱全的液体里/起舞/都被容器紧紧看管”,干事,那些颗粒,在表层被溶化的同时,还不忘抱紧自己的内心;在液体里再怎么起舞,也是被容器紧紧看管。有一种内在的沉重,却表达得平稳宽缓;一面内心冲撞不已,一面又把自己禁锢得不动声色。把内心的下坠感牢牢控制住,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干事的基本素质。“突然有一天 他们发现/自己的表层不再溶化/内心却早已溶解得无影无踪”,这种无奈,在自身生存的空间中是无法轻言的,只有寄托于诗。写诗,也许就是他抵抗内心被消解的一种策略。“在往高处走的人身后/一伙人默然 伛身
轻盈/如风如影/他们惟一的动静 就是/用蚊子打喷嚏的声音/反复哼唱一首儿歌/我们都是木头人儿/一不许说话二不许笑/三不许露出大门牙”,根据我的观察,人们通常会把体制内的工作场所称为单位,体制外的工作场所称为职场。因此,单位往往与体制有关。单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场域,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只要有“单位”的地方,就有升降沉浮;而“干事”所在的“单位”,升降沉浮则更为典型和密集。在上升者的背后,是等待上升者的谨小慎微克制压抑和敛神屏息小心翼翼,言行不消说了,连眼神和呼吸,恐怕都有必要掌控好。每一个上升了的成功者,大概都会有这样一段成功前史。欲扬先抑,没有此时的“抑”,便没有日后的“扬”。在轻舞飞扬中青云直上是不可能的,学会自我收缩、自我抑制,是干事的基本功。张蒙应该也不例外。人的本性是渴望飞扬的,收缩和抑制与人性本能的方向是逆反的。好在,张蒙找到了诗歌。诗歌,为他内心的逃遁与释放提供了一个通道和平台。所有的压抑,都在诗歌中得到了升华。
干事,这个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明明白白地规定着这个角色的职责,那就是要干事儿。干事永远是生活“在事务的襁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事务,就是写材料。“材料”与“单位”一样,大概也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创造。作为与材料无关的一介文人,我始终不明白,材料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单位”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材料?有哪些事是在材料中解决的?有哪些人在看材料?材料有没有人认真去看不知道,但肯定要有人认真去写的,甚至有人一辈子就耗在这些材料上。干事,就是写材料的人,所以也称“刀笔吏”。“刀笔吏/那把刀终究没能扔掉 而是/插在了自己的心头/由此 笔者做不成隐士/而成了忍士/吏也还是隶着/为‘史’徒添了‘一’层/浮尘/而已”,这几句,有一些苍凉,甚至怆然。只要“单位”和“材料”存在,“刀笔吏”就要存在,“刀笔吏”的命运就要延续,“吏”与史,因此被打通了,“吏”的沧桑感,因此也具有了历史感。程式化公文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文化规约。制造程式化公文的过程,就是适应程式化的过程,最终,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篇程式化公文。有没有更有效的方式去代替这些程式化公文,并使人从这种程式化中解脱出来呢?
作为一名军队政工干部,张蒙的工作总是与干事有关,不是在当干事,就是在管干事,《干事》这首诗里面,有他很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悟。这种难言的体验和感悟,也许只有借助于诗歌,才能表达得最充分最到位而又最含蓄最富有美感,诗歌具有这种功能。我们要感谢诗歌,就是因为它具有这种功能。张蒙要寻求诗歌,就是因为他需要这种功能。
我极少鼓励一个人去做诗人,而宁愿鼓励他去做一名好军人、好男人,因为我了解的诗人及其荒唐太多了。但是,我却愿意去呵护像张蒙这样的人的诗以及写诗的愿望,因为那对他们很重要。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对心灵缺少润泽,他最好能在工作之外找到一个有益的润滑和补偿。如果这个润滑和补偿恰好是诗歌,我认为是诗之幸,人之幸。撇开更高的精神意义不谈,写诗毕竟是环保、干净且有助于和谐的事情,低耗能,无污染,无损健康,也不影响家庭关系,比狂赌豪饮之类的事情高尚多了。这不是诗歌的贬值,而恰恰是诗歌价值的最大化。诗歌最初就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它对于那些不以写诗为业的普通人的意义,恰恰是诗歌最大的意义,是回到诗歌的本源。对于像张蒙这样的写诗者,诗歌最重要的意义也许就是“言志”,经由诗,郁结得到抒发,豪情得到挥洒,这就够了。我想,他们写诗,并非为了成为一个诗人,这个世界诗人已经太多了,而他们的主体价值并不体现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奇怪的观念:只有那些除了写诗一无所长的人,才能把诗写到极致。李白虽然自认为政治上怀才不遇,胸中常怀不平之叹,但是,我敢肯定,他的政治才能不会超过他的诗歌才华,他最擅长并确定能做好的,大概还是写诗。大多数写诗者是不必执着的,用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诗最好,有兴致了就写,没兴致了也不要去寻找它。不想做诗人,但想做一个保持性情的人,这是许多人写诗的内在缘由。朝着诗的方向努力,但不朝着一个诗人的方向努力,让诗歌作为坚固的精神坐标竖立于人生一侧,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取的诗歌态度。
一个被内化到骨子里的秩序看管得很严的人,一旦出离秩序,可能会怎么样呢?《海风如此亲切》这组诗,展示了张蒙完全不同的另外一面。从诗中可以知道,这组诗是他去海南出差的收获之一。接到通知,开始准备,那种怦怦心跳的兴奋就跃然而出了。去一次海南,对于他来说,其他方面并非奢侈,奢侈的只是时间。那种按捺不住的兴奋,不仅仅是已经闻见海的气息的兴奋,更是即将出离日常秩序轨道的兴奋。他要飞了,他也真的飞了。“两千五百公里/不是距离 是时间/两千五百年/不是时间 是高度/一绺绺白云擦肩而过/是老子的拂尘轻轻掠过”(《拨动明亮的天际线》),飞翔,不是他常规生活中的包含动作,所以,渴望的风帆更加涨满。在天空中,他想象着与老子、庄子、列子一起逍遥游,一起御风而行,心中挂满叮咚作响的喜悦的音符。“正是花蕊中的花蕊/樱桃中的樱桃/因此她叫海之秀口——海口/飞机急速降落/我以急遽的抵近/置身于这秀口之前。我心对我口/我口对海口/一切 从突突的心跳开始”(《海的口》),“往上攀登/心里的火苗蹿得老高”(《水与火的缱绻》),这样的一次出行,对于他来说就像置于沉重托盘之上的一掬鲜果,他的兴奋,足以从另一个向度衬托出他平常时候的不能兴奋。急遽的抵近,是美的抵近,是诗意的抵近,是自由之境的抵近。冲向大海,他变成了一个“回到家的孩子”。那个他,绝对不再是上级、同事和下属所见到的他了。“海滩是我的长辈/是慈祥的父亲 正远远地/朝我微笑/又是善良的母亲 极亲切地/拥我入怀//看见沙滩那一刻 撒欢的冲动/骤增十万分贝/忘了人到中年的种种规矩和累/急切扑进沙滩/用残存的真诚和勃发的温暖/彻底撒一回娇……在自家的沙炕上歪着/自由自在地打滚/把蓝天看累了就闭上眼睛……回到家的孩子/不任性撒娇 干吗呢”(《回到家的孩子》),那个默念着“低调些心里踏实”(《龙王很忙》)的中年男人终于完全被“撒欢的冲动”所支配。人人都以为拿一把铲子到海滩上去挖沙、挖蛤蜊、挖小螃蟹是小孩子的嗜好,实际上,大人也一样会乐于此道,只要有机会。“暗 概括着一切……不远处 一双眼睛/正依偎着另一双眼睛/几乎无法分辨他们与夜色的差别/而含糖量极高的窃窃私语/成为夜色中特别的灯笼/柔软的海风把他和她轻轻摇晃”(《夜色》),这样的柔情与幽情,也是那个生活“在事务襁褓中”的他所不可能拥有的。与生活拉开一点距离,才可能拥有这样一个内心的空间,才可能拥有这样一双发现的眼睛。
其实,写诗何尝不是他从常规中逃逸的一种方式呢?只有在远离日常的地方,他可以如此放纵;只有在诗中,他可以如此表达自己的放纵。只有在诗中,他才会明确认同“太像别人就失去了自己”(《椰子的亲情哲学》)这样的观点。写诗,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生活的沉重和中规中矩。内心的激情与冲动如地火与岩浆,只有在诗中,才可能得到喷发。作为一名恪守规矩的军人,张蒙即便在写诗时,都是一个克制的诗人,这组诗是个例外。
张蒙还是一位诗国的圣徒,诗歌在他心中的神圣性,与佛在佛教徒心中的神圣性可以相提并论,促使他永不放弃诗歌追求的,可能主要还是这种热爱。他的《昆仑山的身影》这组诗中充溢着的神圣情感,足以使人低眉敛首,为诗歌灵魂的肃穆和伟大所震慑。他来到塔尔寺,“眼前一亮/塔/轻轻走进幽深 仰望/心 一层层长高……诵经声低旋回响 如春雷/一种震颤中的静/轻轻闭上眼睛/低下头 合掌胸前/我 静静拔高/融进圣塔/心久久叩拜/与天同高”(《圣殿——初访塔尔寺》)。作为军人,张蒙并不信仰神佛,他只是在灵魂中为一种神圣情感设立了祭坛,这种神圣情感与任何教义都无关,或者,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宗教。
他在昆仑山的一切膜拜,似乎都化成了对已故诗人昌耀的膜拜;而他对于昌耀的一切膜拜,又同时是对诗歌精神的膜拜。昌耀在他心目中,就是与巍巍昆仑等量齐观的一座高峰,就是一座诗歌精神的昆仑。“不妨猜想昆仑山原名叫昌耀山……心无旁骛 精心修炼/历经磨难 果然/达到了诗的圣境/气睿内敛 以致木讷/而口吐珠玉 异彩纷呈/他炼就了诗意的金刚之身/他从囚徒成为山神//因此 他/躺着都是一座高峰”(《山神》),“在塔尔寺 昌耀是一炷香/他把自己献在佛前/燃烧许多纯洁的想象……昌耀 是其中的/一位圣僧一座白塔一座圣殿……许多游人来到塔尔寺 点燃一炷香/虔诚地顶礼膜拜 默诵佛号/也默诵一个诗国圣僧的名字/香烟缭绕中 人们隐隐看见/诗歌在前藏 盛开成雪莲和藏红花/昌耀在后藏 默然无语”(《塔尔寺的一炷香》),“此后 昌耀依旧做‘密宗’僧徒/而经他点化的诗已成为‘显宗’法器。//忽一日 昌耀隐身峰岩闭目静修/诗复又在日月间徘徊不定”(《在日月间》)。这一组诗具有令人倾倒的神圣之美,那种神圣的气韵,带着宗教般的静默、神秘和崇高,像迷魂的香气,袭向我们的心。“青海 已成为/昌耀的囚徒”(《囚徒》),昌耀在青海跋涉的过程,就是一个诗歌的圣徒在诗国跋涉的过程,是诗歌精神涅槃的过程。在跋涉的尽头,是对苦难之境的征服,所有的苦难之境,都已经成为跋涉者的囚徒。昌耀,最终成了诗国的王。“无须分辨河流的方向是倒是正/他 只管/顺着河流走着……昌耀非常羞怯 只能躲避/他 承受不了这份美好光景/他 早已弄不清/痛苦和幸福的方向和界限”(《倒淌的河》),通过对昌耀人生的追溯,张蒙发现,昌耀的人生,似乎就是一条倒淌的河。是悲悯、心痛,还是敬仰,张蒙似乎也分不清情感的“方向和界限”了。
张蒙是一位贴着地面行走的理想主义军人。他经受过严格的军队基层锻炼,并对军队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饭前唱歌》、《班务会》和《紧急集合》,都是深厚的军队生活体验的积淀。饭前唱歌是所有参过军或真正经历过军训的人都有所体会的,饥肠辘辘,只想快点完成这一固定程序,于是选短的歌,比如《学习雷锋》,并且越唱越快,结果,一声“重来”,欲速不达。真正有经验的士兵是不会选择短歌并越唱越快的,正如真正有经验的士兵是不会第一碗盛得特满的,因为那就没有盛第二碗的机会了。先少盛点,吃完再去盛满,这才是老兵。“你看 一旦歌罢/听到‘进饭堂──/坐下──开饭’的口令/那真是虎狼之师啊”(《饭前唱歌》),在一首诗中读到这种有趣的军队生活花絮,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将会心一笑吧?在《紧急集合》中,他把背包当成自己的战友,无论多么艰难多么沉重,都“必须背着它们跑”,这是一个真正热爱军队的军人才会拥有的感情。在《班务会》中,他对一个小小的班务会上的每人一分钟的发言做了细致的剖析,这是只有扎扎实实当过几年兵的人才会做出的剖析,为军人严谨求实的作风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解。
作为一名理想主义军人,张蒙对军队不仅怀有很深的感情,而且有着极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依稀可见陆游精神的影子。我感觉张蒙选择从军,就是为了实现男儿报国志,同时完成个人的建功立业。这句话经常被说,但我相信,用在他身上不是空的。事实上,发现这一点曾使我略感惊讶,因为,真正的理想主义在今日已成恐龙。但是,他处在一个和平年代,“战争是一座山 又一座山/之间那片开阔地/叫和平”(《嗨,军车》),和平年代,“养兵”远远大于“用兵”,军人的理想似乎处于一种无为状态,这可真如军中拉歌时所唱: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他在写刺刀、枪、坦克、榴弹炮和军车的一组诗中,替武器们没有用武之地而感到着急。你看——营区和公园早已结拜兄弟啦。哨位像是一个休闲的地方。枪的眼睛——枪口虽然瞪得溜圆,却白白熬成了黑眼圈。坦克因为天天吃饱了蹲着不干活,惭愧得跪在履带搓板上默默检讨。榴弹炮身为青壮年却在打盹,但是,谁去叫醒他呢?战争也在打盹呀。军车本来渴望做战马,到那战争的山坡上去奔跑,眼下却只能在街市人流与日子中扭来扭去穿行,心里也是好腻烦啊。
武器总是渴望战争,张蒙之所以会写武器无用武之地的惆怅,与他身为装备人有关,这也是一代装备人的惆怅。他热爱武器:“大炮 我的大哥/九米多的个头一座/典型的黑铁塔/吼一声 能震碎你满口牙/但平时/静默得像老子的哲学”(《大哥》),一声“大炮 我的大哥”,喊得人心里发热,这绝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喊得出来的,那是对大炮的深厚感情。在当今很多人眼里,大炮已脱去了武器的性质,成了在景点供人照相的道具。作为一名装备人,他是多么不愿意看见大炮变成花拳绣腿的东西,看见武器变得慵懒!战场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试炼场,男人的英雄梦在和平年代醒着,他渴望如武器一样,到战火硝烟中把自己炼成传说中的英雄男子汉!这不是好战情绪,这是一个男人的光荣梦想。张蒙对军营的感情,体现于每一件武器,体现于一草一木,也体现于身处的营房。在《挥挥手——告别一座老营房》中,他写道,“东西阔80米 是宽肩/南北深16米 是背厚/屋脊高20米是虎头虎脑的头顶……表情——/深处是苍劲 面上是春风”,他写的不是一座老营房,而是一个男人,一位兄长。当这座营房业已变老,正被拆除时,他又写道:“我的门窗已被卸去/房顶的瓦已卸去/我第一次透视自己/生命的箫 横陈月下/借着晚风的手指/我抚摸自己的肋骨和低低的/心灵火焰/许多思念轻轻吹响/空气里骤然泛起泪的潮汐/晚风搀着我 轻轻说/走吧”。这是跟一位朝夕相处的敬爱的长者的告别,男人的泪,在此可以无愧地落下,落在一首深情的长诗中。
对军队的感情,当然还包括对共同奋斗的战友的感情。《寄一束江南雨季的书简》这组诗,是他从当时工作的南京去新疆马兰基地学习的感触。在《雨巷与走廊》中,他写道:“江南雨下得最多的地方是雨巷/巷边的回廊里也充盈着雨气/那些油纸伞进化成塑布伞之后/依然是巷中徘徊的影子/当然 一些细雨/再好的伞也遮不住/在伞下如织 直湿到/心情深处”,湿气中的江南,是兰的故乡,当他从兰的故乡来到马兰,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兰与马兰、东南与西北、雨水与尘沙的对比,内心被深深触动了。“此时 任何人/从里到外 所有潮气/都被蒸发净尽/人生无比干爽/生命 是一把纯净干柴/因此 驻扎在/罗布泊西边的‘马兰人’/血浓得像烈酒/他们用烈火干柴般/热切的生命激情/做着自己那份钟爱的事情/他们在巷和廊之外 已经很久/在雨季之外 已经很久/他们 真的需要/一封寄自江南雨季的书简”,他多么希望,把江南的水气,移到被搁置在雨季之外的马兰,因为他热爱并敬慕着他的战友们,可是,他只能在诗中寄去一束江南雨季的书简。幸而有诗。对于军人的牺牲奉献,张蒙体会很深,但又真正做到了无怨无悔。因为,“军人 就是意志”(《意志》)。在《哨兵与鹰》中,他借一名哨兵与一只鹰的对话,表达出一个军人细微的心迹——那就是对千家万户平民百姓一般都会拥有的平凡幸福的渴望。一方面,他写道,“他的心飞得更高/远在鹰背之上”;另一方面,他又写道,“幸福生活谁不想呢/告诉你吧 每到傍晚时分/远远看到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俺就想变成一棵普普通通的蔬菜/被爱人用篮子挎回家/用那温柔的手 择净/洗得油油亮亮的……”刚强男儿的内心渴望、七情六欲轻易不流露,一旦流露,便令人动容。在《海魂衫》中,他把滨海路上的白色斑马线与水兵海魂衫的披肩领上的“斑马线”奇妙地联系在一起:“扛着斑马线巡逻的水兵/很少有闲暇走近那些/马路上的斑马线/直到有一天/水兵的青春热血/骤然凝聚成海魂/才从马路斑马线上/悄然走过/如风一般”,这首诗,是对“凝聚成海魂”的水兵的敬礼,一个肃穆的军礼。
张蒙的理想主义军人情怀,与他正统的儒家情怀是分不开的。他是典型的礼仪之邦走出来的人,恪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这种克己复礼的忠义之士,在现代社会已实属罕见了。“五四”以来,反儒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意识的题中之义,从意识上来说,我似乎还算现代,但若判断具体的人与事,我却倾向于儒家,认为出自儒家的更加笃实可靠,对于男性的判断尤其如此。我不想去论证这是不是矛盾,反正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判断是得到了印证的。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儒家情结的人,张蒙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精忠报国的名臣总是给予深切的关注。《千年不散的会议》中,他写道,“我从千里之外急切赶来/向当年的那座荒凉的小渔村/打量搜寻/终究 还是靠了的哥的引导/才在闹市区深处一隅/用颤抖的视觉听觉触觉/整体发掘出土了仍在静静进行的/‘五公扩大会议’/走近红墙碧瓦 穿过牌楼拱门/随身携带的调侃 瞬间/与门票一起剪掉/庄重 在幽径甬道上/勃然丛生蓬展/以致密不透风地堵向胸口/一座座雕像一段段记述/授予青铜和花岗岩史官的权利/——左迁 贬谪 流放/再次左迁 贬谪 流放/字字句句都有沉船的份量/我久久伫立着/静静鞠躬”,五公祠是为纪念五位虽遭贬谪却丹心不泯的名臣而建的,在日渐增多的文化遗产之中,它正在遭受着被遗忘的命运,诗人则从“千里之外急切赶来”,为的是献上自己庄严的敬意。精神具有反射性,一个人所敬重的精神,可能正是对这个人灵魂的最好的说明。《精神与遗体的重量》是献给海瑞的:“人很瘦 遗体没多少分量/水陆接续转运/比活着时的旅行顺当/精神比遗体重不少”。诗人如此敬重精神的重量,正如一首著名的小诗所写:“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
一个具有担当意识的男人,往往更注重对历史的思索,并在思索中获得启悟。《一浪一浪的时光》这组诗看似写河,实则通过写河来写历史,“历史的河流”这一说法,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交汇。“在一条河面前/不必说年龄时间什么的/不必说朝代更替/河 即使干涸了/也同样冲刷着你”(《金水河》),业已干涸的河用什么来冲刷着你呢?用带给你的历史思索,用留给你的历史启迪。“有些事 就得把水搅浑/才能办成……从浑水中取胜/在浑河边立国/建立的却是清朝/此后二百多年 国是朝政/果然有清有浑//一条河 一个朝代/一个浑一个清/矛盾地依偎在一起”(《浑河》),清和浑纠结在一起,透示出历史的吊诡,又似乎符合历史的辩证。不惟历史,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欲清先浑,浑中求清,清中有浑,浑中有清,这何尝不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现实规律呢?这首诗,应该包含着诗人对于现实的深刻而微妙的感悟。这种感悟不好明言,但必定是在一定阅历的基础上才能得来的。在《辽河》中,诗人写道:“河水用柔情团结了两岸”,这是何等的柔骨!然而在《热河》中,诗人又写道,“一茬茬帝王 都在这里/泡成软面条/统统地腿脚不听使唤/扶不上鞍马 提不动刀剑/只轻摇一把纸折扇”,对于某种柔软,诗人以刀剑作比来打击,明显表示自己的不屑。这两种表达,就是诗人的“柔”与军人的“刚”的有机统一。《掌灯后的故事》这一组诗,是张蒙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观照,是以革命的诗情对革命进行溯源,诗歌在这里更多地充当了一种抒情方式,而不是思考方式。对于他这样一位对革命事业充满感情的人来说,这样的诗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相信他是毫不牵强的真情实感。
张蒙还有一些诗写得轻松幽默,体现出他机智有趣的一面。他为军营里刚刚诞生的一个叫小石头的男孩写了一首《小石头》,想象着这个小石头如何长大,长成老爷爷,在中秋夜对孙子讲述他的太爷爷当年事的场景。这个太爷爷,当然就是今日小石头的爸爸、张蒙的战友了。他称今日之小石头为小战友,称未来之小石头为大英雄。——当然,未来之小石头是不能称小石头的了,要堂皇地冠以大名,这一点他也注意到了。虽是虚拟,却像模像样,温暖醇厚,令人莞尔,仿佛见到了那些包含过去时的未来场景。《理由》是张蒙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班的结业感言,中央党校的学习居然还可以写成诗,而且写得那么幽默,实在匪夷所思!大概只有政工干部出身的诗人才有这样的本事。随手拈来一段:“几个月来 我们常常/以学校要求严格为理由/去推脱原单位那些仍然不断/找上门来的繁杂的工作事务/而我们又时常/以原单位的工作急需为理由/向班上请假 急匆匆奔走/我们曾以学校提出的/‘减少应酬’的要求为理由/逃过了不少累人累心的饭局/可我们又不时变着法子找理由/相互请请 加深交流”。《我们在节日里活着》这首诗中,他写道,“清明节 不论世道是否清明/人们都把心中的清明献给祖宗”;《眼皮跳》中,他写道,“好神奇的眼皮/无论多么锐利的眼睛/也看不透离自己最近的/这张帘子”。这样的机智,暗含着警世和反讽的机锋,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了。
苏轼用儒家思想来做官,用道家思想来修身养性,用佛家思想来对付人生的苦难。张蒙是用军人品格来入世,用诗人性情来出世的,他的人生因此达到了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境界。我愿意看着他入世更深,出世更高,然后有一天,他的诗将会使我明白,他已经达到了怎样“高深”的境界。我想象着那一天,他已是他所想象的小石头做爷爷的年纪了,而我也老了。我会戴着老花镜,依然读着他那些苍老的诗篇。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文学评论中心)
——怀念昌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