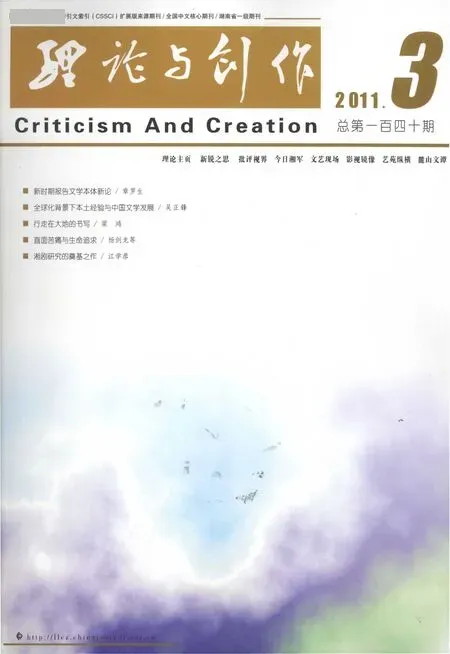历史“开裂”处的理性叙述✳——重读王蒙的《蝴蝶》
■温奉桥 陈金波
历史“开裂”处的理性叙述✳
——重读王蒙的《蝴蝶》
■温奉桥 陈金波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王蒙经过边陲“放逐”后归来“放歌”的年代,他以“急先锋”的姿态向“新时期”中国文坛投出了一颗颗“集束炸弹”,其中,《蝴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中篇小说《蝴蝶》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4期,从时间上来看,正值“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滥觞时期,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这一文学形态所反映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共鸣,与其说引起人们心中涟漪的是那些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不如说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因为建立“新时期”意识形态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把“革命中国”从“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中”剥离出来,进而让人们感受到“新社会”、“新阶段”的来临,此时,这些文学文本“生逢其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就像詹姆逊所说的那样:“置身于意识形态中的个人主体往往意识不到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他们相信自己是自立的主体,从而把那些想象性的再现关系当作理应如此的真实关系。”①所以,当何荆夫(《人啊,人》)在等待光明的未来时,却一步一步滑入“庄之蝶(《废都》)”式的深渊,因为这些从高压的政治权力解放出来的个体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无法把自己的生命落到实处,即使像章炳麟(《绿化树》)、许灵均(《灵与肉》)们把生命落到了实处(大地和人民),那么这里的“人民和大地”也不过是再造的想象之物,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民”大都是“启蒙者”和“救世主”,又不免走入了“民粹主义”的境地,比起“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悲悯的色彩,而且也从另一维度上参与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的建构。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太多的鲜血和泪水,感情炽热而悲怆,但往往只满足于倾诉和指控,理性的叙述几乎被放逐,这种创作症候对革命历史的透视和反思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也没有被深入地剖析,故而历史叙述的艺术魅力为此削弱了不少。今天,面对当下现实的需要,当我们从纸海钩沉中打开那座早已尘封的历史之门去寻找革命的遗产时,却发现“现实”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叙事”的魅力所在,王蒙的《蝴蝶》尤为明显。
一、革命历史的叙述
“革命话语”可以被视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的某种“奠基性话语(foundational discourse)”,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有意“撮合”。“新时期”以降,作为“重灾区”的文学领域如何表达自身以及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存在成为摆在众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为了不至于重蹈覆辙,政治的“矛头”指向只能成为作家们的参照。随着国内政治话语的转换,文学创作有了新的标准,“国家”、“人民”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词汇,一时间,反映这一预设主题的文学作品喷涌而出,甚是壮观,蔚为思潮,《墓场与鲜花》、《布礼》、《绿化树》、《蝴蝶》、《人啊,人》等作品基本可归入这一思潮的名下,这些作品都是以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而阐释以上概念的,其中展现出的“革命话语”始终维持在揭露和控诉层面,这一对革命表面化的叙述不仅没有打开革命历史的“原点”,也模糊了本应清晰的八十年代现实。
由此可见,怎样在恰当的范围内“演绎”这些概念主题自然成为八十年代文学取得认同的方式,因为它不但承担了过多的集体记忆,而且以倾诉的方式弥合了人们的“伤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代人民立言”,其只不过是先前“政治图解”式的翻版。沿着这一思路去重读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作品,我们便会发现王蒙的《蝴蝶》与当时创作的主流话语稍有不合,并发出了个人思考的细雨与呼喊。
新时期以来,王蒙再次拿起搁置了二十年的笔开始了一系列“急先锋”式的创作,革命的记忆始终在他的脑海里跳跃,这一点在他的八十年代早期的作品里表现地非常明显,如《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等等。《蝴蝶》发表伊始,从当时的评论文章来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出的干群关系,比如,陈骏涛评论道:“这篇小说提出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革命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②何西来在谈到王蒙的艺术探索时说:“人的心灵世界,是王蒙探寻人生和艺术时的主要侧重点和落墨点。他用自己的心灵,跟踪各种不同人物的心灵,”③这些评论不免带有“新时期”意识的痕迹,《蝴蝶》在创作形式上的变革作为当时文坛的异质性存在,使人们紧紧抓住“形式的现代化”不放,进而探究个人的心灵叙述和表层主体,这一“结构性”的存在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评论者,要么解读“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要么把《蝴蝶》所反映出的“人民”立场作为缓解“革命焦虑”的途径,这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文本中对革命和生活的思考却被遮蔽和压抑了,因为其中的“革命话语”并非是一个绝对的“所指”——作为被控诉的对象和表现主题的材料。
《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作为老一代革命家,经历了艰苦的革命战争的时代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被“平反”后回京后,他开始浮想联翩,思绪任意地流动,他首先想到了海云,在那个唯革命信仰马首是瞻的年代,张思远与海云的结合正源于这一信仰,然而,造成他们俩个人悲剧的原因恰恰也是因为“革命”,但是,这里的“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种“去革命化”的革命,也就是说掺杂了政治权力斗争的“革命”、全面霸占人的生活和情感的“革命”,继而造成“革命霸权”,王蒙所反思的正是这一种“革命”,而不是那种为了国家存亡和建设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样的革命是王蒙所认同的。当张思远面对死去的孩子时说:“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共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上百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弹下面……”读到这一段话时,我们不想为他的说辞去谴责他,而是被他的革命精神所深深感动了。王蒙对这一情节的设置不矢看做一种“修辞策略”,从而表现出他对革命精神的认同。国家的存亡时刻,张思远靠这种革命精神取得了心理上的平衡,但随着生活的继续,他越来越把这种革命精神当作他生活的全部和自己唯一的意识形态,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痛打落水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更需要一种“费厄泼赖”的态度面对现实,这一切却被人们忽略掉了,这是张思远的悲剧,也是中国革命的悲剧。当张思远被打倒下放到农村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革命与生活是可以分开的,没有革命的世俗生活同样是美好的。“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发现了肩……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秋文、冬冬和人民。
张思远从世俗的观念出发,对自己当初的狂热而悔恨不已,继而产生了自身的分裂:“张副部长”和“老张头”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的互相缠绕推动着整个文本的叙述节奏,进而表现出了革命的不同侧面和小说的“复调性”。小说中,“张副部长”、“老张头”和叙述者的声音都独立的存在,当张思远住进“部长楼”中的时候,他不免就想起了海云,这是他生命中永远的痛处,同时也象征了革命中的艰苦岁月;当他静下心来,作为化身为“蝴蝶”的张思远时,他却想起了那秀丽的小山村,那里杏花如云,小溪潺潺,更有他心中的“山楂树”,每当回忆起此时此刻,他总是有一股非理性的冲动,这股冲动最终化为了“六十岁出门远行”。革命让他悲喜交加,工作之余多了一份焦虑,这时,叙述者的声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一方面借助秋文和冬冬之口说出让张思远回京的理由,另一方面通过张思远大量的心理活动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焦虑,这两方面共同的理由就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叙述者调和了两个身份之间的矛盾,使叙述趋于理性化。这三个声音构成了紧张的张力关系,互为交叉限制,却不失各自的声音,从而突出了文本的复杂性。当然,这种复杂性并不是只靠想象而得来,而是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经验密不可分,并与之产生了“互文性”。革命已经成为王蒙个人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结,这种最初的选择也影响了他对革命历史认知方式。从《蝴蝶》中不难看出,王蒙通过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和合理的叙述方式把革命分为“革命”和“去革命化的革命”,以世俗生活的观念反思了后者,指出了不同时代人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反观同期的“伤痕”和“反思”小说却全部否定了中国的革命历史,缺乏一种理性的分析和思考。《蝴蝶》中所透露出的历史态度和王蒙做的这种尝试性的分析为我们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如何叙述历史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思路。
二、“见证”身份的认同
中国20世纪的新文学作家都有着一种强烈的介入现实的态度,与文学创作中的“俄国态度”遥相呼应,特别是牵扯到一些重大事件或在历史的开裂处,文学的这种承担意识首先要表现为运用各种手段记录这些事件,成为历史的证言,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和内心深处的涟漪。“新时期”以降,众作家纷纷拿起搁置已久的笔开始了潮水般的创作,在“平反昭雪”和“思想解放”的国家意识形态下,其创作的合法性就要来源于对“文革”的控诉,比如,《班主任》、《伤痕》、《爱是不能忘记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这些作品都关注人在压抑、囚禁或隔离下的生活状态,主人公们在荒谬的世界中失去了自由和爱情,人性在那个年代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压抑,由此,“人啊人”的呼喊成为文坛的主流声音。强调文学介入现实、充当时代“记录者”的功能本应是正道,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其自我意识是对生命和灵魂的一种探索,这些应放置在“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等一些抽象的观念之前,如在这些观念之后,不免又成为了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进而又掉进当代某些既定的概念的陷阱之中。显然,当时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不同的是从一种文学体制走向了另一种文学体制,并未实质的反思,这样建构的世界,也许是更加荒谬和非理性的。今天,我们重回八十年代的语境之中,重读《蝴蝶》,文本中虽充满了反思的声音,却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更多了些理性的思考。
洪子诚用“历史创伤的记忆”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而且特别突出“见证”这一身份,④王蒙就是这一身份的持有者,但他“归来”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自己,确认自己,宽容和自省的声音始终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荡,所以,在《布礼》、《蝴蝶》、《春之声》、《海的梦》等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伤感、自由、玄化、释放,同时也感受到了王蒙充满诗意的激情,“新”的王蒙已经诞生。“新”的内核就在于个人对于革命伤感的记忆,《蝴蝶》中的张思远在想到自己激情革命岁月的同时,也回忆起了自己和海云的第一个孩子的死亡以及自己逝去的爱情,海云领着冬冬离他而去,在他遭受批判时,冬冬的两个耳光让他最后的精神支柱也倒塌了,矛盾和伤感的心情溢于言表。“文革”期间,他和冬冬的感情经历了隔阂——和解——隔阂的过程,长期的斗争使冬冬有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这份成熟有点让他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作为父亲的他怀着忧伤的心情走上了上京复职的路。忧伤的记忆内在地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反思,这种反思固然不是血泪般地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构筑了忧伤的情愫和淡淡、合理的反思。
虽然《蝴蝶》的写作具有明确的反思意识,但和1980年代“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叙述不同,它对反思的限度和见证者的身份意识和姿态是有所警惕的。这些见证者主要是指从“文革”走进八十年代的人,尤其是指知识分子,也通常称之为“幸存者”。从当时的“文革”叙事看,这些“幸存者”在为历史提供证词的同时却也摆出了胜利的和“英雄”的身份意识和姿态,正如臧棣所说:“幸存的意识是如此普遍,幸存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幸存的美学是如此体面”,⑤遥想当时见证者的反思和控诉都没有摆脱既定的思维方式,过分注重历史的“开裂”之处,缺乏对历史整体的和深刻的认识,这种“断裂”的反思意识让我们从“一种囚禁生活走入了另一种囚禁生活”,而这恰恰是见证者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意识有所警惕而引起的。读罢《蝴蝶》,小说中对“幸存者”这种身份意识的警惕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小说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进行叙述,但却穿插了张思远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和情境的渲染,这些都构成了另一个“言说者”,起着平衡和限制的作用。比如,当张思远被打成“右派”时,他并没有叙述自己的囚禁生活,反而话锋一转:“我请求判我的罪”,理由就是他对海云和冬冬的愧疚之情,这里一系列“我”的话语充分说明其反思对象指向了自身,这种声音甚至一度盖过了对外部环境的反思的声音,再加上对革命情境的渲染和小山村如诗如画的描写,这些都紧密的缠绕在一起,没有让其中的一种叙述而极端的膨胀起来,作品的叙述范围也只局限于张思远个人的家庭内部,这同样体现了作者谨慎的叙述态度。如果说“鲁迅的深刻处就在于:他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同时洞悉了自身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⑥,那么,王蒙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在“告别”革命的同时,也在告别着自身。
这就牵扯到了促成见证者这种警惕身份的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王蒙对待历史和生活的态度问题。王蒙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话说“红卫兵遗风”》说道:“红卫兵的产生绝非偶然,红卫兵的一套绝非凭空而至,这里不但有历史、社会、文化的根源而且也有人性的依据。红卫兵遗风同样没有也不可能一时绝迹,红卫兵的思想与行为意识仍然保留在一些普通人包括批评红卫兵运动很严厉的人身上。”⑦这种对生活的体察深深地影响了王蒙的创作,在张思远重回山村的路上,他经受了在车厢内来回窜跑的孩子和故意“加塞”的年轻人的羞辱,这些又好像是历史的重演,他想发牢骚,但当想到自己的责任和正在前进的生活,其内心也渐渐平静下来。在作者看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生活本身是相当复杂的,包括荒谬的和理性的,非理性的革命也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既然没有结束,悲剧和荒谬也将伴随,要想摆脱生活的荒谬,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每个人的责任,但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蝴蝶》中所呈现出的见证者的身份意识并不是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而毫不怀疑的接受新的生活,它始终警惕着过去和现在,“在这部小说中,胜利不是与终结有关的历史概念,幸存者也不会经历了苦难而自动赋予英雄和权威的姿态。”⑧
从《蝴蝶》的反思态度来看,其中虽有作者对新生活的警惕,但并没有陷入悲观和消极的氛围之中,因为王蒙知道刚从“废墟”中走出来的人们急需一种希望召唤出自己的主体性,这突出表现在小说的结尾处:“他期待明天,也眺望无穷……他觉得有那么多人在注视他、支持他、期待他、鞭策他。明天他更忙。”王蒙对“见证者”这一身份并不是以胜利者的英雄姿态来取得的认同,而是以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来验证着这一身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断裂与承续之间,王蒙架起了一座“桥梁”。
三、“启蒙话语”的建构
1980年代常常被称为“新启蒙”时期,这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对“五四”时代的想象和重构是分不开的,因为在“新时期”意识的引导下,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的知识分子急需进行自我的身份确认,“五四”的启蒙精神必然成为这一身份认同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新启蒙”意识本质化的过程是以对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历史的批判进行的,因此,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就把那段历史当作一种“封建的超稳定结构”,以至于完全忽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⑨这一点可以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得到印证,比如,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是双重变奏》中说道:“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境地。”⑩这一说法背后的理论支持正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标准,进而回避了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和复杂性,同时又陷入了中/西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身处意识形态中的知识分子却对这一切浑然不知,因此更无法把握现实。
1980年代的现实是中国已经进入或者是被卷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暴露出诸多弊端,而当我们以此为圭臬时,自然迟早会暴露出一系列社会危机,但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所引起的。这时,王蒙说:“人文精神似乎不具备单一的与排他的价值标准,这如人性并不必须某种特定的与独尊的取向。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与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作茧自缚。”⑪王蒙对“人文精神”的阐释不免让我们想起了1980年代的批评话语,从当时的几个文化事件来看,比如,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文化热”、“纯文学”与“先锋实验”等等,它们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仍是一套强大的“启蒙话语”。“话语即权力”,无论是“人道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的人的否认,还是“纯文学”对政治性写作的排斥,都构成了另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文化思潮的理论也变为了一种“认知装置”,不符合这个“装置”的散布系统根本无法进入它的内部。所以,这一套“启蒙话语”无法对现实处境建构起话语,在王蒙看来,也谈不上“人文精神”。那么,王蒙想用一套什么话语来言说1980年代的现实呢?从《蝴蝶》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痕迹。
从《蝴蝶》整部小说的情节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叙述纬度就是表现在张思远和冬冬身上的父子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张思远与海云的爱情悲剧让冬冬的童年生活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第二,“文革”期间,冬冬对张思远进行的肉体打击让张思远产生了精神裂痕;第三,“文革”结束后,两人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分歧,父子和解后,第三个冲突成为主要矛盾,如何化解这个矛盾应是王蒙所极力展现的,因为这个矛盾牵扯到经历经验教训后把握现实的方式。冬冬生于1950年代初期,正可谓是“红旗下的蛋”,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却成了“不相信的一代”,冬冬与张思远的对话足以证明这一代人的精神结构,为了突出这一特征,作者在小说中有意设置了一细节:“冬冬发现有一株山楂树上竟有五颗鲜红的果实没有被摘走,他捡起几块石头去击落那幸存的红果”,句中的几个核心意象极富隐喻特征,这也预示着张思远与冬冬之间的隔阂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两人各执一套言说方式,张思远认为冬冬这代人缺乏历史感,害怕悲剧重新上演,而冬冬却认为张思远这一代革命者的启蒙姿态太高蹈,自身的历史性过于强烈,张思远以沉默的方式承认了冬冬说的这些话,同时通过与秋文的告别也让他意识到用一种生活方式来否定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不足取的,同样也可以导致悲剧的发生,应当承认生活的差异性、多样性,这可以看作是王蒙的“夫子自道”,其与1980年代宏大的“启蒙话语”显现出了别样的声音,因为王蒙对于现实的把握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言说方式。
两代人的隔膜让张思远的“启蒙话语”在冬冬身上失效了,有意味的是,张思远并没有从“启蒙者”转变为一个“孤独者”,而是以“见证者”的身份在他们之间建起了一座桥,因为“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见证便是他的心,便是张思远自己”。鲁迅曾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⑫“五四”时期,在鲁迅与传统之间,与现代之间,与启蒙知识分子之间,与普通民众之间,与青年人之间,他称自己为“中间物”,这种“中间物意识”成为鲁迅介入现实的认知方式,继而形成了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中间物意识”也为我们理解“桥”的意象提供了莫大的启示。在小说的结尾处,王蒙设置了“桥”这一涵义丰富的喻体使张思远找到了把握现实的方式——发挥“桥”的作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崇高与世俗之间,在理想与幻灭之间,在启蒙与孤独之间,在王蒙看来,沉醉于任何一方面都是不足取的,“桥”正是这两极之间的“连通器”和“缓冲区”,为了使悲剧不再上演,现实生活需要这座“桥”,“桥”的意象也构成了王蒙的一套“心灵符码”和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话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蝴蝶》的再解读,我们可以看出王蒙对革命历史的理性分析和叙述,自身历史性的警惕以及把握现实的话语建构,他的这套言说方式和思路为我们打开其文学创作和生活哲学的“原点”提供了话语资源,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或“开裂”处,如何叙述历史,如何走进当下的现实不使历史重新上演,王蒙的经验和理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思路。
注 释
①李扬:《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②陈骏涛:《发觉人物的内心世界——王蒙新作《蝴蝶》读后》,《文汇报》1980年8月27日。
③何西来:《探寻者的心踪——评王蒙近年来的创作》,《钟山》1983年第1期。
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⑤臧棣:《霍拉旭的神话:幸存的诗歌》,《今天》1991年第3、4期合刊。
⑥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⑦王蒙:《话说“红卫兵遗风”》,《王蒙文存》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8页。
⑧洪子诚:《“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⑩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⑪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 5期。
⑫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NCET-10-0721)成果。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