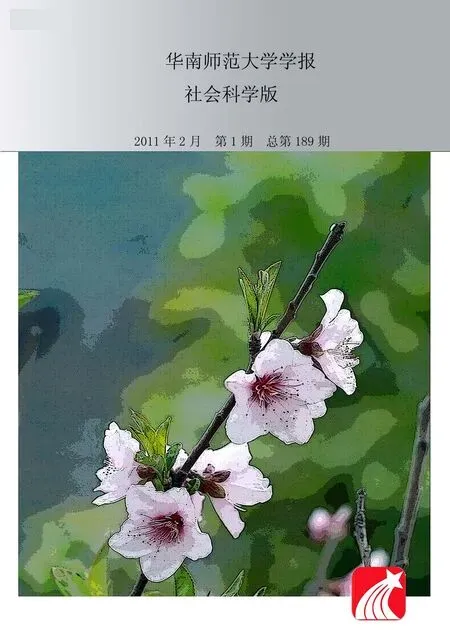北宋熙丰名臣致仕文学研究
吴 肖 丹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宋代“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注]赵翼撰、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五《宋制禄之厚》,第5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致仕官待遇优厚,生活闲适。士大夫处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架构下,又“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注]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第2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们的致仕具有别于前朝的特殊意义,是士大夫由实践政治理想转入回归个人空间的特殊方式。自太宗以来,取士重视年龄,用人注重“老成”,“崇老”的文化对于致仕官而言也是一种有利氛围。在熙宁、元丰的特殊政治条件下,这些特点更是得到充分体现。北宋文学的繁荣,熙丰与元祐都是重要的阶段。[注]萧瑞峰、刘成国:《“诗盛元祐”说考辨》指出从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和艺术质量等方面考察,“诗盛元祐”说难以成立。见《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议论争煌煌”的朝论固然是宋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延续,而熙丰致仕官回归文人身份,追求理趣、归于平淡以及崇尚老美的创作,则无疑对这一时期乃至下一阶段文学成熟有深刻的影响[注]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指出追求雄豪奇峭而归于平淡隽永为北宋变革时期文学思想,以追求理趣和老境美为北宋成熟时期文学思想,而两个阶段交汇于熙丰时期。见该书第80-83、112-121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一、北宋致仕制度述略
官员退休古称“致仕”、“致政”或“休致”、“休退”。《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致仕制度始于秦汉,逐步完善于隋唐。宋代推行祐文政策,“朝廷以恩遇老臣,无所不厚”[注]苏辙:《文彦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泽诏》,《栾城集》卷三九,第7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致仕制度“完成了从礼到法的转变”[注]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第41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主要制度如下。
(一)承袭官员年满七十致仕的惯例
神宗朝“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礼见于经,而于今成为法”[注]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第139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官员经所在州府上表、札,普通官员经吏部审查合格、中高级官员直接由皇帝或中书审定后得到告、赦,便可致仕。
(二)致仕官俸禄待遇优厚,规定也更明确

(三)升转官资、荫补、恩例等待遇宽裕
宋代官员致仕时升转本官一级寄禄官资或官阶成为定制,还享受带职致仕和冠带致仕。“古则皆还其官爵于君,今则不然,故谓之守官致仕,惟不任职也。”[注]赵升:《朝野类要》卷五,第5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保证了致仕官的社会地位。荫补、恩例主要照顾上层官员,相当优厚。
此外,宋代一般以道观设宫使、提举、监岳庙等祠禄官,用有官阶、官名而无实际职权的荣誉官位安置致仕官,还有让致仕大臣参听朝政、修书授业甚至复仕的特例。
可见,宋代致仕制度为士大夫退出官场后的地位和经济提供了稳固的保障。朝廷优贤养老,虽不强硬阻止官员恋栈,但士风也以知止勇退、始终全德为重。如开国元勋王彦超带头致仕、真宗时孙冕题诗挂冠皆传为美谈。从制度及当时致仕官的处境看,致仕生活不是黯淡的末路,而是享受纯粹自由的文人空间的坦途。优渥的经济基础、进退自如的心态,使北宋致仕官的文学创作有别于前代,对于北宋文学思想的构成也有特殊意义。
二、熙丰致仕官的文化背景及创作关系
对于宋代士大夫而言,致仕不仅仅是退休、还禄位于君那么简单。在致仕一事上包含了这一时代深刻的“士”的精神。它与士大夫的政治立场、个人修养和人生志趣密切相关。政见不合,致仕是对政见的坚持;勇于知止,致仕是人格完善的一部分;身缠俗务,致仕是回归自我、寻求自由的方式;倾慕老成,致仕官是令人尊敬的群体。要之,致仕生活是人生一种圆融境界的展现。
去掉官僚的身份,回归纯粹的文人学者的生活,致仕是宋代士大夫实践他们进退观的特殊方式。文官制度使文人成为了政治主体,从庆历新政开始,随着道统的复兴,文人的自觉参政意识高涨。到熙丰时期,通变救弊、志在当世的思潮深刻影响了士大夫的主体精神。围绕因循与变法、理财与重义、君子与小人,士大夫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在此期间,士大夫进退洒脱,为公而不为私,行为磊落。一旦政见与统治者所施行的政策相左,往往不会附和行事,尽力而为仍无法实现自己认为有益的主张,则会选择身退:请求外放、调任闲职或致仕。前两者不干主政,也可视为半致仕状态。这种现象在熙丰时期纷扰的党争中不胜枚举。如:欧阳修于亳州任上五次上奏请致仕;熙宁三年,不愿附和变法,六上札子请出知淮颍间小郡,改知蔡州,又三次连章告老;熙宁四年,致仕归居颍州西湖。其出知蔡州时,实已处于致仕状态,自号六一居士。又如王安石嘉祐五年向仁宗上万言书,知“大事不可为”,在母丧后辞官不出;熙宁七年形势转变罢相,一度复出后见事不可为便彻底辞官而去。在熙丰变法中,致仕前在政为敌、致仕后在文为友的现象颇多,也体现了士大夫容美可观的进退观。像元丰七年,苏轼访王安石于金陵,相与唱和,倾慕对方的文才。当然致仕对一些官员来说并非彻底退休,但是士大夫能恰当把握文人优游自娱和心系君国的尺度。如富弼致仕后专注置酒赋诗,但凡“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注]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第1025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在通达的进退观的影响下,熙丰士大夫在政治纷争中能保有较为豁达的心态。他们的致仕文学,用萧散的笔墨升华出高远的人生况味。
在北宋儒学复兴的思潮背景下,主动致仕成为一种群体自觉,体现出超越政治的伦理美学,也是宋代士大夫在人格修养方面对致仕意义的开掘。白居易晚年闲居,以满足的心态写下了大量闲适诗,这对于宋人是一种启发;但从他的《不致仕》看,主动致仕尚未蔚为风气,而致仕的意义也尚未上升到勇于知止、全德圆满的高度。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背景下,致仕关乎道德修养这层意义才被士大夫发掘出来。从欧阳修的《谢致仕表》、苏轼的《贺欧阳少师致仕表》可以看出,“早退以全晚节”(欧阳修《休致》)已在熙宁年间成为北宋士大夫的共识。将人生作为一个修养累积的过程,将修身贯穿整个参政及致仕生活中,致仕阶段人生阅历、学识的积淀尤为值得关注;而熙丰间士大夫的致仕文学也在白居易的闲适主题基础上,开掘出颐养性情、修身乐道的理趣。
对集政治家、学者、文人身份于一身的北宋名臣而言,参政全身心投入,致仕则是恢复文人身份、回归自我。两者只是人生的不同状态,毫不矛盾。在许多鞠躬尽瘁、辗转仕途的文人身上,都有一份复归山林、释放本真的隐逸情怀。陶潜式返璞归真的生活,加上参禅超脱世外的心境,是他们致仕生活的理想,像司马光在洛阳作诗《呈邵雍》:“紫花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陶潜的意义被充分开掘出来,固然是熙丰时期党争纷纭下审美思潮演变的结果,也与士大夫对自身理想中的致仕状态的寻求不无关系。许多致仕官在现实中实践接近陶潜的生活方式,在心灵上去掉官场的限制,抛弃政见纷争,全身心投入休闲和文学创作,追求更纯粹的文学艺术。他们在闲适容与的状态中,创作上更能接近陶潜诗中那种自由自然的精神,而风格也趋于平淡。
北宋崇老的文化氛围浓郁。在政治上,自太宗起,取士便偏爱年长者,唐代那种“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子”的现象在宋代已经罕见。朝廷授命,也倚重资历深厚的老成者。熙宁二年,范纯仁参劾王安石的一条罪状就是“鄙老成为因循之人”。致仕官的地位及待遇也是政治制度优遇老者的体现。在时代文化精神上,“老”代表一种人生境界上的高度自我完善,为注重修身的宋人所提倡。在艺术追求上的老境、老美,像苏轼赞张先“子野诗笔老健”,是超越了技巧的自然笔墨,在表现上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完满境界,体现了宋型文化对人生、艺术经验积累、转化、成熟过程的重视。正如钱钟书《谈艺录》所说“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诗,晚节思虑深远,乃染宋调”。致仕生活处于人生的最后阶段,最宜于表现表现艺术的老境。才思情感虽然不可避免受自然力限制,但经过长时间创作锻炼,艺术经验却达到人生的巅峰,宜于作艺术总结,像王安石归隐后诗歌从深折透辟走向深婉不迫,正是艺术精进的典型。北宋崇“老”的文化氛围也与致仕官的地位心态相关。在优渥的待遇下,致仕官是一个为人尊重艳羡的群体,他们对社会有不小的影响力。像文彦博等召开“洛阳耆英会”,赋诗绘像,“好事者莫不慕之”[注]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三《文彦博传》,第1026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又如陈尧佐诗曰:“白发光阴得最多”(《年八十致仕》)。致仕官的怡然自得心态,也丰富了“老”文化的积极内涵。
三、熙丰名臣致仕文学与成熟时期的文学思想
文学创作在熙丰致仕名臣的生活占有重要位置。文学是他们连结同道的桥梁、性命所系的功业和慰藉心灵的寄托。进退的通达、修身的谨严、旨趣的天然、审美的老成,使他们的致仕文学不仅局限于白居易式的闲适自在,而是以儒学复兴以来的气格、悟道修身的真淳和他们特有的人生积累,展现出恰如其身份的平淡之美、理趣之美和老境之美。与他们参政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格相映成趣。论北宋文学,常以“元祐”为成熟时期。实际上,熙丰间作家转向人生问题的内省,对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追求,在致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作中已导先声。这是文学思潮连贯发展的现实,也与致仕官所处的人生阶段特点不无关系。下文将以数个案例试加剖析。
(一)洛阳怡老诗会的理趣
致仕官正式的结社唱和,自白居易组织“九老会”、庆历七年杜衍五老会后,在熙丰间出现了一股热潮,并且在组织和主题上较前代有所发展。这些诗社主要由聚集在洛阳的旧党发起组织。熙宁二年新法推行后,退居洛阳的致仕官富弼、赵丙、到西京御史台编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以太尉之职留守西京的文彦博和理学家邵雍、程颢、程颐等人与其他北方故家官僚频繁唱和,形成独特的致仕诗人群。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指出这些诗社形成的文学团体构成了足以与政治中心相抗衡的文化重心。这些怡老诗社实际上是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实践“诗可以群”传统、连结同道的方式。虽然他们的创作有意疏离政治,旨在怡情求真,但是他们的活动及诗歌主题却浸染了北方故家士大夫最为重视的道德色彩。其活动主要如下:
元丰三年,文彦博发起的洛阳五老会,据《五老会诗》注成员有范镇、张宗益、张问、史炤。
元丰五年,文彦博发起耆英诗会,于资圣院建耆英堂,由郑奂画十二人像于妙觉僧舍。据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参加的致仕官有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赵丙、王慎言,还有文彦博、刘几、冯行已、楚建中、王拱辰、张问、张焘、司马光,于富弼宅第治酒赋诗,“尚齿不尚官”。
元丰六年,文彦博又邀程珦、司马旦、席汝言办洛阳同甲会。同年,司马光发起真率会,“以年德为贵”和“以道相高”,立下“为具务简素,朝夕食不过五味”等强调简朴的会规[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二,第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在箪食瓢饮中领略率真精神。真率会活动频繁,参加者主要有司马旦、席汝言、王尚参、楚建中、王慎言等[注]司马光《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步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诗题交代了参与者。,组织随意。
除诗会外,洛中致仕士大夫还有多次唱和,其中一次盛大唱和就是和邵雍的《打乖吟》诗。
这一系列洛中耆宿诗会为宴游唱和创新了组织形式,以年长、道高为贵,突出了洛阳世家文人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他们的唱和诗歌也是紧扣真、道等主旨,格调端正平和,契合名宿大儒气质;而致仕生活的闲适疏放,使这些唱和诗歌在致道中增添了生趣。像司马光的诗“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经春无事连翻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追随任尘甑,歌笑忘霜髯”[注]司马光《和潞公真率会诗》、《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步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其二、《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诗二十四韵书怀献留守开府太尉兼呈真率诸公》。,这样的诗句在他的集子中是难得的轻松自然之作。而致仕官们也为自己的身份、唱和感到荣耀。像文彦博《五老会诗》:“如今白发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绶人。”《耆年会诗》云:“垂肩素发皆时彦,挥麈清谈尽席珍。”这些唱和,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突出返璞归真、天然平淡的旨趣。像文彦博作《闻近有真率会呈提举端明司马》指出“率意从心各任真”、“务简去华方尽适,古来彭泽是其人”;王尚恭《耆英会诗》指出“服许便衣更野逸,坐从齿列似天伦”;张问《耆英会诗》赞赏“清闲几席同禅院,山野巾裘似隐沦”,都是强调悟得真淳朴淡旨趣之乐。他们赏识邵雍“高趣逍遥混世尘”(吕希哲《和打乖吟》),正是对能在日常悟道、并于平淡的生活状态中获得真趣的人生的肯定。这也是致仕官们所追求的境界。熙丰致仕名臣以诗社群聚的方式结合同道,从志趣相投的唱和中获得精神的超脱和愉悦;而注重道德修养和对真淳朴淡旨趣的追求。这对于文学思想的发展无疑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们的唱和引起了当时诗坛的普遍关注以及后代文人的追慕,宋人笔记对此记载尤详。[注]仅宋人记载就见于叶釐《爱日斋丛抄》、洪迈《容斋四笔》、胡仔《渔隐丛话后集》、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葛立方《韵语阳秋》等
(二)欧阳修颍中修文的平淡
对以文学为毕生事业的致仕官而言,全身心投入前期创作的整理、修改、总结以及记录人生阅历是他们致仕后的重要生活内容。他们的这些活动影响到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面貌。浅见洋二指出:“在一个作品从草稿状态走向定稿的过程中,文集的编纂也成为其中的一环。”[注]朱刚译浅见洋二著:《“焚弃”与“改定”——论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载《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3期。改定作品、编纂文集的自觉饱含了作者对自身文学地位的重视和对作品流传的期待。熙丰间欧阳修通过乞请致仕、争取时间修改整理文集、撰写笔记就是一个典型。
相对于留在繁华的两京,欧阳修选择了宁静的陋邦安养晚年。他致仕前几年已处于过渡致仕状态。皇祐元年他自请改知颍州,萌发致仕终老于西湖的念头;治平四年赴亳州上任又取道颖州,为归老作准备。在亳州任上,沉醉佛学、老庄的他心态已与致仕无异,于九月作《归田录》序并开始撰写《归田录》。“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以笔记小说这种轻松的文体总结政治生涯。熙宁二年,《集古录目》凡跋三百九十六篇、《欧阳氏谱图》撰成,则是对一生学术收藏的总结。熙宁三年,他更号“六一居士”,向往提前致仕。熙宁四年,六十四岁的欧阳修归隐颍州西湖之滨,与儿子们一道修订旧稿,编纂成《居士集》五十卷并撰写了《六一诗话》,对一生的文学创作及艺术理论作了完满的总结。
欧阳修致仕前的准备和致仕后的活动,都紧紧围绕文学这一事业,带有明显的总结色彩。即便是创作,也是择取了笔记这一简单灵活的文体,契合他致仕归隐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相对于他蕴含“六一风神”的散文,这些笔记更加平易简洁,淡无痕迹,有情感消褪的因素,也折射出居士生涯的枯寂平和。这种境界,无疑对追求平淡的文学思潮有所启示。《归田录》序成于蔡州任上,编撰定稿在归颖后,择材“掩恶扬善”,少了批判的年少气盛,而是以宽厚平和的心态颂扬士大夫的道德伦理美,像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曹彬“仁心爱物”,多用白描手法,不事雕琢,笔墨简远。致仕后写成的《六一诗话》把读诗感受、写诗体会、诗歌名句与掌故辑录成册,“集以资闲谈也”,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体制。而正是这种非严格的文学批评,体现了欧阳修对平淡自然的一贯追求。作为文学评论,他的分析具有客观性又有感性的体悟,组织结构有很大的随意性,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作为随笔散文,有深中肯挈又形容绝妙之语,但又平易简洁。不作高深的理论,连早期的曲折俯仰也消解。这样的笔墨,抒写致仕官闲适的心境,也适合为一生的艺术经验做总结。
欧阳修致仕后所享的光阴只有一年,但从他致仕前的准备,可见出北宋士大夫对致仕生活以及自身文学成就总结的重视程度。从早年对平易畅达文风的不懈追求,到晚年择取笔记作为总结,愈见平淡精神的延续。
(三)王安石钟山诗歌的老境
相对于欧阳修致仕后的短暂光阴,王安石致仕后隐居钟山十年,潜沉探索,锻炼出了老成精妙的“王荆公体”。王安石欣赏张籍的诗歌“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他的诗从咏史翻案到写景遣兴,从诸体兼备到精炼绝句,将前期深折透辟的诗风转化成深婉不迫,也是一个将诗歌艺术和学养智力的发挥提升到达至“浑漫与”状态的过程,其致仕后“精进”的艺术*古人多有论及,如《漫叟诗话》云:“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石林诗话》云:“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造词用字,间不容发。”,正是老成境界的体现。
王安石晚年诗,尤其是山水诗,虽近于唐音面目,却是以宋人思维将唐韵了无痕迹地化为己用,包裹宋调的精思,追求艺术的化境,呈现出深厚的人生、艺术积淀的老美。王安石在宋调老成境界方向上的追求,上承梅尧臣,下启黄庭坚,造语平淡的诗歌不让梅、黄。自熙宁九年提早开始致仕生涯后,面对宦海的沉浮、爱子的去世、门人的疏离,参禅学佛、登临山水、吟咏诗句是王安石获得超脱的多种途径。他拜相时存念“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比生”;致仕后心态是执着与自适并存,矛盾与超脱交替,使他宁静澹泊的诗歌有着更丰厚的内涵。像《北陂杏花》“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宋诗精华录》以为“恰是自己身份”;其他如《杖藜》、《独山梅花》等,吴之振指出“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于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以其抱负,致仕后的王安石不能彻底忘怀世事;以其胸怀,他的自遣具有深度,他隐曲的心志使面目平澹的诗句有老成的气度。像他的翻案诗,前期咏史生新警策,晚期如《梅花》一诗化南朝苏子卿《梅花落》,了无痕迹,无论是学养技法上还是心态境界上都堪称老到。
王安石写得精致流转的绝句,则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老成,而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化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描绘王安石致仕后的生活:“蓄一驴,每食罢,必一日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定林而卧,往往至日昃乃归,率以为常。”流连佛寺、注疏《楞严经》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恬淡超脱的心境使他那些色彩明丽、情景交融的诗句能状态传神,又有“远而不尽、近而不浮”的韵味,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南浦》),“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之一),“浓绿扶疏云对起,醉红撩乱雪争开”(《池上看金沙花》),对风物明净可喜的传写老到,心境的老成高远也蕴含其中。沉潜归隐的修养、专心诗艺的锻炼使他的诗将早期的斧凿痕迹一并抹去,笔力传神老迈,如对仗“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题齐安壁》),用字“青山无数逐人来”(《若耶溪归兴》),状物“换得千颦为一笑,春风吹柳万黄金”(《雪干》),篇章“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江上》),皆清新天然又非精深功力不到。
致仕后沉潜归隐,正是宋人老成文化心理在生活方式上的表现;以丰厚的阅历学养为基础,将复杂的心志加以提纯,更造艺术的老境,则是“王荆公体”给予宋诗的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北宋进一步完善的致仕制度给士大夫晚年提供了优裕的生活保障。致仕观念的变化、崇老的文化氛围,使他们的创作呈现独特的面貌。熙丰时期致仕名臣追求理趣、归于平淡以及崇尚老美的创作,无疑是考察北宋文学思想发展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