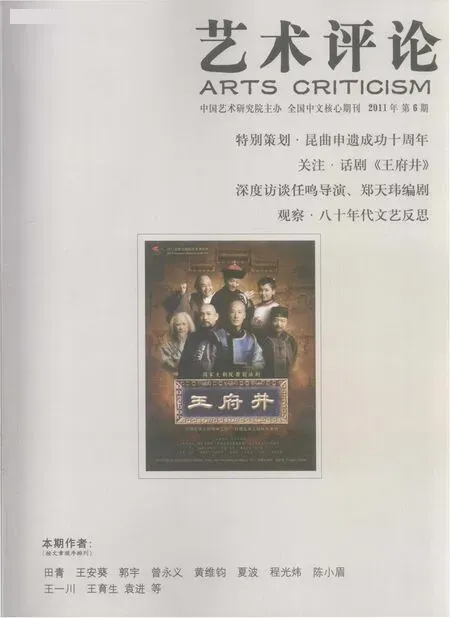正义的回归与民族精神的传承
李鸿雁 熊元义
导演陈凯歌编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对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主要人物进行了人性的深度开掘,挖掘了赵氏孤儿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同与背叛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小人物“复仇”的困境即小人物在遭受戕害后很难找回公道。尤其是电影《赵氏孤儿》对程婴抚养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仍然不能战胜强大的邪恶势力的惨淡人生的直面,具有某种令当代人纠结的悲剧意味。然而,电影《赵氏孤儿》在人性的深度开掘上却没有与时俱进,而是深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风靡一时的“人物性格组合论”的影响,陷入了抽象人性论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人以为只有深刻揭示人在自己性格深层结构中的动荡、不安、痛苦、搏斗等矛盾内容,才能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层次的典型人物。似乎朴素、粗犷和单纯的美在审美价值上远远低于纤细、复杂和矛盾的美。因此,中国当代有些文艺家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即着意表现歹徒的善心、汉奸的人性、暴君的美德。好像只有写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才能表现出全面的人性、真正的人性。其实,文学人物形象是单纯、清澈的,还是矛盾、复杂的,取决于不同时代,很难在审美价值上区分高下。这种人物刻画的中间化倾向不过是这个时代思想危机的产物。电影《赵氏孤儿》对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最大改变就是这种人物刻画的中间化,一是英雄人物程婴等不再高不可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悲剧人物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没有主动挑起悲剧冲突,悲剧冲突主要是邪恶势力屠岸贾引起的。也就是说,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即置身屠岸贾赵盾两家的矛盾和冲突之外,但是他们却毅然决然地卷入这种矛盾和冲突中。电影《赵氏孤儿》则改为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被动地卷入屠岸贾赵盾两家的矛盾和冲突中,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他们救孤的壮烈行为,以至于程婴忍辱负重地抚养赵孤只不过是出于为自己的儿子报仇这种狭隘目的。二是邪恶势力屠岸贾不再十恶不赦。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邪恶势力屠岸贾不但出场就是坏蛋,而且越来越坏。电影《赵氏孤儿》则改为屠岸贾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一个狠毒与慈爱并存、斩草除根与舔犊情深同在的枭雄,并为屠岸贾的残酷屠杀进行了开脱,“他为什么杀赵家三百口人?因为赵朔夺了自己的兵权,抢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屠岸贾的残暴行为,以至于屠岸贾在已知养子赵氏孤儿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还多次放弃杀死他的养子的机会。
电影《赵氏孤儿》这种所谓“人性深度”的开掘不仅消解了中国悲剧精神,而且忽视了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这部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作品在塑造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上的重要作用。显然编导认为程婴用亲生孩子换取其他孩子的生命是违背人性的。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在人类历史上,不少先烈的牺牲都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别人的生命。如果认为这是违背人性的,那么,这些先烈的牺牲就是没有价值的。在邪恶势力肆意践踏无辜的生命时,人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是岂因祸福避趋之?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自觉救孤不仅是拯救一个无辜的小生命,也是对邪恶的坚决拒绝和对正义的誓死捍卫。如果人在邪恶势力的横行面前放弃坚守,那么,正义在这个世界上就丧失殆尽了。在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在邪恶势力横行面前没有闭上眼睛,而是前有程婴、韩厥硬踩是非门和担危困,后有公孙杵臼在遇着不道抽身后转身和献身。“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在这种非常险恶环境中挺身而出拼命救孤就不仅是为了“复仇”,也是为了铲除奸贼和伸张正义。因此,赵氏孤儿的“复仇”就不是狭隘的“冤冤相报”,而是正义在遭到践踏后的回归。而在电影《赵氏孤儿》中,程婴抚养赵孤长大仅仅是为亲子报仇雪恨,就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复仇”肤浅化和粗鄙化了。
其实,抽象人性论是不可能完全把握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有人指出,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不如英国悲剧《哈姆雷特》具有人性的深度,认为《赵氏孤儿》的赵武在明辨正邪方面总有着太清醒、太冷酷的认识,在人性方面却似乎有所欠缺。相比较,英国悲剧《哈姆雷特》的哈姆雷特背负着杀父之仇,但他的左思右想、延宕不前,反倒让人觉得性情丰满,这或许正是《哈姆雷特》更为贴近人性的所在。这种对中国悲剧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1912年,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在系统把握元杂剧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王国维这种对中国悲剧的发现无疑是中国近现代人对中国悲剧认识的高峰。而中国当代人不但没有在这种高峰上更上一层楼,反而退步了。
其实,中西悲剧的差别不是绝对的。如果全面比较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佩斯》,那么,就可以看出中西悲剧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赵氏孤儿》和《麦克佩斯》不但在结局上基本相同,即都出现了后代复仇并战胜对方的结局,而且都是权力欲望膨胀引发的悲剧。有趣的是,他们二人都无后人。即使他们夺得天下,也不可能传位后人。麦克佩斯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才挑战命运的安排而走向毁灭;屠岸贾虽然没有这种担忧,但他收养赵氏孤儿,却是自种祸根,自掘坟墓。这虽然是外在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屠岸贾也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是,中国悲剧没有选择屠岸贾为悲剧人物,这样悲剧冲突就不在悲剧人物身上展开,而在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之间展开。因而中国悲剧就出现了与西方悲剧很不相同的面貌。《赵氏孤儿》是以一系列的自我牺牲的英雄人物为悲剧人物的,而西方悲剧《麦克佩斯》则是以制造血腥灾难的麦克佩斯为悲剧人物的。如果《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和《赵氏孤儿》的悲剧人物一样,以邓根、班戈及其后代为悲剧人物,那么,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中国古典悲剧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反过来,如果《赵氏孤儿》的悲剧人物和《麦克佩斯》的悲剧人物一样,以屠岸贾为悲剧人物,那么,中国古典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就具有相同特征了。中国悲剧对邪恶势力的否定,主要是来自外在的正义力量,是一种外在否定。中国悲剧的邪恶势力是不会自我忏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屠岸贾就没有麦克佩斯的困惑和犹豫。而西方悲剧对邪恶势力的否定则主要是来自悲剧人物的身上的善良力量对罪恶因素的否定,是一种内在否定。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是深深地反省自我,对自我的罪恶进行了扬弃和批判。可以说,《麦克佩斯》和《赵氏孤儿》最根本的不同就是选择悲剧冲突以至选择悲剧人物的不同。虽然《麦克佩斯》的悲剧冲突是在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之间展开,但是这种悲剧冲突不仅表现为外在的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较量,而且表现在悲剧人物内在的善与恶、忠诚与背叛的对立和消长上。麦克佩斯的叛逆的野心是跟麦克德夫和玛尔康的忠义和爱国心冲突的:这就是外部的冲突。但是这些力量或原则同样在麦克佩斯本人的灵魂中冲突着;这就是内在的冲突。仅仅有一种冲突是不能构成悲剧的。在《麦克佩斯》中,女巫的预言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麦克佩斯和班戈后来的命运,而且暴露和刺激了麦克佩斯的欲望。如果说《赵氏孤儿》是被杀的人的后代赵氏孤儿赵武是在一群忠臣义士舍身忘我的救护下得以逃生,那么,《麦克佩斯》则是被杀的人的后代自己意识到了危险而逃走的。可以说,《麦克佩斯》和《赵氏孤儿》在结尾上基本上相同,都是遭到毁灭的人的后代为他们报了仇,雪了恨。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他们即使有缺陷,也不是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之间的彼此较量和决斗上。如果说《麦克佩斯》主要展现了大将麦克佩斯欲望的膨胀,走向邪路,暗杀国王和大臣,那么,《赵氏孤儿》则主要是突出一群义士前赴后继拯救赵氏孤儿的抗争。《赵氏孤儿》虽然与《麦克佩斯》都是历史剧,都有谋杀,都有后代复仇,但是,因为它们的悲剧冲突展开的范围不同,所以,这种谋杀、反抗和复仇就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如果说《麦克白斯》有力地批判了人性的贪婪,那么,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则突出地强调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民族的文化认同这种大义上,赵氏孤儿没有丝毫的犹豫、困惑和矛盾。因此,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不可能像英国悲剧《哈姆雷特》那样充分展现赵武的内心的犹豫、困惑和矛盾。
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清代长篇历史小说《说岳》强调养子的认祖归宗?其实,这种养子的认祖归宗就是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和清代长篇历史小说《说岳》弘扬了中华民族绝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故事已见于《左传》,但较简略,到《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新序》《说苑》才有详细记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基本上依据史实,但情节上有较多改动。如把故事发生的背景,由晋景公改为晋灵公;把孤儿在宫中藏过,改为由草泽医人程婴藏在药箱中带出;把隐居山中的孤儿,改为被屠岸贾收为义子,在屠府长大后杀屠报仇;把在孤儿长大后为他请封的韩厥,改成为放孤儿出宫而自杀;把本为赵盾门客的公孙杵臼、程婴,一个改为原与赵盾同殿为臣的老宰辅,因愤恨昏君奸臣当道而归隐;一个改为与赵家有交情的草泽医生。经过这些改动,不但突出了一群义士前赴后继拯救赵氏孤儿的抗争,而且强调了赵氏孤儿对民族的文化认同。在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不是在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马上告诉他的身世,而是在赵氏孤儿进入书房后,遗下手卷,在赵氏孤儿看了手卷并产生疑惑后,才对赵氏孤儿说明真相。在元代杂剧《赵氏孤儿》中,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也有可能认贼作父,不是报仇雪恨。正如钱穆所指出的:“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诸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奴颜于异族之前。”[2]这就是说,前人的抗争精神能否在后人身上得到延续,不仅要保存后代的生命,还要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这种抗争精神。而电影《赵氏孤儿》则放弃了这种抗争精神的教育,提倡了不把自己的敌人当敌人就没有敌人的天下无敌教育,认为抗争精神的教育是撺掇少年杀人,很不道德。这实际上是默许甚至鼓励赵氏孤儿认贼作父。电影《赵氏孤儿》虽然把赵氏孤儿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尊重赵氏孤儿的成长和选择即让赵氏孤儿自己选择是否杀死屠岸贾,但却割断了赵氏孤儿与赵家的血肉联系。这种血肉联系的割断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古代经典悲剧作品所塑造、传承和弘扬的中华民族精神。
* 黑龙江省文化厅2010年艺术规划项目“当下影视研究”,项目号:10C 023
注释:
[1] 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1-282页。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9页。
——观《程婴救孤》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