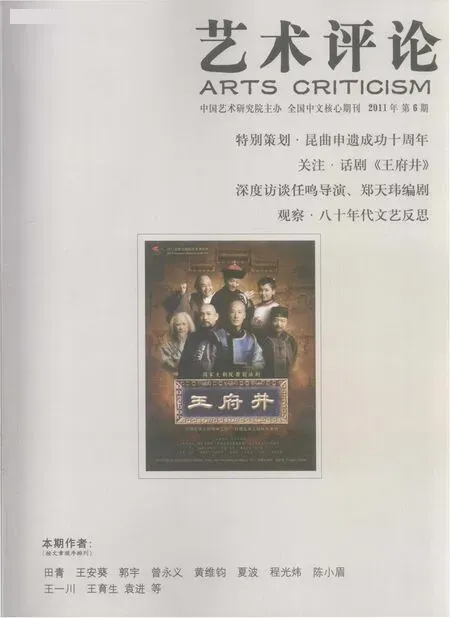重解“应物象形”
姜怡翔
中国传统画论中的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论”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1]“六法”是中国艺术最高准则。然而,理论界对六法的理解却有待商榷。在此先讨论“应物象形”问题。中国绘画一直追求“不似之似”,所以,“应物象形”并不是追求像客体之形的层面,六法是中国绘画的总则,而总则说的即是中国绘画所追求的目标。
在民国初,康有为于1904年游历欧洲后,认为中国画疏浅,“彼则求真,我求不真,而我遂退化”,远不如西洋画。之后,他的学生徐悲鸿,对中西画的融合落实到写实的点上。徐认为中国绘画:“写形不准,少法度,指少一节……无论童子,一笑便老,无论少艾,皱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等,此种偏见,完全出自西方的审美标准。徐悲鸿想要改变“六法”的品评,在1932年提出了“新七法”,其要点为:一位置得宜,二比例准确,三黑白分明,四动态天然,五轻重和谐,六性格毕现,七传神阿堵。以此为基础,中西融合水到渠成。
而中国画的主体内涵并非如此,类似此种理解理所当然地把“应物象形”理解成“形似”,不管“六法”中的“应物”还是“象形”,一并被简单理解为西方写实的“造型”,也即同于西方的观念了,这种理解是出于对中国艺术的浅层字面理解。
《尔雅》云:“画,形也。”《广雅》云:“画,类也。”石涛云:“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2]我们从“应物象形—骨法用笔—气韵生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追求一种生命的活态,从创造“活”的开始,到追求“活”的过程,最后到“活”的境界,即“气韵生动”。所以此“象形”绝非“形似”中“形”的准确,今日所追求的“形似”绝非传统中国画所追求的标准,而此种准确也绝不会列入中国绘画的品评之列。
一、应物
1、感应“物”
中国艺术精神对待“物”,不是物我对立去“像形”,而是主张“天人合一”。《庄子·天地》篇中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也就是说,不执著于物,不执著于自己——忘掉自己,称为与天融合为一。就如庄周梦蝶那样:“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董仲舒认为,天人是同一个生命体,天心(情)与人心(情)的相感、对答之说,其逻辑点便是天人“一贯”的“气”。自然万物之“天”与有情之我“人”之合一。天心(情)与人心(情)的相感,天人同感。在“天人合一”思想模式的影响下,中国艺术形成了以“天人”、“物我”相忘、相容、相混、相合的境界。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
“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的统一,泯除差别,达到人与物的统一与交融。董仲舒认为人的情感的变化同自然现象的变化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存在着某种“以类合之”的思想。并把这种关系称作“同类相动”[4]。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春秋代序,阴阳舒惨,物色之功,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在这里说明了四时不同季节的变化同人的情感变化的对应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了“物情相动”,即“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情以物兴,物以情观。”[5]这是心与物之间的“物我冥合”、“心物感应”,是“心意”与“物象”的妙合,“意”对象化了,“物”情感化了。“应”物实为“感应”于物。
2、与“物”宜——与“物”无对
《周易·系辞上传》云:“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其物宜”,是讲与物相宜,而非描摹物的形。董《广川画跋》云:“无心于画者,求造化之先,凡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6]无心于画者或无心于物者,方能“与物有宜”,才能得之“自然”。郭象《庄子注》提出“与物无对”。郭象注“尧让许由”章说:“夫自任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夫与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离也。是以无心玄应,唯感之从。”(《庄子·逍遥游》注)
“与物无对”的要点为,无心则与物冥合一体,无心则循顺自然。“与物无对”也即同于庄子《养生主》提出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杨雄曾提出“见不见之形”,王弼提出“物物而不累于物”,到了支遁那里,这个思想进一步换了一种说法为“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物”与“不累于物”,是超越具体的实物与具体的无本身的形,而“物物”又要“于物”,是指“于物”而“迁想妙得”,“遗忘己象者,乃能制众物之形象也。”“应物”乃忘掉物本身的具体实像,强调不拘于物体本身。
“放意”而“无心所得”,不执著于具体物,也就是说不以眼睛具体地去实对,而是凭内在的感觉把握对象。“应物”实则是“象其物宜”,而“顺物”乃是不执著与物而“与物无对”。
3、“异类而求之”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周易·系辞上传》)。这里都说的是,不执著于物象本身,象要通过与他物的比拟、象征并感觉物象而引申与物象感觉相通的想象,即“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正义》):“谓触逢事类而增长之。若触刚之事类,以次增长于刚;若触柔之事类,以次增长于柔。”又曰:“天下万事皆如此例,各以类增长,则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尽。”张怀《书断》云:“善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故不取乎似本,而各挺之自然”。“故不取乎似本”,而是“备万物之情状。”[7]这里是指感受万物的性情于状态,不是表象的形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情理和态势,取与眼前之物相“类”的感觉,“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皎然的《诗序·序》:“静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不是被动描画客观自然本身是什么,而是用“心”感悟客观物与“他物”的类同之处,即“故不取乎似本,异类而求之”。
所以真正的艺术品不是对客观自然的模仿中创造出来的,它是艺术家自我与自然神遇的结果,正如孙过庭所言:“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孙过庭《书谱》)中国书法讲如“担夫争路”、“如策马之用鞭”,书家在抽象的线条与具体的可感物象之间寻求一种对应关系。中国艺术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是取其“意”,感物之“性情”。而“应物象形”并非像“物象”本身之形,而是“异类而求之”。这种在自然中体会的是生命的过程。所以就不局限于针对与具体的物质性的相像或某个典型性的综合了。
二、象形
1、象其——形容
《周易·系辞上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是故谓之象”。在《淮南子·要略》中述及《说山训》的主要内容时说:“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即取象时,联系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形状,从而领会人世间事物要义。
东汉蔡邕指出:“凡欲结构字体,皆欲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水,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蔡邕所说的“像其一物”,所指即是情状与感觉的相似。他在《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失,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蔡邕的“形”说的是“法象于物,成象于形”,像自然之物的情态,自然之形的感觉,物、形、态皆活,物具有了人的情感与生命。中国艺术就在这有态、有意、有情的过程中体验着这“若……若……”的感觉,并用“若……造型”或训练有素的“笔法”来表达自己,这“若”便具有了象征之意。
“纵横有可象者”并非象自然物之形状,而是形容一种主体的感受,并用有生命的形式表达。“若”是指“好像是,不是模仿,是“度物象而取其真”,也即“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周易·系辞上》)。在自然万象之百态中寻求与内心需求相契合的东西,是对万物情状的感觉。我们在现实中获取的是情感、感受,而不是物质。
虞世南《笔髓论·叙体》说:“仓颉象山川江海之状,龙蛇鸟兽之迹,而立六书。”文字是靠象“状”与“迹”创造出来的。这种“象”并不是模仿其形,而是感觉与迹化,正如石涛说:“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虞世南在《指意》中进一步说:“用笔须手腕轻虚”。虞安吉云:“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成书邪!”这是告诫书者,抛开束缚,舍形取神,不能陷入追求物形的“象本”,拘泥于物的原本形状中。
2、象形之目的——像生命的存在
“象形”是见“性情”而不见“物质的实像”,不徒得形貌,而得物之生命。邹一桂“八法”中,讲“笔法”云:“笔笔非笔,无一率笔;笔笔非笔,俱极自然。……花心健若虎须,苔点布如蚁阵。用笔则悬针、垂露、铁镰、浮鹅、蚕头、鼠尾,诸法隐隐有合。善绘事起于象形,又书画一源之理也。”(《墨池编》)有生命的形式也即是在物中感觉到一种生命性的存在,并通过一种形式语言表达出来,这种形式亦具有生命性。
首先是象自然生命形态的感觉,这种形式存在着一个生命体的完整过程。所以称作“有生命的形式”。书法中讲的是“起笔、行笔、收笔”,朗格认为“把这些内容传达给我们知解力的就不是相关的信号而是符号形式”,并为艺术下了定义——“艺术即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8]
艺术家需要从不同的事物之中寻找和表现它们生命感觉的等同价值。在山水画的传统技法中,着意画树时画家笔下的形迹却是鹿角、蟹爪、雀爪、丁香头、月牙、鼠足的参差结合,画山石时更是借用山石以外其他物形势态的纹理或肌理予以适当表现,即“异类而求之”。 在传统的描法中,画者在勾画每一根线时,都不是为了直接与客观本身相像,也就是说不是去在现实本身寻求对应物。而每一根线自身有独立的生命价值。朗格从抽象与象征的统一来论证艺术:“因此没有必要用生动的词语去‘摹仿’某一事物,以传达生命的现象。一件作品的任何元素(指作为符号的线条等)都反映生命的多样形式。”在这里由客观的物形升华为一种“象”,感觉到的是物的情态、物的生命,而创造出的形式也便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要注意从不同的事物之中寻找和表现它们的等同点,“例如,当诗人吟诵出‘燕子像剪刀似地掠过天空’时,他实际上已经在一把锋利剪刀和一只在天空中迅疾飞过的燕子之间找到了共同点。”[9]
综上,中国美术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和审美标准,但是当下中国艺术发展仍在西方的审美观念及造型体系的“影响”与“观照”下成长,至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与发展,没有自身的面貌。中国美术不应在西方文化与观念中认识与解读中国传统理论,当下急需对传统艺术深入研究,对传统概念进行重新剖析、认识。
注释:
[1]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 石涛:《石涛画语录·了法章第二》。
[3] 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
[4] “……美事召美类,恶事遭恶类,类之相应而起。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同类相动》)
[5] 梁·刘勰:《文心雕龙》,郭金稀注释,岳麓书社2004年。
[7] 唐·李阳冰在《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中说:“缅想圣达立象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转之形……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矣。”
[8]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9]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藤守尧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