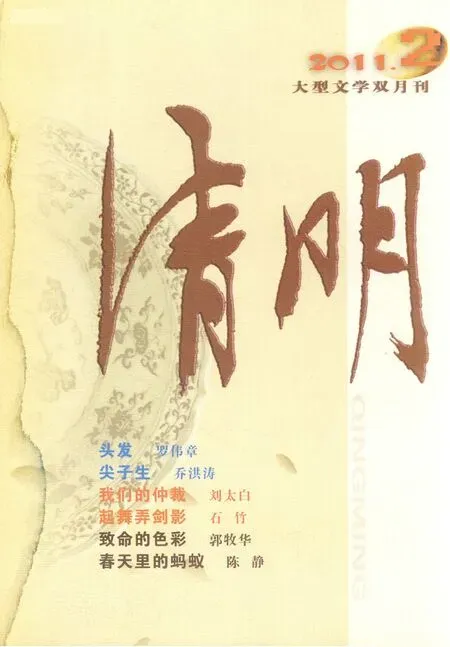回到常态:走出诗歌囧途
杨四平
回到常态:走出诗歌囧途
杨四平
新世纪刚刚过去十年,新诗创作并非如人所愿地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用谢冕的话来说就是期待中的诗歌奇迹还没有出现。现在,人们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诗在囧途,给力予诗。在此,我将从积极的建设性层面,探寻破解走出诗歌囧途的难题。
价值虚位、悬浮、游移,是制约当下诗歌发展的最大难题,也是当下诗歌乱象丛生的首要原因。也许有人又会说,我只管写,至于写什么,那不是我的事;于是,不少诗人成了“写奴”,制造了大量不知所云的分行呓语,力求在这一大堆脆弱的分行呓语上,构建一个自我陶醉的通灵者神话。当然,也有不少富于激情的诗人,关心国计民生,把写什么视为诗歌写作的一切,把题材选择等同于价值判断,至于如何去写,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于是,他们就被贴上了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底层生存写作”、“打工诗歌”、“地震诗歌”等看似有效的标签,殊不知,这类反“天启神话”的写作,其实也在构建一类“题材诗歌”的现实神话。总之,以上这些写作都没有很好地调适诗歌自主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良性关系。而这里的刘春、十品、张敏华,以他们朴实的写作,努力修补诗歌自主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裂缝。他们既没有故作姿态、以玄说玄,又没有为现实所困、深陷琐屑。他们能够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找到平衡点,而没有犯厚此薄彼或非此即彼的毛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走“天启诗歌”、“题材诗歌”的老路子,而是在走“常态诗歌”的路子。
所谓“常态诗歌”,就是诗人面对生活、自然、世界、国族、自我、人性、个性、艺术、写作、诗歌、语言,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常态地看待一切,不把它们“崇高化”、“崇低化”,当然,更不能把它们“庸常化”,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点,素朴地呈现出它们的本色。因此,我认为:诗歌写作的难度,不是堆砌事物的知识,不是调高技术的指数,更不是在话语上玩耍“弯弯绕”,而是回到事物的起点,回到最简单的技法,回到最透明的语言;平常而不平庸!
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刘春、十品、张敏华的公民意识以及回到诗歌写作常态的价值取向。他们首先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然后才想起自己是一个写诗的诗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自己划出普通人的范畴,没有把自己另类化(英雄化、低俗化)。比如刘春的《偶得》,把高傲伟岸的大王椰与腰身低矮的棕榈进行并置,然后在外在高大与内在强大的比照中,诗人像常人那样作出了自己的常态的价值选择:要做“一个灵魂站立着的人”;而这种价值判断不是那么简单就给出的,而是在诗人对现实、对自我进行了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才作出的,因为他说:“我曾抱怨尘活的折磨/感觉人生无趣,对现实思忖太多”。这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呢喃软语,而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大实话,却写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经验与心声。这里既有知识和技艺,又不只是知识与技艺,而且知识与技艺退到了诗歌的背后,诗歌的前台上尽是平常人的平常事和平常心。正是有了如此朴实的情怀,所以刘春愿意揣测“下禾村的何七妹呆在草垛边/把初春的心事缠了又缠”(《下禾村》),能够对“一个两岁的孩子”在纸上画月亮的全过程产生浓烈的兴趣(《纸上的月亮》),还能够对那些最不起眼的小小的冬菊在“生命的淡季”勇敢怒放表示赞许(《雏菊》);还有,张敏华能够对一个离异女人的单身生活表示出了同情的关切,把女人还原成普通女人来写,而不是像通常的女性诗歌那样热衷于写女性的强悍,毕竟现实世界中女强人不算太多(《善良》);而且她也能够对自己邻居的生活处境和精神贫困表示出邻居性的道义关怀(《邻居》)。这些都是一个普通公民应有的责任担当。
当然,关切现实,还原现场,并不意味着认同现实、认同世俗。“常态写作”不同于以往的“原生态写作”仅仅满足于在诗中尽情地展示鸡零狗杂、吃喝拉撒、一地鸡毛;它要在现场、事实面前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与评判,正如刘春在《黑暗中的河流》里写到的:“芦苇——这些有思想的头颅/对尘世不拒绝、不随从”,这里的“不拒绝、不随从”就是指既要直面现实又要与现实之间保持理性的距离,即既在现实中又在尘世外。而我们有不少诗人常常写着写着就忘了这种诗歌写作的辩证法,十分简单草率地处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有时乃至在不知不觉中还扭曲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刘春在《路灯下的草影》就较好地处理了路灯与灯下的影子、我与他、近处与远处、苇岸与梭罗、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复杂纠缠。概言之,要想写好诗,就是要注意对现实保持既开放又幽闭的开阖有度,方能使自己的想象、言说、写作建立在厚实的基础上,方能在不自由的空间里进行自由的飞翔,方能在快慢之间找到匀称的飞翔节奏,如十品的《会飞》和《越来越快》所示。
这种回到初始、回到常识、回到现场的,既不溢美也不嗜丑的“常态写作”,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后,我要以十品在诗中写的:“明知在前方不会有更多的欢乐/我的目的地总是停在我的前方”来结束我的这篇劝勉性的、进言性的短文。
责任编辑 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