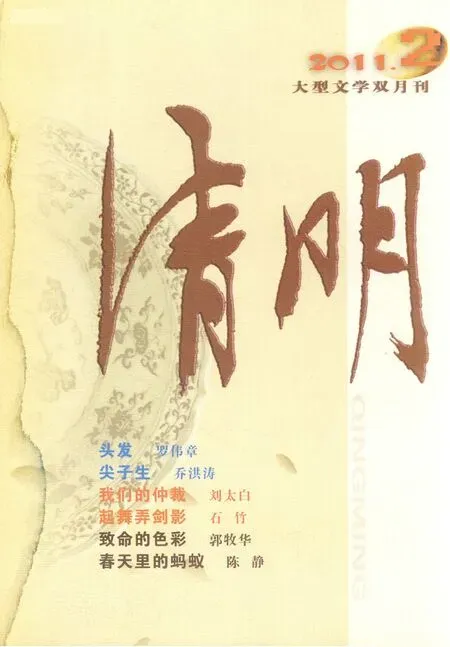妖娆之地
孙建成
妖娆之地
孙建成
船行黑龙江
三十年前,我插队在黑龙江省嘉荫县的荒山老林中,去江边的富饶公社的所在地要走五十里山路。实际上并没有路,在山林和沼泽草甸间,各种车辙杂乱地伸展着,泥浆泛起,树枝横岔。一般去江边,我们会搭乘去拉货的拖拉机。人坐在履带拖拉机后面的爬犁上,要提防不时从爬犁下涌起的泥水和两边戳来的树枝。在晴天,飞扬的尘土把人喷抹成灰人。这一路,步行大约花大半天时间,坐拖拉机却也要三四个小时,因为在途中几乎还少不了陷车,以及其他意外的耽误。
过了一个名叫小河沿的地方,下坡,拖拉机一个拐弯,便可以看见黑龙江了。远远望去,江水黝黑,水势沉稳,宽阔的江面泛着乌云似的波光。此地正处在中国版图的“鸡冠”和“鸡嘴”之间的皱褶里,似乎小兴安岭至此突然止步,踉跄了一下,踩出一地碎步。黑龙江在这一段里蜿蜒曲折诡异多变,数百里间,夹杂着雄浑和奇丽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色。在以后的数年里,我多次往返于江上,深深地被它迷人的魅力所吸引。
进入富饶公社的所在地乌云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路两旁夹道排列的参天白杨,那种树枝杆青白,年年在不停地向天上长,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不枝不蔓,不偏不倚,上下一般粗细似的。参天的白杨是一种地标,在苍茫荒凉的岸边,往往几十里地不见人烟,但只要看到有白杨树这么成群结队耸立着的地方,大概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了。
头一回在黑龙江上坐船,是在下乡那年的八九月份吧?和知青同伴去嘉荫县城开“积代会”。
乌云镇在嘉荫县的上游。此处地势平缓,两边大多是平原和丘陵,在船上登高远望,可看到两岸纵深很远的地方。江上载人的客船外表古怪,它的推进系统用的不是水下螺旋桨,而是在船的两翼装了两个巨大的像水车结构一样的轮子,一半浸在水里,一半露出水面。柴油机驱动巨轮缓慢而有节奏地旋转,如划桨一般推着客轮向前。这种船称呼它“水车船”最是贴切。多年后的一天,在好莱坞的西部电影里见到它,马上回想起当年那一刻,恍若身处十八世纪。
人在船上,眺望两岸风景,山、树、人、屋缓缓退行,山绿水黑沙白,天深云厚,江风拂面,静寂如画,有出神入仙之感。江水浩瀚湍急,势不可挡。下水的客船顺水顺风轻盈畅快;迎面交会的上水客船,则是黑烟冲天如牛喘气,船身颤抖,像伤寒病人打摆子。
江对岸是苏联(现称俄罗斯),地广人稀,难觅人踪。船行江中,看苏联近在咫尺,目所能及的建筑物,大都是与我方相对而设的边防哨所。即便是居民点,也很少见人游走,气氛空寂。偶尔,江上漂过苏联人运煤的驳子,船上的水手光着上身在舷边打水,胸前的黑毛清晰可见。寂寞的航行让水手对客船充满好奇,老远,挥手冲我们打招呼。咿里哇啦,不知道在说什么。客船上的反应却没有他们那样热情,许多人站着,默默地看着煤驳子,看着它远去,直到看不见。
客船一路上要停好几个点。枯水季节,江水远离岸边,上船下船要走长长的跳板。许多村民聚在堤岸上看热闹,高呼小叫,犹如过节一般。在船上的人,需抬头仰望,才能看到岸上。也许,这种“水车船”与黑龙江江底的坡度平缓有关,船在靠岸时船底几乎贴在沙滩上,螺旋桨根本无法插入水中……
嘉荫县城,一条丁字路,直线和横线交叉的点上是电影院,“积代会”的大会会场就设在此。我参加过两届“积代会”,会议的内容早已忘了,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吃饭。
在乡下,每天吃的是馒头、高粱饭或玉米饼,外加一碗菜汤,终年不见荤腥和油水。开会期间,早饭有大油条、糖糕和豆浆,中午和晚上是四菜(两荤两素)一汤的桌头饭。很亮堂的饭厅,凑满一桌就开饭,没有人在吃饭的时候聊天,因为稍有怠慢,台面上的好菜就被同桌吃完了。那几天里,坐在会场上,脑子里盼望着会议快点结束早点开饭,早饭吃了盼中饭,中饭过了等晚饭。共产主义的好日子。这种吃法,在插队的那些年里就有过这么两次,后来就再也没有享受过。
自头年打麦子发了两个星期高烧,病后又没有条件补养,我的身体一直很羸弱,一干力气活就浑身虚汗。也许是出于恻隐之心,队里安排我去公社的信用社学习。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份求之不得的美差,没有人会拒绝的,所以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通知我马上去公社报到。
那时候我少不更事,对这一人生道路的变化一点概念也没有,以为只是很平常的出工,做完了还要回来。
就这样,我离开生产队来到乌云镇,住在紧邻黑龙江堤岸的信用社里。这是一幢有着俄罗斯风格的老房子,青砖砌成的墙壁,木制的大窗户,窗户外面的防护板表面墨黑如焦炭,屋檐的挡雨板上雕刻着镂空的花饰,廊沿下还有窄窄的走廊和栏杆。房子高出地面一米多,有五六级木头的台阶。站在走廊上,倚着栏杆,俯看街面上走过的芸芸众生,会有莫名其妙的“高贵”之感……许多年后,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看到其中描写的俄罗斯没落贵族的住所,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幢房子。
这幢建筑白天是信用社对外办事的窗口,晚上就是我的宿舍。同时,我还兼顾夜间值班。由于是金融重地,又与“苏修”一江之隔,信用社特地给我发了一支驳壳枪——电影里经常看到的匣子枪,估计还是抗联时期留下来的,枪身的烤漆早已看不出来,木制的枪把也磨出了木头的本色。和枪一起,还有三发子弹。由于没有持枪证,那枪只能在信用社这个范围内使用。我把枪放在睡觉的枕头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拿出来把玩,把子弹装进去,又退出来,举着枪在房间里四处瞄瞄,嘴里“叭叭”有声,像煞有介事似的……新鲜了几天,很快就玩厌了,驳壳枪压在枕下,再也不去动它。
江边的夜,比大山里空旷,永无止息的流水声成了入睡的催眠曲。从窗内眺望黑龙江,星光下如巨硕的游龙,从上游山影的间缝里游出来,游过白杨树簇拥的乌云镇。水波粼粼是龙身上的鳞片,低沉的涛声是龙的呼吸。人睡在温热的土炕上,宛如枕着江水睡觉,安稳中又有几分异样。
那个年代,乡村信用社几乎没有事情可做。白天闲得发慌,又没有熟人可以聊天,于是我去街上晃荡,街上也见不到几个人,便踱向江边。江边的沙滩上有人,大都是孩子,有的在嬉水,有的在玩沙。还有几个成人,站在浅水里,向江中甩出长长的鱼线,用钩子钓鱼。我寂寥地站在堤坝上,看人、看船、看水。
太阳下,水像墨鱼的汁,黏稠的波纹丝绸般起伏。天空飘过大块大块的云,在江面上投下阵阵阴影,快速地滑动。阳光照在身上,感觉有点温热,舒服得让人昏昏欲睡。江边,几个穿着裤衩的大男孩,大呼小叫地扑进水里,手脚并用拍打着水面,水花四溅,奋力地顶水上游,可不管他们怎么的努力,身体还是一点点地向下游漂去……最终,那几个人在我目所能及的地方,爬上岸来,抖一抖头发上的水,向回走。回到原来下水的地方,再一次扑入水里。一遍又一遍,欲罢而不能。
我看得心热眼痒,跃跃欲试,干脆回去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回到江边。下了堤岸,踏着粗砺的砂砾,一步步走进水里。冰凉的江水贴着肌肤升上来,顿时寒意沁骨,水温和气温起码相差有十几度。浸入水中,双脚离底,身子便浮起来,被水流裹挟着顺流而下。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江水的流速之猛烈。在这样的水流中,再有力量的人所能做的,也只有随波逐流,充其量顶水划动几下,延缓一下被冲向下流的时间。人被漆黑如墨的江水所控制,埋头水中,所见的只是一片黑暗,恐怖油然而生……
后来的几年里,曾在乌云镇和嘉荫县城的江边多次游过泳,都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因为每次游泳以后,让人的自信心备受打击,饱受失败感的折磨。
在我半个世纪人生中,见过黄河的浑黄,长江的青苍,渤海的深蓝,南海的湛绿,都有让人可亲可近之处,但黑龙江水之黑,只能用“心生敬畏”四个字来形容。人在水中看不清水下的一丝一毫,哪怕是透一点光也好,但它就是不给你机会。这条从无数极地草甸的水汇集而成的大江,寂寞而又坦荡地向下游流去,把一切秘密注入大海。
信用社的日子,单调得让人看不到尽头。下乡插队的目的,也不是混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短短几星期,我便对这份工作心生倦怠。还是向往五花八门的农家活,想念那些一起下乡的同伴,希望过一种自在热闹的日子。于是,我告别公社信用社,独自一人踏上了回生产队的路。
如果,当然人生没有如果。
假设我当年在信用社干了下来,几年后成了一名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那么,人生会怎么样呢?无法想象。人生无数的岔路,顺着每一条路口走下去,都是别有一番风光。
一九七七年,我离开黑龙江,去安徽省芜湖农村插队。临走之前,我再次去了嘉荫县城,与几个已经上调在县办企业工作的中学同学道别。这一次,去了县造纸厂、乌拉嘎金矿和马连木材厂———这几个工厂是为安置知青就业特地开设的,都属草创阶段,除了县造纸厂在县城,其他两个地方都在深山里,还是住帐篷睡通铺,是上海知青的又一次创业。
马连木材厂在嘉荫往下的江边密林中。还是乘坐“水车船”前往。由于是下水,船体轻盈,两边的水车轮子慢悠悠地转动,分不清是轮船自身的动力还是江水在推动。嘉荫县城而下,黑龙江上风景陡变,在雄奇中添了几许诡秘。江面时而河汊、河湾环绕,时而山峦、奇峰夹峙,令人目不暇接。船行途中,山峦怀抱之中,突现一片湖泊,岸线模糊难以辨别。江中沙渚、小岛星星点点,小岛上草木葱郁。若不是船在江中的主航道行驶,若是阴天,几乎很难辨别东西南北。湖面如镜,波澜不兴,如入仙境,如临异域。
在船上远眺江岸,茅草、芦苇茂盛,绵延数里,却是江南景色。听说早年这里有鄂伦春人的渔村,独木舟在江上出没。估计这段江中,鱼是不会少的。在黑色的江水衬托下,这段风景竟然让人有童话世界的联想。如果不是边境重地,人烟罕至,放在江南,又是一处旅游之佳胜。联想到冬日冰封之时,这片辽阔的雪原,将会给人带来多少欣喜。
船近马连,山势逐渐逼仄,站在船舷,江边的山体清晰可见。崖壁上的危岩似乎随时都可能倾倒下来;石缝间的小树向江中伸出枝桠,人在船上仿佛触手可及。江水冲刷崖脚,波涛声变得响亮起来,在崖壁与江水间回荡。两岸陡崖夹得江面变窄,水随山转,如影随形。此地的江面大约只有上百米宽,冬天冰封以后,估计用不了几分钟便可过江。只是这里山高水险,不是熟悉地形的当地人不可能涉足。
“水车船”向山缝间的一小片沙滩前靠近,听了广播才知道,这里就是马连木材厂。远望岸边,谷幽林深,树木杂芜。几个帐篷在山沟中若隐若现,有人在走动,但没有听到锯割木材的声音。看不出一点村庄、工厂的影子。将木材厂设在这么一个人烟罕至之处,唯一可行的说法是,这里江面狭窄,春天开江后上游放排的木头,在此易于集中打捞。原木归拢以后,运入厂内加工成材,再装船运往各地。这也算是靠江吃“江”吧。
下了客船,同学已在岸边等候。稍作休息的时候,正遇江边渔人在煮鱼。枯枝燃在瓦釜下面,釜中鱼汤翻滚。渔人与同学相熟,热情地邀我们同食。各式鱼种不分大小放在一起清炖,不用调料,只加少许盐粒和葱花,清水沸煮,汤色乳白似牛奶。还未上口,鱼香先将人醉倒。待到开吃时,伸出筷子夹起一段鱼肉,塞进嘴里,鲜味顿时弥漫口腔,精神为之一振。这里的鱼,肉白少刺,肥而不腻,似有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没有泥腥味。如此鲜味佳肴,我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
落日晚霞里,坐在江边的巨石上,吃着野炊,静静地看江看山。傍晚,云彩变化万千,低低地压在江面,远处山影蜿蜒,脚下江水涌流。“水车船”下了人装卸完货物,又要起航。船笛鸣响,缓缓离岸,在暮色中渐行渐远,很快消失在水天一色间,它的下一程便是松花江口了。看着远去的船只,静坐沙岸,身心俱寂,莫名地想流泪,想倾诉,想吟唱……
天色渐暗,江水苍黑湍急,岸树碧绿如烟,远山隐显若云,人生在亘古不变的自然面前,渺小得不值得一提。万般不如意,此时化作一丝轻烟飘散。人也渐渐变成了一块石头,成了江边的一景。
车走森林路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办完了所有迁移手续,离开黑龙江边,转去安徽省芜湖农村插队。
没有坐船从县城走,那里离最近的汤旺河火车站还有几百里地,加上水路的时间,要走上两天。所以选择了一条近路——走小兴安岭的森林公路,从当地的卫东林场到乌伊岭火车站,再从那里上火车去哈尔滨。当年下乡,我们也是走这条路,进了嘉荫县的福民屯。所不同的是,那一次是进,这一次是出;那一次是轰轰烈烈一大帮子人,这一次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
乌伊岭是哈尔滨进小兴安岭林区铁路的终点站,那里有医院、邮局、饭店、商店、旅馆,小城镇该有的一应俱全。饭馆好像只有一二家,我们都进去吃过,花一二角钱,水捞面条加一点浇头,或者饺子,或者白菜汤加面饼……等火车或者等卡车的间隙,一般会去商店逛逛。店里有一种纸包的酥糖卖,至今还记得,长圆形的,黄黄的主体上绘着一丝丝红线或绿线,嚼在嘴里,松松的有点粘牙,甜得喉咙发痒。邮局去的不多,因为没有这个需要。医院却是不错,当年一个插兄的腿伐木时被树砸断,最初是送到这里医治的。医院的病房看上去很干净,与农村灰溜溜的土炕相比,这里有床和暖气片,温暖而明亮。从病床上看窗外,云层压着山梁和满坡的小松树,世界是宁静的。总之,在这里可以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那时,嘉荫属黑河地区,是农业县,乌伊岭是林业区,归伊春市管。两地居民的消费不是一个档次。
一九七零年春下乡,从乌伊岭到卫东林场,坐的是解放牌卡车,敞篷的。途中四五个小时,黑色的松林,白色的桦树,深不见底的沟壑,迎面笔立的陡崖,连绵不绝。最初时,一路风景引得车上的人大呼小叫。不一会儿,大伙便沉默下来,无心旁顾。车身在剧烈地颠簸摇晃,人的屁股无法在行李上坐稳,两只手死死地把着车厢挡板,稍不留心,人就有被甩出车厢的危险。车轮扬起一路黄尘,笼罩着车上每一个人。相顾左右,所有人都变得黄乎乎灰蒙蒙,只有一双双眼睛黑白分明,是干净的。
到卫东林场,天色完全黑了。从林场到福民屯,要走十八里地,没有公路,连简易的土路也没有,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好在有履带拖拉机碾压过后留下的纵横交错的泥辙。循着黑色的辙印,一伙人在高低不平的灌木、草甸里步行前进。不时有人踩进水洼里,发出一阵阵恐惧的惊叫。夜色漆黑,没有月光,看不清地形山势,只是跟随着前面模糊的人影和此起彼伏的呼喊,踉跄向前。
半夜,看到了点点火光。随后见到了屯子里来接应的人。进了屯子,昏黄的煤油灯下,有人端上热乎乎的玉米粥,大伙趁热喝下。一群人挤进了一个四面漏风的大棚子,还没有理清头绪,便累得在白桦树杆搭就的铺上倒头就睡。
天亮,睁开眼睛,惊讶地坐起。原来我们睡在牛棚里,牛屎的气味到处都是。再看身边,男男女女,混杂横陈,和衣蜷曲在桦树杆铺成的通铺上,身上是泥浆斑驳的衣服,湿漉漉的鞋子还套在脚上。
走出棚子,极目望去,心绪茫然。点缀着残雪的漫天荒草,向低缓起伏的山丘铺展。黄色、灰色、白色,还有踩成黑色泥浆的泥路。棉絮似的乌云,层层叠叠,浮动在头顶上。远处的山脊线上,云层静止不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不时露出一簇簇整齐的白色,是小片的白桦树林。四顾村庄,除了近处几间半埋在土中的茅草屋,一口轱辘摇晃不停的水井,再也看不到更多生命的迹象。
与世隔绝的荒凉,千年不变。命运之手不经意地将我们放在这里,然后挥手远去。离开上海时,有过无数的想象,唯独没有想到眼前的景象。人生严酷的一幕就此开始。
七年后,我背着行李,无言地向它告别。同时,也告别了我的青春,走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卫东是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林场,属伊春林业局管,与嘉荫县不是同一行政区,虽然与我插队的福民屯相距只有十八里地。双方相互间联系甚少,套用一句老话说“老死不相往来”,也不为过。
不过,只要到了林场,在那里搭上便车,走林区公路,到乌伊岭火车站只有不到半天的时间。
那时没有公交车,只能搭乘给林场运货后空返的敞篷卡车。站在林场的大道上等车的滋味,可以用“惶恐”两字形容,第一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车,第二不知道有了车能不能搭上。因为,那些卡车并没有义务一定要让你们白乘。遇上司机心情不好,或者载了货,只能眼巴巴看着它弃你而去。
那天,不知怎么的,要乘车的人特别多,大概是林场放假吧?总之,一辆解放牌卡车挤下了二三十人,满满一车箱,前面的人站着,后面的人蹲着,摇摇晃晃地启程了。卡车上山岗的时候,我朝插队的方向回望了一阵,群山障目,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过,我知道,那个地方不再属于我了。我与这个地方相联系的所有证明:户口和档案,都在我随身携带的行李里。那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迁出。”
这一路是往小兴安岭的深处走。卡车上坡、下坡,一会儿从中间劈开的陡崖间穿过,一会儿贴着湍急的山涧盘旋。坐在敞开的车箱上,卡车显得头重脚轻,大部分时间里,人心总是紧紧地揪着。尤其是车经过在山腰间辟出的路段,一边是笔立欲倾的崖壁,危岩高悬,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深涧,巨石如卵,眼光不管投向哪一边,都觉得命悬一线,车轮稍有偏差,随时有车翻人亡的可能。闭上眼睛,更是不敢,生怕危险来临时,连个逃命的机会也没有。还有就是卡车爬长坡,长长的上坡路仿佛没有尽头,发动机喘得像个病人,眼看着就要熄火似的,坐在车上的人紧张得浑身抽紧,默默祈祷:“别熄火,千万别熄火。”在大于三十五度的坡上熄火,司机即使拉上了手闸,载重的卡车也会顺坡溜下去,结局很可能是翻车。这时候只能听天由命……
直到卡车穿行在松树成荫的树林间,坐车的人才稍稍松口气。铺天盖地的松树林,白天黝黑如洞穴,阳光从树梢间射入,如万箭穿梭。密密的松针铺在树下,层层叠叠,洒满了一地金黄,没有一丝杂色。时而有密不透风的白桦林,在路边时隐时现。白桦亭亭玉立,清新妩媚,织成的林带如绵亘的粉墙,将整个山头围了起来,埋葬了一切肮脏。
行车途中,密林深处渐或显露出一两个破旧的大帐篷,炊烟袅袅,与世隔绝中透出一丝人气。这些原来都是采伐的作业点,现在只有寥寥几个留守的林业工人。靠近路边的成片的成材林已不多见,到处可见被砍伐过的圆圆的树墩,如星如棋,散落在正在恢复生机的次生林间。这里已经不是主要林区了,要等次生林成材,可能要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森林公路中途有一边境检查站,大家都称呼它河口检查站,专门检查经由这里去黑龙江边境的人员。这在当时中苏冲突的背景下,是很有必要的。当年,我们知青经过这个检查站时,心情很是激动,有一种自豪感。到边境去,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去的人都要审查批准。我们每人发了一张边境居民证,以备边防人员检查。无证的人,先要在省公安厅办临时的证明,才可以去边境。因了这番一本正经的折腾,经过检查站以后,似乎就有了临战的气氛……
在黑龙江边生活时间长了,才发觉这仅是人为造成的错觉,边境线并不像常人想象中的那样草木皆兵。生活在江边,除了看到两方边防人员在每星期有一次例行会面,平时几乎不见军人的影子,更不要说坦克大炮战壕掩体了。
再说,很少有人走这条路去边境。林间运送木材的公路到卫东林场便终止了,还要翻山越岭走近百里山路,才能到江边。陌生人走这条道,简直是在给自己添麻烦。但毕竟是一条通道,设一个关卡是必需的。这里山高林密水险,只此一条通道,扼守很是方便。从乌伊岭来,两山夹峙一条公路往边境方向去,公路两边陡崖贴着深涧,上天入地都是难。要想翻山越岭绕过检查站,不熟悉地形的人一般很难办到。而检查站地处河谷,视野广阔,人在屋顶上一站,四面八方尽收眼底,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下乡的那一年,中苏边境刚刚发生过珍宝岛事件,正是紧张关头,边境的概念不断强化,后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便逐年减弱了。这条道上我来回经过多次,很少遇上正儿八经的检查。到后来几年,我的那张边境居民证也不知放哪里去了。检查人员验证,一般站在车下扫视一遍,抽几个人看看,便挥挥手将人车放行了。估计一旦形势紧张,或者上面有通知,他们还是会仔细检查的。
不过,我之所以觉得这个检查站是必需的,还是出于旅途安全的考虑,设想如果没有国家出钱在这里设一个点,中途路过的人和车万一出点问题,连一个求援、歇脚的地方都没有,茫茫大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是很可怕的。
有一年冬天,我搭乘一辆卡车回屯子。卡车开过河口不久,爬一个大坡时,怎么也上不去,最后干脆熄火了,顺坡溜了下来。虽然命大没有出什么危险,但卡车是不能走了,前不着店后不靠村,大伙被抛在山里,等着过路的车来帮忙……眼看着天黑了下来,又没有别的车路过。我只能和一同搭车的人往回走,回到检查站。这时候,才感到这几间小小的砖房温暖和安全。大伙围着火炉,坐了一夜,虽然人困得七倒八歪,心情还算安稳。因为在这个大山里,这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地方。
山间的公路是为了运输木头而开的,简易的沙土和碎石铺就,车在上面碾过,一路扬尘,久久不落,大老远就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行驶最多的,还是捷克130马力的拉大木车。高大的车头和车身,后面拖着几十米长的六七根原木,中间有一个四轮的托架支撑着。车开动以后,马达的啸声如喷气机升空,车头和原木像长龙一样摆舞在山间,扬尘滚滚,势不可挡。
开这种车的司机大多年轻,喜欢开快车。
那天,解放卡车行驶在依崖傍涧的山道上,我们坐在车上的人,远远地看到后面一溜黄尘。不一会,一辆捷克130拉着一车长长的原木追了上来。解放卡车的司机似乎不想吃土,加速跑在前面,但终究不及捷克130的马力大、车速快。在身后连连喇叭声的催促下,司机无奈地放慢车速,将卡车向崖壁一边避让。
捷克130从解放卡车的外侧驶过。
两车相向并行时,我看到了原木车驾驶员的那张脸,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冲着我们瞪了一眼,似乎不满意卡车的怠慢。也许是为了出气,想惩罚解放卡车一下;也许是瞬间思想开了小差,反应慢了半拍。那辆捷克130在超车以后,车头稍稍一个扭动,车后长长的原木尾梢在解放卡车的前面扫了一下——可能这是他们之间常玩的游戏。
大祸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当我还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身子下面的卡车突然如脱缰的野马,车头一甩横了过来,冲着崖壁撞了上去,随着一声巨响,车头戳立在石壁上,车身从中间弯起。卡车底盘的大梁断了。一车人在巨大的惯性带动下,一齐向前扑去。幸好是人多,肉贴着肉,减轻了撞击产生的冲力,只可怜原来站在车厢前占了好位置的几个人,被后面的人猛力的撞挤,胸前的肋骨被压断了。
还没有从惊魂中缓过神来,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大家抬头朝前看去。只见那辆原本得意洋洋的捷克130,在山路上扭了几扭,突然失去控制,一头冲进了山涧,巨大的原木横着滚了一下,便不见了踪影。好几秒钟,山林间顿时一片寂静,所有的声音消失了——捷克130的和解放卡车的。
片刻,才从悬崖下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我们也顾不上自己的处境,纷纷爬下卡车,奔向前方的路边,伸头朝山崖下探望。
极深的山涧里,捷克130的车头像玩具似的仰头朝天躺着,十几米长一米来粗细的原木,筷子一样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嶙峋的山石间。慢慢地,看到从车头里爬出一个“小虫”——那个开车的小伙子。没有下山涧的路,也没有上来的路,他爬了一阵,又趴在石头上,不再动弹。无法判断他的身体状况,看样子是伤得不轻,但怎么下去救他呢。还有,在卡车上的那几个断了肋骨的人,也急待救援。众人束手无策。司机蹲在路边,呆呆的,还没有从刚才的险境中缓过神来。
这也许在林区常见的景象,从捷克130驾驶员开车玩命的样子来看,这好像还是小菜一碟。
安定下来,卡车上的人才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如果是我们这辆车在路的外沿,如果窜下山涧去的是这辆卡车呢?车上无遮无挡的肉身,呈自由落体纷纷下坠,砸向山涧的巨石,那情景……
出事的地点,大约离乌伊岭火车站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及时呼救。好在,不一会儿,从后面又来了一辆运木头的捷克130。车上的司机问明了情况,开车去了最近的伐木点,打通了电话。一个多小时以后,救护车和警车来了。他们开始抢救深涧下的驾驶员和卡车上的伤员,我们这些没有受伤的人,则挤上了随后路过的车,直奔乌伊岭车站……
这一别,三十年过去了。
责任编辑 鲁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