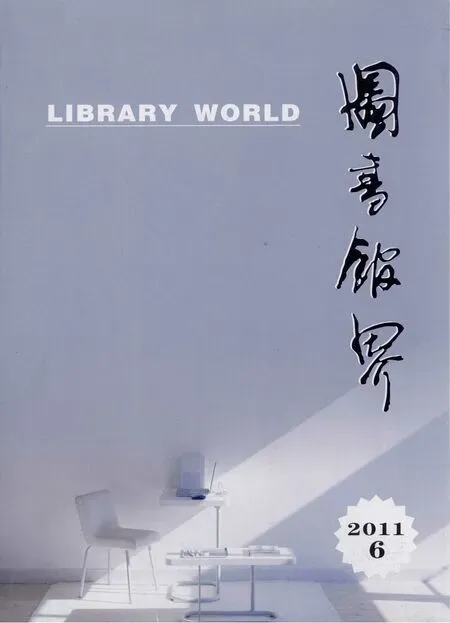颜之推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探析
樊 普
(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 南阳 473061)
颜之推(531—约591),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颜家随晋元帝渡江后,成为著名的侨姓士族即琅琊颜氏。颜之推是一名出色的古文献学家,著述颇丰,并曾主持编辑北齐大型类书《修文殿御览》。流传下来的著作有《北齐书》本传载其著《文集》三十卷、《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载其《证俗音字》五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载有他的作品《还冤志》三卷(此书《册府元龟》著录为《冤魂志》)等。凭借博览群书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语言文字学造诣,颜之推在文献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文献整理的思想、方法和实践集中体现在其《颜氏家训》中的《勉学》《书证》《音辞》等篇章,为后世学者所遵从并产生积极的影响。
1 颜之推文献整理的思想
1.1 实事求是的文献整理态度
《颜氏家训·勉学》篇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1]220,表明了颜之推对学术和文献的求真的态度。他不仅认识到了要尽可能多搜集资料,更要广求异本,“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失,不可偏信一隅也”[1]220,注重异本间的校勘对比。《颜氏家训》书中对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有特定的名称,如“河北本”“江南本”“俗本”“误本”等,他注意搜求不同地区的版本,相互对比,以验其实,并从中选出善本,作为校勘的重要资料。这种求真的态度和验证方法,表现了严谨科学的学术精神。
1.2 博通的文献观
颜之推的文献整理的视野和方法,一方面体现在他所研究领域的广博上。综观《颜氏家训》二十篇,学术研究方面,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无所不通;杂艺方面,书法、绘画、卜筮、算术、医方、音乐、博弈无所不晓;宗教思想方面,阐述了儒佛一体论;教育方面,既有对家长教子的时间、方法的说明,更有对子孙学习目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的劝诫,这是《家训》流传至今最为称道的经典;此外还有治家之道、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人生智慧的经验浓缩。
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所秉持的通达的学问态度上。在文献典籍利用上,从司马迁试图“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到郑玄遍注群经,都体现了广征博引的思想。颜之推在文献整理中则扩展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在文献校勘中,他重视字书、音义书的运用,如《说文》《尔雅》《广雅》等,认为字书音义书相对充满谶纬的经典来说更加科学可信;扩大了引书范围,在《书证》《音辞》等篇里,引用了《离骚》《说苑》《韩非》《搜神记》《月令》等子部、集部著作,冲破固守章句的藩篱和当时狭隘的思想限制;颜之推也是第一个运用出土金石碑铭文字来校正传世文献的古文字学家,开拓了校勘资料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推进了我国古代的校勘学思想;南北朝是汉字字体发展的重要阶段,字形变化很大,也出现了大量的异体字。古字、今字、正字、俗字交杂,易产生歧义。因此,颜之推认为,整理文献除了纠正错讹,也要规范字体。他极为推崇《说文》,“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3]457,认为许慎按六书解释文字,以部首归类,不易出错。但是他也承认文字的历史发展变化,“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互有同异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3]462。这里颜之推提出了“通变”思想,认为不可拘泥旧说。“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4]颜之推认为古今言语不同的原因,包括时代变迁、人文风俗等,是一种通达的历史发展观。
1.3 积极的文献保护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取代了简帛,书籍制度不断变化,文献保护方法有了新内容,文献修补技术也有了新发展。史书记载,晋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5]。颜之推认为,“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6]。虽然没有说明具体的修补方法,但是颜之推把爱护文献、积极修补作为士大夫的品行之一,足见其对文献保护的重视。
2 颜之推文献整理的方法
颜之推《颜氏家训》并非专门的文献整理著作,也没有一套系统的文献学理论和方法。他在版本、校勘、辨伪、音韵等方面的原则、方法与成就,集中体现在《书证》《音辞》《勉学》等篇章。
2.1 广收异本,重视善本
熟悉文献、广收异本是做好文献校勘整理的第一要素。自文献产生后,就存在版本异同的问题,孔子整理六经的过程就是搜集、利用不同版本的历史文献学萌芽活动。汉代刘氏父子校理群书,其整理古籍的第一步就是广罗众本。南北朝时期,文献数量剧增,书籍形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因版本不同而产生的问题就更加突出。《颜氏家训》明确记载了“江南本”“河北本”和多家收藏的文献,彰显版本特征。由于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各地文风也不同,颜之推很注重同一书不同地区的抄本。如“《诗》云:‘有杕之杜。’江南本并木傍施大,……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读亦如字,此大误也”。[3]379又如“《汉书》云:‘中外褆福。’字当从示。褆,安也,音匙匕之匙,义见《苍雅》《方言》。河北学士皆云如此。而江南书本,多误从手,属文者对耦,并为提挈之意,恐为误也”。[1]218即是通过不同版本比对来校错字。
颜之推认为在无法用意义求证用字的情况下,版本互校就显得很重要。如他对“田肎”的“肎”字的考证中,就利用了不同版本。《汉书》曾有“田肎贺上”一语,江南诸本“肎”皆作“宵”,但是精通《汉书》的刘臻却呼为“田肎”。梁元帝曾问他原因,他说“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为‘肎’”。刘臻无从解释,颜之推后来到了江北,发现江北诸本皆为“肯”,这一问题便得到了解决。[3]405
颜之推注重从引用过此文的不同的书来求证版本的正误。如《书证》篇中江南本《诗》云“将其来施”,颜之推考校对比《毛传》《郑笺》《韩诗》及河北本《毛诗》等不同版本,认为江南本少一个“施”字,应为“施施”。
颜之推备至多本,广征博采,择善而从。他曾举例误芋为羊、误读颛顼为专鹮的笑话来说明读书一定要选择好的版本。而《家训》中多次的不同版本优劣比对,也是颜之推求真求精、重视善本的体现。
2.2 广征博考,纠正错讹
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错误,文字的错讹、次序的颠倒、人文风俗不同而造成的以讹传讹,害人匪浅。所以,“书不校勘,不如不读”。[7]大规模的校书活动始于汉代。汉代刘氏父子用“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的本校法和“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的对校法来校勘讹文脱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除了根据文义来判定错讹衍脱,还运用了本校和他校的校勘方法。[8]72颜之推继承前人的校勘规则与方法,并拓展了校勘引用资料的领域。
根据语法和字形来校订错文脱字。颜之推以文籍中常见的语助词和语尾词“也”为例,说明有些“也”字是不能没有的。《书证》篇有云:“《诗》言:‘青青子衿’。《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邺下《诗》本,既无‘也’字。群儒因谬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3]399可见少了“也”字,造成理解的极大偏差,贻笑大方,所以不可随意改动原文。颜之推还列举了因字形相似而产生的错讹。如《书证》篇云:“《后汉书》: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守,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悟。夫虎豹穴居,事之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宁当论其六七耶?”[3]424校订了江南本因“穴”与“六”混淆而造成的迷惘。还以“策”的字体演变为例,说明后人以“荚”为正字,以“策”来注音是颠倒错误的;举例批评了《史记》中“悉”误写为“述”、“妒”误写为“姤”,而裴骃、徐广等后世注家也以“悉”字给“述”注音、以“妒”给“姤”注音的错误做法,“既尔,则亦可以亥为豕字音,以帝为虎字音乎?”[3]406
结合古训诂书和亲自见闻来释疑考证。颜之推对《月令》中“荔挺”一词的考据,先引前人训诂之解:“郑玄注云:‘荔挺,马薤也。’《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广雅》云:‘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马兰。……”又结合个人见闻:“然则《月令注》荔挺为草名,误矣。……”[3]383来加以评述,说明由于地域的不同,把“荔挺”认作“马苋”是错误的。
根据出土文物中的铜器刻辞来校订古书记载之误。《颜氏家训·书证》篇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乃召丞相状、绾……凡四十字,了了分明,其书兼为古隶。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尔。”[3]415颜之推根据出土实物,订正了《史记》中“隗林”为“隗状”之讹,探索了新的校勘途径和方法,扩大了校勘资料的范围,他是利用出土实物中的金石文字进行校勘的第一人。同时他还利用汉代碑刻铭文与传世古籍互相印证,考证出“宓”字乃“虙”字之讹,而“虙”与“伏”自古以来就通用。运用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实为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先驱。
此外,颜之推还利用同义词的训诂、方言等方法来校正书籍文字,遍及经史,定其是非,已类似后人所撰校勘记。[8]81
2.3 综合勘察,考辨真伪
《孟子·尽心篇》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这是疑古的开端。辨伪之学在汉代已出现,汉代学者在文献编纂整理过程中,利用各种方法开展文献价值、真伪的考辨工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辨伪之学,在南北朝也有了更大的发展。颜之推继承和发扬了“疑者阙焉”的求是精神,恪守“多闻阙疑”,综合考校,以求真伪。《书证》篇中有颜之推对世间题河南服虔造《通俗文》的考辨实例:首先,他以作者和书中人物生活年代来辨伪,“虔既是汉人,其叙乃引苏林、张揖;苏、张皆是魏人”。汉人岂知魏人之事,这是明显的作伪嫌疑;其次,他利用目录著作进行辨伪,“阮孝绪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书,家藏一本,遂无作李虔者。《晋中经薄》及《七志》,并无其目,竟不得知谁制”。西晋荀勖《晋中经簿》、阮孝绪《七录》、王俭《七志》都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书目,其中都无记载,实属可疑。虽然从书目和书中自相矛盾看都有作伪的嫌疑,但是颜之推还是谨言慎行,不妄下结论:“然其文义允惬,实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3]436他觉得书中行文高明,也不能贸然定为伪书。颜之推辨伪的方法和原则,为后世文献学家所遵从。
此外,颜之推在《音辞》篇中总结了音韵学发生、发展的历程:从《春秋》《离骚》南北方言的不同到汉代扬雄《方言》对各地方言的详细记录,从汉末反语出现到曹魏之后反语标音之法的盛行,简短勾勒了一幅音韵学的发展史,这也是音韵史上的第一次。
3 结语
颜之推一生,历仕萧梁、北齐、北周、隋,三为亡国之人,历经南北朝之乱象,坎坷流离;同时他早传家学,博学多闻,精通诸艺,是南北朝学问之集大成者。范文澜先生曾对其一生有精炼的总结:“他是当时南北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9]正是对南北学术的通透和坚实的小学基础,《颜氏家训》所呈现的文献学价值和成就,无不体现着颜之推通达、求是、不拘泥旧说的治学态度和文献学精神。在文献整理实践中,颜之推强调校勘和辨伪之法。在版本上广罗异本、重视善本,注重版本比校;在校勘上广征博引,注重字书、音义书以及非经典著作的运用,并且第一次用出土金石文字考校传世古籍,扩大了校勘学的引书领域;在辨伪方面谨慎科学,其辨伪之法为明代辨伪专著《四部正讹》所遵从。总之,颜之推的文献整理思想和方法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勉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85.
[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书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音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7.
[5]李 昉.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63.
[6]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治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6.
[7]叶德辉.藏书十约[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50.
[8]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