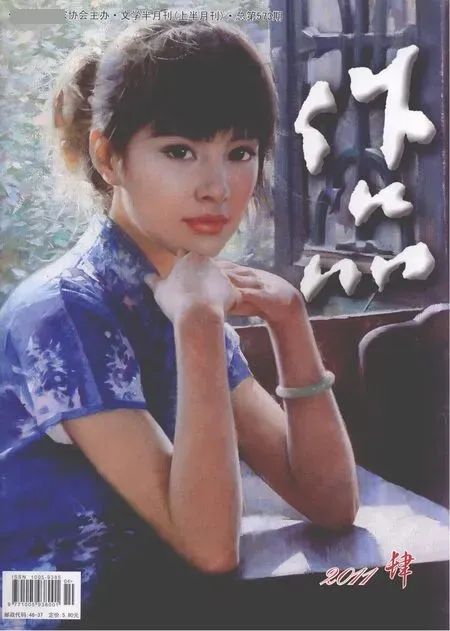妈妈不是我杀的
□裴 蓓
刘香梅的死让我终生愧疚。尽管她只是我妈妈的邻居,她的死和我毫无关系。
刘香梅死得很惨,伤口在颈动脉上,一刀致命。
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我妈妈只是在吃完晚饭的时候,听到了对门有争吵声,但验尸官说,刘香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4点。
争吵声是刘香梅和11岁的儿子王曲曲的。争吵的原因大概还是为王曲曲的网瘾。王曲曲的话向来极少,更极少顶撞他妈妈。但那天傍晚,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个脸色有些苍白却比同龄人长得高大帅气的男孩,眼神不同寻常地阴郁。
我妈妈在凌晨4点半听到敲门声,开门时,抽了一口冷气。王曲曲满身血迹地站在门口,脸色纸一样的白,一个字说不出,只是用手很困难地指指自己的家里。
我的弟弟是刑警队的一个小头儿,那天正准备出门。见这光景,冲了出去,小心翼翼地进了王曲曲家。刘香梅死在床上,门窗完好,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也没有搏斗的痕迹。
弟弟和闻讯而来的同事们检查了现场后,说,这案有些悬。
这个“悬”字,让我惊惧。可我不敢想下去,王曲曲才11岁。
弟弟看着我的表情,又说,有点悬。
一
我的弟弟在凶案现场发现的细节令人费解,一把掉在刘香梅身边的刀,塑料的,逼真,形态锋利,但毫无杀伤力,塑料刀上只有王曲曲的指纹。割断刘香梅颈部动脉的是水果刀,水果刀掉在塑料刀的旁边,上面有两个人的指纹,王曲曲的和刘香梅的。床头柜上有一个没吃的水果。最费解的是,一直放在王曲曲房间的手提电脑放在了刘香梅卧室的电视机柜上,电脑接了摄像头,摄像头对准刘香梅的床,可是,电脑里没有任何录像资料。我的弟弟怀疑录像直接存进U盘,可他们翻遍了王曲曲家的所有角落,没有U盘。
我的弟弟遇到了做刑警以来的最大难题,这些看似和凶杀无关、却无法忽视的细节似乎展示着一个绝对不寻常的案情。弟弟和同事们一时间却无法把这些细节连串起来,还原成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凶杀现场。
那么,那天晚上,刘香梅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时找不到头绪。我的弟弟向我求助,我是一名心理工作者。
我在王曲曲搬到我妈家对门的一年里,一直关注着王曲曲。我试着读懂这孩子阴郁的眼睛里隐藏着的不为人知的东西,读懂这个母亲没有合法妻子的身份、终日见不到生身父亲的孩子的内心。然而,我还没有读懂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刘香梅死了。孩子被作为最大的嫌疑人暂时放进了少管所。而我妈家的对门成了凶宅。
我母亲原来每个下午都在刘香梅家打麻将,现在再也不打了,她说一打麻将就想到刘香梅死的惨景。我儿子由由有些懵懂,每次看到那贴着封条的大门,总不开心,他很崇拜王曲曲的游戏技术,说王曲曲是他见过玩游戏玩得最好的强者。
由由还对王曲曲的自由羡慕得不行。王曲曲的妈妈刘香梅一年365天有364天、一天24小时有16个小时都在麻将桌上,而王曲曲的爸爸一年365天有364天都不回家,虽然他就在这个城市,据说很有钱。
于是,由由总叹息,妈妈你干嘛不和曲曲的妈妈一样打麻将呢?还有一句话,由由想说不敢说,他希望爸爸也和王曲曲的爸爸一样不着家,免得动不动板着脸两只眼睛像盯猎物一样地盯着他。
刘香梅还好好的时候,我每个周末都犯难。我得带着儿子去看母亲,由由总是死乞白赖地往王曲曲的电脑上蹭,而由由的爸爸总为我教子不严十分不悦。我的丈夫,这个从小苦难着长大、又在部队强化训练过几年的男人,不仅用强烈的进取心和近乎苛刻的处世原则折腾自己,也折腾孩子,我成了父子间的磨心。
现在,刘香梅不在了,我不犯难了,可是,我很愧疚。我愧疚的不只是之前对刘香梅母子的嫌厌,我更愧疚的是,我应该早一点介入这母子俩的心理,或许,我能挽回一个家庭。
二
我没杀我妈妈。王曲曲说。
王曲曲被带走后,只说过这一句话。而且,不再重复。
王曲曲的脸比妈妈生前更苍白,眼睛里的阴郁变成了冷漠和木然。
我的弟弟在勘查了现场后,把王曲曲的书包给了我。书包里很乱,虽已是期末,课本却都是新的,只是因为胡乱塞放,弄得七翘八歪。作业本都只用了几页,而且大多是红色的X。只有一本日记,几乎写满了整整一本。
日记都是一些零言碎语,大多没有日期,没有连贯。我仔细阅读了这本日记,那些看似不经意不连贯的文句,串联出王曲曲的心路轨迹。从日记里可以看出,王曲曲很想念他的父亲,可他父亲已经大半年没有回家了。日记记录了王曲曲最后一次见父亲的情形。
那是去年的中秋,王曲曲被他爸爸从网吧拽出来。那天,爸爸的脸发黑,爸爸对着他的脸永远都是发黑的,那次最黑。爸爸解开腰上的皮带,一抽,皮带便顺势打在他的身上。一下,两下,一鞭,两鞭——王曲曲数着数,看着爸爸发黑的脸,不哭。
妈妈跑进来一把夺过了皮带。妈妈后来老是对麻友们说,要不是那次她眼疾手快,这小子连命都没了,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哟!他讨厌妈妈那张嘴。
爸爸没了皮带的手使劲在他的背上擂了几拳,然后,发黑着脸走到客厅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妈妈手里拿着皮带,低眉顺眼地看着爸爸,讨好地似笑非笑。平日那八婆劲不知道哪去了。
王曲曲走出房间,把皮带从妈妈手里一夺,双手捧着,走到爸爸面前。他没说话,只是看着爸爸,要爸爸继续抽他,狠狠抽他,抽得他皮开肉绽,抽得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爸爸不该生他,妈妈不该生他,不该!
爸爸没有接他手中的皮带,走了。爸爸走了,再也没来过。
王曲曲捧着皮带的手半天没有放下,一直捧着,眼泪流出来。王曲曲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身上一点都不痛,心窝子痛。
三
杀害刘香梅的凶手,是王曲曲。我弟弟和其他办案人员都这样推测。以我对王曲曲所有的分析,这个推测似是成立的。这个自幼亲情缺失的孩子,恋网成瘾,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混淆,把母亲当作了泄愤的敌人。
然而,无论是我,还是我弟弟他们都好想推翻这个推测。如果王曲曲真的是凶手,那个刀口的形状为什么类似自杀?塑料刀怎么解释?电脑是怎么回事?留有录像的U盘又在哪里?
我试着从我以往接触王曲曲的任何细节,找到答案。
我认识王曲曲母子是在一年多前。那时,他们刚刚搬来和我妈做邻居。我每次带着由由去看我母亲的时候,总是听到刘香梅家嘈杂的人声和麻将声。人声里大多是刘香梅的高音频,你碰不碰?你不碰我吃了!你这是打什么牌啊,这不是着火坑邻居么?快出快出,打牌像生崽一样难,危险危险,哪张牌不危险?不危险还打什么牌?
这个周日下午,我妈在刘香梅家搓着麻将打发下午的闲暇。由由第一时间溜进了刘香梅家,我便也跟了进去。
一进刘香梅的家,原来被门关着的麻将声人声就更大了。刘香梅的家永远很乱,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两只一样的拖鞋,她家的拖鞋皮鞋各种鞋东一只西一只地散乱在地板上,布艺沙发的坐垫上显出一目了然的黑色坐痕,茶几上,茶杯、香烟、火机、棉签、牙签、指甲剪、拆开没拆开的零食饼干,开始腐烂或已经干得皱皮的水果,乱七八糟地摆满了茶几的上下两层,几乎找不到空余的地方搁东西。
我进到客厅时,由由已经一边喊了一声外婆阿姨好,一边冲进书房了。
我走到客厅一角的麻将桌前,只是和大家笑笑,便坐在母亲旁边放筹码的椅子上,打麻将的人都没心思顾及礼节。刘香梅几乎连回一个笑容都没顾得上。按刘香梅的话说,这麻将真是好东西,好得不得了的东西,当得老婆当得饭,当得被子当得帐。
我看了一会儿麻将,便走向书房,门关着,没锁,两个孩子玩得正酣。
我一进去,王曲曲没来得及回头,只是看着电脑说,赶紧关门,赶紧关门。我赶紧关上门,外面的吵闹声立即小了很多,书房门后那层厚厚的吸音膜效果不错。
我一进屋,便有一股食物的馊味直扑鼻尖,我四周看看,却找不到馊味的源头,只是在空空的书架上看到几本散乱放着的杂志,我翻了翻,都是关于家庭八卦情变仇杀之类,时间过了很久了。
王曲曲发现是我,赶紧起身叫了一声阿姨,有些不知所措。
我说:你们玩,我只是转转。
王曲曲给我搬了一张椅子,站着看着我。我说,你玩啊,别管我,我想看看你们的游戏怎么玩。
王曲曲这才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由由一直在快速地按着键盘,说:妈妈,你看这干嘛,你哪看得懂啊?
我没搭话,只是坐到一边。王曲曲不自在地时不时瞟一眼我。这时,由由说,看我怎么收拾你!随着声音,我好奇得往电脑的显示屏凑,见一个武士一刀挥出,几道华丽的刀光划过,一只巨大的怪物轰然倒下。
行啊,你!王曲曲兴奋地说着,推了一下由由。王曲曲神采飞扬的样子和平时判若两人。
王曲曲用手指在显示屏上比划着,很有点指点江山的味儿,说,还是慢了点!走位到这里,得用这几个连招,那就大不一样了!
我惊讶地看着王曲曲,我从没见过王曲曲神色如此光彩激越,从未见过王曲曲这般兴奋放任的孩子气,以往所有的时候,我眼里的王曲曲,表情都是寡淡的,苍白的,阴郁的。
我一直惶惑于这个11岁孩子的阴郁。我读不懂这个孩子阴郁的眼神,那里面有太多的不属于孩子的东西,似乎不是哀伤不是忧愁不是怨怼不是仇恨,但又似乎什么都是。这些元素夹杂在一起,便成了冷漠与疏离。我害怕一个如此年龄的孩子如此这般的冷漠疏离。我更害怕的是,这种冷漠和疏离是以他的礼貌和腼腆呈现出来的,而且这种礼貌和腼腆折射出两种很不相融的东西,自卑和不屈。
此刻,王曲曲呈现出的阳光气息,感染了我,我的感觉顺畅了很多。我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我又闻到了那股很浓的馊味,我终于找到了那馊味的源头,书架边的角落里有几个饭盒,饭盒里的残饭剩汁发着霉发着味儿。
正值春夏之交,南方总是很潮湿,发霉的馊味在潮湿的空气里分化和凝和。我打开窗,到刘香梅到处是油污斑痕的厨房里找到了垃圾袋,把那些发臭的饭盒放进去,把口子扎紧,然后放进厨房的垃圾桶里。垃圾桶很满,也发着馊味。
我洗了手,进到书房,问,几点钟吃饭?
两人孩子根本不理我。我又说,半小时后,我们吃饭。
王曲曲看了看时间,拿起旁边的电话要叫快餐。我说,曲曲可不可以和我们一块吃饭?
王曲曲没有吱声。由由用胳膊肘碰碰王曲曲,说,没问题。
趁着这半个小时,我把王曲曲的电脑书房清理了一遍。我把书架和台面上厚厚的灰尘抹了,把胡乱放着的杂志叠了叠摆了摆,把地板擦了擦。然后,我再到客厅把一盆小小的文竹和一盆仙人掌放到窗台上,把窗帘拉开一些。就这么简单地弄了弄,整个房间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着,麻将真的不像刘香梅说的那样千好万好。
正打算结束游戏后外出吃饭时,没想到由由爸爸提前回来了。由由的爸爸是直接闯进书房的,脸色很阴沉。他站在由由的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由由开始以为是我走近他,兴奋地说,妈妈,我要赢了!感觉有点不对,一抬头,看见是爸爸,不吭声了。
由由很小声说,快了,快了,就一会儿。
由由爸爸看着由由,不说话。由由颓丧地离开了电脑。
王曲曲本来可以继续玩下去的,但王曲曲停了下来,看着由由的爸爸把由由拉走。我看到王曲曲眼里有泪。
四
王曲曲从妈妈的血泊里走出来,一直半痴半傻的。至始至终,他只说过两句话。而且,很少重复。
最早,他说,我没杀我妈妈。
后来,他说,我杀了我妈妈。
再后来,他又说,我没杀我妈妈。
从我的专业分析,王曲曲对发案过程处于失忆状态,专业上叫潜抑,就是人对太过刺激受伤的场面下意识地选择遗忘。
我深深地愧疚,如果我早一点介入刘香梅和王曲曲的心理冲突,可能情况不至于那么糟。
本来,有一个绝好的契机,我可以和刘香梅交流的。
一个周六的上午,我还在上母亲家的楼梯,就听见了骇人的声响。
啪,啪!咚咚!好像是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又好像是什么东西打在身上。声音大得连楼道都有些颤动。声音是从刘香梅家关着的门里传出的。
接着是刘香梅高频率的声音:“你还要不要读书?你不读书明天我到你学校去把你的学费退了!你一天到晚除了电脑,电脑,还会什么玩意?数学50分,你咋不考个5分给我看看?你这个不争气的孽子哟!就是你不争气!你要争气,你那死鬼爸爸他敢这么对待我们?他还不当宝贝一样整天捧着你,护着你!现在好,他看不得你那窝窝囊囊蔫里吧唧的样子,一年半载连面儿都不露一个,整天被那妖精弄得迷迷瞪瞪的。你要是我儿子,就给我争口气儿,你争了气,他就是人不来,也还多拿些钱来,现在倒好,人也见不到,钱也见不着多少。你不读书,不读书,长大了干什么营生?偷鸡摸狗,拐骗做贼?你要是争气,像人家隔壁张奶奶家的由由,人家那才叫读书,哪个学期不抱着奖状回家,你要拿一个半个奖状给我,我也好拿着到你爸那里去讨个说法,我去塞他的嘴,免得他说我们娘俩没一个有出息!我们没出息,他那婊子就有出息了,就知道把自己打扮得狐狸精似的,没事就会发嗲,就有他妈的出息了?!
始终只是刘香梅一个人的声音,没有回应,好像刘香梅疯子般的自言自语,骂着空气。
安静了一会,还是刘香梅的声音:你还在那里磨叽什么?还不赶快做功课?每天扒拉开眼睛就是电脑,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脑拆了,现在就拆!
“啊!”一声尖叫!我一惊,半天才听出是王曲曲的正在变声的童音,我从没听过王曲曲如此放量的声音。
王曲曲尖叫着说:你拆,你拆就是!
刘香梅喊:我就拆,就拆!你这没出息的东西!
王曲曲叫:我没出息,你有出息?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你够出息!
这回,是刘香梅尖叫了: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这孽种,你反了啊!
王曲曲不尖叫了,回到了他一贯的漫不经心的腔调:我是孽种?我不是你生的么?我是孽种,你是什么?你有什么脸说这话?
咚咚!两声很大的撞击声。
刘香梅的尖叫变得很沙哑:你敢这样说!你反了啊?你那没良心的老爸看不上我,连你也看不上我!你还玩什么狗屁电脑,我就拆,我就拆!
王曲曲说:你拆吧。你拆,我看着你拆!你试一试!
然后是噼噼啪啪的很多东西被摔到地上的声音。
我妈妈敲开了刘香梅的门。门是刘香梅开的。刘香梅白白的脸涨得通红。王曲曲耷拉着脑袋站在一个角落,他的脚下全是玻璃碎片瓦罐器皿,额头上流着血。
我和母亲赶紧把王曲曲拉到我们家。用酒精药棉清洗了伤口,就一个小口子,可能是碎玻璃溅上了额头,其它地方倒是完好无损。妈妈用创口贴给王曲曲贴上。
这时,刘香梅冲过来,冲到王曲曲面前,手忙脚乱地要摸王曲曲的头,慌不迭地说: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吧?
王曲曲一把将刘香梅伸出的手拨开,王曲曲用力太大,刘香梅猝不及防,往后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刘香梅本能地举起手想打王曲曲,立刻又放下,咬着牙看着他的伤口。
这一瞬间,我有些惊骇,我惊骇于王曲曲的眼神,在他推刘香梅的瞬间!一个寒颤从我的头顶瞬时蔓延到脚底。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眼神,在一个孩子的眼里。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啊?异常的抑郁,异常的阴森,那抑郁阴森里透射出刻骨的仇恨。
只是,那骇人的眼神只那么一瞬就消失了,我们帮王曲曲整理了伤口和衣服后,王曲曲回复了平静,眼里和平日一样,漫不经心里是隐晦的忧郁。王曲曲很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王曲曲说谢谢的时候,表情有些腼腆,眼睛有些红。
那之后,我本想和刘香梅聊聊,可每次见她,她都筑着“围城”,我总想着等到适合的时间再说,没想到这一拖,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五
刘香梅死前一个星期,王曲曲割过脉。这事,我是从王曲曲的日记里知道的。
王曲曲惹了一次说大不小的祸。
惹祸是中午放学时,上了半天课的王曲曲了无意趣。整个上午,王曲曲对老师的喋喋不休厌烦透顶,只好想他的网游。昨天,他在回城的路上遇上了一个“红名”,那个滥杀无辜被通缉的红名,居然明目张胆地“作案”,守在城门口屠杀进出的新手。他毫不犹豫地挥刀上前。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不把别人当人的人,对这种人,他绝对不会饶恕。
以王曲曲的高超技术,一上手就制住了对方,王曲曲一刀就可以结果红名的命,但王曲曲存心不杀,他觉得教训教训这个坏蛋也挺好玩。他撩拨着那个红名,让他想赢又赢不了,想走走不掉,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王曲曲得意地笑着,这下,你该知道天高地厚了吧。
王曲曲在饭堂排队买饭时还没从遐想的刺激里缓过神来。如果不是同桌刘元受了欺负,那天和其他的日子没什么区别,他会熬到下午放学,然后回家继续做他的副会长,继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继续带领着手下挑战更强大的boss。
可是,那天,那个号称“独孤大侠”的飞仔堂而皇之地横插到刘元的队伍前,堂而皇之地买了饭,还把汤洒在了刘元的身上。矮小的刘元是王曲曲唯一的朋友。
站在另一队的王曲曲冷眼看着,待独孤大侠走到他旁边,他一下站了出来,挡住了去路,一把揪住“独孤大侠”要他向刘元道歉。“独孤大侠”不屑地挑开了王曲曲的手,轻蔑地绕了过去。王曲曲不依不饶,再次挡在了独孤大侠的面前。
独孤大侠怒了,把碗往边上的人手上一递,说了一声,你找死啊?活腻了!当头就是一拳。王曲曲一个闪避,躲过了。王曲曲闪避的瞬间,出其不意,一记重拳打在独孤大侠的脸上。刹那间,独孤大侠的鼻血喷涌。饭堂所有的人都围上来,兴致勃勃地等待着一场精彩的武侠片开幕。
独孤大侠和王曲曲身高相仿,却魁梧壮实很多。当那魁梧壮实的身体猛扑过来的时候,王曲曲闪到侧边,一记勾拳,把独孤大侠打了一个趔趄。独孤大侠像一只疯狂的困兽,再次反扑,两人撕扯着,在地上翻滚。围观的人惊叫,喝彩!
王曲曲越战越兴奋,越战越觉得自己天生就是PK之王!这一次,这个PK之王可是现实里的。现实里的强者和网游里的强者一样过瘾!
王曲曲已明显处于上风,他骑在独孤大侠身上,掐住独孤大侠的脖子,眼睛瞪着,你是什么狗屁大侠?真正的大侠在这里呢!我要挑战人世的所有不公,何况你这垃圾!今天就要你瞧瞧欺负弱小的下场,尝尝我孤胆英雄的滋味!
要不是体育老师和班主任过来,这场厮杀还会更精彩一些。可是,那个健壮的体育老师一把将他们拖开,挡在了他们面前。
在校长办公室里,独孤大侠说:他没事找茬。
王曲曲冷笑:好意思说!
校长根本没兴趣听两人的争辩,他早就领教够了。校长只是说:各写一份检讨书,然后在全校同学面前道歉。
王曲曲的脸变了色:我道歉?凭什么我要道歉?
校长不说话,脸上眼里全是说不出的疲倦,说:明天,你得道歉,都得道歉!
王曲曲刚才还豪气万丈的大侠之气顿时萎靡了,脸阴郁下来。他看了看校长,打开书包,拿出笔盒,从笔盒里拿出铅笔刀,刚买的铅笔刀,很锋利。校长慌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校长的脸色惨白,和王曲曲一样。
王曲曲伸出手用铅笔刀在手腕上割着,一条,两条,三条!校长这才反应过来,绕过巨大的办公桌抢过了铅笔刀。
王曲曲半抬着被割伤的手,走出了校长室。那流血的地方,曾经有伤,是爸爸的鞭痕。早就没了,现在又有了,原来伤痕只在皮肤表面,现在用刀嵌进了皮肤里。
王曲曲看着血在汩汩地流,心里又有了大侠般的得意。王曲曲愿意在游戏里,永远在游戏里。那里,有的何止是智慧力量,那里还有公理公平,一切透明。那里,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老师,没有校长,那里有流血,有失败,但没有欺骗,没有歧视,没有心疼。
校长和站在门外的体育老师追上了王曲曲,七手八脚地把他弄到医院。王曲曲的每道伤口缝了7针,总共21针。他在缝针的时候,总是不停地看着门,他希望爸爸从门里进来。爸爸没有来。
从此,校长再也没找过王曲曲,就像王曲曲的爸爸再也不看王曲曲一样。从此,王曲曲在学校里成了隐形人,来也好去也罢,旷课也好迟到也罢,没有人再喝斥处罚,也没有人再过问关心。就连那个他为之流血的刘元也在家长的再三要求下,被调换了位置。王曲曲坐到了最后一排,刘元只是偶尔会用胆怯的眼神看他一眼。
六
我进少管所看王曲曲时,正是傍晚,倦鸟思返的时分。我相信在这个时分,王曲曲会对人多一些亲近。弟弟告诉我,任何人走近王曲曲,他都视若空气。
弟弟把我领到王曲曲的房间。房门外两个看守把着枪来回走动。那是一间最西边的近乎独立的高房,窗户开在墙顶上,一束斜阳悠悠地射进来,王曲曲面色苍白地坐在床边。
王曲曲见我进去,站起了身,表情拘谨。弟弟很诧异,并悄悄示我以赞许。我有些感动,我不知道是否因为黄昏斜阳的感伤诱惑,王曲曲才给我以特殊的礼遇。
我拉着王曲曲坐在床边,王曲曲的眼圈很黑,头发很乱,头顶的那撮头发横七竖八地翘起。我有点心酸。
我说:由由很想你。
王曲曲愣了一下。
我说:由由现在玩那个游戏,因为没了厉害的人帮手,老是打不过关,由由说,什么时候曲曲哥才能教他玩啊?只要曲曲哥来了就一定能过得了的。我告诉他,曲曲哥再要和你玩,不可能再那么没黑没夜的了,我会管住他。
这时,王曲曲看着我发涩的眼睛,愣了愣,叫了一声阿姨。这是王曲曲在妈妈死后说过的第三句话。前面两句是,我没杀妈妈。我杀了妈妈。
我的心很热。做心理的人通常是理性的,冷静的,但此时我的心很热。
我说:我要把你带出去,可今天不行,以后行不行,那就看你了。
王曲曲不再说话。我把语气放得尽可能的温和,说:你不想离开这里?
王曲曲的头动了动,像是点头,又像是摇头,很小声音地说,离开这里,我去哪里?
王曲曲不再说什么。
我说,曲曲,我联系了你爸爸。王曲曲的头抬了抬。
我说,我已经和你爸爸联系上了,我会和他见面。王曲曲脸色惨白,不言语。他的双手在相互搓着,很轻,几乎看不出。
我看到王曲曲头顶那撮胡乱翘起的头发,还有滴在地上的泪水。
七
我在茶楼等王大曲。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开着奔驰车过来,下车,锁车,走过来,每个动作姿势都有一股“奔驰”味儿。说实话,我只觉得那味儿只取了奔驰车的霸气和招摇,却没有霸气里的那种高贵。
王大曲是地道的本地人,本地人中有这般高大身材的男人确实不多,这大概是王大曲有着那种步态的最初起因。王大曲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靠着水路让人不明就里地发了大财,这些年生意虽然清淡,但底子很厚,不影响他五光十色的生活。
王大曲看我的眼神是居高临下的,却又似乎因为没有足够的底气而有些游移。王大曲把车钥匙和最新款的手机往桌子上一放,脸色铁青地说:我想揍死他!那衰仔!
我的语气不大客气,说:现在可能不是揍不揍死他的问题,他现在在少管所里,我直觉他没有杀他的母亲。
王大曲对我的态度很不高兴,说:他没杀?谁杀了?香梅还会自杀啊?香梅那八婆一样的性子,不杀别人就不错啦!你这样看我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还杀我的女人不是啦?我就是要杀人,也不杀香梅啦,我会杀了那衰仔!那个不争气的衰仔,让我受了多少闲气,告状,转学,退学,上网,旷课,逃学,打架,从来没一件好事,就是再在意他的老子,心也凉了,我又不是他一个儿子,我要个个儿子都和他一样,那我早死了几百回啦。
我说:我想问问你的私隐,很冒昧,刘香梅是你第几个女人?
王大曲一听,把身子往后面一靠,很不以为然地说:哎,你这话说得不对啦,第几个女人,这就不好说啦,几个老婆我就可以说,香梅是老二。
我有些好奇,说:你们领证了吗?
王大曲说:怎么领?没证,没证也是老婆啊,生了崽,得买房子得花钱养啊,别的女人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王大曲得意的面孔油光发亮。我说,王曲曲出来后,他去哪里?你打算怎么办?
王大曲一下子颓丧下来,大声说: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杀人了,我都敢留啊!就让他在少管所,那里最合适,我怕了他了,我怕了他,他今天可以杀他妈,还不知哪天把我也宰了。
我说:要是他没杀人呢?
王大曲看着我,有些愣,这大概是他没有想过的问题。在他看来,生崽就和养小猪一样,生下来,丢给女人,然后再丢一些钱。现在,问题没那么简单了。
我说:曲曲可能没杀他妈妈,你帮帮你的儿子,有什么线索告诉我。
王大曲真的愣了。他本来全当王曲曲死了,现在王曲曲没死,照顾他的妈妈刘香梅死了。
从茶室出来,我很心灰,为那个在高墙里被两个看守把门的11岁的孩子,那个渴望强大的爸爸拯救他的孩子。
八
我带王曲曲离开了少管所。当然只是暂时的。我把他带到我的工作室,我想找出他的那段失去的记忆。我的弟弟一直陪着,我只让他在外间等候。
我的工作室的最里间是沙盘室,沙盘室有各种各样的小模型,都是日常用具。我让王曲曲在沙盘上随心所欲地搭他想搭的东西。
我以为王曲曲会搭一个电脑台。但不是。王曲曲看了那些模型,搭了一个家。家里的陈设很简单,只是一个客厅,两个单人沙发,一把椅子。然后,王曲曲拿了两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孩子,两人放在地上,面对面坐着,然后在两人之间放了一个棋盘。他把妈妈放在什么地方?
椅子本来放在沙发旁边,他拿了一个女人,是妈妈,他把妈妈放在椅子上。看看不对,他拿着那个放着妈妈的椅子一直往外移,移到门边,没地方再移了,才停下。开始妈妈的脸是朝着他们的,想了想,他把妈妈的身子和椅子换了一个面,于是妈妈便背对着他们俩了。
我解读这个图形,他希望妈妈离他越远越好,最好不要看着他,他甚至希望他的妈妈不再存在。
王曲曲停了下来。
我说,还能继续吗?
王曲曲想了想。妈妈没有动,他把爸爸放在沙发上,先把自己放在另一个沙发上,随后又把自己放在爸爸的腿上,用爸爸的手臂抱住他。
王曲曲搭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搭了一个房间,刘香梅的卧室。我把一个孩子放在王曲曲的手里,让他放在他想放的位置。王曲曲的脸一下子煞白,手迟迟放不下去。他的这段记忆仍是空白。
我牵着他的手往外面走。我的弟弟跟在后面,我的弟弟腰上有枪。
初春的珠海有些冷,今年更甚。我打了一个寒噤。王曲曲也打了一个寒噤。我搂着他的肩,感到从他身体里面透出来的冰凉,他的浑身有点哆嗦。
王曲曲被弟弟送回去时,背影有些佝偻,一个11岁孩子的佝偻。
我在工作室给王大曲打了电话。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王大曲极不情愿地来了我的工作室。我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搭的模型。
王大曲看完模型,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声,这衰仔!
王大曲没再说什么。离开时,说了一声谢谢。我送他上车,这次他的车开得有点慢。
我的弟弟告诉我,王曲曲回少管所后,总在半夜醒来,尖叫,然后一身冷汗,全身湿透。这信息让我兴奋。王曲曲在逐渐恢复那段记忆。
九
我没想到,那天深夜,我接到王大曲的电话。王大曲从没主动给我打过电话。王大曲说要见我,给我看一样东西,问我住在哪里,他送过来。
我在我家的小区门口等到了王大曲。王大曲给我一封信,是刘香梅的信。王大曲很少开信箱,刚刚才发现。
刘香梅的这封信给我的惊骇不亚于她的死亡。我从来没想过,大大咧咧的刘香梅有如此丰富的内心,我也没想到没念完高中沉湎麻将的刘香梅有如此细腻的文笔。
那封信的日期是1月25日,也就是死前的一个星期。
信中写道——
老公,我活得很累,很腻。没有男人的日子本来是很乏很空的,我却活得很腻。我的腻,在没有希望的等待里,在学校没休没止的告状里,在曲曲永远关着的门里。曲曲缝针时很疼,却不叫一声妈。老公,我真的很累很腻。
我是麻将鬼,死了还把麻将带到棺材里去。你和曲曲都这样说。可你们没有人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麻将。你知道每次散场后,我心里的空虚么!打麻将就像吸毒,谁会喜欢毒品呢,吸了难受,不吸更难受。老公,我为什么活着,活着是为什么?我只有打麻将,天天打,时时刻刻打,不打麻将,我又能做什么?我真像你说的,没出息,连生的孩子都没出息。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你说你大婆贤惠。你在外面怎么花女人,她都不闻不问,照样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尽职尽责。可是,你尽职尽责了么?当初我和你好,以为自己进了天堂,以为这辈子有了倚靠,可是,这个倚靠就是每个月给一些钱。你说那几年我不该和你闹,可你的心不在了,我不闹又能怎么样?但我闹了,又能怎么样?你知道我心里的痛么?你说女人要贤惠,你要的这种贤惠,我做不到,我只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和自己的男人好好地过日子。
曲曲今天缝了21针,没有哭。你也没有来看他。曲曲无药可救了,我也无药可救了。这日子,真的好难,太难了。
信的落款是,深爱你的香梅。
王大曲拿回了信,说,我那时是好喜欢香梅的,有才,每天给我写一封信,信写得好好,你都看到了,我小学都没毕业,娶个这样有才的女人,生个孩子一定聪明啦,曲曲真是好聪明啦,可那些年,她天天和我闹,天天闹,闹了几年,闹得我心灰意冷,孩子的教育也耽搁了。北方的女人我是怕了,广东女人就是好。女人嘛,就要忍受一点,谦让一点,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好了么?
我说:我倒是觉得香梅真的睁一眼闭一眼的,对你不闻不问。
王大曲叹气道:那是闹累了,那不是睁一眼闭一眼,她那是坐吃等死,除了麻将还是麻将,家不像家,妈不像妈,女人不像女人,你说,这样的女人我还有什么兴趣,我连想到他们母子两个都累,除了每个月给他们一些钱,懒得见他们,免得见了心烦。
王大曲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我也没话可说,只是看着远处的街灯,闪闪烁烁的,鬼气精灵。
王大曲突然说:香梅不是曲曲杀的,曲曲不会杀他妈妈。
一会儿,王大曲又说:香梅心直口快,什么事说完就完了,不放在心上,她不会自杀,不会的。
我看着王大曲的脸,这张在夜色里也能看出保养得很好的脸,和王曲曲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有着上天入地般的差别。我突然很刻薄地说:那你到底希望事实是怎么样的?香梅是曲曲杀的?还是香梅自杀?
王大曲突然用手蒙住脸,哽咽出声。
十
刘香梅的信让我内心的负疚减轻了很多。我们开始相信,刘香梅是自杀。
可是,刘香梅自杀时为什么王曲曲在现场?为什么除了水果刀,还有一把塑料刀?为什么电脑呈录像状态?那个U盘到底在哪里?
把王曲曲带回家,这很残酷的,但别无它辙。
之前,弟弟差人打扫了房间,但所有物件保持不变。我放了两个苹果在刘香梅的床头柜上,还放了一把和刘香梅自杀用的相同的水果刀。
王曲曲进了刘香梅的卧室,脸色煞白。我坐在刘香梅的床上,拿起水果刀给王曲曲削苹果。我留意着王曲曲的表情。
王曲曲看着我的手,不,看着我手中的水果刀。突然,王曲曲冲过来,抓住我的手,全身发抖。我用手按着他的肩膀。我看到他的眼里全是惊惧。他拉着我出了家门,站在我母亲家的门口。那天黎明时分,他就是全身血迹地站在那个位置敲我母亲的门。
门上有一个牛奶箱。王曲曲指指牛奶箱。牛奶箱是开放着的,我伸手进去,我摸到了一样东西——U盘。
我拿出U盘,上面布满了指纹,血色的指纹。
一直悄悄跟随着我的弟弟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用纸巾包着手指,拿过了U盘。
在另一个刑警的陪同下,王曲曲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书房那台台式电脑依旧原封不动,但王曲曲连碰都不碰,只是傻呆地坐着。
我和弟弟在家里打开了U盘。画面,摄人心魄。
王曲曲拿着刀一步一步地走近刘香梅,刘香梅熟睡。王曲曲将刀对准刘香梅的脖子,这时,刘香梅惊醒,一下坐起来。王曲曲手中的刀,是塑料刀。刘香梅惊恐地瞪着眼睛看着王曲曲,说:你这么讨厌我?连你都这么讨厌我?王曲曲傻了,塑料刀掉到地上。刘香梅想捡起塑料刀,可是她看见了床头柜上的水果刀,她拿起水果刀往脖子上一抹,血刹那间四处飞溅。刘香梅没有立刻倒下,而是看着王曲曲,笑笑地说,这下,你们都好了,你爸爸好了,你也好了,你们再也没人讨厌了。
我看了录像,走到王曲曲身边。我轻声问,你根本没杀你的妈妈,你只是用塑料刀和你妈妈闹着玩。
王曲曲摇头,拉着我的手,走到客厅,看着墙边上一条电线发呆。那是上网的宽带线。
我轻声说,曲曲,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曲曲的语言是断断续续的。他断断续续的语言,还原了整个案件的原委。
那天,王曲曲这个工会副会长正带领着公会的全部精英,向全服务器最强的boss发起挑战,迄今为止,从没有一个工会战胜过这个boss。他,王曲曲,将会改写历史。那样,他们的工会将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全服最强,不折不扣!
王曲曲带着他的队伍在通往boss的曲折的崎岖的狭长的山洞里行进,那真是一段千难万险的征途!每前进几步就遭遇强大的狙击,但他们依然在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boss的老巢靠近。
战斗比预想的还要艰险,已经持续了11个小时了,从上午9点,现在已是晚上8点。团灭了4次!每一次都在boss还剩百分之十几血命悬一线时,总因个别人的一点操作失误,而使瞬间团灭。王曲曲昂扬激越,在公会聊天里摇臂呐喊:这是一场血战,一场真正的战斗!兄弟们,前面就是胜利的希望!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拿下,一定能!全服务器第一是我们的!”
前四次的艰辛战斗,为他们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次,他们很快就来到了boss的身边,最后的战斗开始了!
屏幕上到处是炫目的技能效果!王曲曲的左手娴熟地敲击着键盘,右手的鼠标总在第一时间对准最佳的进攻角度,这个公会副会长的一流操作,没有任何失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boss巨大的血条不断减少:百分之75,百分之50,百分之25,百分之10,百分之5……
突然,电脑房门被“砰”地撞开。王曲曲吓了一跳,眼睛不敢离开电脑,只是用余光看到冲进来的妈妈。妈妈手里拿着他的数学试卷,那张试卷他得了10分。
天啊,我怎么没把试卷藏好,偏偏在节骨眼上出事?!但王曲曲哪顾得上跟妈妈多说,只能口中大喊:妈妈,再给我10分钟,不,不,5分钟就行!求你了!求你了!
王曲曲的手丝毫不敢停!只要他有一丝失误,就全盘皆输了,这场阵容最齐全最强大的战斗就会功亏一篑,他就是公会的罪人了!
气急败坏的刘香梅哪能明白这个。刘香梅冲了过去,想拔了电脑的电源。可王曲曲用身体保护着电脑,一边保护着,一边还在全神贯注地操作键盘。
刘香梅转身走到客厅,拿起剪刀,将宽带网线拽下来,一卡两断。
书房里,电脑画面噶然而止,王曲曲的心跳也嘎然而止!他的手猛烈地颤动着,脸比平时更加阴沉,双眼迸着火花。
王曲曲放了电脑,跑出房间,像一只小疯狗一样往刘香梅身上扑。刘香梅从来没见过王曲曲这样,刘香梅把王曲曲使劲一推,王曲曲再次扑过去。这时,刘香梅举起手里的剪刀,刀尖对了一会儿王曲曲,又对了一会自己,说,你过来,你过来,要不你死,要不我死。
王曲曲停止了反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一瞬间,他只有一个念头,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王曲曲回到书房,把门锁好,脑子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妈妈敲门,他斜靠在电脑椅上,懒得理会。如今,他是公会的罪人!门敲了好一会,停了。又过了好久,妈妈进了卧室。夜很深了,他听到了妈妈的鼾声。
时间好长!这么长的时间里,王曲曲策划着一个行动。他看着那断了网线的电脑,觉得应该玩一个新游戏了,全新的游戏,别人从来没有玩过的。
他蹑手蹑脚地把另一台手提电脑搬进母亲的房间,然后接上摄像头,把镜头对准熟睡的母亲。他打开了电脑,调试了摄像程序。然后,他从他的玩具箱里找出一把塑料刀,很像真家伙的塑料刀,他举着刀,慢慢走近妈妈。妈妈睡得很熟,发出极大的鼾声。在那一瞬间,在王曲曲的脑子里,有两个影像重叠在一起,一个是鼾声大作的母亲,一个是他的终极敌人boss。
他一步一步地向母亲或者那个boss靠近,手握着刀。刚才嘎然中止的刺激和兴奋又回来了。他在继续着那场中断的战斗,战斗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了!他的心狂跳着,他的眼睛因为狂喜而溢满了眼泪,他几乎看不清敌人的面容。他举起了刀,对准了脖子的动脉的部位,他手上的刀在睡眠灯下发出微微的白光,他一刀割下去。
这时, boss一下子坐起来,不是boss,是妈妈。
他吓呆了。妈妈看到了他手中的刀,瞪着眼睛看着他,然后,拿了床边的水果刀,往脖子上一抹。一股东西飞溅出来,喷射到他身上,他闻到了很浓血腥味。在网上。他从来没闻过这种气味。
十一
少管所挺大,从王曲曲的房间到大门口有很长一段路。我走在后面,由由和王曲曲走在前面。
由由拉着王曲曲活蹦乱跳的,和王曲曲说着网游。刘香梅去世后,由由的爸爸就绝对禁止由由玩网游。由由的爸爸还每次都用王曲曲做活教材训斥我和由由,还玩网游么?王曲曲这就是最好的样板!
但由由一看见曲曲,还是说网游,尽管说的都是以前的游戏。王曲曲好像在听,又好像根本没听。由由也不管不顾王曲曲的反应,只是一个劲地说。9岁的由由不会明白,看着妈妈惨死的孩子心里想的什么。不仅由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王曲曲走出少管所大门的时候,愣了好久。王大曲的车停在路边。我没想到王大曲会来。我本打算先把王曲曲接到我家,然后再作安排。
王大曲没有下车,只是打开车窗用嘴示意王曲曲上车,坐副驾驶位。王曲曲机械地走过去,王大曲在车里把另一边的门打开。
车玻璃蒙着黑色的膜,车里光线很暗,我看不清王曲曲的表情,看不清他是不是在流泪。王曲曲最后一次坐爸爸的车是小学一年级,6岁,那时,他学习不错,爸爸有时不仅送他,还会接。后来,他再也没坐过爸爸的车。
过了一段时间,王大曲打电话来,执意要请我吃一餐饭,说想和我聊聊。我去了,我也想和他聊聊。
王大曲依然开着奔驰车,但动作不再那样霸气招摇。王大曲以最高规格宴请我,弄得我不大自在。王大曲说,应该的。
王大曲在外面弄了一套房,把刘香梅的妹妹接过来照顾王曲曲,他自己每天都过去陪他们吃饭。王大曲为王曲曲请了两个家教,一个教写作,一个教美术。两样,王曲曲都喜欢。
王大曲说:学校干么都要学什么那些课本?我家曲曲不喜欢那些,不喜欢就不学!我小学也没上完啦,活得不好好么?你不要不相信,我还让他玩网游,我就让他玩!这世上让人上瘾的东西多着啦,吸白粉啦,赌博啦,抠靓女啦,多的是,哪一样不让人上瘾,做大人的管得完么?这成事的人,得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你看,现在我家曲曲每天学写东西,画画,学得快活啦,下午玩玩游戏,你叫他整天玩,他都不玩了!
我不得不对这个男人另眼相看了。我发现,成功的人,无论哪种类型,无一例外都有过人之处。我想,那么多女人对他趋之若鹜,不仅仅是为钱吧?刘香梅是这样,其他的女人大概也是这样。
王大曲后来决定要把王曲曲送去香港的一所私人学校,这学校是我介绍的,很多有心理创伤的孩子在那里都得到康复。康复后,王曲曲再转到正常的学校去。
王曲曲临走前,来家里收拾了一些东西。我们一家三口在楼下送了王曲曲。由由对曲曲有点依依不舍,说,那我们以后可难见面了?王曲曲点头。
由由说:那里有网游玩么?王曲曲摇头。
由由说:真没劲!
王曲曲说:不玩网游也没什么的。王曲曲说的很淡然。
那天,我终于问了我一直疑惑的问题,为什么王曲曲不排斥我。王曲曲想了想,说,说不好,你从来不大声对由由说话,你还让由由玩网游。
我把王大曲叫到一边。我说,其实曲曲要的东西,那学校也未必能给。王大曲说,我知道啦,我明白这衰仔啦,香港那边我有业务,经常去,去了就去看看他啦。
我点点头。
王曲曲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家的窗户,眼里有泪。
王曲曲的车走远。由由拉着我的手,看着他的爸爸,央求道:曲曲哥没事了,以后我可以玩网游么?
由由爸爸说: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