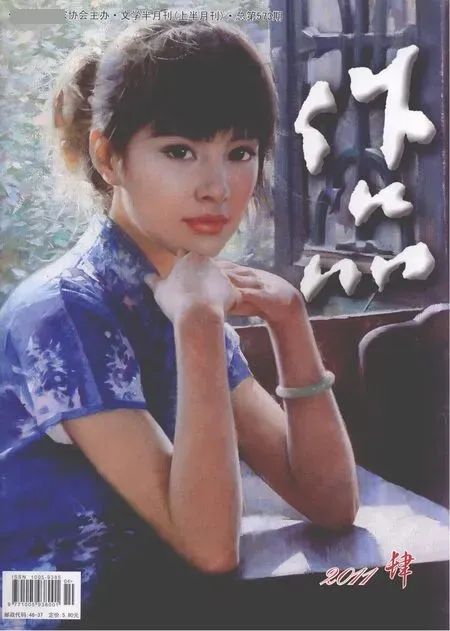歌
□江 子
1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歌,这句话大抵是不会错的。一个国家要有国歌,一个民族也理所当然地拥有自己民族的长歌短曲——她的自然、气候、物产、风俗、历史也都在一首首歌中。一部电影有主题歌,一个稍有规模的会议要有会歌,这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情。在哪怕最为凋敝的民间,更会有疑似下流不堪其实风情万种的民歌在肆意流传,仿佛野花在荒野粲然开放,或者河水在大地上奔流不息。
1927年10月,有一支队伍从长沙越过湘赣边境,过铜鼓,穿萍乡,抵莲花,跌跌撞撞地向罗霄山脉中段奔去。他们是长沙兵败后被迫退却的秋收起义队伍。他们看起来衣衫不整,士气不振,也许出于对前途的担心,担架上面目模糊的伤员的哀叫声显得略有些夸张。随着大量的非正常减员(路上对手的围追堵截,以上厕所为理由或者借黄昏为掩护逃跑),这支队伍的枪似乎越来越多,而队形越来越短,最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背了两到三支枪,以至每到列队集合时都只听到一阵凌乱不堪稀稀拉拉的枪支碰撞的声音。这是一支几乎是毫无来头还说不出名堂的队伍。这样一支队伍从脱身于国民革命军集结湘赣两省到兵败退却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还没有自己统一的旗号、军服,还来不及整肃军纪号令,当然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歌。他们只是一堆不成调的音符,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的节奏、声线、乐谱和调门。
他们一进入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就开始整编队伍,颁布纪律,打土豪,分田地,辟圩场,圈地盘,结交四方朋友,探索革命新途。原本偏僻的井冈山,变得热闹,原本绿森森的山谷深处,到处是红色的口号书写,红色的旗帜飘舞。
2
江治华是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草林镇的一名青年农民,是草林镇百里挑一的好后生。江治华比现在更少年的时候,十里八乡的媒婆都争着给他做媒。她们走到哪里,就把江治华夸到哪里。她们说江治华模子周正,勤快本分,人品高,八字好,上山捉得到猛兽,下河摸得到脚鱼,树上打得到鸟,走路捡得到金子。更值得夸赞的是,江治华还唱得一手好歌。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有时候他在上山的路上唱起了歌——打只山歌过只岭,满山竹子青又青。茅草底下石阶路,弯弯曲曲到草林……所有和他一起上路的人都感觉脚下驾起了浮云,而如果在山林里伐竹驮木,当他的歌响起,所有在山上各自为阵的劳作就似乎有了指挥,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的整体行动,江治华喊着号子的歌声成了这支队伍的号令。江治华在劳动的时候唱,在休息的时候也会唱,比如在有月光的夜晚,江治华的歌声就会一反劳作时候的粗犷洪亮,变得深沉温婉,充满了一个男人的柔情和伤感。每当此时,会有多少邻家女子借故从他家走过,目的就是为了听一两声他的歌声!
包括遂川县在内的井冈山地区,是个盛产歌谣的地方。井冈山多山。山上多林木,就有了砍伐和搬运。就有了热气腾腾的伐木号子在山林回荡。生存产生哲学,劳动创造美,井冈山人的山区生活自然就需要山歌陪伴,那些从山民心里自然唱出的歌谣就如林木葱郁如山路绵延如山泉跌宕奔腾。井冈山多客家子弟,他们带来了属于自己民系的歌。他们的一句“哎呀嘞”,是歹命人的叹息,还是爱人的表白?是对经过家门的清风明月的殷勤挽留,还是对正走出山门的亲人们的依依送别?百感交集的一声“哎呀嘞——”,唱出了客家人的曲折婉转的心路历程,成为客家人在声带上的地理标识!在偏僻的山区,井冈山人用歌声指挥劳动,表达爱情,慰藉心灵。草林镇的好后生江治华,正是这漫山遍野的井冈山民间歌者中的出色的明星……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一天,草林镇的好后生江治华参了军,成了一名穿灰布军装打绑腿的井冈山红军战士。红军在草林镇开辟了红色圩场,江治华把山上砍来的树木给红军换了银子。红军在草林镇刷了许多标语,做完买卖的江治华看得有些痴。红军在草林镇招兵买马,江治华毅然地把自己交给了红军。那时候,在井冈山地区,好后生就应该当红军,进步的青年就应该上战场建功立业。参军打仗,可是一件时髦的事儿!
革命的队伍里人尽其才,唱一手好歌的江治华,做了一名管宣传的兵。
3
穿上军装的江治华发现这个世界完全变了样。平常的走路叫“行军”,睡觉叫“宿营”,战士相互间称作“同志”,过去自己称作叔伯姑婶的父老乡亲现在统一成了群众或老乡。原本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山体,现在统统改了名,山头叫制高点,山坳叫伏击区或埋伏圈,挖条壕沟叫做掩体。最寻常的站立,要挺胸,收腹,姿势分立定和稍息……
江治华经常把这些新名词和旧名词混淆——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要完全熟悉部队上的叫法,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经过一定的军事和政治训练,江治华学会了刺杀和瞄准,了解了革命与主义。参加了几次战斗,江治华听惯了呼啸的枪声,看惯了流血牺牲。这个军中的民歌王子要歌唱,他要把他最喜欢的歌献给他的战友们,那些从战场上刚刚归来的可爱的人,躺在担架上血肉模糊的人,还有身体的热气还没有散去的刚刚捐躯的人。他唱:“高山顶上唱山歌,唔晓(方言,不知道)妹在哪只窝。唔晓妹在哪只岽,等我妹妹来回歌(遂川民歌《等我妹妹来回歌》)。”
“哎呀嘞——石壁流水流下河,哪有河里莳得禾。你冇年纪大(方言,意为没有多少年纪)的心肝哥,自己的老婆都靠不得,哪有靠得伙计婆(方言,意为情人,特指女方)。
“哎呀嘞——石壁流水流下河,哪有河里莳得禾。你冇年纪大的心肝妹,自己的老公都靠不得,哪有靠得浪荡哥(遂川民歌《石壁流水流下河》)。”
他满腔热情地唱。在许多地方他还卖力地加花,让一些原本平常的音节变得峭拔生动。他会把“哎呀嘞——”尽可能地唱得婉转悠扬波浪起伏。他的歌声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战士们的广泛兴趣——是的,不管何时何地,没有人会拒绝美好的、嗓音悦耳的歌唱。在这远天远地的井冈山地区,有多少伤员会因为聆听江治华唱歌而暂时忘记了疼痛?有没有人在江治华的歌声中偷偷想念起故乡?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江治华肯定受到了军中战士的热烈欢迎,井冈山的人们说起江治华,无不响起啧啧的赞美声。
可是人们很快厌倦了他的歌唱。他天天唱伐木号子,可他的听众并不是扛着斧头的伐木者,而是背着枪的战士。他一再唱起表达男欢女爱情感热烈的当地情歌,可后来忙于操练的战士们只是不痛不痒地笑了几声。是呀,他的歌声中并没有战士们的生活战士们的情感,怎么可以引起他们长久不衰的回应呢?
江治华开始与他的战友们一起钻军营下连队,向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请教南腔北调的民歌,听战士们讲述他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每次部队攻城拔寨,江治华在刷写标语之余就是到田间地头寻访当地的民歌手,了解当地的民歌,记录下每句词每个音符。江治华把这些叫做素材,他相信,那厚厚的记录下来的歌本里,会孕育出一支连队那么大数量的歌曲。
在井冈山严酷的战争年代,有一支小分队的使命特殊而浪漫。他们除了要在前线打仗,还要负责创作和演唱,捕捉整个队伍的情感和行动的节奏,用歌声记录这段历史的心灵真相。而江治华是这支小分队中的一员。
明晃晃的月光下,江治华们躺在垫着稻草的床铺上久久不肯入睡。他们在考虑怎么对现有的调子进行改造,怎样填写出有新意的词来。他们要通过音乐,唱出这一支特别队伍的历史、情绪、节奏和调门。
他们写到:“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嘿罗嘿、挖野菜那个当粮罗嘿罗嘿,毛主席和我们一起罗嘿罗嘿,天天打胜仗打胜仗……”“啊呀勒,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小心路上就有石头,碰到阿哥的脚趾头,疼在老妹的心里头……”“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带来工农革命军,红旗飘飘闹革命。千恩万谢毛委员,工农革命掌政权;穷人翻身做主人,革命到底心不变。当兵不要当白军,白军给人指背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哥当红军妹光荣。”
黄洋界保卫战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战胜了国民党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对这次胜利,他们改编了京剧剧目,写出了井冈山版的《空城计》。他们唱到:“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介石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在茨坪的红军造币厂里,战士们在抓紧铸造属于红军自己的货币,在新铸的银元上,他们小心地打上“工”字标记,以区别国民党统治区的银圆货币。在茅坪的红军驻地,军中秀才们抓紧撰写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旨在解决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任务。在一本泛黄的、纸张粗糙的本子上,江治华抄写了数十首歌曲,其中既有当地的许多民歌,又有自己和战友们创作的歌。在这个歌本的封面上,江治华郑重地写上“红军歌谣”。苦出身、读书不多的缘故,江治华的字写得并不太好,其中还有不少白字,可是他并不介意,因为上面的歌曲,已经传唱至井冈山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也许并不完全合乎音律的歌曲,使残酷的战场变得抒情浪漫,艰苦的生活,有了修辞意义上的美学价值,一直原本喑哑的队伍,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4
江满凤出生于遂川县草林镇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成年后嫁到井冈山小井村一个普通农家做媳妇,后来成了井冈山龙潭景区一名月薪七百来元的保洁员。江满凤是井冈山地区极其普通的那类人——是井冈山任何山旮旯水疙瘩都可以碰见的称作“表嫂”中的一个。这样的女子热爱劳动不过是本分,这样的女子走在路上毫不引人注目。
可与其他的井冈山女子相比,江满凤还是有其非同凡响之处,是个特别爱唱歌的女子,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整个家乡草林镇几乎都知道她爱唱歌。江满凤到学校上学,到镇上赶集,在田野劳动,都喜欢让自己的歌声陪伴。江满凤的歌的确是唱得好,她唱节奏舒缓感情沉郁的歌会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而节奏明快的歌会让人产生通体舒泰的愉悦。江满凤嫁了人,江满凤做了母亲,江满凤成了井冈山龙潭景区的保洁员,可不管她的身份怎么变化,只要有江满凤的地方,就会有她的歌声如影随形。
江满凤很小的时候唱过《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唱京剧《红灯记》李铁梅选段,从小到大都喜欢唱遂川民歌。比如她会唱:“高山顶上唱山歌,唔晓妹在哪只窝。唔晓妹在哪只岽,等我妹妹来回歌。”江满凤最喜欢的歌还是井冈山红色歌谣。她会唱:“送郎当红军,革命要认清,豪绅呐地主呀,剥削我穷人,哎呀我的郎我的郎。”“红军鞋,红军鞋,红军鞋……苏区的乡亲送给我这双鞋,棉布的鞋帮密密的针线,千层底上绣的字,激荡了我的心……(《红军鞋》)”在所有的井冈山的红色歌谣中,江满凤最喜欢唱的歌是《红军哥哥你慢慢走》:“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小心路上就有石头。疼到阿哥脚趾头,疼在老妹的心啊头。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走到天边又记心头,老妹等哟你长相守,老妹等你哟到白头。”这首歌本就是女声,是表现特殊时期井冈山女性情感和命运的歌,理所当然地被井冈山女儿江满凤所喜爱。江满凤唱这首歌最是投入,仿佛她自己就是歌里唱的当年亲手送走情郎然后守望白头的井冈山妇女。她用全部的身心唱,每次都把人的心都唱疼了。
江满凤的歌声有一种青山绿水中浸润的宛如天籁的甜美悠扬,以及井冈山寻常百姓与生俱来的纯朴、热情、泼辣,和与井冈山红色历史相得益彰的哀伤、疼痛,以及一块土地经过生死锤炼大难不死之后的平静。这是一种让人悲喜交集的声音,因为没有经过科班训练所以更是情真意切,因为无欲无求所以最为大俗大雅。这样的歌声,怎么能不从那些装腔作势的流行歌曲中脱颖而出?这样的歌声,怎么能不被人喜欢?
江满凤的声带上,有与井冈山地理和历史相对应的密码。江满凤以井冈山做舞台,一边为井冈山景区清洁,一边唱起歌来。她一唱多年,有了无数南来北往的“粉丝”,比如爱写博客的游人,好事的媒体记者,采风的文化人,来井冈山受教的政府工作人员。江满凤的名声不胫而走,人们纷纷称她为“井冈百灵”,虽然这样的过于通俗的名号并不能完全概括江满凤的歌声,而在大家找到更加适宜的外号前,人们还是愿意这么称呼她。
山窝里有了金凤凰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许多沿海开放城市的商业演出机构慕名纷纷邀请江满凤走出山门。对商人们来说,江满凤的歌声是可以盈利的商品,只要她愿意,经过他们的包装,她的声带完全可以成为一条财富的跑道。可是江满凤没有答应。她还是守在井冈山,安分守己地做着保洁员的工作。她说,唱民歌的怎么可以离开自己的故乡呢?唱红歌,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舞台。
江满凤还是有一天走出了山门,去了首都北京。那是反映红军历史的电视剧《红色摇篮》剧组邀请她演唱《红军阿哥你慢慢走》。那是一次荣誉之旅,井冈山的环卫工人江满凤,从来没有学过一天演唱的江满凤,来到了北京,在灯光晃眼的录音棚里,毫不怯场地唱起了《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她的样子朴实得与录音棚的环境毫不相称,可她的歌唱让专业的歌手习惯舞台的明星大腕都自愧弗如。江满凤用她的本色演唱,征服了剧组几乎所有的人。
为了感谢她的演唱,导演要按市场规则给江满凤一笔丰厚的报酬。那会是江满凤做保洁工作数十年才会得到的一笔巨款。她本来完全可以受之无愧地收下这笔钱,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江满凤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钱。她说我不要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片尾这首歌的作者一栏里,打上一个名字。他是这首歌的真正作者,也是她从未谋面的祖父,他的名字叫做:江治华。
5
1930年前后,井冈山著名的红色军营里的民歌王子,在一场战斗中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死于这场战斗,只是井冈山山高林密,他的尸体或许被炮火改变的山体掩埋,或者不慎滚落到僻静的无人能发现的山沟里。有人说他也有可能被国民党俘虏,在辗转的过程中患病或战争原因客死他乡。江治华到底去了哪里?没有人知晓。而从此这世上,再也无人听到过江治华的歌声。
江治华失踪后他在遂川草林镇的家一片狼藉。短暂的悲伤后他的妻子毅然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井冈山女性坚强而勤快。井冈山女性从不畏惧苦难。数十年来,江治华的妻子承受着战争带来的伤害,在穷乡僻壤的、经过战争劫难的遂川县草林镇,含辛茹苦把江治华的遗孤养大成人。
年年清明江治华的家人都尴尬万分。没有了顶梁柱,生活照样可以延续,虽然有时候会捉襟见肘。但因为没有江治华的肉身为证,没有江治华确切的死亡消息,遂川草林的青山绿水之间,没有一座墓碑上写着江治华名字的坟,这给他们一家的清明祭奠先人活动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他们的悲伤无所凭依。他们的祭扫多少显得凌空蹈虚。他们只能向着井冈山的方向潦草烧几把纸钱,对着远方的青山祭几次酒了事。
江治华的血脉在井冈山延续。多年以后,江治华有了孙女江满凤。从小喜欢唱歌的江满凤天真活泼,和平年代里长大的她无忧无虑。可有一天,江满凤在家里翻到一个泛黄的、纸张粗糙的本子,上面写着“红军歌谣”,里面有30多首红军时期的歌。她的祖母说,那是她祖父的遗物。里面歪歪扭扭的字迹,是祖父的亲笔。轻轻吟唱着歌本上的红色歌谣,江满凤知道了自己有一个红军祖父。他喜欢唱歌成为井冈山管宣传的兵,留下了一本泛黄的歌本自己却不知所终。他有一颗赤诚的革命的心,这世上却没有一座可供后人凭吊的坟。江满凤从此知道了,所谓的井冈山的历史,不再仅仅是纸上的渲染,政治课上的说教,博物馆里的讲解,还是她的家族无法愈合的伤口,她的血脉里隐埋的痛楚,自己家的一本遗物上的歌声。而她自己,何尝不是,那段历史的一件遗物。
从此江满凤更是爱上了歌唱。她用她的祖父遗传给她的一副好歌喉,来探问她祖父的去向。她的歌声传遍了井冈山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长眠于地下的江治华是否会听见?通过歌唱,江满凤能否感受到从没有享受过的与祖父相依相偎的亲情的温暖和幸福?
谁说江治华没有坟?那一本写着红军歌谣的泛黄歌本,就是他的最别致的坟。而江满凤的歌唱,就是对江治华最美的祭奠和怀念。
6
是在一次赴井冈山的文化采风活动中,我见到了江满凤。老实说,她给我的感觉是太普通了。她个子不高,脸上是风吹日晒的颜色,走起路来是干体力活的把式。她留短发,但没有型,似乎是乡村或城镇小理发店里的师傅所为,图的是方便,并无需美学意义上的考虑。她穿一身黑色的运动服,也不是为了漂亮,而是劳动时可以利索些。她戴一副墨镜,比起她的脸来,墨镜显得有些大,她不停地用手去扶那墨镜的脚,仿佛是担心墨镜会掉下来。她告诉我们,她的眼睛不太好,有较严重的结膜炎,戴眼镜是医生的嘱咐。她的话里有农家妇女仿佛妨碍了别人的歉意,带着明显的、井冈山地区的乡音。
她的样子,就像是农村中常见的邻家大嫂的样子,热情中露一点怯,朴实中带一点憨,认命的同时有一点倔,勤劳中含一点怨。然后我听到了她的歌声。是那首由她的红军祖父创作的《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只一句“哎呀嘞——”我就感觉到整个会议室有一股逼人的气浪汹涌。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走到天边又记心头,老妹等哟你长相守,老妹等你哟到白头。”
在让人悲喜交集的歌声中,我似乎看到当年的井冈山女子倚在门楣,眉心里隐约结了愁,可嘴角上努力绽开了笑。她挥动着手臂,做出告别的架势。而她前面的不远处,是穿着打了补丁的灰色军装准备远征的青年男子。他的身边,是万丈悬崖,和灿烂野花。爱在挽留,他会坠入悬崖还是手捧鲜花?战场的生死无可预料。恨还没说出口,那着灰色军装的爱人,便融入了脚步铿锵的灰色队伍之中。远山如黛,那已经破烂成条的红旗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一片苍茫暮色。
听着这用井冈山的风情和历史锻造的歌声,我感到多少年前的井冈山历史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