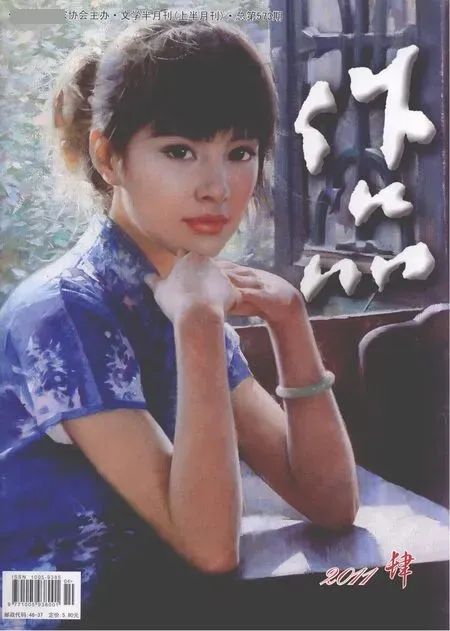好小说就应该悲天悯人——与滕肖澜聊天
◎梁 红 滕肖澜
以上海为背景的叙事,自张爱玲、王安忆之后,谁能引领风骚,一直是评论界瞩目的话题。滕肖澜以十年的写作生涯,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她的小说,在细屑幽微处,看得见柴米之外的心灵困惑,小人物的卑微中,强调着“生而平等”的倔强。娓娓道来的故事,平淡的叙述下波谲云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惊心动魄。她的小说,近年来常常登上各种选刊,而坊间读者,也因为其小说的“通俗”好读,而乐意捧场。
滕肖澜对敏感的诸如“你如何看待同为70后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这样的问题避而不答,只说自己,言词间,不故作高深,也不拽术语,简单率真。和她聊天,不必斟酌遣词造句,可心舒适。
梁红:你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吗?你的童年在哪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选择写作?
滕肖澜:我父母都是上海知青,在江西南昌工作。我出生在上海,由外婆抚养,十岁的时候去了南昌,十五岁又回上海了。我外婆家在浦东,是那种老式的弄堂。一个很大的天井,各门各户住着不同的屋子。起居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记得门牌地址是花园石桥路1号,后来拆迁了,现在“花园石桥路1号”变成了金茂大厦。虽然不见得是那么精确,但位置大致不错。我有一个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写的就是浦东这些年来的变化,与我小时候的这些印象分不开。老上海的感觉,像是素描,黑白色的,一笔一划却又很深刻。现在的上海,比那时斑斓得多了,当然这是表面现象,是上海给人的第一感觉。其实老百姓的日子,依旧还是黑白色的,一笔一划,一点儿也不花哨。
我一毕业便在机场,从事地勤工作。走上写作这条路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喜欢,试着写了,打印出来到处投稿,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信封上写着某某杂志社编辑部收,然后就寄出去。我觉得自己算是个非常幸运的人。这些自由投稿几乎都有回音,没碰太大的壁。我的第一篇小说《梦里的老鼠》发在《小说界》上,那时是2001年的夏天。这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就正式地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当然一开始写的并不多,主要还是兴趣,一年最多发个一、两篇。真正有规模地写作,大概要到零四、零五年以后了。
梁红:印象中,你的小说特别擅长“男女叙事”,背景都是上海,有这个都市的特色,风格细腻,可读性很强,这种“家长里短”的小说,琐碎寻常的细节,要想形成自己的特点,不太容易,但是你做到了。
滕肖澜: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都不怎么会写爱情。真正的爱情小说太难写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即便是感情再木讷的人,都有属于他(她)自己的爱情的期待与感受。作者煞费苦心写出的一个爱情故事,自己感动得要命,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陈词滥调,无甚新意可言。可爱情又不能太过天方夜谭,离现实太远,那便不是爱情而是神话了。所以我通常不直接写爱情,而把着重点放在爱情背后的东西上。像《倾国倾城》、《小么事》等,爱情有目的的,是别的东西的介质。当然这也不好,爱情毕竟是天底下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出于对美的事物的倡导与发扬,也不该老是这样。去年下半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大城小恋》,预计今年《收获》会发表。这篇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姐弟恋,双方条件天差地别,可两人就是相爱,爱得一塌糊涂。按我往常的写作习惯,也许会替这个爱情故事加上许多外插花的东西,让线索更加复杂些。可我尽量避免了。这也算是一种纯情的尝试吧。写的时候非常累。两人爱来爱去,除了爱没别的,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做文章,又不能太过单调乏味,真是需要一些耐性与坚持的。写完这篇后,我又写了一篇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中篇《拈花一剑》,是用纯文学的方式写一个古代的类似于武侠题材的小说。也算是一种休息与放松,在节奏上调整一下。后来这篇给了《上海文学》。编辑老师很好奇,问我,为啥会写这种小说?我想了半天,回答,中学时爱极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想找个机会过把瘾。
至于题材、风格方面,我并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刻意的限定。正如上面所述,我是想写什么便写什么,很随意的。但无论写什么,我都倾尽心力完成,绝不敷衍。这是我可以保证的。
您说我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是谬赞,很不敢当。至今我仍认为自己是个“新手”,处于生长阶段,需要在写作中进行反复地摸索与完善,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子。我会继续努力的。
梁红:我看了你近期大部分中篇小说,比如《倾国倾城》、《美丽的日子》、《小么事》、《爱会长大》等等。《爱会长大》写了一个上海“作”女的成长史:任性刁蛮的女主人公董珍珠,在生活中终于成长成熟。如果说这个小说还是你所擅长的“男女叙事”,那么《美丽的日子》,你开始关注上海的“外来媳妇”,或者说是上海另一个阶层的生活形态;而《倾国倾城》是职场版的“色戒”,最后女主角也选择了和“王佳芝”一样的道路:放过了她的猎物。《小么事》的顾怡宁,从一个清高的白领,变身为一个简直可以媲美特工的复仇女神,这和去年10月本刊刊发的大作《人间好戏》,有异曲同工之处。你的小说,已经开始突破单纯的“男女”,开始关注更多的社会因素,或者用一句政治术语来表述——关注社会的公平公正,关注被践踏的弱势群体,并且总是让主人公有办法伸张正义,强调“善”的力量,蔑视强权的蹂躏——你是不是特关心社会新闻,骨子里有种愤青劲儿?
滕肖澜:我在我的第一本作品集《十朵玫瑰》的后记里曾经写道:
“小说应该是悲天悯人的。当然,作者本身并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但至少,应该有一点责任感,把目光放远放宽,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广大老百姓,用笔勾勒出一个现实生活。”
我希望我的小说是丰满而有力量的,而不止是描写一些小情小感。对于社会上一些不怎么“和谐”的现象,不应该去回避它,而应当正视。当然,小说本身不是纪实报告,如果仅有信息量而无文学艺术的加工,那读者倒不如去看报纸,还来得直接些。我理想中的小说类型,表面应该是波澜不兴的,甚至有些“俗”,吸引你渐渐读下去,读着读着,才发现下面原来是暗涌丛生,有着无穷无尽的意思在里头,值得细品,最后读毕了,还余味袅袅。
我其实并不比别人更关心社会新闻,也谈不上是“愤青”,事实上,我的性格还是比较“随大流”的。我一直认为作者本人的性格其实与小说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你在每一篇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都是不同的,而你只是一个单一的人,并不见得非得是精神分裂者才能进行各式各样的小说创作。我早期有一篇小说叫《月亮里没有人》,写一个很能干很有心计的女孩子。后来有个朋友见到我,便说,“啊,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出那样的女孩,真是不可思议!”这其实并没有太大道理的。我身边有一些作家朋友,看上去棱角分明,写出来的东西倒是很温婉。这是两回事。
上海有一个专门协调家庭纠纷的电视节目,叫《新老娘舅》,我经常会看。都是真人真事,大多是贫苦百姓,透着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个不错的素材来源。写作的人再怎么贴近生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报纸上的社会新闻,也不会如此有血有肉。我去年有一个中篇《美丽的日子》,便是受了《新老娘舅》里一段小故事的启发。这个法子有些偷懒,但也不失为一条捷径。
梁红:你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这次发的《天堂再见》,是个凄美的故事,男主人公拖着残存的腿敲摩斯码的一幕,让我想起2010年最火的谍战剧《黎明之前》:两个地下党在窃听器前,说着言不由衷的寒暄话,眼含泪花,用手在桌子上敲摩斯码祭奠牺牲的同志。当时怎么想到这样的细节?六六的电视剧《蜗居》、《双面胶》都是以上海为背景的,你有没有想过写电视剧,或者已经写了?
滕肖澜:之所以在《天堂再见》里加上摩斯密码一节,主要是因为男主人公手脚俱废,敲打密码是他与妻子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除此之外,我一时想不出其它更合适的方式。况且,这种方式确实也比较能够打动人,也有视觉冲击感。
六六的几部电视剧,我大都看过。觉得不错,很贴近生活,挺有味道。电视剧与小说相比,需要更深厚的生活基础,否则你三句两句一说,观众便晓得是假的,便没兴趣看下去了。好的电视剧与差的电视剧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说“人话”,而后者不是。这其中除了水平问题,态度也是关键。不能把观众当傻子。好莱坞这点就做得相当好。去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部电影《波斯王子》,在进影院之前压根没抱什么太大希望,根据游戏改编的商业片一部而已,看个热闹吧。可看完后,大吃一惊。就算是假的,人家也把它当成真的来做。老老实实地编故事,编细节,一步一个脚印。很好看很扎实。反观国内一些大片,自以为深刻得不得了,其实连故事都没编圆。这才是真正的小儿科。比起国内的电影,我倒觉得现在的电视剧要好一些。佳作不少。
关于写电视剧,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也许我会尝试一下。
梁红:张爱玲说过,她是个爱看小报的人。按照评论家的分类,你的小说可能也要被划入“通俗小说”的范畴里去,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滕肖澜:我不太去想小说以外的事情。划分小说范畴应该是评论家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只是努力想把小说写好,其余的并不十分关心。想的多了,小说反而就写不好了。
况且,“通俗小说”并没有贬义。许多著名的小说家,像金庸、张恨水、秦瘦鸥,还有西方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都是通俗小说。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写好了就是本事。如果再过几年,事实证明我确实比较擅长于通俗小说,我觉得这也无妨。那就一直写下去吧,也挺好。
梁红:想过如果不从事这个行业,你最想做什么吗?最近的写作计划可以谈谈吗?有想过转型写别的题材吗?
滕肖澜:我很庆幸自己能当上一名专业作家。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从事创作。暂时好像还没想过做别的行业。呵呵。
最近在写一部长篇,也是上海日常百姓生活的题材。已经完成了一半。计划上半年完稿。目前没有考虑大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