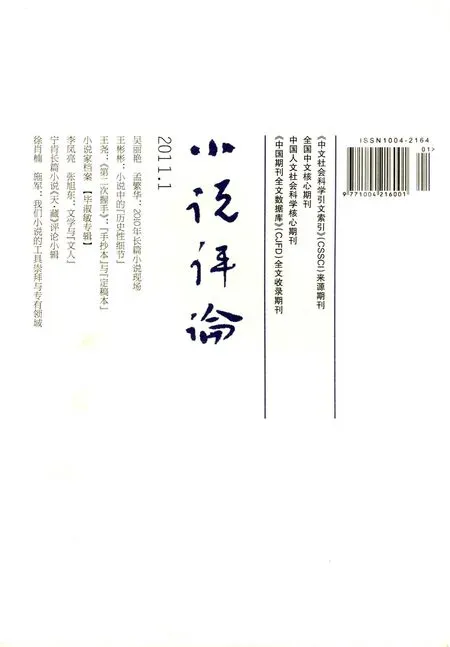历史之镜与现实之思——论大武汉地区小说创作的新向度
肖晓堃
历史之镜与现实之思
——论大武汉地区小说创作的新向度
肖晓堃
2010年底,《芳草》杂志第6期推出了“大武汉地区小说提名展”专号。这是近年来武汉地区新崛起的青年作家作品的首次集体亮相。纵观这些作品,无论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对现实社会的关注,都展示出该地区作家创作的新向度。它们既保持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精神困境的关注,又常常潜入生命的内部,着力表现人性的温暖——仁义之心、人情之暖、人伦之爱。
一、历史之痛与仁义之心
作为中国历史中不可忽略的记忆,“革命化的历史”已给当代作家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因此,对“革命化历史”的不断审视、剖析成为他们发掘不尽的题材。李国胜的《螺蛳湾》与宋离人的《阀门厂的秘密》,就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沉浮折射出社会历史、伦理的变迁,“展示了个人的身心启蒙与历史意志之间的复杂冲突,传达了强大的社会伦理对个体生命发展的制约与规训”①,探析特殊历史中复杂的人性,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追问。
《阀门厂的秘密》通过“食”与“色”两条线索,展示了特殊历史境遇中艾集体一家的苦难史。饥荒年代,艾集体一家渴望吃饱穿暖,而国家则希望人民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冲突由此展开。最终,周桂兰不忍家人为饥饿所苦,盗取国家用以支援阿尔巴尼亚的大米。为此,艾集体深夜受审,周桂兰命丧黄泉,艾红旗成为半个孤儿。表面上看,让艾集体家破人亡的是米,其实,真正扼杀周桂兰生命的是“米”所承载的历史意志与社会伦理。可想而知,当支援阿尔巴尼亚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时,米的价值自然也凌驾于个人的生命价值之上。基于此,周桂兰的盗窃行为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当时的社会伦理不可能予以谅解,死亡便成为她唯一的选择。
缺“食”的悲剧过去之后,禁“色”的时代又来临。文革时期,男女之间除了同志关系是“合法”的,其他的情谊都不被认可,男女之情更被定位为“作风问题”。这种“纯洁”教育以儿歌的方式渗透到少年的心里,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它却无法遏制艾集体对情感的渴求——他坦言“想钻的不是铁板上的洞而是女人的肉洞”,他声称一看到贺阿姨,病便不治而愈。被文化大革命洗礼过的艾红旗并不能洞悉这一点。父亲的偷情让他羞耻不已。为了阻止父亲偷情,他先暗示后提醒。这些措施失败后,他用猪油涂在窗台的挂钩上,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造成了贺阿姨的疯狂,间接断送了与小月的友情。启蒙的缺席导致艾红旗成为“杀人凶手”,同时也成为了被伤害的人。无论是周桂兰之死,还是艾集体的悲剧性命运,这一切都映射了社会伦理与自然人性不可调和的关系。即,在社会伦理面前,个人的欲求不是被漠视、就是遭到有意的搁置。而在历史天空下生活的人们只有遵守社会伦理才能活命,如若不是,他们只能以死亡告终。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人们的伤口却无法愈合。而对于这一切,无论是历史意志,还是社会伦理都无能为力。《阀门厂的秘密》里,饥饿与人祸的双重灾难赋予了艾集体长久而深刻的创伤记忆。多年后,饭后擦嘴依然是艾集体的必修课。显然,这不是为了整洁美观的需要,而是历史给个人留下无法愈合的创伤后所产生的条件反射。同样,宋离人通过一场工厂的意外事故叙述了艾红旗断指之后的“无痛”感受。其实,艾红旗并非失去对痛的感受能力,而是他内心所郁积的“杀父之痛”远比断指之痛深刻、绵长。对于他们内心的伤痛,历史无法对其弥补、无法挽回。这一点《螺蛳湾》中也有很好的阐释。作为右派,罗欣具有其特殊性。首先,她被划为右派的时尚未成年。其次,罗欣是军烈属。不管是哪一层身份,她都应该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然而,罗欣非但没有得到国家的爱护,反而沦为政治的牺牲品。最可怕的是,其他人因为有被划为右派的材料证明,在文革结束后尚能够平反,重获生命的尊严,而罗欣却因为缺失的记录而无法摘掉右派的帽子。无论是罗石头、罗欣的申诉,还是肖书记等人的努力均因“查无证据”而宣告无效。至此,众人终于发现,荒诞的历史对个体的精神僭越根本无法弥补。
在打开历史帷幕之时,李国胜没有将个体的生命悲剧完全归罪于“时代”,而是透过人性的幽暗来审视人的弱点在革命化历史中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人们为了保命往往会将灾难转嫁于他人。魏太平和朱会计为求自保而将右派的罪名强加于罗欣。万金鹏和邵长发现这一错误不但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将错就错。同事的软弱和上级的不负责任轻易地改写了罗欣的命运。她的政治前途、事业、婚姻乃至精神皆毁于一旦。谢汝昌、黄希恒等人的悲剧命运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被划为右派,仅仅是因为得罪了万金鹏。因此,右派的划分往往与个体的思想倾向无关,而是以个人恩怨为依据。右派的划分已经从矫正不良的思想作风异化成私人报仇雪恨的工具。由此看来,人性的弱点成为了个人命运悲剧的推手。
《螺蛳湾》在揭示人性的阴暗的同时,也表现了在一幕幕悲剧中人们的仁义之心。作者安排了不同阶层的人为罗欣奔走,其中包括以肖书记为代表的官员,也包括了崔一尘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他们大部分人与罗石头、罗欣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特别交情,他们的举措可以说是出于仁义之心。在人人求自保时代,这些官员不怕惹祸上身,甚至冒险利用军权干涉。与其说他们的举动是出于对罗欣父母的感激,不如说是他们在特殊时代对正义的维护,对历史错误的补救,对义理的坚持。与手握权力的官员相比,崔一尘、高云沛等知识分子的仁义则颇有侠义的意味。作为下放的知识分子,他们尽自己所能为罗石头等人四处奔走。这无疑彰显了在荒诞年代人们依然残存的忠实、厚道、不功利、不势利的美好品质。
螺蛳湾人的身上同样也蕴藏着传统的仁义。在革命化历史的挤压下,传统的儒家文化被否定、被批判、被抹杀,但是,螺蛳湾的罗家家训依然是“诗礼传家远,忠孝继世长”。正是诗礼、忠孝的品质的传承,螺蛳湾人才能抵抗人性弱点的侵袭。罗石头在突围中救护罗欣,将其抚养长大成人,并倾尽所有供其读书。同样,当罗传炎得知崔一尘与高云沛因为《襄北星火》而获罪,便贸然跑去顶罪。虽然他的行动不乏冲动的成分,但他为相识不久的编剧、导演两肋插刀却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味。无论是罗石头抚孤,还是罗传炎“顶罪”,抑或是罗家炳出让指标,无不彰显了螺蛳湾人情至上的品质。正因为这些品质,螺蛳湾犹如遗世而独立的世外桃源,美好而温馨;也正因为这些美好的品质,苏达、方晶等知青才安心在此安家落户,甚至连远在城市的王元成,也千里迢迢寄来御寒的帽子以表示他对罗家村人的感激。在这里,仁义不光是螺蛳湾人的行为准则,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亦是他们对抗残酷的革命化历史的唯一有效武器。
二、现实之痛与人情之暖
无论是傅博《城里的猫》、钟二毛的《谁在黑暗中歌唱》,还是王小木的《代梅窗前的男人》,抑或是宋小词的《天使的颜色》,这些小说都真实地反映了现代都市中痛感十足的生活状态。在这些小说世界中,人物或是为孤独所苦,或是为缺失的尊严而感伤,或是为至亲无法痊愈的病痛所煎熬。面对难以承受的现实之痛,他们要么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要么试图通过与他人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来摆脱寂寞的纠缠,要么在伦理之爱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管是农村人还是都市人,都被高昂的医药费与无望的治疗效果所击倒。在《天使的颜色》中,小说着力描写父亲与南音面对癌症时双方承受的痛苦。父亲承受着来自化疗的肉体之痛,而南音则被留不住父亲生命的剧痛所煎熬。钱财之“大”与疗效之“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一点点催生出患者家属的绝望。这种生存之痛与生命之痛彼此交织的生存困境,反映了现代发达的医疗技术在疾病无能为力的事实,也由此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生存境遇中普通人所遭遇的亲情与现实困境之间的激烈碰撞,寄寓着作家对现代都市人生存际遇的思考。
如果说疾病是都市人最为无奈的生存困境,那么,孤独是都市人最为普遍的精神困境。德国学者孙志文曾说:“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代人,我们还得更深入一步探究他们的孤独和绝望”②。确实,孤独一直是现代城市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习惯于蜗居在城市一隅的人们,以邻为壑,以己为伴,人与人之间便关闭了相互了解的窗户。在《谁在黑暗中唱歌》中,从迁徙老人“我”的父亲到隔壁的老太太,丰富的物质无法填满他们虚空的心灵。“我的父亲”从农村迁徙到儿子工作的城市,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交际圈。每当儿子上班孙子上学之后,面对空荡荡的屋子,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隔壁的老太太一个人住着复式结构的大房子,家里连个保姆都没有。老太太的生活无人介入,自然也没有人倾听她的心事。在某种程度上,老太太的命运隐喻了都市老人这一群体的命运——远离了自然,疏离了社会,城市中的老年人疼痛无处诉说,甚至连也生死无人问津。孤独不是老年人的特有生存镜像,它也是白领丽人的生存状态。《城里的猫》中的安娜娜是一个单身母亲,虽然她拥有优越的生活,但是其情感世界却残缺不全。除了工作,她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从来“没有外出会朋友,也没看到她在家里接待客人,固定电话几乎是整日保持着缄默”。友情的缺席,使安娜娜只能退居到相对封闭的空间,孤独成为她无法逃避的境域。
孤独不仅仅源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断裂,也源于家庭成员沟通的欠缺。“这个小区的人都是忙碌夜归人,天都黑了,居然没有一点万家灯火、共享天伦的迹象”。即使与家人同住,长辈与晚辈互动的一点点减少。当沟通成为一种奢侈品时,孤独的情绪自然就慢慢侵蚀了他们的心灵。如《谁在黑暗中唱歌》中“我”的父亲与儿子、孙子虽同住一屋檐下,交流却微乎其微。即使在父亲生日,他们也相对无言,只能在回忆中寻找父子的血脉相连。而《城里的猫》中,安杰作为安娜娜的独子,他本应是妈妈的贴心人。但是,相依为命的母子却几乎处于“零交流”的状态,安娜娜与猫为伴,安杰则与玩具为伴。因此,她“常常用脸依偎着丑猫,用极细微的声音喃喃地诉说着什么,一说就是几十分钟”,以此来排解寂寞、消解压力。
不管是社会人际关系的断裂,还是友情的缺失,抑或是代际互动的淡漠,这一切都让现实成为了都市人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为此,他们在左冲右突中寻找突围。《谁在黑暗中歌唱》中,老太太因为可乐罐坠楼事件而因祸得福。少年义工的到来给老太太带来了快乐,但这种快乐并未延续多长时间。孩子们离开后,她只能在静谧中回味那遗失的美好。她既没有儿女环绕膝下,也无人慰问,就连她的生日,也只有一个八音盒为之歌唱、为之祝福。孤独如同梦魇一般挥之不去,老太太的绝望可想而知。最终她只能选择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以此来逃避孤独,告别冷漠的人际关系。而父亲则以每天偷听隔壁的动静为乐,其窃听行为,其实也蕴含了与他人互诉衷肠的渴望。随着少年义工的离开,沟通的可能性被打碎,孤独再次蔓延,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日下。不管是父亲的偷听,还是父亲病中的内疚情感,这一切不仅包含了同病相怜的痛感,更多的蕴含了他对建立沟通的渴望。《城里的猫》的安娜娜也期冀与郝嫂建立一种相互帮助、彼此扶持的关系,但最后他们却因为财喜而决裂。即使在出走时刻,郝嫂依然忍不住为安娜娜着想,埋怨自己不考虑安娜娜情绪失控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小说结尾,安娜娜打电话给郝嫂,两人双双哭泣。从她们的哭泣中,我们可以猜测到,安娜娜与郝嫂最终达成了理解,并将继续相互扶持。
在疾病面前,爱则是唯一救赎。《天使的颜色》围绕身患癌症的父亲治病的过程,展现了巨额的医药费、无望的疗效与人伦孝道之间的冲突。但是,作家的叙述重点并不在揭露悲剧的人性的弱点,也不在控诉医疗制度的不公,而是立意于展示父亲与南音及家人之间的伦理之爱。面对死亡,父亲求生的本能使其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但是,当父亲获知女儿钱财已经用尽时,他终于理解女儿的难处并为之着想。为了女儿的婚事,他没有倾尽所有来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是把三万的存折留给了南音。大爱无言,父亲对女儿的情感,为南音的心灵注入了温暖与力量,使其在面对父亲的疾病之痛时没有被击倒。
如果说父亲在求生本能与因父爱而不忍拖累女儿之间斗争,那么,南音则饱受亲情与现实的煎熬。一方面是要尽一切力量医好父亲,一方面是无力承担的医药费和无望的治疗效果,两者不可调和的关系撕扯南音的心。尽管如此,南音内心的天平始终向前者倾斜。为了延长父亲的生命,她差点丢了工作;为了延长父亲的生命,她厚着脸皮向张辉借钱;为了延长父亲的生命,她甚至想卖身给报社……在南音这里,父亲的生命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因此,她明知无力回天却依然细致入微地照顾父亲,始终坚持“要让爸爸在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南音的坚持,既蕴含了对生命的尊重,更蕴含了对父亲的感激与爱。和南音一样,北华每天吃馒头住地下室,短短两个月筹了一万块;大姑呆了她们柑橘山的蜜橘;小姑带来了一袋子土鸡蛋和生鸡;张辉无条件借钱给南音;母亲为了省钱到小门诊部医治骨折。正是儿女的孝顺,母亲相濡以沫的爱,让父亲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并心怀感激。
三、碎片化的历史叙事与含而不露的现实表达
就故事情节而言,《阀门厂的秘密》和《螺蛳湾》对历史记忆的表达上或许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它们的成功得益于其破碎化的文体结构。这两部小说均通过对人物所处的不同时空进行拼贴,赋予叙事以陌生化效果。
首先是时空并置的叙事模式。作者把“当前”与“过去”两个时空拼贴在一起,让叙事穿梭于其间。在《阀门厂的秘密》里,作者以交叉的叙述结构表现了艾集体一家在革命化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沉浮。小说的时间从艾红旗的孩提时代一直延续到其青年时代为止。前后时间跨度十几年,期间经历了数次革命。宋离人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让叙事在“过去”、“当前”与“未来”之间穿梭。具体而言,小说以1975年至1976年这个时段为基点,或上溯“许多年以前”的过去生活,或穿越到“许多年以后”的未来世界。而每一次的时间的跳转,都意味着个人命运的一次转变。比如第二节,作者先是叙述了“一九七五年五月”,艾集体警告儿子不能在脸上留下米粒,紧接着,时间便跳回到“过去”,叙述了艾集体因脸上残留的米粒而被问罪的过程。在交错的时空跳转中,艾集体的命运悲剧便一点点地铺展开来。
《螺蛳湾》的时空转换亦十分频繁。作者让人物穿梭在“解放胜利前夕”与“文革到新时期”两个交错的时空中,叙说当时或过去。在小说的前半部,作家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时空转换:“一九七四年,夏”,“一九七三年”,“一九五八年,一月”,“一九七五年,夏”,“一九四六年”等等。此外,小说细节也存在时空交错的结构。这种时空转换的叙事机制既推进着故事情节,同时折射出人物在不同时代的命运遭际。一九四六年罗石头在突围中救出罗欣,一九五八年罗欣被划为右派,文革后期肖书记等人千方百计为罗石头罗欣平反。乍一看,这些故事情节是断裂的,但是,这些情节之间蕴含着内在的因果逻辑,在经过拼贴之后,人物的命运、故事的发展在交叉时空里得到某种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罗欣无辜被划为右派,众人为了“义”而相助。
其次是多重文体的融合。无论是《阀门厂的秘密》还是《螺蛳湾》都不是纯粹的历史叙事,显然,作者不满足“单纯的叙事手段,并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不断地加入各种非叙事性的文本,使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不同文本相互杂糅的特征”③。这两部作品都在叙事中融入了大量的非小说的文本,如儿歌、新闻、剧本、法院布告、证词等。在《阀门厂的秘密》中,融入其中的非叙事成分起着被解构的功能。作者以官方新闻报道构建了一个话语系统,而坊间传言及红旗的窥视构建了话语系统。一方面,这两个话语系统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艾集体形象,另一方面,它们相互解构。众所周知,报道具有真实性,而坊间留言则具有八卦的性质。那么,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发现,艾红旗的过程揭秘是对官方报道的解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对个体生命戕害的展示过程。
李国胜在借鉴西方的碎片化手法时只延用了其互文性的外壳,而屏蔽了非叙事性成分的解构功能。基于此,《螺蛳湾》中的非叙事文本并不承担解构的功能,而是承担预叙的功能。在每一章的开头,作者都采用剧本、法院布告、证词等非叙事成分作为引子。这些引子与许多古典小说在开头给出简短故事一样具有全局性的预叙功能。如第一章的预叙:汉子甲 石头?!汉子乙 石头?!汉子乙 石头!有本事!带个娃儿回来了?(石头晕倒在地)这个引子预叙了石头呆着回到罗家的情形,预设了娃儿是谁的悬念。接下来,小说以解密的方式叙述了罗石头回家的真实情形。在这里,剧本只承担的预叙功能。它意在制造故事的悬念,保持读者阅读的“期待心理”。
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代梅窗下的男人》《城里的猫》以一种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方式处理人物之间的冲突。前者中的代梅与麻顺顺因为撞人坠楼事件而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原本可以演绎成剧烈的冲突,但作者却从代梅的内心感受出发来表现他们的爱恨情仇。作者遮蔽了麻顺顺的身份,让代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之相爱。当获知麻顺顺的身份时,作者则冲突内化为代梅的情绪流动,借助她的意识流动,展现抉择的痛楚。一方面,麻顺顺剥夺了自己的美丽、健全与梦想,另一方面,他是自己的爱人,腹中孩子的父亲。不管是宽恕还是举报,她都会受伤。最后,她选择了报警。即便如此,作者依然不让人物产生正面冲撞。代梅向警方通报麻顺顺的下落,然后,“她慢慢往前走去的时候,一辆警车风驰电掣地超过了她,停在她的裁缝铺前。一些邻居开始围拢了过来”。到这里,小说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在含而不露的叙事中,代梅那坚强与脆弱、自卑与自尊的内心世界慢慢地铺展开来。
而《城里的猫》则采取了引而不发的叙事策略。郝嫂与安娜娜因为猫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冲突,但作家始终将她们的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当安娜娜因为财喜擅自上沙发而用坤包扔它,郝嫂只是喝斥财喜;而当安娜娜因为花瓶而对财喜咒骂时,郝嫂虽然没有抗议,心里却开始犯嘀咕。我们发现,虽然安娜娜与郝嫂的冲突没有被引爆,但却呈螺旋状上升,一步步逼近郝嫂的底线——自尊。直至安娜娜扬言要把财喜赶出家门,郝嫂的底线彻底被击垮,她们的关系也随之决裂。而在这种盘旋式的叙事中,安娜娜的孤独,郝嫂的宽厚便慢慢彰显出来。
肖晓堃 暨南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洪治纲:《从“寻根”到“审根”——论苏童的〈河岸〉和艾伟的〈风和日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
②[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③洪治纲:《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