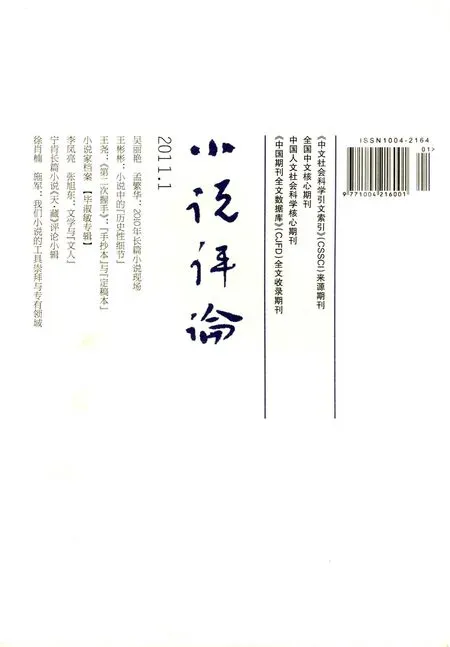身体叙事与精神高地
——以宁肯的《天·藏》为话题
王德领
身体叙事与精神高地
——以宁肯的《天·藏》为话题
王德领
我甚至认为,宁肯的《天·藏》的出现,是十分奇特的现象:因为,作为先锋写作,作为精神性的探索,早在80年代末期已经基本终结了。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散文化的时代:平庸、复制的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许多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早已改弦易张,转而向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热烈地拥抱。促使宁肯这样写的冲动到底来自哪里?我不知道阅读给宁肯到底带来了什么?我所了解的是,当宁肯读完了《乔伊斯传》《尤利西斯》之后,他找到了进入这部小说的通道。在《天·藏》中,他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性地用注释的方式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内涵十分复杂的文本,面对这么一部复杂的精神文本,有许多进入的方式,我想找到一种如同解剖刀一样锋利的角度进入文本。我认为,在这部强调精神诉求、知识分子情怀的小说中,从身体叙事的角度进行解读,也许是切入文本的一个较为恰当的视角。
身体叙事的简单回顾
身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母体之一。身体积淀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很显然,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规训是通过身体来进行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可以说是身体叙事的历史。福柯曾经说过:“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①小说对身体的具体描写,隐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
到了90年代以至新世纪,随着先锋写作的转向,身体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只是更多地存在于一些具有主旋律色彩的小说中,而在大多数小说中,身体往往对应的只是个体欲望或者群体意识,并不一定应和主流意识形态。如果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的身体是一个政治身体的话,80年代先锋小说中的身体则是一个象征性的苍白的过去时的身体,而90年代至今的文学中的身体则绝大多数是一个被个体欲望驱使的现在进行时的狂欢化身体。
我想说的是,宁肯的《天·藏》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的。小说里的身体叙事并不是以往的简单重复。可以说,它十分靠近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先锋小说,运用了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抽象、晦涩、多解、隐喻味十足,但是又截然区别于先锋小说。《天·藏》的独特性在于,它所描述的身体是带有主体性的,整个小说具有一个由叙述者的心灵建构起来的广阔的精神屋宇。正如前所述,无论是“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身体,先锋小说里的象征性的身体,还是90年代以来的感官狂欢化的身体,大都是符码化的,取消了身体的主体性和个体精神世界的探寻。2006年问世的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可能是个例外,《生死疲劳》里的身体叙事显得特立独行,小说主人公、西门屯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这是一个魔幻化的身体变异的精彩故事,借助身体叙事,表现了建国后丰富复杂的乡村场景与激烈的话语冲突,表现了时代对个体的碾压,身体的变异与意识形态是合一的,是高度民间化的身体叙事的典范。而《天·藏》的特色在于,它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气质,更多地是从知识分子的视角,从哲学的角度俯视身体,将哲思冥想在身体上铺开。与《生死疲劳》相比,在这个由知识主宰的时代,我更看重由《天·藏》这一知识者的视角。在整合了历史与现实、本土与西方、宗教与世俗的基础上,在强调主体性、心灵世界,在对历史、现实的反思,乃至对于宗教、中西方文化的思考方面,这部作品显然有着更为复杂、博大、深邃的精神空间。
意识形态与虐恋的身体
《天·藏》的主人公王摩诘,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主动的。他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经历过许多政治的风浪,90年代初主动来到西藏支教,教书、读书、思考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他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醒,始终思考的是带有终极性的宏大命题。譬如,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暴力在历史进程中的思考。王摩诘精心打理的菜园被无情地践踏,一片狼藉,小说反复描写被毁坏的菜园,为它罩上了隐喻的色彩。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破坏,王摩诘在菜园的废墟前联想到了历史的暴力。历史的暴力在主人公王摩诘这里成了一个死结。或者说构成了他持久的梦魇,甚至可以说部分摧毁了他内心最珍贵的东西,成为烙在他身体里的一个致命的伤痕。这进一步印证了福柯所说的规训“对肉体的干预”的巨大力量。王摩诘高深莫测,满腹经纶,学贯中西,温文尔雅,恃才傲物,可谓饱学之士,但是他来拉萨教书之前即具有强烈的虐恋倾向:
他给妻子脱大头鞋,给妻子洗脚,吻妻子的脚,吻妻子的鞋;他不是用手而是用嘴把妻子的大头鞋脱掉,闻鞋里的气味,就像吸毒一样,然后用舌尖轻轻地舔马蹄状的鞋跟,舔鞋尖,让他的妻子用他舔过的鞋跟或鞋尖踩在他的胸、嘴、乳尖,然后是他的腹部、小腹……
可以说,他没有健全的人格,这个貌似具有强大的主体性的男人内心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无底黑洞,他的主体性是不彻底的。这一切的发生肇始于历史的暴力。尽管他是个模范丈夫,可是妻子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虐恋,和他离了婚。时间并没有治愈他的创伤,反而深深地嵌入他的皮肉之中,深入他的意识深处,掌控了他。在拉萨他结识了穿制服的援藏法官于右燕,和她也玩起了这种虐恋的游戏。他对于制服具有特别的亲近感,渴望女人穿着笔挺的制服来蹂躏他,摧毁他,从精神到肉体,他在遭受鞭打、捆绑、羞辱、学狗叫的过程中感受到彻骨的快感,痛苦但是快乐着。意识形态在这里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雨点般的皮带抽打下,王摩诘在思索:
不过他要的不就是这种真实的屈辱与疼痛吗?什么是屈辱?什么是暴力下的屈辱?人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曾怎样低过?怎样舔食内在的屈辱?他需要它们释放出来。②
历史深处的暴力在这里转换成了强烈的欲罢不能的自虐。自虐的同时也是一种深度的释放。吊诡的是,王摩诘所渴望的碾碎自己身体的暴力,恰恰是历史强加给他的,实际是历史暴力的隐喻式表达。对暴力的反思、拒绝与身体对暴力的极度渴望,竟然如此奇特地扭结在了一起。王摩诘虽然没有被摧毁,但是他显然已经被部分地异化了。在某一个时刻,暴力回到了他的身体之上。当施虐的于右燕掐住了他的脖子,王摩诘在失去意识的一刹那突然看到了如下的景象:
他看到了近在咫尺因而无限大的大壳帽……他看到她(于右燕)在张大嘴喊他,但他听到的却是众多的广场上的喊声。她的帽子放大了他的视野和当年的恐惧。他们在死亡的喧嚣中撤出,死,屈辱,如同地狱之旅,还不如死。③
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的提示:正是由于过去的经历,才造成了今天变态的受虐狂形象。它们互为镜像,再一次通过回忆,将看似不相干的二者成功地缝合在了一起。原来,过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早已积淀在他的血液里,借助身体,顽强地复活下来!
如果说,女性在困境中往往扮演了一个拯救的角色,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失去性功能的主人公,在女人的帮助下恢复了自身,而在王摩诘这里,却失效了,爱情也不能拯救王摩诘。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维格,迷恋王摩诘的学识,爱上了他。他们同居在一起,同居而不做爱,维格力图想以爱情的魅力拯救扭曲的王摩诘,她很自信,她相信自己身体的魅力,但是在关键时刻,王摩诘破碎的撕心裂肺地呼喊:“强暴我吧——”让维格觉得他已经无药可救,这个创伤是个巨大的黑洞,连爱情的火焰也无法照亮……
同样是以性变态隐喻历史的暴力,《天·藏》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因为,不仅是性本身隐含着意识形态的意味,潜意识、显意识、本我、自我的矛盾和撕裂,由此带来的肉体和灵魂的挣扎,过去和现在的纠结,永难驱除的梦魇和自信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乃至对强大然而脆弱的主体的吞噬,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来自灵魂的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
面对王摩诘这具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身体,我们看到作者的处理是很有意味的。1968年,王摩诘三岁时,他的“右派”父亲被一群学生带走,从此失踪了。这给王摩诘造成的伤害是终生的。但是“文革”伤痕显然并不是这部作品表现的重心,小说着力表现的是另一种“伤痕”,是当代许多作家没有认真提及的80年代留下的心灵创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创痛。王摩诘从80年代走来,却没有消沉,依旧不停地学习和思索,拷问过去,思索现在和未来。他学贯中西,对中国哲学、佛学、西方现代哲学都有着精当的理解,具有知识者的优越和自信。最后他留学法国,毕业后在法国某大学任教,并兼任西藏大学的教职。而这个貌似具有强大的主体性的知识分子,又是极其脆弱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被扭曲的一面。譬如他反思暴力,却又渴望暴力的蹂躏;他推崇人格、尊严、启蒙等,有知识分子的傲骨,却又卑下地让女性折磨自己,哪怕是受鞭笞、学狗叫、狗爬、穿绳衣;他具有强大的形而上的思辨力,形而下的欲求却又那么下作。他在正常与变态之间摇摆,在矛盾中前行。
身体与意识形态就这样在宁肯的作品中成为一种核心的存在。身体往往是意识形态的镜像,透过身体,我们看到了时代的灵魂部分:龌龊的和纯净的部分,腐朽的和天真的部分。在新世纪的小说中,还没有一个作家,清醒地避开时代的喧嚣,摈弃对于欲望、琐屑、小团圆、小悲欢的描述,从身体的关联处、从精神的高度由现在向过去眺望。我觉得,这是一个情结。对于一个在北京长大的作家来说,关注当代人的心灵,尤其是关注真正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从而在精神的高度,深刻地俯视这个时代及其历史,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宗教、族裔与身份觉醒
对于身体来说,当规训不再以极端的方式进行的时候,觉醒的不仅是肉体、精神,同时还有自己所代表的文化身份。维格作为本书的主人公之一,她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王摩诘,撑起了这部小说的另外一部分精神空间。与王摩诘一样,作者也是从身体的角度叙述她的,从而揭示“维格现象”的精神内涵。王摩诘和维格,他们是一对“恋人”,共同组成了精神的屋宇。宗教、族裔、文化身份,以及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锋,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精神指向。
维格是一个现代女性,在北京和巴黎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她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两人在北京上大学时认识并相爱。维格的母亲是西藏著名的苏穷家族的后代。苏穷家族不仅仅是权贵人物,而且还是西藏近代民主改革派的代表。苏穷·江村晋美曾经偕同维格的外婆长住英伦,回西藏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下推行新政,掀起了“苏穷运动”,触怒了既得利益者,被保守派剜去双目,投进牢狱。她的外婆在“文革”中离家出走,不知所终。西藏和平解放了,维格的母亲去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她把自己的内心藏起,因为那是一个趋同的年代,在趋同的时代,保持差异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维格的母亲还是保存了一尊佛像,“神秘的佛像锁在立柜门里的一个小柜门里。小柜门有一把专用钥匙,钥匙什么时候都放在母亲贴身的地方,就连晚上睡觉她也不摘下来。”维格的母亲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了一方净土:每逢藏历传统节日,她在家人熟睡之后,偷偷礼佛,重返那个维系自己灵魂的世界。改革开放以后,维格的母亲退休后回到了西藏,再也没有回北京。在拉萨她身穿藏装,平日主要就是念经礼佛,重新回到了过去,像是要把几十年该念的经补回来。
维格到了法国之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西藏血液,当她学成回国,返回拉萨定居,她回到了自己精神的故乡:
她看到了……自己在这里的独特的根系。这根系使她同过去的自己以及别人区别开来,一切都让她激动,她的一直沉睡的那部分血液涌遍周身以至沸腾。但同时这部分血液又让她陌生,甚至也让别人陌生。某种意义,她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属于内地,不属于法国,不属于西藏——她是被三者都排除在外的人,又是三者的混合……
过去的很多年里,她的另一半西藏的血液没人知道,包括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从小到大,她所填的各种表格都是汉族,所有的证件,学生证、身份证、护照都是汉族。很长时间以来她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实际上她知道——她很小就知道——自己身上有一种和别人不同的东西。她虽叫沈佳嫒又“秘密”地叫维格拉姆,小学、中学、甚至直到大学,她没向任何人说过自己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的名字……但是后来,慢慢的,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那些源自自己秘密名字的自卑、恐惧、不安慢慢地消失了,不仅如此,她秘密的名字反而一下变成了她内心骄傲,甚至是她最大的最隐秘的骄傲。但她还是不说。许多年了她已习惯了不说,她不愿轻易把自己最骄傲的秘密告诉人。④
维格身体里的藏族血液的苏醒也是民族身份的觉醒。也就是说,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个人。她和母亲的寻根,就是寻找自己的民族记忆,民族身份,并对趋同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趋同、复制是时代的潮流,如何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进而保护自己的心灵,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对于维格及其家族来说,始终贯穿着一个寻找的主题。“寻找是一种信念,一种类似可能而又虚无的悬念,就是要找没有而又可能的东西,她内心的一切都有类似的倾向。”⑤维格寻找自我,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寻找宗教的支撑。而寻找“文革”失踪的外婆,更是一直萦绕在维格的心头,成为她挥之不去的内心情结,为此她曾四处奔走,却难以有所斩获。寻找外婆就是对于自己精神家族的追寻与认可。维格的寻找,不仅是对自己血液的寻找,对自己精神家族的寻找,更是对藏族精神、民族记忆、民族身份的寻找。
王摩诘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拥有知识,当然也就拥有了权力,这促使维格迷恋王摩诘,爱上王摩诘。维格对王摩诘的爱,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更具有文化意味,可以说是对于汉民族文化的推崇与敬仰。一开始她发现了王摩诘内心的黑洞,但是并不太介意,她想用自己强大的爱情治愈王摩诘的受虐疾患。但是,最终,她亲眼目睹了那个黑洞的巨大和无边,连爱情的光芒都不能将它照亮。那是一具残留着鲜明意识形态的身体,经历过扭曲的身体,她注定是无能为力的。后来,维格进了博物馆,做了一名讲解员。博物馆是一个隐喻,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她向中外游客讲解自己民族的文化,相对于以前的困惑而言,包括她对自己身份的疑惑,现在都不见了,她在讲解中找回了自己,找到了文化自信。她可以自信地面对王摩诘了,终于可以平静地面对这个在文化上曾经很强大、引领自己的哲学教师了。
维格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借助的是宗教的形式。维格通过回归传统,主要是回归佛教仪式,重建自己的信仰,从而找回了失落的自己。
因此,我们看到,身体不仅仅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西藏,它无可回避、不容置疑地具有宗教的意味,它指向更辽阔、神秘的形而上的精神屋宇。显而易见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存在着一个无所不在的宗教的身体。这是藏传佛教的身体:神秘、幽深、庄严、博大、深邃、虔诚、古老。小说里写到了一些修行的上师:马丁格、卡诺仁波钦……法国人马丁格纯粹是宗教的身体。他超越了国家、种族乃至意识形态的界限,为了探究藏传佛教的秘密,毅然放弃了自己已经做出了斐然成绩的生物学研究,来到拉萨潜心修行,并且和自己的父亲——著名的怀疑论哲学家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作了一场有关佛教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精彩对话。这是有关佛教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也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场对话贯穿了小说的始终。王摩诘、维格也是这场对话的参与者、协助者。对话展示了中国本土智慧的魅力,是对西方文化的世纪挑战。维格寻找自己身份的努力,也是在这场成功的对话中完成的,她看到了东方的智慧的真正力量。
对于马丁格来说,佛教是一场精神修行:
在马丁格面前,谁都不能不承认藏传佛教几乎首先是一种身体艺术,然后才是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这方面没有哪种宗教的身体能同佛教的身体相比。面对这样的身体,你无需话语,只需默默的注视就会感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时间的流动——感到这个身体在向你注入流动的时间和空间,这时的时间就像泉水和黄昏巨大的光影一样,无所不在。⑥
在上师马丁格、高僧卡诺仁波钦面前,西藏是以精神的高度屹立在我们面前的。维格虔诚地拜马丁格、卡诺仁波钦为师,她是通过向宗教的身体的接近而确立了自己身份的。维格第一次见到宁玛派高僧卡诺仁波钦时的感受是这样的:
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围绕了她。不,不是有形的东西,是无形的东西,但是非常有力量。她感到了某种顷刻的照耀、提升、心里好像升起一朵火焰。她分明听到他叫她的声音,她终于勇敢地抬起头!
至今她还记得,也就是在这一瞬,她内心的那朵火焰变成一朵微笑、一朵的莲花——卡诺仁波钦正微笑地从上面看着她。是的,正是这罕有的微笑和目光围绕了她,像魔法一样让她低垂的头禁不住抬起来,否则她怎么敢抬起头来?
她没想到他这么年轻,简直年轻得神奇,他的眼睛就像高山的湖水,那样纯粹,那样光彩,又那样自在。⑦
相比之下,王摩诘的身体是一个世俗的身体,积淀着意识形态、带着伤痕的身体。而维格骨子里向往的是一个打上宗教烙印的身体,因此,她和王摩诘的分手似乎是一开始就注定的。
在王摩诘身上,存在着宗教的身体和世俗的意识形态身体的交锋。他对宗教具有超常的理解力,有一般人不具备的慧根,譬如他和维格的母亲之间默契而又神秘的心灵感应,他和马丁格的充满哲思的对话,但是他对宗教始终是敬而远之。他显然还有一种更高的追求,对西方现代哲学的解读,显示了他拥抱世界的学术抱负。应马丁格父亲的邀请,他前去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这是一个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立足本土,拥抱世界,在知识分子王摩诘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这个时代的隐喻。
维格通过回归本民族的宗教传统,通过对自己家族记忆的寻找与追忆,她找到了自己一度失落的身份,从而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完成了对自己的心灵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守卫。由身体意识到族裔、身份的觉醒,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只有在80年代以来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可以得以更好地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宗教的身体和世俗的身体,尽管二者的精神指向不同,但同样是从个体出发对形而上的精神诉求,都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性眺望。
结语:超越身体构筑精神高地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结尾处说:“现代社会的各种规训的手段,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⑧《天·藏》中的王摩诘、《沉默之门》中的李慢无法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规训,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宿命,但是他们试图重建自己的精神主体以摆脱这种规训,或者说尽量弱化这种规训,哪怕这种规训在他们心灵上烙下巨大的伤口,但是他们拒绝同一,拒绝对心灵的规约和驯服。这是一种包含悲壮的努力,这正是他们的意义之所在。某种程度上说,宁肯塑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边缘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是精神富有、具有独立判断的现代人,他是在为这种现代人画像,为具有良知的理想的人格画像。从《沉默之门》到《天·藏》,作家都是循着这一精神轨迹走来的。甚至在他的成名作《蒙面之城》中,也是塑造了一个不合社会规范的叛逆者形象马格,尽管这一形象显得青涩了一些。马格精神强悍、青春勃发、思想锐利、独立特行、拒绝现实对自己的规约,流浪天涯却对世事洞若观火。宁肯是在写我们普通人内心的一种梦想,一种压抑已久的蓬勃的愿望,那就是对理想的召唤,对自由的渴望。他借助一种强悍的青春、残酷的青春的游侠方式呈现出来。其实这是一场借助青春的身体进行的一次精神漫游。主人公经历了九死一生,他的身体经历了巨大的考验,而他的锐利,足于刺破最尖锐的世俗的铠甲。他挑战整个的世界,他是玩世不恭的,愤世嫉俗的,孤独甚至有一点悲壮意味,但是他不是唐吉坷德,他具有挑战世俗所具有的身体、精力、智慧和力量,孤独但又是必然胜利的。谁也无法阻拦这具骡马般强壮的巨大躯体,他游走于西藏等地,将一种强大的呼啸带给了我们。
与《蒙面之城》激情四射的“青春记忆”相比,《沉默之门》《天·藏》则成熟、内敛、节制,更趋向于“中年心态”。当时代被物欲过分遮蔽,当精神被物质放逐,当心灵的优雅、高尚、节制逐步被粗鄙、猥琐、放纵所取代,青春期应该彻底、残酷地终结了,“中年写作”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意味着需要反省、思索、排斥、重建等一系列的理性行为来开拓精神空间,需要和我们这个疯狂的呼啸的畸形的资本时代拉开应有的距离。这样一来,和流行的写作自然就拉开了距离。流行的写作如同时尚,如同网络灌水,是整个时代的流行性感冒,是以速度取胜的。相对于时代的加速,我们的写作需要慢下来,“有许多快的理由,才华,金钱,生存。但如果一个人慢一点可以写得好一点,为什么要快呢?现代小说是慢的艺术……现代小说节制、低调、多义、讲究控制力和玩味,这一切不慢怎么行?”⑨慢下来的写作,却是锋利的写作,是具有开阔的精神疆域的写作。
从以上可以看出,宁肯的写作,在当代作家中是卓尔不群的。他超越了身体叙事,专注于对个体灵魂、精神世界的探究,塑造的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是为具有理想气质的现代人的灵魂画像。从个体的人身上,投射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取向的整体思考。它和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时代、和整个人类的精神,构成了一种繁复的对话关系。由此,宁肯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构筑了我们荒疏已久的精神高地。
王德领 北京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⑧《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 杨远婴 译,第27页、第35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②③④⑤⑥⑦《天·藏》,宁肯著,第40页、第202页、第207页、第113—114页、第195页、第103页、第11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
⑨《关于沉默——后记》,见《沉默之门》,宁肯著,第32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