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歧义与城市营销
陈林侠
《唐山大地震》的歧义与城市营销
陈林侠
《唐山大地震》在国内电影中之所以非常特殊,不仅在于影片拍摄有着较强的政府性质(影片的缘起即是为了纪念唐山大地震,唐山市政府邀请冯小刚拍摄这一电影),而且,在这一本身有着明确的城市与地域限定的题材中,其他城市非但没有回避,反而是不乏参与的热情。杭州市政府积极投资,并约请冯小刚以杭州作为电影拍摄的外景地。由此,标题的“唐山大地震”所限定的,本来是一种“不跨”城市的地域创作,却成了“跨”城市的“多地性”创作;本应凸显特定的“地域精神”,却出现了“去地域性”的特征。因此,《唐山大地震》带来的思考是,当下的艺术不仅为资本的经济属性服务,而且其政治属性开始直接介入创作,迅猛发力甚至超越了经济力量。
具体说来,唐山与杭州的政府投资是影片得以创制的根本原因,然而也正是这两座城市平分秋色的出现,使得影片出现较多的歧义。片名《唐山大地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唐山在影片中的重要性。“《唐山大地震》总投资达到1.3亿元,其中,唐山市政府以‘有偿赞助’的方式成为最大的出资方。该片唐山方的制片人姚建国说:‘我们坚持要占有至少5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影片中的话语权,才能保证我们所需要的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我们希望影片既主旋律又要充满人性、直指人心。’”这个说法非常清楚地传达出影片的拍摄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唐山市政府之所以邀请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就因为三十四周年的纪念契机,因而其公共性放在第一位。它决定了主体事件与城市之间的明确关联,看来冯小刚的拍摄即是一次“命题”作文,这在影片发行时他自己也一再表达。但是,这种公益性的当下表达,已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宣传教化的思路,而是借助商业运作模式,大面积地播撒开来。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发展、教育普及与代系的更迭,公益性事件以各种方式逐渐沉淀、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经验与记忆,尤其是伴随“80后”、“90后”构成观众主体后,对重大历史题材、社会事件的叙述,就成为一个回顾个体成长的重要契机,因此,对他们来说,此类电影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教化,而具有崭新的娱乐信息与消费可能。可以说,目前这一类型的电影创制正是合理地利用了这一观影心理。电影对公益性事件的选择,不再是简单、被动的应景敷衍(用电影这一现代媒体实现教育的功能),而是主动选择此类事件,完成政治(赢得政府支持与获奖)与经济(高票房回报)的双重获利。总之,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公众事件、带有集体记忆的公共题材给电影制作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已经屡试不爽。如陆川拍摄的黑白电影《南京!南京!》虽是一部典型的文艺片,但借助“南京大屠杀”这一敏感题材,还是进入了亿元票房“俱乐部”,这在1990年代主旋律电影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再如《建国大业》利用明星机制,重述“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票房高达三个多亿。在这样情况下,冯小刚接受“唐山大地震”这一重大题材,实际上是将历史性(成长记忆)、公共性(集体记忆)以及当下性(汶川地震)融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说,《唐山大地震》票房超六亿的骄人成绩,与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提示着我们,电影“说什么”的题材选择,对票房的影响远大于“怎么说”的艺术性;从另一个角度说,高企的票房揭示出电影的“说什么”与大众关切之间的秘密,但并不能成为证明电影艺术性(“怎样说”)的充分根据。

与此同时,姚建国的说法也明确了影片“主旋律”的政治属性。众所周知,城市的宣传与媒介形象的建构归属政府的职能。唐山市之所以投入“至少50%的股份”,就是要保证唐山的“话语权”,传达“主旋律”与“主流价值观”,以此构建、宣传“新唐山”形象。有媒体报道:“借助《唐山大地震》电影片头一分钟的城市宣传片和影片中的城市实景,没有到过唐山的人认识了这座新城,到过唐山的人则看到了新唐山的巨大变化。据了解,随着电影的热映,唐山的关注度、知名度、美誉度都在迅速提升。网络调查显示,外界对唐山的关注度已经提升到65%以上。”(《<唐山大地震>带热“新唐山游”,北京市民自驾前往》,《北京晚报》2010年8月5日)毫无疑问,随着影片上映,“唐山大地震”在媒体推动下已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话题,关注度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从电影创作的角度看,被唐山市政府所投入资本保证的“主旋律”与主流价值观,实际上限定了只能是一系列以主流价值为标准的光鲜影像,只能是一种“从灾难到光明”的“呈现”叙事,而离开了灾难片关于人类的价值判断、关怀与体验的审美本质。这种“光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影叙事的流畅性。原作《余震》属于探究内心世界的小说,它设定了一个极端的故事情境,王晓灯在特定的生死情境中遭到母亲选择弟弟的打击,而后在继父家中备感隔膜,因继母的去世再次感受到被遗弃的恐惧,并且受到继父的性侵犯等,整个人生笼罩在“被孤立”、“无价值”中,更糟糕的是,这种创伤记忆挥之不去,顽固地破坏着王晓灯当下的生活,如对丈夫极端的冷淡与不信任,对女儿的强权控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靠得住”等等,虽然主动地采取自我保护的行为,如毅然拒绝继父、远走加拿大、自杀,但是面对这种创伤性记忆毫无办法,直到她重新回到唐山、寻找母亲、正视这一段记忆。显然,小说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话题,集中在创伤性记忆在个体成长中的精神意义,一方面,不断设置负面的人生阻碍,另一方面,却在持续地自我拯救,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以故事进行理性论辩、观念表达的力量。电影并没有如此周折变化,而是在一个方向上无限延伸。如果说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是起点的话,那么,人生延展的未来便是走向幸福与成功的正面价值。无论是断臂的方达,高中毕业就下海淘金,后来拥有私人公司、宝马车,还是未婚先孕且生下女儿的王登,大学退学却也能单独抚养女儿,继后远嫁加拿大,幸福地生活。电影似乎表明,只要是“遭遇地震”的“灾民”,都是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偶像:非富即贵的成功人士。这种地震结果再“主流”不过了,灾难后遗症(如王登的头痛,在高考前还曾发作过,而当成人后,却主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横亘在王登心底深处的“被遗弃”,但这种“被遗弃”也是有情可原、能够获得谅解的,当王登目睹了汶川大地震的另一位母亲的选择后,创伤性记忆悄然治愈,于是,最后的遗憾也获得弥补,大团圆的结局不可阻挡地出现。即是说,影片用主流价值观叙述了当下认为最美满的人生梦想,想象性地补偿了自然灾难带来的损失。这种补偿集中在了世俗层面的“幸福”,而有意地遮蔽、忽视灾难遗留下的更深的可能是永远都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从这个角度说,唐山大地震虽然论及灾难,然而重点恰恰不是灾难,而是关于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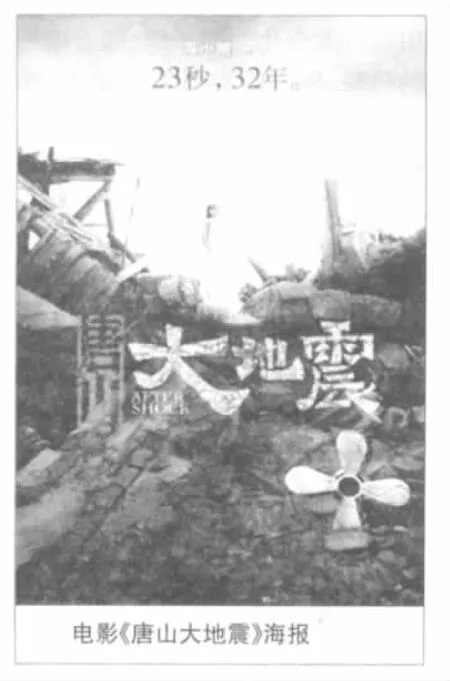
从姚建国的话里看出,政府投资是以明确的商业回报为前提。从大处着眼,政府以唐山大地震三十四周年作为城市宣传的契机,目的在于树立积极健康的形象;而塑造这一形象,不仅是承载着公众性,而且也为了城市经济的更好发展。从小处看,唐山市政府的“赞助”是“有偿赞助”,它遵循商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运作逻辑,因而呈现出开放性。也就是说,当自身的资本力量不足以完全支配电影生产时,出于商业的需要(也是一种商业谈判与协商),它允许其他资本的参与介入。如此一来,由于资本来源、性质的多元化,造成文本的众声喧哗,各种资本的声音,相互抵触,撬动、抵消主体话语。这在《唐山大地震》中屡屡可见。如按照商业电影的运作模式,邀请名导、明星,将片名本应有的“纪实性”完全变成“煽情”的情节剧,再如类似剑南春等的植入性广告。我们认为,虽然观影令人感动,但是就地震题材来说,反而因虚构削弱了表达的力度。“唐山大地震”在本已沉重的建国史中对民族如雷霆万钧般的打击力度,本应在这一灾难性事件获得更有深度、分量的表达,却因这一极端偶然、戏剧化的故事被弱化,而非增强。
然而,说到广告,由于宣传城市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而也就成了电影中最大的广告。杭州的介入使影片出现了“跨地域”叙事,代表地震灾难的唐山,很快在杭州的城市表达中消失,这在更大的范围内消解了地震的真实性与力度感。在唐山的陈旧、灾难与欠发达的映衬下,杭州的秀丽、浪漫、发达愈发分明;尤其是影片点缀着招牌式的西湖风景:永福寺、杭州乐园、千岛湖宣传、浙大之江校区,等等,这些太过明显的标志性外景,迫使缺乏标志性影像的唐山不断后缩退让:由此《唐山大地震》成为了杭州的宣传片。


唐山地震纪念碑
说起来,到杭州拍摄《唐山大地震》,无论如何都有些令人惊讶。原作的王晓灯在逃离继父之家后,是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结婚,继而出国留学,方达则到广东打工;而影片缺乏对唐山与杭州关联的铺垫,直接就把王登、方达设定为不约而同地来到杭州,“杭州医学院”似乎很难对应王登学医的梦想,方达说“山里的人都到深圳”还是把打工目标确定在广东。然而,杭州就这样突兀地成为既是王登初恋的浪漫之地,也是方达创业的乐土,甚至将杭州别墅当作加拿大的外景。这一切完全授意于杭州市政府的城市形象推广与宣传策略。据媒体报道,杭州市政府为了城市宣传,制定了“外景地杭州”计划,旨在通过邀请国内外影视公司来杭拍摄外景,借势借力宣传杭州,让更多的人认识杭州、了解杭州,走进杭州、爱上杭州。2008年冯小刚执导的《非诚勿扰》就在全国刮起一股“西溪热”。很明显,冯小刚拍摄杭州并不是因剧情的需要,而是由于政治与文化结盟的结果。它以自然、人文的“外景地”,吸引、介入具有社会效应的文化事件,并借助这一事件的社会影响,宣传杭州,并以有偿投资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回报。应该说,凭借自然、经济、文化的先天优势,杭州的城市发展策略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具体城市的推介总是带有区隔性。当我们将之放在更大的范围时,杭州市政府制定的“杭州外景地”计划的特殊性就显示出来。首先,由于“外景地”的模糊,它可以用各种方式参与任何一部影片(如或显见的风景标志,凸显本地城市;或抹除地域符号,但大多情况下是,既然参与,总是按捺不住表现城市的资本欲望,如“九溪烟树”的别墅群,虽然化身为加拿大,缺乏城市标志,但是,它是以杭州城市形象已然获得表达为前提的);而介入与否,不是衡量影片与杭州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也不依据影片剧情、制作目的与社会功能,而是以导演、题材的社会影响为标准,这就必然造成参与的盲目性与介入的粗暴性;其次,这一计划的实施与推广,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的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一次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结合,虽然强调公益性,但如上所说,它也正是借助公益性,抵达了“经济获利”的腹地。如果说1990年代以来在政治的放松、推动下,文化与经济出现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结合,那么,新世纪以来,政治就直接出场,开始与文化结盟,这在激烈的城市竞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越来越清晰。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受到商业资本的强烈收编,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形象地概括的那样,文化成为包装外壳,经济才是目的;新世纪的创意产业、内容经济,却是文化被政治统摄、整理、改造。政治与文化的结合,是第一层面,其次才是经济的获利。如果说1990年代经济与文化的结合是在政治允许的规模、范畴、形式中进行,具有较多分散性、差异性与个体性;那么,政治与文化的新世纪结合,则是政治直接出场,往往以打造城市形象、推广城市影响的公众面貌出现,率先与文化会合,因而带有较强的全局观与宏观的集体性。然而如上所说,具体城市与地域的宣传营销,在城市竞争中存在着明显的排他性,优势城市如东南沿海城市,以发达、现代与先进的姿态,形成了一种因政治、文化、经济占优的新型“霸权”,这种霸权深刻影响到电影的创制。如由于城市资本的介入、城市形象的必然发声,造成其中宣传城市凸显地域性的段落与剧情部分的脱节,难以和缺乏地域性的故事水乳交融。冯小刚的另一作品《非诚勿扰》就是如此,它虽然借助“见面相亲”,把各地风景连缀成篇,旅游经济适机而入,“西溪湿地”能够成功地在全国推介开,但借助“导游”之口使这段“西溪湿地广告”独立成篇,观众对此已是心知肚明,即便是风景秀丽,但于剧情也无太多关联。而《唐山大地震》的杭州介入就更显“城市暴力”,具有如此清晰地域的电影,杭州政府依然如此强力介入,冯小刚如此大面积、长时段地表现杭州,无论如何都显得牵强。原本需要表达的城市及其地域性,遭到在现实层面上各种资源占优的发达城市的“跨地域”叙述,这多少引发一些关于影像之外的城市比较,尤其令亲身经历过灾难的人们深感不快,完全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陈林侠,学者,现居广州。曾在本刊发表评论《华语大片中的“人海战术”与“反智现象”》、《虚妄的“双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