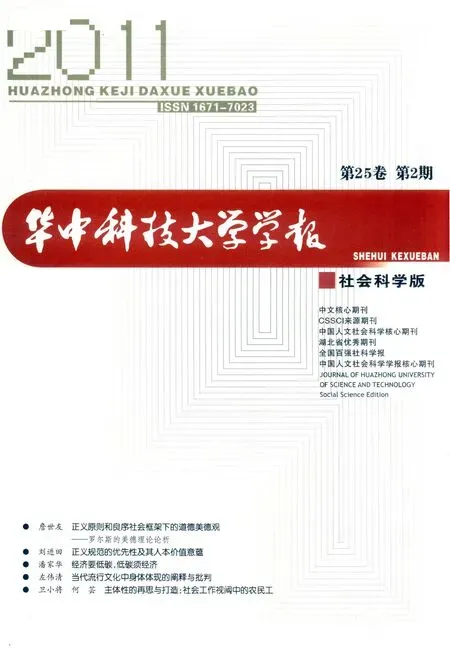“金砖四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比较及思考
戴卫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金砖四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比较及思考
戴卫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被誉为“金砖四国”的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巴西,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等因素,先后于20世纪80-90年代进入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阶段。四国医改主要在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系统、公立医疗服务的筹资机制、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引入以及医疗卫生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不同路径的改革。通过建立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对四国医改的成败与得失做出评价,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新医改”的核心所在。
“金砖四国”;医疗卫生;改革;公平与效率
自2001年以来,中、俄、印、巴四国被誉为“金砖四国”(BRICs)而风靡全球。作为较早走进新兴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如同经济领域改革一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新一轮改革(以下简称“新医改”)正在进行之中。对“金砖四国”医疗卫生改革举措(中国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5年前的“旧医改”)加以系统地比较研究,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现阶段新医改的完善与推进。
一、引言:四国改革前医疗卫生体制的桎梏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随之改革也触及到事关亿万国民健康的医疗卫生体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也先后在医疗卫生领域推行了改革。改革前,四国医疗卫生体制虽不尽相同,但却都弊端百出,不仅难以保障国民的健康,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各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中国与转轨前的俄罗斯一样,奉行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由国家财政全额拨付医疗卫生经费,个人不负担医疗费。与中国相似,巴西在1988年全面改革前实行“二元医疗保障体制”。一部分是面向公务员、工人和银行职员等在正规部门就业的职工个人健康保健制度,另一部分是面向穷人、农民以及失业者的非常有限、低水平的公立医疗服务体系。印度立国初,也奉行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医疗保险制度,但该制度覆盖面很小,而且,医疗保险在卫生筹资中所占份额非常小,政府对卫生的投入重点集中在公共医疗体系上。1983年,印度政府制订了国家卫生政策,在城镇和农村建立初级卫生保健网络。由于缺乏财政投入,印度基层卫生机构缺医缺药现象十分严重,公立医疗卫生系统远远不能满足全体国民的医疗服务需求。
综上,四国基本上都实行了公费(或部分免费)的医疗卫生制度。但公费医疗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等级化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交易成本固然没有,但却产生了大量官僚成本[1]121-128。总体来说,四国医疗卫生体制大多积淀了如下的弊端:缺乏监督机制,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浪费的现象严重;财政全额拨款制度,使得医疗服务缺乏竞争,工作效率低下;尤其是,缺乏费用约束机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四国改革前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各国GDP的比重是这样的:俄罗斯大约为4%(1990年);巴西在改革前1985年为1.6%,改革后1990年为2.3%;而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该比重则相对要低很多,中国为0.85%(1980年),印度为 0.9%(1990年)[2]525-530。
二、全民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选择
根据经济学原理关于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性质,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属于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不难理解,政府应当是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者,而且,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完善也有利于降低国民疾病治疗的成本。在四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方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势。
(一)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网络:构建与问题
印度独立后50多年来,政府一直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防疫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城镇、农村都形成了三级卫生服务网络。2005年1月,针对农村卫生事业的落后状况,政府推出国家农村健康目标(2005-2012),重点在于解决影响国民健康的一系列问题,如厕所与环境卫生、安全饮用水、控制传染病和营养摄取等。目前,印度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15万家,42%卫生总费用用于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等初级卫生保健领域,国民60%的产前服务和90%的免疫接种服务都是由它们提供的[3]96。但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印度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系统还是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1.农村中,贫困偏远地区的保健站尚未建立者居多;有初级卫生中心的大多缺乏必备设施、缺少医务人员和基本药物;农村卫生官员和医务人员不尽责尽职现象相当普遍等。2.在城镇,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不如农村居民;初级医疗卫生站的覆盖率远低于农村;公立医院普遍存在医疗设备、药品严重短缺;转诊渠道不畅等问题。
上世纪30年代以后,巴西开始重视公共卫生,进入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发展阶段。1988年,由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以及“全国卫生大会”的推动,巴西提出了“全民覆盖、公平、连续性、一体化”的改革理念,创建了“统一卫生体系”(SUS)。该方案一改过去强调疾病的做法,开始重视家庭健康服务,它不仅提供传统卫生服务,而且更加关注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营养不足以及居住环境的健康等问题。免费的家庭健康服务是当今巴西初级公共卫生体系的显著特征。如同印度一样,巴西覆盖全体国民的SUS制度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1.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有限的政府财政投入不能保证初级保健、疾病预防和基本治疗等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2.农村缺乏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虽然家庭健康计划、内地化计划等项目正在推进,但仍有将近10%的人口难以得到卫生服务。3.公立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较低,医药供应不充分等[4]。
(二)原有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崩溃与重建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非常贫困之际就创建和发展了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系统。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合作医疗覆盖了农村90%左右的人口,基本保障了大部分国民的健康水平,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称赞。80年代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削弱,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从1978年的90%降低到1990年的5%[5]35-36,农村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情形下,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悄然从农村移向城市,医疗卫生工作形成了“重治疗、轻预防”的局面。2003年“非典”爆发以来,尤其是2005年至今中国政府开始高度关注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建,新的医疗卫生体制重点放在健全基层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1991年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前苏联具有较为健全、覆盖面广的尤其强调预防保健的社会化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后,俄罗斯公共卫生系统长期面临着疫苗、燃料等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中央卫生管理职能的削弱和计划免疫项目存在的不足,使得到控制的传染病重新出现,人口传染病死亡率由1989年的l%提高到1994年的2%[6]32-34,这种现象给俄罗斯敲响了警钟。目前,俄罗斯实行的联邦专项计划有《社会性疾病预防与控制计划》、《俄罗斯联邦高血压预防与治疗计划》和其他地区性的医疗卫生计划。公共医疗卫生再次受到重视,俄罗斯患传染病的人数减少了,平均寿命也有所增加。
三、确立公立医疗服务的多方筹资机制
上个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各国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福利的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的调整。这股浪潮也促使“金砖四国”对本国医疗卫生体制重新定位,开始对公立医疗服务的资金来源渠道着手改革,但四国的筹资机制却不尽相同。印度在建国初就建立了疾病和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方式主要是现金救助和医疗救助。
(一)社会保险筹资:个人责任为主,政府责任为辅
8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企改革,中国传统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遭遇了很大的挫折。经过多年的探索,1998年终于确定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个人责任为主,政府责任为辅”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第一,统账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架构的设计,企业缴费进入社会统筹账户,而职工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改变了过去劳保医疗费用从企业成本中列支、职工不用直接缴费的制度;第二,医疗服务费用由医疗保险支付后,患者个人还要承担相当比例的自费。如起付线以下、封顶线以上以及指定药品目录外的用药开支都是病人自付。基本上形成了医疗服务供给商业化、市场化模式,政府责任退到辅助的地位。
1991年6月,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居民医疗保险法》,1993年通过了《关于建立联邦和地方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规定》。基本原则是强制和自愿医疗保险缴费是医疗保健的主要资金来源。其中,在职人员的强制医疗保险缴费由企业承担,基金的来源是各企事业单位按工资总额的3.6% 缴费,其中0.2%上缴联邦基金,3.4%上缴地方基金,被保险者本人缴纳工资额的1.8%[7]13-20。非在职人员和预算范围内就业人员的强制医疗保险费由政府预算拨款支付;另外,在企业额外缴费和公民个人缴费的基础上实行自愿医疗保险。可以看出,奉行市场经济的俄罗斯摒弃了过去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实施主张个人责任的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国家只对失业者和无工作居民的医疗服务负责。
(二)税收融资:政府责任为主,个人责任为辅
巴西是典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但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构建,却始终依靠积极的政府行为。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占机构总数的70%[8]93-95。以SUS为支撑的巴西公立医疗机构承担着免费医疗服务的主要任务。SUS的筹资为公共筹资,由三级政府(国家、州和市)共同筹集,资金来源于一般税收,包括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以及部分人群交纳的社会保险税等。巴西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按GDP的1%~2%安排医疗保健费用;联邦、各州和各市政府财政预算中,卫生经费分别不少于15%、12%、15%[9]13-18。巴西政府医疗卫生费用的财政支出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一半以上。
四、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引入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世界各地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都相继进行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竞争。基于竞争机制、市场化特征的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引入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吃紧的压力。
(一)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扩张:公、私并存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巴西境内私人医疗服务开始出现,到90年代已形成了公、私医疗服务机构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私立医疗机构集中提供专门服务和住院服务。私立医疗机构从运行质量、效益、管理水平、技术质量上明显优于公立医疗机构。但是,私立医疗机构仅仅满足了20%人口的医疗需求,大部分人买不起私人医疗保险,主要依靠公立医疗机构[10]7-10。因而,巴西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只是对“统一卫生体系”(SUS)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印度独立之初,私立医疗机构的比例仅为8%。公共免费医疗服务的资金不足,导致服务水平和质量都存在很大问题,为此刺激了私立医疗机构的急剧膨胀。1976年该比例为14%,1990年则猛增至60%[11]129–135。到2000年前后,私立医疗机构已经占到医疗机构总数的93%,床位数量占所有床位数64%,估计医生数量为总数的80% ~85%[12]。这一数据仍处于不断上升状态,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几乎垄断了农村和城市医疗门诊服务[13]309–317。可见,私立医疗卫生服务在印度处于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机构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接受服务的人群规模上。
经济体制私有化改革同样促进了俄罗斯医疗卫生领域的私有化改革。除了一些重要的医疗保健设施仍由国家控制外,俄罗斯鼓励私人兴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还将一部分国有医疗保健设施进行了私有化,以建立多元化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体系。由于国家医疗预算不足,俄罗斯政府鼓励民众参加私人医疗保险。俄罗斯高收入群体中,自付医药费盛行,一方面,这对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产生了较大的负担[14]407-423,另一方面,尽管有正式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包,俄罗斯人在资金相当不足的情况下仍愿意或被迫去选择高质量的付费医疗服务,因为付费医疗服务能够较快地从医生和护士那里获得服务。健康状况不好的人则无力支付私立门诊服务,这又刺激了对公立住院和门诊服务的需求[15]331-338。由此,俄罗斯医改模式必须保持过多的公立住院设施和减慢“休克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二)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化:中国的“私有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全面放松干预和控制,医疗机构“自负盈亏”,政府投入逐步降低,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独立经营方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方面普遍推行企业化管理模式,层层实施经济指标考核甚至层层承包,充分将个人收入与业务收入挂钩等等。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化,不符合医疗卫生发展的自身特点,也成为中国医改的一大特色。这种改革方式终于导致了国人一致诟病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目前中国私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市场份额很小,主要提供初级医疗服务和一般治疗诊断服务。私立医疗卫生市场发展限制重重,健康有序的市场机制没有形成,政府和市场在医疗卫生系统中的职能还没有彻底清晰地定位好。
五、医疗卫生服务管理体制的变革
发达国家医疗服务日益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实践表明,只要存在恰当的制度,市场化不仅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而且也可以有社会公平的效益。这种恰当的制度就是有管理的市场化,这是全球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趋势[16]18-29。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医疗卫生服务体制也有管理,但涉及到具体的管理形式有所不同。
(一)从政府集权管理到商业基金管理模式
俄罗斯医改前,承继前苏联的集权管理模式,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险事业,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医改后,俄罗斯的医疗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医疗保险公司。按照1991年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有关规定,医疗保险公司是不受政府的医疗保健管理机关和医疗机构支配的独立经营主体。医疗保险公司履行承保人的职能,负责为受保人支付医疗费;也有权选择医疗机构为受保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可对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进行检查和监督,必要时对医疗单位提出索赔和罚款制裁。(2)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在行政上不隶属于医疗保健管理机关,是独立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商业信贷机构,采用商业经营性基金管理模式。这意味着在医疗保健系统改革中又出现了新的主体。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不仅履行给医疗保险公司拨款的职能,而且履行直接给医疗机构拨款的职能。另外,它还负责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
由医疗保健管理机关、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和医疗保险公司构成的俄罗斯医疗卫生管理体制,虽然属于分权管理模式,但已越出官方性质的平级、上下级之间的分权,商业基金管理模式是其显著的特色。另外,俄罗斯实行医、药分离,避免了药物浪费和“以药养医”的现象出现。
(二)“大部制”科层管理
印度根据本国国情,建立了比较综合的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国家卫生与家庭福利部下属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卫生与家庭福利管理局和传统医药管理局。前者全面负责对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基本医疗服务、医学教育与科研、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后者负责印度传统医药的管理职能。这样的管理制度设计避免了部门之间由于职责分割、目标分歧和工作重点的不同造成的政策协调障碍,提高了管理效率。
巴西医疗卫生管理更体现了科层分工合理的特点。(1)行政管理。建立了集“医疗、医保和药品合一”的“大卫生部制”的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统一医疗体系”由卫生部、州卫生厅和市卫生局三级政府统一领导。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虽然由总统任命,但是要向卫生部长负责,专门负责监管药品的生产和流通。医疗管理局、各级医疗理事会以及私人保险机构分别负责对医疗行为的监管。此外,全国有一支庞大的基层卫生稽查队伍。(2)医生管理。多数州的医生由医师协会负责管理,医生是自由职业者。(3)服务管理。公立医疗机构的双向转诊和“分区分级”制度使卫生资源得到了充分合理利用。(4)药品管理。1998年的国家药品计划实行基本药品的管理制度,通过公共卫生系统免费提供基本药品。
(三)“多头控制”式越位、缺位管理
自上个世界80年代中央、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分灶吃饭”和医院经营“自负盈亏”的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呈现以下一些主要特点:(1)行政管理部门各自为阵。人事部管理机关事业单位的医疗事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卫生部管理公共卫生,进入新世纪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纳入其管理体系;建制于2001年的国家质检总局承担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的部分职能;2003年组成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药品方面的公共安全。(2)医院的“婆婆”很多。有卫生部、卫生厅直属的医院,有各行业系统内的医院,有大型厂矿企业医院,有军队系统的医院及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的乡镇卫生院和卫生所等。(3)政府越位管理。众多的公立医院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关系密切”,政府对医院管得过多过细,医院虽名为公立,却不能为每个公民提供公平的服务,也不能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4)政府缺位管理。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现象其实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与社会医疗机构特别是个体医疗机构相对疏远,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缺乏对个体医疗机构实施必要的管理,以致市场混乱,等等。
六、对“金砖四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考
对“金砖四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内容做分析和比较后,进一步思考其中得失、成败,我们将从中更多地受益。
(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
为解决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得主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概念性框架,这一框架被用来确定一系列影响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17]329。据此,我们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做一框架性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
表1概括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公平与效率上的一般规律。在公立、私营医疗卫生服务的多元体系上,如果以私立服务体系替代公立服务体系,那么,按照资本逐利的本性,其公平性必然是丧失的。在医疗卫生体制管理模式上,采用商业基金经营模式,其效率性是显然的;但其公平性如何要看与其他部门的职能划分是否明确。而大部制管理模式,偏向集权管理,资源过度集中,在处理问题时效率可能较高,但公平性难以保证;但如果权力在制衡中消失,效率也成为一句空话。
(二)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
通过表1的分析框架,我们对“金砖四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做一综合性评价,以观察各国改革措施的公平与效率效应。如表2所示。

表2“金砖四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效果
通过表1、表2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情形:
1.初级卫生保健方面。中国、俄罗斯在医改初期忽视了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保持,导致了医疗卫生大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但后来重建的社会效益在短期内难以显现。而印度和巴西对城乡尤其是农村卫生保健的重视,但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财政投入不足,导致了效率下降,医疗卫生覆盖面、服务水平和质量存在着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与重视初级医疗卫生体系构建本应会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效率性相违背。
2.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筹资机制方面。俄罗斯和中国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效率在改革中间不够明显,这与医疗保险覆盖面、征缴机制以及投资机制成正相关关系。始于2002年,中国农村居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三级政府财政补贴做法,则扭转了政府责任淡化的现象。印度和巴西采用一般税收融资,具备了税收的普惠性原则,但印度真正享受免费医疗卫生服务的人群只占20%,巴西76%的人口只使用SUS体系,主要是贫困人口。
3.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面。中国公共医疗机构的市场化,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而且使其公平性几乎丧失殆尽。俄罗斯公立、私营医疗服务并存,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享受私营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效率,而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则陷入了无力支付私立医疗服务和公立医院门诊服务不足的两难窘境。在印度和巴西,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现了效率与一定程度公平的统一,其公平性表现在私立机构每年向中低收入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服务。正如有学者指出,只要不存在垄断,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所有制形式对于医疗费用的高低以及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并不重要[16]18-29。如果制度不恰当,公立医院也会损公肥私;如果制度合理,私立医院也会承担社会责任。
4.医疗卫生管理模式方面。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大部制管理制度都取得了公平和效率而克服了这种体制下公平与效率不一致性的缺点。俄罗斯的商业基金经营模式改变了原来国家财政拨款的不足状态,但由于医疗保健管理机关、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和医疗保险公司之间的职能远没有理顺,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屡见不鲜现象使得效率下降。中国医疗卫生的越位、缺位管理体制则完全符合了这种不科学管理模式既无公平也无效率的特征。
(三)进一步的认识
从对“金砖四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中国“旧医改”的弊端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了。针对“新医改”笔者进一步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构建公共卫生保健“安全网”的力度。摒弃“重治疗,轻预防”的错误思维,但很难恢复到改革开放前的全民政治性卫生运动和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因为集体经济的不复存在和“赤脚医生”廉价服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此,只有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力度和效仿印度发展民族医药业,这样,在预防和低成本的双重作用下,国民健康才能得到保障。
2.适度水平的医疗保障。且不说西欧福利国家正在削减刚性的福利水平,单就印度和巴西免费医疗的低覆盖率、低质量就足以说明全民免费医疗难以为继,无法提倡。我国个别地区曾轰动一时的全民医疗模式因其地方经济的特殊性不可能在其他地区复制。我国宪法中“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正是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得以证明的真理。
3.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保证公立医院的主导性,规范并扩大私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明确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高效管理责任,推进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制定法律法规,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兴办非营利性、营利性的医院,使之成为公立医院的重要补充。如前文所述,只要立法规范、监管到位,私立医院也可以为穷人服务。
4.医疗、医保和医药三位一体,同步改革。就医疗而言,目前探索社区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尤为重要;选择并建立什么样的费用补偿机制是医保的核心;针对医药来讲,除了斩断医院与药房之间的利益链要增加财政补贴之外,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是重点,同时,要注重纳入疾病谱改变下的慢性病用药范围。“三改”联动,需要先行的是医疗管理模式的改革,包括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进而,要强调的一点是,医院内部管理者管理方式的转变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也是一个核心点,否则,医疗领域再多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1]顾昕:《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郑功成等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石光、雷海潮:《印度卫生体制面临的挑战与改革》,载《中国卫生经济》2008年第9期。
[4]William Savedoff.“Tax-Based Financing for Health Systems:Options and Experiences.”WHO Geneva 2004,http://whqlibdoc.who.int/hq/2004/EIP_FER_DP_04.4.pdf
[5]葛延风、贡森等著:《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版。
[6]饶克勤、刘远立:《经济转型与健康转变: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之二)》,载《中国卫生经济》2001年第5期。
[7]张养志:《俄罗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评析——以医疗保障制度为视角》,载《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年第6期。
[8]姜相春、徐杰:《巴西医疗卫生体制考察与思考》,载《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3年第7期。
[9]石光、雷海潮、高卫中:《巴西和智利卫生改革考察报告》,载《卫生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10]张新梅、徐杰、周伟:《巴西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考察》,载《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3年第7期。
[11]Ashok Vikhe Patil,K.V.Somasundaram,R.C.Goyal.“Current health scenario in rural India.”Aust.J.Rural-Health,October,2002.
[12]World Bank.India,Raising the Sights:Better Health Systems for India’s Poor.The World Bank Report,2001,Nov.3.
[13]Duggal R.“Poverty&health:criticality of public financing.”Indian JMed Res,2007,126(4).
[14]Blam I,Kovalev S.“Spontaneous commercialisation,inequal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mpulsory medical insurance in transitional Russi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6(18).
[15]Galina Besstremyannay.“Out-of-Pocket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by Russian Consumers with Different Health Status.”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2007,14(2).
[16]顾昕:《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6期。
[17]Elinor Ostrom,Roy Gardner,James Walker.Rules,Games,and Common-Pool Resources.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责任编辑 陈卓淳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Reform s of“BRICs”
DAI Wei-dong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China)
China,Russia,India and Brazil are known as“BRICs”.Becaus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the four countries began a series of medical and health reforms during 80-9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They introduced different reforming paths,mainly in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financing mechanisms of public health care,private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rule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the paper evaluate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medical and health reforms in the four countries,and explains clearly what focuses China's"new medical and health reform"should put on.
BRICs;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reform;fairness and efficiency
戴卫东(1968-),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JY033)
2010-09-08
C913.7
A
1671-7023(2011)02-01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