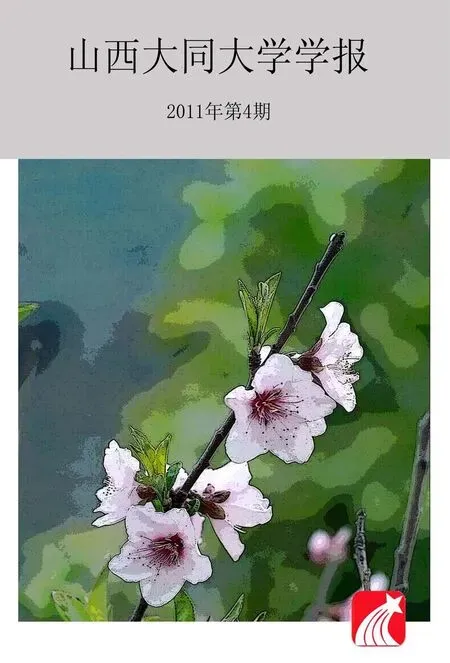北朝时期中原正统观念下的民族身份坚持
——北朝音乐的文化精神
蒙丽静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82)
北朝时期中原正统观念下的民族身份坚持
——北朝音乐的文化精神
蒙丽静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82)
北朝音乐系统中,一直有两种文化并行,一种是代表中原正统文化的儒家社会政治文化,另一种则是草原文化。北朝统治者对于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继承并没有同步到艺术精神领域。一方面他们以汉化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国家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则又保留了强烈的民族艺术特质。具有少数民族特质的音乐文化中的民族性的彰显,正是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表现。
北朝;国家文化形象;民族文化身份;差异
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民族的音乐艺术在整个中国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少数民族的音乐在经过官方的编订修改而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音乐方面的成就极具代表性。音乐在古代时期,总是伴随着歌辞和舞蹈,这就要求语言的畅通和艺人的艺术传承体系有一定保障。但是随着少数民族语言的逐渐消失,北朝音乐的保存与流传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流失。因此,对于北朝音乐的研究,随着鲜卑语的失传,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音乐史料的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可以采用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文本类资料。北朝时期魏收所著的《魏书·乐志》、唐代魏徵等著《隋书·音乐志》以及文学文本中涉及的乐府歌辞。这些文字性的文本对北朝的音乐都有涉及,不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西北部地区的音乐发展情况,在这些历史典籍中都有所反映;第二,是历史文化文本,包括考古发掘以及北朝时期的石窟庙宇的壁画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音乐艺术表演的静止的画面。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北朝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和文化取向提供了可能。
一、北朝音乐文化在观念上的接受与改变
北朝的建立者本就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于音乐有着不同于汉族的狂热和喜爱,音乐在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少数民族使用音乐的场合非常多,包括祭祀、节日、婚嫁、丧葬、战争前后以及畜产丰收等等,歌舞几乎渗透到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且伴有各种具有自己民族气息的乐器。在各地的墓葬出土文物以及北朝时期的石窟庙院的壁画上,都可以看到大型的歌舞场面。关于鲜卑人早期历史中的音乐情况,可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见到间接的记载。据史书记载,乌桓人“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1](卷90,P2980)鲜卑人与乌桓同属东胡系统,习俗与之基本相同。也就是说,鲜卑族在汉代之时已经拥有纯正的本民族歌舞,然而用于郊庙祭祀,建立完备的礼乐制度,却是在进入中原之后。拓跋鲜卑开始逐步走向强大是在始祖力微时期,从那时起,拓跋鲜卑在保持自己传统歌舞的同时,开始吸收中原地区和其他民族的音乐。史籍记载:
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2](卷 109,P2827)
由于北魏正处在中国古代多民族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所以音乐艺术的发展也相应地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点。上述资料显示,拓跋鲜卑不仅在早期部落时代就有自己的音乐,而且在定都盛乐的代国时代,除与中原地区交往而获得乐器相赠以外,更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的音乐艺术相交融,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音乐艺术。不过在吸收同时期音乐的时候,更偏重于本民族的喜好,只是“因时所行而用之”,对于中原音乐中代表典雅的“金石之器”类大型乐器,则采取了放弃的态度。至北魏王朝时期,音乐歌舞开始被有目的地纳入国家的礼乐制度之中。
北魏王朝建国以后,对于音乐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设非常重视,从魏收的《魏书·乐志》到《隋书·音乐志》,对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在文字的表述上基本是一致的,都采用的是汉魏以来的正统音乐观念。魏收这样描述音乐的作用: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昧任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2](卷109,P2826)
这说明在北魏时期,音乐的作用已经非常明确,一是以“和”为核心,二是以“娱”为核心,从敬鬼神到娱乐再到国家祀典,音乐已经开始了由单纯的审美艺术向儒家政治功用的转变。中国古代的文化常常将礼乐并称,在儒家的学说中,更是将“乐”作为孔门教化的一大传统,《论语》中多次提及孔子对“乐”的赏析与理论。“乐”不仅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君子达到“道”的一条必经之途。徐复观先生在谈及儒学中音乐的美与善时说:“乐是通过感官而来的快感,通过感官以道为乐,则感官的生理作用已完全与道相融,转而成为支持道的力量。此时的人格世界,是安和而充实发扬的世界。”[3](P10)徐复观先生对于中国的音乐精神分析得非常到位,音乐首先就是感官的享乐,这与北朝社会大多数时期的审美要求都是一致的;其次,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是音乐与“道”的联系,音乐作为艺术符码,秉持着以和为贵的原则,和谐是音乐要求的最基本要素。这种特性进而被拓展为社会的和谐和政治领域的和谐,因此音乐也就肩负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北朝的各代统治者都接受所谓的“礼乐治国”主导观念,并且也努力按照这种观念积极地建设音乐中的“礼乐”体系。音乐的管理在北魏的文化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即下诏让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定制音乐:
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2](卷 2,P33)
同年(398年),又由左丞相卫王仪率领百官,请道武帝身着袞服,仿照历代帝王追尊祖先,以庄严正式的国家祀典仪式宣告自己的合法性,而邓渊则负责建立官制和礼仪,并且改制出一套适合北魏宫廷在各种正式场合下使用的雅乐。
北魏高祖时代,音乐的礼制作用更为明确,孝文帝拓跋宏连续下两道诏书,强调音乐的道德建设作用。太和十五年(491年)冬的诏书曰:
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2](卷109,P2829)太和十六年(493年)春季又下诏书:
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2](卷109,P2829)
在孝文帝以后,不仅更为激进地肯定了“乐”在礼乐系统中的重要性,更具体到音乐的种类,即对古代雅乐的规定曲目有了要求。帝王对音乐的这种儒家礼乐治国观念,始终贯穿北朝各代,并延续至隋代。《隋书·音乐志》有这样的记载:
其用之也,动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谐邦国。树风成化,象德昭功,启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则,宫商垂范。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外敬内和,合情饰貌,犹阴阳以成化,若日月以为明也。[4](卷13,P313)
除却对儒家音乐代表的社会秩序与教化观念的认同以外,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北朝君主也非常重视音乐建设。北魏的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曾就“乐府”之事多次下诏,采取措施加强音乐的管理与修正,如《魏书·的音乐志》记载: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2](卷109,P2829)
随着与汉文化的深度接触,从北魏到隋代,关于音乐的礼乐制度建设观念也不断地被刻意强化。音乐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以娱四方之民”,也不仅仅如同原初的草原居民在各种场合下传声达情的需要,它的目的已经直接和儒家文化中的“礼乐”所传达的政治秩序相契合。从音乐方面的文化政策、音乐的使用场合以及音乐的使用理念上来看,北魏、北齐、北周直至隋代统一中国,都以汉族的儒家文化观念来建立礼乐制度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封建化统治秩序,这的确是北朝的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历代史家的研究都认为,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钦慕汉族文化,先进的文明取代落后的文明,在这里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很有力的佐证,至少我们从官方的文件上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转变轨迹。
二、北朝音乐的审美倾向
当我们考察北朝文化精神的时候,回到当时的文化语境最为有效。在儒家观念贯穿全部中华历史的时候,北朝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异类,文化的接收和转换在这里有机地进行着。音乐作为文化文本,以最真实地表现解释了这一观念在这个时期的转变,这种文化现象的互文性作用对于打开北朝文化精神的通道提供了最直接的路径。文化观念会引导文化精神的走向,而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艺术气息的变化。从上一节我们知道,北朝对于音乐的观念已经接受了儒家的礼制观念。那么,按照中原传统的代表国家形象的雅乐系统,必须采用正统的乐曲和乐器,才能显示出其正统的合法性地位。北朝的音乐乐曲以及歌辞流传下来的并不多,我们不可能直接听到或观赏到北朝时期的音乐,但是就历史上遗留的文化文本显示,北朝的雅乐系统中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汉族乐器及乐曲,而是在儒家礼制外衣的笼罩下,清晰地表现出北朝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气息。北朝的音乐从乐器到乐曲,并不都按照汉魏以来中原地区流传的礼仪规范选用,而是直接以本民族特色的音乐和乐器进入到官方郊庙雅乐系统中,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一)郊庙雅乐系统中的音乐表现 北朝的各个王朝都希望自己是正统政权的代表,作为宫廷的雅乐系统就应该选取能够代表儒家正声的音乐。从周公制礼开始,礼乐制度就是建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社会各个等级秩序合法化的重要标识。音乐在礼乐的环节中,不是简单的文化行为,而是代表国家秩序的文化模式。因此,汉族的文化传统都很重视对于音乐的建设,从周公制礼到孔子的修订六经,再到汉代的音乐管理的不断加强,作为国家象征的雅乐系统已经较为成熟。虽然乐曲因战乱有所流失,但依然在音乐管理的各个方面有着严格规定,包括对乐理的探讨、乐器的使用和不同乐曲在不同场合的选用都较为完善。《宋书·音乐志》记载:
扬子云曰:“声生于日(谓甲己为角,乙庚为商,丙辛为徵,丁壬为羽,戊癸为宫),律生于辰(谓子为黄钟,丑为大吕之属)。声以情质,质,正也。各以其行本情为正也。律以和声,当以律管钟均,和其清浊之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协,和。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谓之八音。声和音谐,是谓五乐。”[5](卷11)
传统的汉族雅乐系统,声律与天干地支相配而形成八音五声,而能够传达天地阴阳和谐的正式乐器才能称为八音,即金、石、匏、革、丝、竹、土、木。传统的汉族正统乐器有以下几种:打击类乐器如钟、磬、鼓等,吹奏类乐器如埙、笙、箫、笛等,弹拨类乐器如琴、瑟、铮、箜篌等,这些乐器配以宫、商、角、徵、羽的音调,才可以演奏出典雅纯正的宫廷雅乐。对于雅乐乐曲的曲目也十分明确,如《隋书》中记载的:
黄帝乐曰《咸池》,帝喾曰《六英》,帝颛顼曰《五茎》,帝尧曰《大章》,帝舜曰《箫韶》,禹曰《大夏》,殷汤曰《护》,武王曰《武》,周公曰《韶》。[2](卷13)
而且在不同场合下使用的音乐曲目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经过多代帝王的努力,北魏王朝最终确定了比较完整的礼乐制度,完成了纷繁复杂的祭典音乐制作,并且在国家祭典的各项活动中实行。但是我们在史书以及历史留存却发现,北朝从十六国时期到代国时期,再到北魏王朝时期,实际使用的礼仪音乐与正统的中原雅乐并不一致。
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以汉魏模式为基准的官制。官制代表者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确立则依靠“礼”的合法化来展现,诸如宗庙的建立、各种祭典仪式的确立,因为具备“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的功效,音乐便成为这种仪式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定律吕、协音乐”也就成为拓跋硅在立国之初创设基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就是在这样重要的场合下,道武帝拓跋珪仍以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皇始舞》进行郊庙祭祀。《魏书》记载:
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乐用《皇始》之舞。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2](卷2,P34)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2](卷 109,P2827)
《皇始舞》为太祖拓跋珪亲手所定,虽不一定是拓跋珪亲自所创,但是它不是汉族的礼仪宗庙用乐是毫无疑问的。这部歌舞“以明开大始祖之业”为核心,必然是拓跋珪熟悉的鲜卑族所流行的音乐舞蹈经过加工改编而成。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文化信号,北魏王朝虽然以儒家的观念来建立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文化的选择上却很坚定,这种文化即为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之后,拓跋珪又下诏: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2](卷 109,P2828)
由魏收所记来看,在北魏坚持“礼不忘其本”的原则下,长达150章的《真人代歌》是作为郊庙雅乐使用的,以歌颂拓跋鲜卑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为内容。《真人代歌》到唐代时就因语言不通而失传,根据《旧唐书》所记载的目录,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录的北方歌辞相比照,很多乐曲来自于其他的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音乐大集合。除去《真人代歌》以外,《簸逻回歌》也是早期进入郊庙音乐的曲目。《隋书》中记载: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邓渊奉诏“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4](卷14,P313)《簸逻回歌》也出自于鲜卑族,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横吹曲辞”卷记载:
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6](卷21,P309)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以邓渊为代表的官方音乐机构,在北魏早期所定郊庙雅乐系统中,具有强烈的鲜卑和其他少数民族音乐色彩。当然,以少数民族音乐为主流的北魏音乐对于中原的音乐也有吸收,如《真人代歌》在演奏之时就以“丝竹合奏”。但是,汉族音乐对其影响却极为有限,不足以撼动北魏郊庙音乐的整体格局,甚至还有消极抵触之嫌。《隋书》中记载:
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4](卷14,P342)
《魏书》中对太武帝拓跋焘获得中原音乐后的态度也有记载: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2](卷109,P2828)
对于中原雅乐,道武帝直接抛弃,太武帝也只是“择而存之”或“间有施用”,与对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开放式吸纳有着很大差别。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采取强硬措施推行汉化政策时期,作为国家形象之一的音乐也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太和初年,孝文帝就试图以中原雅乐为摹本,建立北魏的郊庙雅乐系统,但“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2](卷109,P2828)这说明,即便是在北朝汉化的最高潮时期,除去增加歌舞的数量以外,依然不能改变郊庙音乐系统的少数民族特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齐和北周。《隋书·音乐志》记载:
(北齐)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4](卷14,P331)
(北周)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4](卷14,P342)
北齐和北周的郊庙雅乐的内容由此可见一斑。北齐宫廷音乐中有西凉、鼙舞等少数民族音乐,到北齐后主就只以胡乐为主。北周号称文化直接承袭“周礼”,却将康国与龟兹的音乐交付管理音乐的大司乐练习,他们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偏爱可以说更胜前朝。后代的魏徵在《隋书》中谈及周太祖制乐时说到:“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4](卷14,P346)音乐的少数民族气质始终鲜明。《旧唐书》也有这样的说法:“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7](卷28,P1040)北朝少数民族音乐占据宫廷雅乐的传统,直到隋唐时期都有很大的影响,隋唐的乐部中就保留了很多少数民族音乐。
(二)民间文化中的音乐表现 郊庙雅乐系统毕竟要受到礼乐制度的影响,在正式的场合之下表达着政治秩序的威仪。相对而言,北朝民间音乐既没有“礼”的制约,又不受“道”的制衡,因此更为自由也更为真实地体现了北朝社会的文化精神。前代许多学者谈及北朝文化的时候,都或多或少把它与文化荒芜和文明落后联系起来,但是历史文本和出土的文物却让了我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让我们感受到了北朝文化精神的丰富以及北朝朝气蓬勃的文艺气息。在汉族地区,民间也有音乐,但是在上层社会流传并代表身份的依然是文人的雅乐,音乐的修养是文人贵族重要的标志之一。以少数民族为政权主体的国家,爱好歌舞本身就是他们的民族传统,歌舞由下而上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致于北魏著名的大臣高允曾上书给文成帝说: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2]
(卷 48,P1074)
高允上书的结果我们不去考究,但从侧面可以看出,北朝音乐风气已经奢华到了一种需要强行制止的程度。从各地出土的北魏墓葬中,有很多都可以看到大型的音乐场面,包括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的司马金龙墓(太和八年,即484年)的石雕乐伎棺床、近年在原雁北师院墓葬群出土的乐俑及乐舞图、敦煌壁画的歌舞以及云冈石窟等,都可以看到大型的乐舞场面。其中坐落在北魏都城的云冈石窟在音乐表现上极具代表性,所展现的音乐材料也极为丰富,显示出音乐在各种意识形态间的有机融合。云冈石窟的早期洞窟和中期洞窟开凿于北魏王朝的鼎盛时代,即北魏平城建国后直至迁都洛阳之前的近百年时间内。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统计,云冈目前尚有22个洞窟雕刻乐器,可辨识者600余件,近30种。中国艺术研究院肖兴华研究员对云冈石窟中期洞窟考证后指出:
在使用的吹奏乐器中,其中横笛、排箫、箫、笙都是中原汉族地区常见的传统乐器,……还有唢呐、中间横吹的管乐器吐良(或者是两头笛)、筚篥、笳分别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在弹拨乐器中,琴、筝、瑟、阮是中原汉族的传统乐器,而琵琶、五弦、箜篌则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或西方的国家。打击乐器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8](P643)
云冈石窟的开凿虽然是皇家工程,但是对于音乐场面的描述并不似郊庙雅乐那样拘于形制,只是工匠根据所见乐器与乐曲演奏场景的再加工。石窟中显示出的乐器让我们可以捕获到这样的文化讯息:北魏时期,不论是对中原还是对北方草原地区的各民族乐器都有广泛吸收,所选的乐器大都精致玲珑,适宜于马背上演奏。对于大型的音乐场合的描绘则要数蔚为壮观的云冈石窟的第12窟。它素有“音乐窟”之称,也称“佛籁洞”,其表现内容为释迦牟尼成道“初转法轮”而举行的盛大庆典。洞窟顶部以平棋藻井为界,十朵莲花摇曳着千年音乐的芬芳;六座歌舞飞天的圆凸浮雕环绕石窟顶部四周,其体形圆润健康,形制大于四周浮雕乐伎,中间一位手无乐器合掌上举者,宛若偌大的音乐盛典的指挥,其余五人手持不同乐器,宛若各音部领队;加之以层层叠叠的歌舞伎,组成了庞大的音乐场面。与汉族音乐的疏朗雅致不同,北朝的音乐歌与舞相配,使得静态的场面具有了生动的气息,也不拘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整个画面具有强烈的音乐节奏感,热情而急切地传达着喜悦的感情(见图1)窟内乐器多为少数民族乐器,虽也夹杂着阮与筝等中原传统乐器,但适宜于马上演奏的乐器配置,显示出以民族音乐文化为主的多元化音乐格局(见图2)。图中乐器从左到右依次为贝、羯鼓、排箫、五弦琵琶、羌笛、阮、曲项琵琶、筚篥、竖箜篌、弹筝、细腰鼓等,多属西凉、龟兹、天竺乐器,均适宜于马背上演奏,具有强烈的多民族风格。它不仅生动地展示出北朝社会音乐集会的盛况,更清晰地表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已经具备很高的音乐素养,音乐文化已经高度发达,有能力操控大型的音乐盛典,并且完美地演奏复杂多变的乐曲。

图1 云冈石窟第12窟前室北壁顶部

图2 云冈石窟第12窟前室北壁顶部与窟壁连接处(局部)
北齐和北周继承了北魏的音乐传统,社会的音乐的交流更为广泛,中原音乐在北朝的土地上也发生一定影响,如北魏末年到北齐初的李元忠就以善于弹奏汉族传统乐器“筝”而著称。《北史》中记载:“会齐神武东出,元忠便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引入,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9](卷33)但以少数民族为政权主体的主流上层社会,都还没有改变自己的文化习惯,依然喜爱少数民族音乐,例如典型的少数民族乐器——琵琶,在北朝社会就广为流传,很多人都会演奏。北朝的典籍就此多有记载,如北齐一代才子祖珽,就可以熟练地弹奏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9](卷39)北周周武帝宇文邕灭掉北齐后,俘获君臣多人,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二子高孝珩也在被俘之列。此二人均为帝室贵胄,周武帝可以弹少数民族乐器琵琶,而高孝珩则能够吹奏汉族传统乐器竹笛,“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裁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10](卷11,P145~146)北朝的少数民族音乐,也深入到各个阶层,不似南方成为文人的专宠。北齐大将斛律金作为一介武人,竟然可以传唱出能够打动军心令人声泪俱下的北地歌谣:“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10](卷2,P23)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朝文化精神中的少数民族审美倾向非常明显,即便是中原的儒家文化观念对于意识形态系统有着很深入的改造,都难以抹去旧有的文化习惯。
三、北朝音乐中的文化性格及文化意义
中国的艺术文化发展到北朝这个时段,已经开始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中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不同的文化系统的相互碰撞。虽然如同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北魏王朝的文化以汉化为主要特征,但是汉化恰恰是因为许多固有的少数民族特质一直存在,而且这种汉化过程的结果又使得中原的文化精神具有了浓重的北方民族特性,为新型文化精神的出现启发了先声。在北朝过去的研究中总有这样的偏见,似乎北朝时期属于文化的荒漠,或者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北朝时期的中原文化相较于草原文化而言,或许有过停滞或发展迟缓的时期。然而,对于整体的北朝文化来讲,艺术的气息从来就不曾少过,曾经一度在这个区域的上空弥漫着无比灿烂的草原文化。文明或许有先进的或是野蛮的,但是从文化艺术的角度考虑,却只有多样化的共同繁荣。北朝的音乐文化告诉我们,这个时期的北朝帝国强大而且繁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面对各种各样文化的摄入并不拒斥,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
出于对意识形态的实用的和功效性的建设,北朝的帝王及其官吏虽然以少数民族音乐系统构筑起宫廷雅乐系统,但是对于以中原礼乐文化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却非常坚定。中原的儒家音乐文化自周公制礼以来,在文化空间的表现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是在特定仪式下,以神性的方式彰显着社会等级秩序,并以天道的方式传达着王权的合法和威仪。这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稳定社会以期国祚久长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北朝社会对于中原礼乐文化的认同和构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既然对于政治有如此的益处,北方的统治者毫不犹豫地启用了汉族的礼乐体系,并把它纳入自己的官方政治系统之中,催化成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至于对仪式中音乐文本本身的要求,北魏的统治者以“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2](卷109,P2828)为由,自信地按照自己的审美习惯,把民族音乐放在宫廷雅乐的位置上。这样,既完成了神圣的道德秩序的建设,又满足了自己的审美需求,促进了音乐的良性发展。从此,北方在鲜卑乐歌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多民族音乐融汇的胡乐系统,并显示出朝气蓬勃的活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的音乐文化系统中,有两种文化一直并行存在着:一种是代表中原正统文化的儒家社会政治文化,另一种则是草原文化。体现在音乐中,则是对旧有文化习惯的坚持,由此显示出北朝文艺思想审美取向的标准。对于中原实用的政教观念的继承并没有同步到艺术精神领域,拓拔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由草原社会进入中原农耕社会,必然要求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他们以汉化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国家文化形象,使得自己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保留了强烈的民族艺术气质。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是可以被感知和确认的,因此在文化的交融中,当艺术形式所承载的文化超出本民族文化区域时,差异就被凸显出来并达到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的作用。北方音乐与代表着正统的南方音乐在选择上的巨大差异表明,在与异质文化相比照的过程中,具有少数民族特质的音乐文化中的民族性被彰显出来,这正是北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表现。音乐文化传统是组成北魏文化身份的要素之一,“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而“不忘其本”就是民族历史记忆对本民族凝聚力的强化。
[1](刘宋)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北齐)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唐)魏 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萧梁)沈 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后晋)刘 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肖兴华.云冈石窟——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带来了音乐繁荣的历史见证[A].云冈石窟研究院.2005年云冈石窟学术会议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9](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编辑 赵立人〕
National Identity Holdout under O rthodox Mentality in Northern Dynasty in Central China
MENG Li-ji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Movie Arts,Beijing,100082)
In themusical system in Northern Dynasty,there existed two cultures,one was the Confucianism,standing for the orthodox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and the other was the grassland culture.The rulers in Northern Dynasty did not inherit art and spiritual things as quick as they did in political culture.On the one hand,they established their national cultural image in the way the Hans did,and on the other hand,they preserved their strong ethnical art characteristics.The display of theirminority nationality in theirmusical culture was exactly the expression of their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of northern people.
Northern Dynasty;national cultural image;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difference
K235
A
1674-0882(2011)04-0023-07
2011-06-30
蒙丽静(1971-),女,山西大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