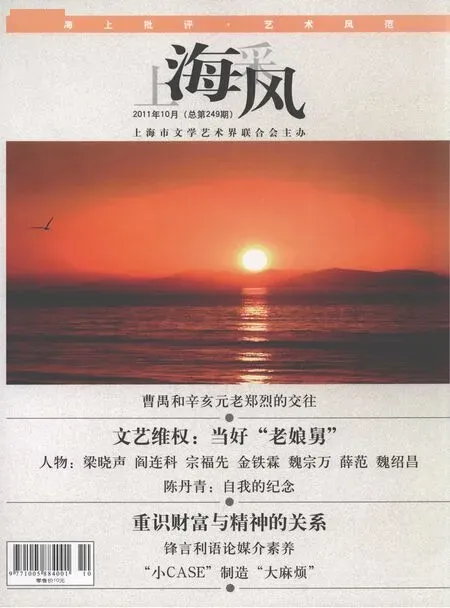阎连科:文学之上,生活之下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阎连科
河南嵩县人。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8年应征入伍,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等。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受活》等;小说集《阎连科文集》(5卷)、《阎连科小说选》等;散文集《回望乡土》、随笔集《桎梏》等。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其中《黄金洞》(中篇小说)获第一届(1995-1996)鲁迅文学奖,《年月日》(中篇小说)获第二届(1997-2000)鲁迅文学奖 。

在约好的时间采访阎连科,却被太太告知不好意思请再等等,因为,“他去楼下溜狗啦,有时候我们家狗要抱着回来,所以会有点慢”;正好奇是怎样的名犬如此得宠,阎连科果然抱着狗回来了,却不是什么名犬,只是一只貌不惊人的京巴。阎连科说,这只京巴已经14岁了,“算起来也是个百岁老人了”,所以上下楼有时候走不动了,这才抱着回家的。“它和我们生活了十几年,已经是像家人一样了,”阎连科说:“你别小看它,这狗身上也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呢,以后等它不在了,我打算要给它写一本书。”
茅盾文学奖——“今年还算靠谱”
这一次想要采访阎连科,最初是因为看了他的微博——是的,并不是只有郭敬明才有微博——在8月12日的微博里阎连科半调侃半呼吁地写到:“文坛离我越来越远,今天才听说茅奖初评的前列名单,觉得‘靠谱’就有一种欣慰感。文学已经没有好坏标准,‘差不多’就让人觉得评委们还有人心文德。法律都草绳一样让人到处扔了,不指望把草绳一样粗糙散乱的文学标准变为文法之准绳。亲爱的评委们,只要评个靠谱和差不多,俺就向你们致敬了。”如今茅奖尘埃落定,我忍不住好奇这个结果在阎连科的眼里可算“靠谱”么?于是拿这个问题问他,阎连科连连大笑,说:“还是比较靠谱的吧。比起往年,今年的评选过程就很靠谱,评委从数量上就比较多,有60多个,这种情况下至少想要去通关系拿奖的也没那么容易了吧——评委太多通不过来嘛。”至于五部获奖作品里面最喜欢哪一部,阎连科回答得很技巧:“我实在说不出个‘最’来啊,因为这5部作品我觉得水平都差不多。可能是因为评委多吧,所以选出来的作品水平也是很平均的,都不错。”但“很技巧”就不是阎连科了,果然他话锋一转,又说:“这5年来,其实我觉得国内作品的水平都是比较平均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都不错’,反之也可以说‘都没什么特别好的’。几乎,不,是根本没有像头几届茅盾文学奖的某些获奖作品那样,出现个别非常出挑的、得到大众广泛认可的好作品。这是值得思虑的现象。”
记者:对于这一次获奖的5部作品,有很多读者认为它们几乎都是在讲落后的农村、鄙陋的民俗以及弱势的群体,而且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或者趋势,就是很多作家可能为了迎合国际口味,而有意无意去写中国农村的愚昧和落后来吸引外国人眼光,以获取国际关注甚至奖项。比如这次获奖的莫言的《蛙》,作品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是拿“计划生育”和“超生游击”这种中国特有的国情做卖点,这个作品写出来就是为了到外国拿奖的。作为一个作家,你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阎连科: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先说茅奖,我们往年评奖肯定不会特别以题材来划分的,难道最后获奖的作品一定要给改革题材一个名额、给军事题材一个名额、给城市题材一个名额么?怎么可能。我的观点是,文学的好坏优劣不是以题材来划分的,我们不要有思维定式,什么写农村的就是落后愚昧的、写改革的就是主旋律的……文学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只有水平的高下,没有题材的好坏。
至于读者和评论界认为的,作家靠故意写中国农村的落后来与世界接轨,我认为这个是大家的杞人忧天吧。如果说写点农村的落后的就能与世界接轨,那中国文学应该早就和世界接轨了(笑)。结果到现在也没接上轨,不就说明这些假想都是不存在的么。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世界各大电影节拿奖的时候,这种拿中国的落后去取悦外国人的说法就一直有,可是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也没见哪个作家哪部作品是仅凭借这个捷径就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那些走出去的凭的都是作品本身的艺术力量。而且说到与世界接轨,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文学首先要满足中国的作者,这个和中国的经济不一样,它并没有一个迫切的在某个时间点要与世界接轨的需求。并且文学也不是靠签几份国际合同或者输出几个外文版权就能与世界接轨的——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并没有像宣传里说的那么有影响。
记者:所以近年中国作协确实非常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
阎连科:可是这个问题可能是越关注越走不出去的恶性循环,不关注说不定就走出去了。我这么说可不是在贫,我个人确实认为,文学的传扬不是靠作家协会或者国家力量去推荐了,西方或者全球的读者就能接受的。有的时候不管不抓不推荐反倒是最好的文学生态。文学需要一种宽容的生态,当我们去“推荐”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选择”的行为,而我们推荐出去的东西就等于是把我们自己主观意志的选择硬塞给了人家——就好像我喜欢吃辣的我就把我认为最好吃的辣酱推荐给你,我是真心觉得好的,可是也许你根本就不吃辣呢。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最好的传播状态应该是我们敞开胸怀,以自由、开放的姿态欢迎世界各国的读者来选择、来了解。
《四书》难出版——“审慎过头就是神经了”
在台湾麦天出版社出版的阎连科长篇新作《四书》一书的腰封上,赫然标注着这样的文案:一本尚未在中国出版,便已消逝的传奇禁书。当然当然,这只是出版社惯用的夸张式宣传手段,何况台湾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情况是,《四书》确实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得到出版,其他语言的版权也已经落实并处于翻译阶段,而最原始的简体字版本却还处于无期等待之中。
大约在六七年前的一天,阎连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念头:一个人,手里有一杆枪,遇到谁都把枪递给对方,说你把我打死吧。而到了2008年底,阎连科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转型,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引进成为大学教授。学院领导叮嘱他,只管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其他都不用担心。于是,他开始把那个荒诞的念头写成一部小说:他把故事背景放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到一个叫做“育新区”的地方劳动改造,要求他们成为“国家新人”。小说的叙述亦真亦幻,高度抽象同时又极其具象,十分荒诞同时又异常真实。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姓名,几个主要人物依他们先前的某一种社会身份命名。“学者”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学者;“音乐”原来的身份之一是钢琴家;“宗教”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基督教徒:“作家”原来的身份之一是作家;“实验”原来的身份之一是实验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以其生理年龄命名的,这就是“育新区”第九十九区的管理者“孩子”。阎连科别出心裁,把这第九十九区一百几十号文化罪人的管理者设置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并且“孩子”是这里惟一的主宰者。孩子管理他们的方法是实行幼儿园式的“红花、五星管理制”,即谁表现好就发给他小红花和五角星。攒够一定数量的红花和五星,就算成为“新人”了,就可以自由回家去。为了自由, 这些知识分子都成了红花与五星的奴隶,孩子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如果他们不听孩子的话,孩子就会拿出一把铡刀,让对方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孩子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听说很早以前,这个国家和日本人打仗,有个16岁女孩,头被日本人铡下来,因此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英雄。那孩子一直想成为英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梁鸿在读到这些情节的时候忍不住叫绝:“在中国历史上,小儿皇帝并不少见,而在《四书》所描述的那段历史上,不正是十几岁的红卫兵决定着无数知识分子的生死命运吗?”而这也许正是阎连科写《四书》的目的:把现实中看似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进小说,并让它们在小说中读起来非常合情合理。也正因如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阎连科的小说就经常被冠以“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诸多名头;但在那个时候,其实阎连科自己也并不能很清晰地说出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写的原因。然而就在《四书》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阎连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厘清了自己那种写作方式的思路——他将其命名为“神实主义”。于是,他又把这个发现写成了长达十万字的文论《发现小说》——在创作中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被现实主义掩盖了的真实。
今年,《发现小说》终于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作为这本文论的实践主体《四书》却依然在继续等待着与读者见面的合适时机。不过阎连科对此并不介意,他说,《四书》在创作的最初就是被自己当作一次“不以出版为目的的写作”。而今年2月在人民大学举办的 《四书》以及文论《发现小说》研讨会上,阎连科更是自己印刷了几百本《四书》作为“亲友赠阅本”送给了与会学者和朋友,把一个原本有点敏感的难题处理得轻松自然。
记者:《四书》都已经在开研讨会了,是不是意味着大陆的出版指日可待?
阎连科:这次的研讨会上我是自己私人印刷了几百本送朋友的,目前来看,恐怕在大陆出版短期内还是希望不大。这本书我到现在可能送了差不多20家出版社吧,都被退回来了,我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我写得不好,哈哈。其实我知道,但凡作品和现实的距离保持得过近就很容易引起争议,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都是这样。也许有的作家经历了几次这样的遭遇就会尝试改变表达的方式,但我不会,我认为,作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独特性,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是作家中少有的固执的人,又是特别笨的人,我已经浪费了较长的时间,也不想当官,我的日常生活过得比一般百姓好,为什么不彻底放下包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放下一切功利的思考写出来的作品,即使不出版我也释然。可以说,因为某些原因,这几年我的写作是原地踏步的、犹豫不决的,甚至是妥协的;但至少《四书》是一本我觉得完全放开自己的作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完全放开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写作的张力,在艺术性上、语言上都非常接近一种从心所欲的表达状态。《四书》是一次让我放下各种束缚的写作,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记者:可是对于你这样重要的一部作品,至今在大陆还无法出版,你会不会很遗憾?
阎连科:虽然《四书》是不以出版为目的的写作,但我当然还是希望它可以出版啊——港台的读者可以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读者可以看到,可是我们本土的读者却看不到,我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也非常理解出版社,毕竟我们有我们的出版环境。不过现在的这个出版环境我真的说不准,好像很多书“居然”都可以出,很多书又“居然”都不可以出。
记者:真的那么理解出版社么?我看到你的微博上对《坚硬如水》再版时出版社不通知作者自行删改的事情很有些抱怨啊(笑)?
阎连科:是有这事。而且除了这件以外,最近朋友编一本小说集,收入我的短篇《柳乡长》,写的一个村庄靠小姐们致富的故事,竟觉得不宜出版需要更换。这我就太不理解了——连早已出版、已经再版无数次的小说都要在今天再一次阉割,这究竟是文艺政策所致,还是个别的文化官员和脑袋如木的编辑所致?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看不懂的——很多书“居然”都可以出,很多书又“居然”都不可以出。
所以《四书》的遭遇其实是我写作之前就预料到的。难以出版的原因,是大家将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最表面的“写的什么东西”上,而没有集中在内在的“叙述想要表达什么”上。其实除了出版界,中国作家也有这个情况,作家本身在写作中有本能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约束,明白地知道这些是可以写的,那些是不可以写的,而有的写到那里就必须拐个弯的——我们的文化界用六七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自我约束的过程,让自己心中有了牢笼。而我想的是,一定要有那么一两次,我能自己亲手打破牢笼。
而对于出版社,我真的能够理解他们的审慎,但审慎过头就有点神经了。 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是不怕别人管理我们,就怕自己管理自己。
记者:那么如果最终大陆可以出版《四书》但要删节,你接受么?
阎连科:我接受的。我还是希望有更多本土的读者能阅读到这本书的,其实我也曾经为一家出版社改了好几稿了,可是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无限延期了。但是我也不怪他们,不同于对《坚硬如水》事件的不满,对于《四书》的情况我很理解他们。
记者:说到对出版社的理解,我看你微博上对出版社总是找你为新书写推荐很是为难,对么?
阎连科:哈,你也看了我微博上的“推荐门”啊。对于这件事,我第一感觉就是现在的出版部门怎么创意越来越少,这个“名家推荐”的宣传方式已经用了多少年了,读者早已从一开始的新鲜变成今天的厌倦了,出版社就没有新招了么?当然从个人来讲,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人家,如果因为我多说了两句而给后辈写作者带来机会和促进,我本身是很愿意做的——前提是确实值得推荐。可是每年总有那么几本书,内容并不值得,可是碍于友情、关系等各种因素,我也不得不写了推荐,这种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为难,特别对读者过意不去。
记者:也别那么过意不去了,其实现在的读者都懂的,很多推荐都只是出版社的营销手段,都不会很迷信那个的。
阎连科: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很缺乏一个权威的、有公信的荐书平台。我们很多报纸的阅读版面和图书销售网站都有畅销书排行榜,可是有几家榜单是公平公正的呢?有几家是能够得到读者信任的呢?在欧美国家,总会有几家媒体的书评是绝对权威的,比如英国卫报的书评,纽约时报的书评,读者甚至作家和出版社都对它们非常买账,这样的媒体就起到了引导公众阅读的积极作用。而这种具有公信力的引导或者说这种“公信力”本身正是中国社会目前非常缺乏的。
生活之下还有生活——“我不会再绕道而行”
今年年初,顾长卫导演的电影《最爱》大热,引发关注的除了具有争议性的“卖血”和“艾滋村”话题,除了郭富城和章子怡颠覆性的表演,还有一个就是这部《最爱》与之前阎连科遭遇再版禁令的小说《丁庄梦》之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血脉关联”。对此,阎连科总是在各种采访场合中一再声明:“作为一个记者和观众,你也许有你的看法和判断,但我还是要说《最爱》和《丁庄梦》没有关系,和我本人没有关系。”但是,《最爱》作为一部耗时四年险些没有机会面世的电影,《丁庄梦》作为一本关于河南艾滋村的至今不能再版的书,阎连科作为一个据说内地写出“禁书”数量最多的作家,三者之间任何形式的关联组合都具备足够的话题性:比如,《最爱》的编剧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那个“言老施”,真的不是“阎老师”阎连科吗?
记者: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说《四书》是一部你写得非常放松的作品,《丁庄梦》应该就是一部写得比较紧张的作品了。
阎连科:《丁庄梦》对于我并不是一个好的写作体验。我始终认为在作家的一生中,遇不了几次最好的小说题材。我遇到了,但我把它浪费掉了。
当年《丁庄梦》写出来就有很多人称赞它的“现实”与“残酷”,但其实那个村庄的现实更残酷,2003年9月当我第一次走进河南开封尉氏县某艾滋病村时,最先看到的就是村边土墙上用白石灰刷的三个字——“卖棺材”。村里时有裸体行走的人,裸体是因为感染艾滋病皮肤起疮,浑身痒痛无法穿衣;而那些裸体的人,没有人认为他们不正常。在那个村子里我确实受到了震撼,所以我原来的计划是先写一部非虚构作品的,百分之百真实地记录这个村庄,用最真实、最朴实的文字写一本书。之后再写一部完全释放想象力的虚构小说,一部极其疯狂的小说:靠卖血,让一个农民变成一个皇帝、一座村庄变成一个富有的国家的过程。我想过一个疯狂的情节:有一条像石油管道一样的血液管道,通到欧洲,通到美国,从无数人身上采来的鲜血流到那边去。你不听我的,我把阀门一关,你那个国家就彻底灭亡。这是我在构思这部小说时让我极其疯狂、极其得意的情节。
结果阴错阳差,非虚构作品没写成,我构想中最好的小说故事也没写成。因为2004年《为人民服务》的风波,导致我对事实的揭露向后收缩了很多。即便今天人们说《丁庄梦》在海外有多少翻译,说它多么多么好,事实上我自己知道我原本能把它写得更好,但是我在现实的困境面前选择了“绕开”,这也是我的无奈和遗憾。现在写作的激情过去了,没有任何办法补救了,写小说就是这样,它是个一次性的活动,是不能重复的劳动。
记者:你觉得自己浪费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且无法补救,那么会希望今天可以出现另一个作家去直面你当初“绕开”的那些吗?
阎连科:其实我觉得即使是今天也很难有作家可以写出一个真实的丁庄梦,因为根本没有其他作家到艾滋病村去,很多作家根本都没有机会直面生活。我经常想,我们掌管文化、文学的部门每天都在提倡大家要体验生活,可一旦某种更深刻、复杂的生活到来时,大家就集体沉默了。没有其他的中国作家到艾滋病村去,也没有作协的领导支持大家去,大家知道的也都是通过媒体知道的,而媒体又只能把一些过滤的消息告诉大家。我觉得,中国作家从根本上说是不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或者说是不参与“老百姓生活”的。今天的作家包括我在内,过的都不是“老百姓生活”了。
我们为什么不是主动、自觉地去感受生活,为什么老是被组织、被安排去体验生活?比如“黑砖窑”、“毒奶粉”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没有作家去表达个人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一代作家,甚至比我大的1950年代作家,比我小的1960、1970、1980年代作家,都是有问题的。
记者:那么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应该是什么呢?
阎连科:就是写作要直面真实的当下,面对现实不要绕道而行。比如,我始终认为,现在我们大谈中国经验的同时,还应该谈中国教训。不能只谈所谓好的一面,对不好的一面闭口不谈。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谈中国经验,经常谈到的是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谈的是改革开放成果,这些都是不完整的。而对于作家来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都不能脱离“真正的、完整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