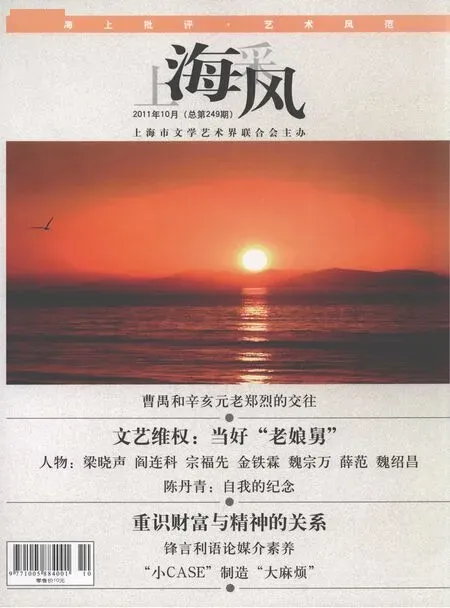曹禺和辛亥元老郑烈的交往
文/曹树钧


曹禺清华毕业照(1933年)
郑烈,字晓云,早期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的元老,我国杰出戏剧家曹禺第一位夫人郑秀的父亲。曹禺与郑烈的交往在他早年生活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交往,曹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讳莫如深。今年欣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段尘封已久的史实,理应还它的本来面目,这既是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也是对曹禺这位我国现当代戏剧史上首屈一指的杰出剧作家生平研究的一个应有的补充和还原。它还需从曹禺和郑烈女儿郑秀的初恋谈起。
清华园演话剧月下定情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期的初恋更洋溢着诱人的芬芳。1933年,一个女大学生闯进了曹禺的生活。她叫郑秀,也在清华大学读书,是法律系的学生;曹禺当时在西洋文学系学习,与后来蜚声文坛的钱钟书是同班同学。
曹禺与郑秀第一次见面在193l年,曹禺在清华大礼堂演《娜拉》的时候。那时郑秀还在北京贝满中学念高中。
演出结束后,郑秀听清华同学成己介绍刚才演娜拉的就是曹禺,大吃一惊。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矮个子男青年,圆圆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布长衫,貌不惊人,简直想像不出刚才台上活蹦乱跳的娜拉就是他。
曹禺也凝神注视着这位陌生姑娘,趁成己介绍的时候,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她:高高的鼻梁,红润的脸庞;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发出动人的光彩;身材苗条,面容清秀,一副大家闺秀的仪表。不知为什么,曹禺第一面便对她有一种亲近感。
第二年秋,郑秀考进清华法律系,曹禺闻讯暗自高兴,但苦于没有接近的机会。
1933年春,清华话剧社排演英国话剧《罪》。高尔斯华绥著,三场话剧,又名《最前的与最后的》。此剧由曹禺翻译、导演,男主人公拉里由他主演,拉里的女友汪达,曹禺特邀郑秀担任,借机可以接近郑秀。
排练在二院九十一号曹禺的宿舍里进行。前后排了一个月。每次排完之后,曹禺都送郑秀回新南院宿舍。在一个月的接触中。郑秀感到曹禺这个人聪明、有才华,对自己有一种灼热的、特殊的热情。
但又觉得他个子太矮,自己穿着高跟皮鞋比他还高一点,不是理想的朋友。她想找一个学理工科的,人再漂亮一点,更有魅力些。
曹禺知道郑秀每晚都在校图书馆自修。他每次到图书馆阅览室,总看见她专心致志地在用功。一天晚上,快八点的光景,曹禺拿着一张剧照,约郑秀出去走一走。郑秀正在专心看书,便说:“有什么事?待会儿吧!”
曹禺说:“好吧,我回头再来接你。”
到九点半,图书馆快要关门了,曹禺又来了。他将一张他扮演《娜拉》的剧照送给郑秀,并说:“我们沿着新南院后面的河边走走,好吗?”
郑秀心里想,他盛情邀请我,就当是我的老大哥,跟他一块走走吧。于是,就大大方方地同曹禺一起出外散步。
曹禺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爱好,谈起他的父亲、母亲。郑秀很奇怪,家宝(曹禺本名万家宝)平时沉默寡言,排戏时话也不多,今天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话。她只是听,不大搭腔,而且走得很快。曹禺老觉得跟不上她。
又一天晚上,曹禺约郑秀出来散步。他戴着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左臂夹着一大叠书。他拿出一张照片给郑秀:“这是我母亲的相片,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接着又说:“郑秀,我有句话想告诉你。”
可是停顿了好一会,他又不吭声了,只是一个劲地朝前走。走着走着,忽然左臂夹着的一叠书散落在地上。曹禺忙蹲下去捡书。慌乱中,一副眼镜又掉了下来。郑秀见他的窘状,禁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忙帮他将眼镜捡起来。这时,她忽然发现曹禺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现出异样的光采,蕴含着深邃的智慧之光,似乎有一种摄人魂魄的美。郑秀凝神注视着曹禺,曹禺也深情地看着她。好一会儿,郑秀才醒悟过来,满脸绯红,掩饰地说:“天不早了,该回去了。”
“还早呢,再走走吧!”曹禺挽留地说。
说也奇怪,郑秀也不由自主地同他又并肩散起步来。她的脚步自然地放慢起来,听他谈将来;谈她的优点:聪明、大方、用功、活泼……听着他那娓娓动听的言谈,郑秀心头荡起幸福、甜蜜的感觉。
“我认为我们两个性格不同。我是家里的大女儿,从小在教会学校读的书,我讲究严谨、洁净;讲究仪表,花钱花惯了。从小过的是独立生活,长大了脾气也不好。我们两个交朋友,怕不合适。”她很直率地向曹禺说。
“性格不合,相互会了解,多谅解就行。我觉得你很像我母亲,慷慨,落落大方,有大家风度,又有抱负。不光我喜欢,我妈妈也一定会喜欢你的。”曹禺也很直率。
原先两人散步,是曹禺一人谈的多,郑秀很少插话。自从“捡书”事件之后,似乎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她的芳心,郑秀开始主动地谈她的家庭,她的经历,尤其喜欢谈宠爱她的爸爸郑烈,于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辛亥元老的形象,在曹禺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起来……
扮邮差黄龙岗九死一生
在散步过程中,郑秀滔滔不绝向曹禺谈起她父亲郑烈的往事。
“我的父亲郑烈,字晓云,福州人。他和辛亥先烈方声洞是至交,还是亲戚。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宣统三年(1911年)父亲与方声洞一起,在同盟会最高军事指挥员黄兴策划下参加广州起义。起义缺乏武器,方声洞、郑晓云等商议,事先买了一口大的楠木棺材,将武器放在空棺内。进广州城门时,清官喝令开棺检查。方声洞急中生智,谎称开棺钥匙忘带在身边,同时又给清官塞了一些好处费,这才将棺木运进城里。不料起义时,寡不敌众,方声洞、林觉民等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方声洞身中数枪逝世,也有人受伤被俘惨遭杀害。广州起义共死难烈士86人,事后收拾烈士遗骸72具,合葬在广州城郊黄花岗,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听父亲说,在这次起义中,他幸免于难。他和辛亥元老胡汉民一起从死尸堆里爬出来,胡汉民化装成琴师,父亲化妆成邮差,才逃出封锁线,捡回了一条性命。方声洞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广州起义前一夜就写好两封遗书,一封给父母,一封给妻子王颖。在给父母的信中,方声洞说:‘先男儿在世,若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视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在给妻子王疑的遗书中,方声洞还写道:‘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并叮嘱妻子他死后要‘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旭儿指的是方贤旭,他生于1910年,和你同年。二姨夫父亲罹难时,他刚满周岁……”
谈起方声洞的姐姐方君瑛,郑秀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她告诉曹禺,方君瑛是父亲最赞叹的一位女杰。她领导能力、组织能力特强。在同盟会中,大家一致推举她当实行部部长,负责行刺、暗杀清廷巨官。孙中山先生特别看重她的头脑冷静,为人正直,办事缜密果断。福州光复后,父亲等共举她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后往法国留学,成为我国女留学生在法国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人。
“可惜,”说到这儿郑秀忽然长叹了口气,“她1922年回国不久,就在第二年,在寓所吸吗啡自杀,因服得过多,不治身亡。”
“她为什么要自杀?”曹禺急切地问。
“她对当时国内复杂的状况,国事日非,社会腐败,人民悲惨,感到十分愤怒伤痛。我父亲当时亲眼见到她留下的两纸遗书,并应南洋一家报社的邀请,写过许多同盟会时代福州革命同志的史实。在文章中,父亲盛赞方君瑛是‘同盟会女杰’。他还对我说,同盟会女杰,一般人只知道有浙江的秋瑾,而不知道我们福建也有一位女杰,她对革命的贡献,以及她的德性之美,都不在秋瑾之下。”
听着郑秀满含深情的描述,曹禺对尚未谋面的未来岳丈及满门忠烈的方氏一家充满了崇敬之情。
金陵城翁婿畅谈《精忠柏》
曹禺与郑秀的初恋在美景如画的清华园迅速升温。初夏的夜晚,皓月当空,如水的月光洒在清华大礼堂前白色大理石圆柱上,将礼堂周围照耀得像银色世界。从礼堂前大楼窗口传出横笛、黑管、萨斯管和圆号吹奏出的悦耳旋律。

方声洞

方声洞与妻王颖、子方贤旭

同盟会女杰——方君瑛
“这么晚了,校军乐队还在演奏。家宝,你能听得出这是什么曲子吗?”郑秀故意考考曹禺。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真美!贝多芬真是了不起的音乐天才!”曹禺赞叹道。“颖,咱们坐会吧。”郑秀号颖如,曹禺简称“颖”,有时又叫她“多拉”,那是狄更斯自传体小说《大卫·考帕菲尔》中一个女孩的名字。
两人在旗杆底座的石板上尽情聆听美妙的乐曲,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
然而,不久郑秀将她和曹禺的恋情写信告诉父亲郑烈,父亲起先却一个劲儿不赞成。郑秀有姐妹八个,她最大。父亲对她的婚事很慎重,希望她嫁给一个既有才华、家庭又有一定地位的青年。父亲还从侧面了解到万家已是一个败落的家庭;万家宝平时穿着也很寒酸,常常穿一件竹布长衫;个子不高,夹着一大堆书,在清华园踽踽独行。尤其让他不放心的是,相传这个万家宝还是个激进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共产党。为此,他特地托人到清华大学询问有关情况,问此事是否属实。对方回答说;清华有两个姓万的,一个是共产党,已经跑了,剩下的这个姓万的,看样子也靠不住。这个回复,又让郑秀父亲增加了烦恼。他特地写了一封信,劝女儿头脑不要太热,要冷静,要三思,婚姻乃终身大事,一失足会成千古恨。不久,他接到郑秀的来信,坚持要同家宝相爱,并详细地介绍了曹禺的家庭情况,说他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并详述了万德尊的经历。
收到女儿的来信,郑老先生在书房里踱过来,走过去,思考良久。最后他将秘书喊来,吩咐他去南京历史档案馆跑一趟,在前清档案中查一查,有没有一个留学生叫万德尊的。秘书查阅后禀报说:确有此人。在“清国留学生公馆第五次报告”中,载有“同学姓名调查录”,有一个叫万德尊的,字宗石,是湖北潜江人,与他同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还有阎锡山、黄国梁等。
听了秘书的禀报,郑老先生这才放心,便回一信给郑秀说:只要你自己中意,为父不加干涉。郑秀将此复信告诉家宝,两人都欢喜不已,相约晚上进城观看意大利著名歌剧《风流寡妇》,以示庆贺。
此后,郑秀每隔一段时间,将他们两人的情况简要告诉她父亲。职业剧团“中旅”公演的《雷雨》,风靡全国大获成功,很快各地掀起《雷雨》热,曹禺成为名噪一时的剧坛新星,郑老先生也感到家宝确是一个突出的人才。
1934年—1936年,曹禺的两部大型话剧《雷雨》《日出》发表,轰动全国。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多次邀请曹禺来校任教。1936年秋,曹禺终于来到南京任教。在郑秀的引见下,拜会了仰慕已久的郑老先生。老先生见他彬彬有礼,又能侃侃而谈,越发喜欢。在曹禺的影响下,郑老先生竟对话剧创作也发生了兴趣,并试着写了一部多幕话剧《精忠柏》。他让秘书用毛笔认认真真抄了一遍,亲书“请家宝斧正”几个字,送给曹禺过目。曹禺一看啼笑皆非,剧本写得不伦不类,既不像京戏,又不像文明戏,但他仍恭恭敬敬地提了一些修改意见。郑老先生看了连连点头:“讲得极是,讲得极是。”
为了进一步修改剧本,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曹禺的了解,郑烈多次邀请曹禺到他寓所、南京山西路一幢带车库的洋房里详谈。
郑烈的《精忠柏》写得很长,取材于宋朝岳飞抗金的历史题材,从岳母刺字、受宗泽重用、朱仙镇大捷,一直写到十二道金牌召回、在风波亭遇害等情节,都写得十分详细。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少,除岳飞、岳云等主要的正面人物之外,秦桧、王氏、万俟占等卖国奸佞也都全部出场。郑烈当时任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负责检察署、监狱等部门,他又是辛亥元老,因此曹禺在他面前十分谦恭,敬称为“伯父”。但谈到剧本意见,他也较坦诚。他说:“伯父,您的这部剧作好在不胡编,主要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处处有出处。情节发展原原本本,脉络十分清楚。不过,剧本本身可能长了一些,搬上舞台的话,至少要七八个小时以上才能全部演完,您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冒昧帮您再作一些删削。”同时,曹禺又谦虚地请问:“剧本为什么取名‘精忠柏’?”
“这是因为杭州西湖的岳庙中,树枝均向南倾斜。后人认为这是岳飞坚决抗金的精诚感召所致,故赞誉为精忠柏。岳庙久经沧桑,此事是否属实,已难稽考。但我几次去过杭州,岳庙内仍有精忠柏亭。亭中陈列若干柏树树段,据云精忠柏已枯萎而死,留此以供后人凭吊。我觉得这是国人对岳飞精神的敬仰之情,故之取名‘精忠柏’,你意如何?”郑烈问曹禺。曹禺极口称赞,两人共同赞誉岳飞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的精神。
“很有深义,它象征了岳武穆的精神,一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悲剧精神。”未来的翁婿越谈越投机。
1987年,郑秀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父亲后来喜欢曹禺甚至超过了喜欢我。”
订婚宴群贤毕至
南京,曹禺住在四牌楼十七号一幢两层楼的楼房里,楼上楼下各两间。这幢楼,原先是白杨、马彦祥当初同居时的住所。后两人分离,白杨去上海明星公司拍电影,马彦祥另住别处,将原住房让给曹禺租用。1936年夏,郑秀从清华大学毕业,系里的教授想留她在学校当助教,待遇不错,而且可能一边教书一边做学问。郑秀有些心动,写信征求曹禺的意见,他一连来了好几封信,劝郑秀无论如何要回南京,说若是两地分居以后各方面都很不方便,郑秀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在南京审计部当了一名科员。住在青年会,与曹禺每周见面。

曹禺继母薛咏南
1936年秋,经两家协商,决定在南京举行订婚仪式。曹禺继母亲自来南京与亲家公郑烈一起张罗安排。继母薛咏南,为人精明能干,落落大方,举止很有分寸。她第一次进亲家公家,手头只有一百二十五元大洋,郑烈家有十个佣人,她当场每人给十元大洋。
这年11月26日,两人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德瑞奥同学会在南京颇有名气,里面有舞厅、餐厅,可容四五百人。每位应邀的宾客,都收到一份精美的请柬,那上面写着:
兹定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正假座德瑞奥同学会。
为小儿家宝
小女 秀
举行订婚典礼 恭请
光临
万薛咏南
谨邀
郑晓云
十一月二十日
这天下午,宾客盈门,薛咏南穿着一件狐皮大衣,当着亲朋好友的面,从一只盒子里拿出白金镶金刚钻戒指,作为订婚礼,祝愿郑秀、曹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万老太太让曹禺将这只戒指给郑秀戴上。曹禺拿起戒指,郑重而深情地给郑秀戴上了。
许多文化名人,像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参加了这次典礼。那时上海与南京刚刚开辟了飞机航线,巴金与靳以是特地坐了飞机从上海赶到南京的。他们带来的礼品是一个特大号的洋娃娃,做工十分精巧:那洋娃娃的一对大眼睛眨巴眨巴会动;嘴也能一张一闭的,还会表演吸奶的动作。郑秀看了十分喜欢。
临开宴的时候,忽然仆人向曹禺通报:正在剧校兼课的田汉先生来了。曹禺原听说田汉去福州游览去了,故而未送请帖。
不一会儿,田汉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一见曹禺就说:“家宝,恭喜恭喜!”
曹禺介绍田汉与母亲、郑秀认识。见过礼后,田汉将手中拿着的两卷东西展开。那是一幅中堂,上面是田汉亲手书写的“蜚声诱和”四个大字。另有一张条幅,上面是田汉亲笔题诗一首。诗曰:
女以男为家,男以女为室。
室家至足乐,国亡乃无日。
万兄殆国宝,英年擅写实。
揭出黑漆团,病者可讳疾。
从来舞台上,非无救亡术。
时局虽万变,出路只有一:
不与强敌战,无由脱桎梏!
携手火线下,羡兄得良匹。
从容画蛾眉,且待战争毕。
譬如《雷雨》后,登山看《日出》!

曹禺与郑秀演《最前的与最后的》(1932年)
“一份薄礼,不成敬意。”田汉豪爽地说。
“谢谢田先生,写得好极了。”曹禺、郑秀齐声道。
“田先生,请共进晚餐。”万老太太热情地邀请说。
“不,不!我是专程贺喜,送上这份薄礼,表示敬意。至于喜酒嘛,改日再来讨扰。”说完田汉就要告辞。万老太太、曹禺、郑秀等一再挽留,田汉坚辞,迈开大步一阵风似地离开了宴会厅。
夜12点,订婚仪式在欢腾热闹的气氛中结束了。曹禺郑秀送郑父上车,郑父对郑秀说:“万老太太真是个能人,落落大方,举止很有分寸,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她要是个男的,那可真了不得。秀,有这样的婆婆,也是你日后的福气。”一句话说得郑秀粉脸绯红。
望着父亲远去的汽车,郑秀、曹禺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
石头城争看家宝演朴园
1937年元旦,南京各大报纸登出了赫然醒目的广告:
一九三七年中国剧坛第一声
中国戏剧协会假座世界大戏院
六幕剧《雷雨》作剧曹禺导演马彦祥
姿态新颖,技巧纯熟,30余人登台
时间 日场二时 夜场八时
演员阵容表也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出场先后为序):
鲁 贵 马彦祥 周繁漪 郑挹梅
四 凤 李 萱 周 萍 戴 涯
大 海 裘 水 周朴园 万家宝
周 冲 王英豪 鲁侍萍 于真如
当晚,在世界大戏院,紧张的预演在进行着。

曹禺饰演的周朴园(1937年)
后台,演员们正进行着有条不紊的化妆。服装管理员王先生帮挹梅穿一件杏黄色的长旗袍,她感到很奇怪:“怎么穿这种颜色的衣服?”王先生告诉她,“这是万先生特意关照的,他说这样的色彩打上灯光更能衬托出人物性格。”挹梅将信将疑,放眼一看,万先生正在化妆,便不便再打扰他。
不一会,万先生走过来了,戴一副椭圆形的金边眼境,穿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头发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宛如换了一个人。在郑挹梅的印象中万先生个子不高,今天好像突然长高了一些,便好奇地问:“万先生,您今天怎么忽然长高了?”曹禺微微一笑,将左脚的一只皮鞋脱了下来,“秘密在这儿!”挹梅一看,那鞋底加厚了许多,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真有办法!”
“这叫天无绝人之路!”曹禺笑着说。
激动人心的正式公演开始了。世界大戏院的池座里鸦雀无声,人们被台上精湛的表演迷住了。尤其是曹禺扮演的周朴园,更引起观众的注目。他既演出了周朴园专横、虚伪的一面,同时又揭示了这一人物变异复杂的人性,体现了剧作家的悲悯情怀,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全剧结束时曹禺的表演:周冲和四凤相继触电而死,周公馆笼罩在惊恐之中,场上只剩下周朴园和繁漪。周朴园突然想起了周萍,他惊慌地叫道:“萍儿呢?大少爷呢?萍儿,萍儿!”曹禺连叫了三声“萍儿!”紧接着传来的是书房内周萍自杀的枪声,室内死一般的沉寂。在这一段戏中,曹禺处理这三声“萍儿”,用的是气声,一声与一声不同,越来越强,将人物惊慌、不安、恐惧的心理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紧紧地攫住了观众的心。直到幕落,观众紧张的心情还难以平息。五十年后,同台演出的郑挹梅回忆说:“这三声‘萍儿’给我的印象极深,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扮演鲁贵又兼导演的马彦祥回忆起这次演出,也兴奋地说:“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写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谁比他演得更好的了。”
曹禺扮演的周朴园这一舞台形象,又一次显示了他卓越的表演才能。曹禺亲近的朋友,有的甚至认为他表演艺术的成就高于剧作,若不是受身材限制,“他真是中国能够演多型角色而艺术修养最高的优秀演员。”
中国戏剧学会演出的《雷雨》是一台珠联璧合的演出。除曹禺外,其他几个角色也演得十分成功。马彦祥扮演的鲁贵,将这个猥琐的狡仆演得维妙维肖。尤其第三幕,他被周家辞退后,在家里百无聊赖,躺在竹躺椅上,跷起腿,挥着蒲扇,哼着“天牌呀、地牌呀”的黄色小调,还冷嘲热讽地数落四凤,抠着脚丫子,不时地放在鼻子跟前闻闻,一见周冲深夜送来一百元钱,忙挥起蒲扇扇去凳子上的灰,又阿谀地给他打扇,活画出一副善于逢迎、见钱眼开的无赖嘴脸。
《雷雨》在南京的首演引起了出人意外的轰动,口碑载道,佳评满街。演出连场客满,要求延长演期的函电纷至沓来,愈演愈满,观众如潮。
郑秀与郑老先生一家也来看戏了。《雷雨》在南京的轰动,使郑老先生觉得脸上也有光彩,他逢人便夸家宝“真乃奇才!既会编戏,又会演戏。”他在南京世界大戏院为《雷雨》的演出还特地包了好几场,要亲戚朋友们都去看看。郑秀也为自己选中这样一个好对象而感到自豪。
奉父命郑秀避难芜湖城
1937年7月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寇又大举进攻上海。在三个月的战斗中,大约有27万中国士兵伤亡,不久日寇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南京岌岌可危。
郑秀遵照父亲意见,避难到安徽芜湖,在老同学周燕家暂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由于战火频繁,接连数月,郑秀与家人失去联系。她在芜湖度日如年。情急之下,在老同学陪伴下,到街上请一个瞎子测字,占卜一下家人、曹禺吉凶如何。只见那瞎子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吐出一番话来:
“小姐不必担忧,你所思念的亲人、好友,不出半月便有音信。”
郑秀听了大喜,多给了一些钱,并连声谢过瞎子。当晚睡在床上,郑秀对瞎子的话将信将疑,她自思自忖,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呢?这样一想,也就心安了。不久,便沉沉入睡。这是三个月来,她头一回睡得这么香。
第二天一早,郑秀忽然被人推醒。
“秀,好消息!”周燕拿着一张电报纸笑嘻嘻地说。
“什么好消息?”
“你猜猜看。”周燕神秘地笑了笑。郑秀见她一双手抄在背后。
“拿过来吧,别逗了。”趁周燕不提防,郑秀猛地一把将一张纸抢了过来。一看,是曹禺母亲从天津发来的电报,全文为:“万已乘英轮平安赴港,即赴汉。”
郑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将电报一个字一个字地又看了一遍。读完,高兴得抱住周燕直打转。
这一时期,曹禺、郑秀正处在热恋中,来往书信很多,郑秀的表弟、沈澧莉的弟弟沈祖戡为郑秀当信使,每天来回为他们发信、寄信,忙得不亦乐乎。
第二天,郑秀又收到曹禺写来的一封信,告诉她,他已离香港到达汉口,现住在外婆家,让她尽快赶到武汉找他。
9月底,曹禺和郑秀赶到国立剧校迁校所在地长沙,租了两间破旧房子,将就住了下来。
在长沙,曹禺除了指导剧校学生进行《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街头剧演出,还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大礼堂举行剧场公演,演出《毁家纾难》《炸药》《反正》三个抗敌独幕剧。
一天,曹禺正在指导学生的剧场演出。演出的最后一个剧目是《反正》。可能因为今天的观众一半以上是伤员的缘故,这个戏的演出效果特别好,许多场面都使刚强如铁的伤员低下头擦泪。有一个伤员被感动得无法控制,突然在楼座上站了起来,挥起拳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到底!”
演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胜利结束。学生们到后台,高兴得跳了起来,女同学互相拥抱着,有的激动得哭了起来。看着这样热烈的场面,这样可爱的学生,曹禺含泪而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正在曹禺欣喜、激动不已的时候,一个学生来喊他:
“万先生,外面有一位小姐在找您。”
来找曹禺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郑秀。一见曹禺走出剧场门外,郑秀忙笑嘻嘻迎上去,说:“家宝,爸的回电来了。”
原来曹禺与郑秀相约在长沙举行正式婚礼,为了郑重起见,决定两人分头发电报征求家中意见。前几天,曹禺已收到万老太太发来的电报,电文为:“同意,祝你们幸福。”这几天就等郑秀父亲的回电了。
曹禺接过郑父回电一看,电文极为简练,只有一个字“可”(这也是民国初年一些革命党人惯用的写法)。
不久,曹禺与郑秀在长沙青年会举行婚礼。余上沅校长为证婚人,参加婚礼的有吴祖光、余上沅夫妇,陈治策夫妇,教务处的两个同事等二十余人。婚礼简朴而又隆重,是一个合乎规格的、很正式的仪式。婚后,两人便迁往稻谷仓居住。新房布置得也非常质朴,两把藤椅,两张帆布床,还有一个大书桌。
曹禺和郑秀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家里开始了他们的生活。身处乱世,郑秀随着曹禺颠沛流离地去过很多地方。对她来说,那是一段虽苦犹甜的珍贵记忆。
别生父泪洒机场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上海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
龙华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专机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郑秀一个人站在飞机旁,焦急地向机场入口处张望。
“颖如,你还在望什么?”郑父焦急地问。
“你不是说通知家宝与我们一起去台湾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谁知道呢,也许他碰上什么事……”郑父含含糊糊地搪塞着,其实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处,根本就没有派人去接曹禺。为了让女儿同自己一起离开大陆,郑父四次动员女儿。

此时,郑秀与曹禺的感情已渐趋冷漠。从江安迁居重庆后,曹禺住南岸复旦大学教书,每周回来两三次,与孩子们恢复了感情,但与方瑞仍藕断丝连,方瑞仍苦苦地追求他(注:这一段情缘详见《江安之恋与<北京人>的诞生》,曹树钧著,载本刊2010年7月号)。回到重庆之后,郑秀如鱼得水,交游广泛,与男性朋友接触频繁,既有清华过去的老同学,也有新交的朋友。这引起曹禺的误会,以为郑秀经过江安一场风波之后已不愿意同他恢复关系,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渐渐疏远起来。1947年,曹禺从美国讲学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一度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任教,又经黄佐临介绍,担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创作并导演了电影《艳阳天》。此时,郑秀则带着万黛、万昭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偶尔到上海小住,也总是很快返回南京,因为她在南京就业。时局紧张以后,当局通知郑父携全家撤往台湾。这使郑秀感到十分为难。一头是父亲,一头是丈夫,哪一头都依依难舍。她爱曹禺,父亲说已通知曹禺同行,她这才同意动身。
郑秀看看手表,离飞机起飞的时间只有五分钟了,她仍痴痴地等着。
时间过了,还不见曹禺的人影,飞机响起了启动的响声。
“颖如,快上机吧!他不会来了!”
“不,他不去,我也下去!”郑秀毅然将两个女儿叫下机舱。
“颖如,颖如!”郑父焦躁地阻止她:“颖如,难道你忍心抛下为父吗?”两鬓白发的父亲深情地望着女儿郑秀。
郑秀心中一阵酸痛,但又决然地说:“爸,女儿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说着她含泪拉着两个女儿,转身就往出口处走。
“颖如,颖如!你给我回来!回来!”
郑父声嘶力竭地叫着,郑秀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她就这样和父亲一诀成永别了。
忆往昔难忘翁婿情
从1948年至1988年,曹禺与郑烈的音讯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从事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曹树钧、俞健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5月初版)创作和第一部关于曹禺的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的拍摄过程中,多次访问郑秀,才重新打开了郑秀多年讳言的记忆。
一次在交谈中,我告诉郑秀,有一位德国记者叫乌韦·克劳特,他酷爱中国文化,热爱曹禺,特地请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为他引见曹禺,同曹禺结成好友,他特地写了一篇长篇专访《戏剧家曹禺》,文中曹禺在建国后第一次提到了他的岳父郑晓云。
郑秀十分感慨地说:“他现在又想起他的岳丈了!”她问此文刊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发在两个刊物上,一个是《中国文学》1980年第11期,英文版,向全世界发行,一个是北京的刊物《人物》1981年7月第4期。
我对郑秀说,曹禺的内心深处是不可能忘却他的岳父的,在南京的日日夜夜里,曹禺与岳丈畅谈话剧《精忠柏》,岳飞留给他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1943年1月,在重庆,《戏剧月刊》创刊号(曹禺是九个编委之一)上“特刊稿件预告栏中,公布了曹禺创作的有关岳飞的历史剧《三人行》即将问世的消息,曹禺为此还写了一篇《创作经验谈》。这年2月,曹禺又应邀在上清寺储汇大楼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作了一次题为《悲剧的精神》的学术讲演。在讲演中他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普鲁托斯、中国的屈原、诸葛亮、岳飞是有着可歌可泣悲剧精神的人物,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要存在,“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我们要救亡,要反抗,”就要弘扬这些真正的悲剧人物雄伟的气魄,他们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悲剧精神。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曹禺希望民族富强、国家要立足于世界的崇高理想,始终与岳飞和郑烈的心是相通的,与辛亥先烈的精神也是一脉相通的。
关于这部已经预告的歌颂岳飞的剧本,曹禺这样描述道:“《三人行》是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的故事。在重庆只写了一幕,太难了。全部是诗,没有别的对话,吃力得不得了。大热的天,搞得累死了。是马宗融为我找到的房子。马宗融是巴金介绍我的,一个法国留学生,是非常好的朋友。这家农民大概是个中农吧,有三四个孩子,我是自己背着米下乡,自己烧饭。我是想试一试,用新诗写一部诗体剧,终于搞不下去了。第一幕是从金回来,我想写出点新意,但是,也没有历史可考,材料上遇到问题,不得不罢手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写在一个记账用的条纸上,写了无数次,只写了一幕。‘文革’期间,我把它撕毁了。”
遗憾的是这部历史剧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但它所要歌颂的悲剧精神,我们从曹禺的讲演中,已经可以触摸得到了。
“不思量,自难忘。”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血浓于水,民族的感情、爱国的感情、骨肉的感情更是无法切断的。
曹禺和郑秀在南京订婚,订婚照摆在郑烈的客厅中,郑秀表妹沈澧莉母亲曾赞扬说:“这张照片拍得好,曹禺微微笑。”郑秀还曾托笔者寻找这张“微微笑”的照片。
郑秀又怎能忘记父亲用他的自备汽车,亲自送女儿、送表妹、表弟上车避难安徽芜湖,逃过南京大屠杀这一劫的情景呢?
郑秀更忘不了“四人帮”粉碎后,方声洞夫人王颖邀请郑秀、沈澧莉、沈祖戡在北京举行欢迎远方来客的家宴上,所讲述的黄花岗72烈士们可歌可泣的壮举。
一百年前,辛亥先烈为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永载史册,而且将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