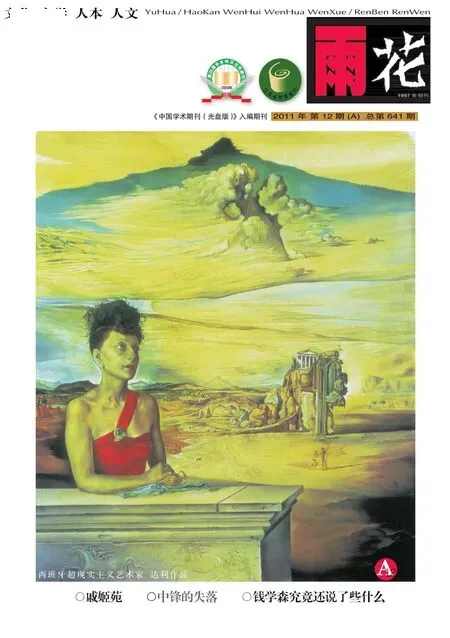老主编张未鸣
● 黄东成
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近30年了,我心里始终有着他的一块碑,时不时常会与一些老友念叨,这位让人难以忘怀的老领导,老编辑。

也许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作家辛田了。上世纪50年代初他可是常有文艺作品在报刊发表,是江苏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协华东分会会员。辛田真名叫张未鸣,是《江苏文艺》老主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近30年了,我心里始终有着他的一块碑,时不时常会与一些老友念叨,这位让人难以忘怀的老领导,老编辑。
他确是一个现已不多见的正直无私的老党员,一个很容易与大家融在一起的好领导,一个为人低调不擅张扬的解放区作家,一个朴实厚道待人亲切的好老头。不,50年代中期他其实还只是30大几的青年人。因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常年穿一套半新不旧的干部服,看得出生活十分俭朴。个儿不高,不多言语,老烟枪。大概因此肺不太好,常咳嗽,牙也被烟侵染,脸色不太敞亮,戴着副近视眼镜,还有点驼背,看上去特显老。故说他老头他也不以为忤,还憨憨地笑着说,早有人喊他老头了。
1953年建省前,江苏原为苏南、苏北两大行署,他是苏北文联的《苏北文艺》主编,建省后,苏南、苏北文联合并成立江苏省文联,《苏南文艺》、《苏北文艺》也合并创刊《江苏文艺》,张未鸣也就理所当然成了《江苏文艺》负责人之一。至1956年,中央贯彻“双百”方针,省文联党组决定在《江苏文艺》基础上,创办专业性文学杂志《雨花》。于是一部分人进了《雨花》;《江苏文艺》由张未鸣领衔继续办下去。
我是1956年7月调到《江苏文艺》的。因迎接全省文艺会演,为剧团赶写一台大戏,将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搬上舞台(最终获得三等奖),报到推迟近两个月。我走进传达室,见一老一少两个工人在。年少的问我:找谁?我递上介绍信。年老的接过一看,笑着说,你终于来了。年少的对我说,正好老张来拿报纸,你跟他上楼吧。到了楼上我方知道,这老头就是主编张未鸣。
当时正值贯彻“双百”方针,报纸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每天早上大家都等着看报读新闻。文艺界讨论得尤其热烈,我也禁不住写了一篇谈文艺应坚持工农兵方向的评论:《主要的和次要的》,在当时的《文化新闻》报上发表。老张看了很表赞同,说,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绝对不能变,尤其我们这样的群众性文艺刊物,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你如今可是我们《江苏文艺》最年轻的编辑了。
老张办刊非常用心,凡事亲力亲为,依然保持着长期在农村摸爬滚打的传统作风。他细致地教我们如何初审作者来稿,工农兵作者的稿件,可能不成熟,但只要基础好,就该努力帮助修改好,像部队编辑洪荒对待高玉宝那样,这是一个编辑人员的态度问题;他还亲自动手教我们如何排版,用红笔在一本旧刊物上,一页一页划出不同的版样来。一个同事对我说,老张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可以说不遗余力。他说,有一次主编交待他以编辑部名义写一篇短评,他将稿子写好后交上去,两天未见下文;第三天主编将他找去。他的稿子主编已改了一遍。说是修改,莫如说是重写,但原稿凡有可用之句均保留着,让原作者感到一种尊重。
我那时经常配合时政热点在报刊发表一些诗作。他都看了。他鼓励编辑搞创作,说,这样,编辑对创作的甘苦才有亲身体会,处理基层作者的作品才会带着感情,更慎重,更谨严。而作者对编辑,也会更尊重,更信任。他对某些大刊编辑对待工农作者的老爷作风十分不屑。他时时告诫,一定要摆正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尤其对于工农作者,只要作品有苗头,就应该努力扶持他们走出来。他一以贯之的编辑作风感人至深。
他不时会到大办公室察看编辑们的工作情况,问问近来各自联系作者的近况。有一天下午,恰好大家都不在,就我一个人趴在办公桌上写信。他走进来,看得出很高兴,说,平时就应该多与作者联系,多交朋友,而且应该是真心诚意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在给外地的女朋友写信。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我写的一篇短文,说,文章写得还到位,但行文一定要注意口语化,诗歌和散文有别。写诗,可以天马行空想象,可以不受文法拘囿,讲求意境和形象,比如杜甫的“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传诵至今。散文也讲意境和诗意,行文却必须受文法制约,不宜学电影的蒙太奇过分跳跃,也忌形容词太多的学生腔。
最让我敬重的,是他高尚的人格,为人的正派和宽容。1957年4月,已开始进入整风鸣放,办公室和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凭直觉,我觉得张未鸣是个很正派的领导。有的大字报是善意的,有的明显是泄私愤,但提意见会上,老张一言不发,低头默默记录着大家的意见。195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文章以后,形势陡然变得紧张起来,许多单位都开始反攻倒算,贴满了秋后算账的大字报。我钦敬老张的厚道,依然平时一样热情招呼大家,结果,单位里没有打一个右派,有些明显带有泄愤情绪的人,也仅只让他们下放锻炼,不背政治包袱。我事后曾侧面试问老张,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单位领导,对每一个人,政治上都要负责任。反右斗争,《雨花》几乎覆没,打出了一窝右派,因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探索性作品。从省委宣传部专门调去任主编的文艺处副处长施子阳,首当其冲成了右派。
整风反右过后,就是如火如荼的大跃进。随之大跃进新民歌似决堤的洪水汹涌澎湃,成麻袋地往编辑部送。大家连夜看稿,连轴转地跃进,甚至大炼钢铁老张和我们一样,从小高炉回来后也不得休息,直看得眼冒金星昏天黑地。老张说,现在是真正检验我们对群众感情的时候了。我能理解一个笃信《讲话》的老革命不掺丝毫杂念的群众观念。但是,我对当时文化部某领导说的“只要会讲话的就能唱歌,会走路的就能跳舞,会拿筷子的就能写诗作画”,心里总有点疑惑不解。再说这些新民歌作品,看来看去差不多,自“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被当作范本传开以后,来稿更加势不可挡,无非都是极度夸张,一篇比一篇离奇。我曾试探着对老张表示看法。这些新民歌不像是农民写的,农民忙深翻土地,挑灯夜战,根本没有闲空的工夫,也不可能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肯定都是一些基层文化干部和教师编出来的。老张说,我们还是要忠于生活,多选有生活气息的稿子,只要不粗制滥造,改好就行。我后来就按他的意见选稿,看到有一首来自苏北泗阳的修水利的诗歌,40多行,我觉得有内容,但作为新民歌太长了,便掐头去尾删剩12行。老张看了说不必太实,可再凝炼。我又改成6行。最后发表时仅4行:“老头对老头,挖泥喊加油,引得老鹰停翅飞,乐得柳树直点头。”这首《老头对老头》新民歌,后来被选入了当时顶级大空话的《红旗歌谣》。
老张外冷内热,始终和颜悦色,从来没有对下属高声批评过。某个同事做错了事,他总是循循善诱,让你从内心领悟,改了就好。他是工农干部,却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从来没有像某些单位那样,领导对知识分子总居高临下地命令和训示。他事事以身作则,用无声的榜样感染人。有回我晚上9点偶然到办公室,却见老张在低头审稿。有人进屋,他的高度近视眼镜也没有抬一下。我很不好意思,只得蹑手蹑脚到办公桌前悄悄坐下,也看起稿来。他没有看我一眼。这事大家知道后,晚上也都自觉来加班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年轻编辑的信任和放手。1958年秋,编辑部开会,老张决定实行编辑值月制,即每个编辑轮流责编一个月。从策划设计、组稿、选稿、编稿、审稿,直至排版、封面设计、请美编插图、校对、出版,就是说,一期刊物,从开始到出刊,一笼统由责编全面负责。当然,整个过程,离不开老张手把手的辅导。这样的锻炼,使我终生受益。文革后刊物复刊,七、八页诗歌版面都是我自己排版,尤其出诗专号时版面的大气,大开大合的创意,都得感谢老主编张未鸣的教导和培养,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当时正大讲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在民歌和古典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老张指定向当时初露才气的南京工人诗人朱光弟、徐州煤矿诗人孙友田和南京印刷工人作家孙剑影约稿,说培养工农兵作者是我们的任务,让工农兵作者发表意见,代表着刊物“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方向。老张是老老实实不越雷池一步地完全按《讲话》精神忠实执行的刊物主编,因此,《江苏文艺》没有犯过大错误,就这么平平静静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直到他后来调去江苏人民出版社当副总编辑,仍不忘编辑部的同仁们。还约我为他们写了两本应时的小册子。
老张走了快30年了,始终还在我口头上挂着。他去世时才64岁啊。他的大儿子张鹰上大学时喜欢写诗,我还曾让他到编辑部来誊抄过修改后的诗稿。他现在外地一所大学任教;小三儿张展,在省新华书店工作,现在也已五十开外了。八、九十年代,他也一直写诗,时不时到我家中来与我谈诗,我不能不联想到他父亲,及与这位五十年代的老主编共事时的一幕幕难忘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