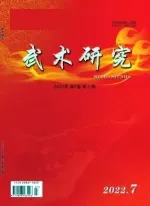“超越奥运”:基于中国武术本质的反思
李厚芝 沈越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200241)
“超越奥运”:基于中国武术本质的反思
李厚芝 沈越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200241)
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而言,技击价值并不能全部体现其本质特征,中国武术弥久愈新的根本还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武术未来的发展指向,应超越奥运目标。
武术本质技击文化
1 技击:非中国武术独有之特质
长期以来,在我国武术界,只要论起武术的本质,无不认为技击是中国武术最本质之特征。诚然,纵观天下之武技,其原始目的都是为了搏击,失去这一层含义便无所谓武技。然而,对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为博大精深的体系的中国武术而言,就并非专指单纯的打斗伎俩了。
众所周知,武术起源于生产实践和武装战争。在原始群落时代,“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五蠹》),“古者禽兽多而人少”(《庄子·盗跖篇》),人们为了维持生存需要,不得不利用简陋的工具去狩猎,并从中学会了简单的劈、砍、击、刺等格斗技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萌发,各部落出现了频繁的战争。在战争中,人与人的搏斗厮杀使攻防格斗技术得以不断积累,并最终脱离了生产技术。有意识的技击,是武术萌芽中质的飞跃。武术在随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也始终是围绕着技击技术这一基本特点而发展变化的。因此,可以说具有攻防技击价值是武术最基本的特点。但是,是否据此即可认为武术的本质特征就只是技击呢?
武术的本质特征理应是武术安身立命的根基。参阅《新华词典》中对“本质”一词所下的定义:“本质”就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技击,是武术与生俱有的自然属性,也是天下一切武技所共有的。然而,武术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武术,并在世界武坛独具魅力,经久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其技击特性之中所蕴涵的丰富博大而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武术的文化内涵与技击功能共同构建了中华武术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东方武技形象。武术,无论是徒手拳脚还是持械动作,其一招一式无不经过人们的精思巧想、精选优化而成的,是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创造、检验、完善而形成的优秀的精神创造物,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因此,某种意义上讲,“武术的文化性也是从原始时代起,就是在不同的民族、部落与民族的战争交流中融汇发展的”[1]。另一方面,武术植根于民族土壤之中,无可避免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刻上传统文化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对武术的熏陶与影响,不仅表现在武术自然地接受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历代武术家都自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规范武术技法、阐述武术原理,达到了文武合一,交融一体的程度。深厚的文化积淀不仅影响着武术理论,而且决定着武术的运动特征、功能特征,成为中国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因此,对中国武术本质的认识,必须从武术的技击功能和文化价值两方面来把握。离开传统文化,纯粹谈“一招制敌”的技击,决不是中华传统武术的本质特点;反之,抛开技击实效,而一味追求“高、难、美、新”的视觉感观效果,也就只能属异化了的“武舞”而非人们心目中的传统武术了。对中国传统武术本质认识的偏颇与不足,必然导致武术发展方向上的失误。建国后,出现的“唯技击论”和“唯套路论”就是一个例证。前者过分地夸大对武术的全面继承而忽略了发展,坚持武术即是搏击技术的观点,而否定武术的文化价值,最终落得个“拳击加腿”的批评;后者抛弃了传统武术的技击内容,替之以华而不实的肢体动作组合,无视传统中国武术的技击攻防,反以跳的高、跃的远、旋子打的周数多等为标准来评判水平的高低,使武术向体操、舞蹈的现实方向发展,最终也落得个“东方芭蕾”的戏称,武术套路比赛被斥为“武舞”而遭世人诟病。由此可见,对中国武术的本质的认识,必须兼容技击与文化的统一,偏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将使中国武术丧失应有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2 文化传统相异:中西方武技有别之根本
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项目,武术当然具有体育属性,即健身娱乐之功能。但是,“武术属于体育,又高于体育”。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代西洋体育,是建筑在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西医和解剖学基础上的,主要研究人体的外形,武术除重视形体之外,还讲究精、气、神,讲究心身运动和天人合一,注重人与环境的统一和自身的和谐,与中国古典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2]。中华武术与西方技击体育不论在发展渊源、价值取向还是功能结构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任何类型的历史文化总是在一定类型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西方技击术是在西方传统文化土壤中繁衍而出的。西方文化是在西方历史和人文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它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古罗马时期。当时古罗马征服了迦太基(北非),西班牙大部、马其顿及希腊诸地区。他们的军队依靠重铠、重剑、厚盾、强弓,不惜大批士兵死于超体能的训练,以此换取战场上的生存和胜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文化必然是强者哲学。“弱肉强食”、“强者生存”被视为天经地义。西方技击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表现为崇尚力的强者哲学。在体育手段和价值取向上,西方竞技体育强调超负荷训练,战胜对手是它的直接目标。对抗中,“进攻即是最好的防守”。讲求主动进攻,快者赢、强者胜、技法简单实用,重打击效应。因此,惊险性、刺激性、功利性就成为西方竞技体育固有的追求。与此相反,中国武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在封闭、自然的农耕经济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古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和富饶的物产使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是男耕女织,各居一隅,人各自给,安于里井,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心理性格是忠厚、质朴、忍毅、内向、中庸。然而,自秦汉以来,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不断受到北方强悍民族的侵扰与掠夺,中华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解决“以弱胜强”的问题,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宇宙观视人天为一整体,注重把局部纳入整体来考虑,从整体来认识局部。因此,中国武术素来崇尚“巧取”,如内家拳的“以精制动”,以柔克刚”,“以小力胜大力”,其根本是“以弱胜强”,讲求“借人之力,顺人之势”的整体技击思想。中国武术受中国传统哲学“中庸之道”的影响,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在技击理论和方法上吸取了中国兵家、医、道、佛、杂技的一些思想和方法,由此而表现出一种守内、崇实、尚礼和自娱、修性、保身的鲜明民族特色和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因此,在体育手段和价值取向上,中国武术注重“养”,习武练艺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精神和肉体的完善统一。真正武林“高手”的比试,从来讲究“点到为止”、“礼让为先”,呈现出东方文明的气质——争斗而有礼让,艺纯熟而不炫浮。由此而见,即使同为“技击”,东西方的技击观念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在功能结构上,西方体育是一种分离的,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外倾竞技方式。在人体生理机能对运动负荷的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循环训练中,以破坏生理系统原有平衡,而不断向人体生理极限逼近的挑战,极大损害了人类健康。纵观当今竞技体育项目的冠军得主,最后无一不是带着满身伤病离开竞技场的。在辉煌灿烂的荣耀背后,是以损害个体生命健康为惨重代价的。因此,西方竞技体育的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内在功能与外在功能是对立分离的。中国武术则不然,作为一种人体内倾保养生命的运动,武术是个体用以养生、自卫、修身养性、自娱娱人的综合性实用技术,是个体生命力量的自我完善和外在弘扬。因此,武术的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内在功能与外在功能是和谐统一的。其功能的优越性和复杂性是西方竞技体育难以比拟的。
3 超越奥运:21世纪中国武术应持的发展指向
综上所述,中华武术要走向世界,真正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必须认清西方竞技体育与东方的武术技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其演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心理、气质、价值标准而造成的。无视这种差异的实质,急功近利地为了迎合奥运,早日进入奥运而不惜对中国武术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只能是将传统武术改的面目全非,最终导致“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局面。
中国武术的发展,首先必须紧紧围绕其本质特征,以传统武术为主,既要强调技击功能,又要突出其文化属性。据有关报道,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至今保留及流传的,仍以传统武术为主,欧美武术界至今还是把中华武术分为功夫和武术,前者指的是传统武术,具有养生保健及技击防身功能,后者被视为体操式的运动。日本武术界也将其归纳为运动(sport)及武术(Wushu)两大类。论及武术,他们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传统武术。中国武术不能因科学的发达及武术在军事上的作用减弱而尽往架势、造型、舞蹈方面发展,忽视其实用价值;中华武术所包涵的传统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不能以曲解了的“科学性”使之变质。在当今世界诸多的体育项目中,唯有中华武术形成了庞大的文化体系,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中国武术的发展决不能走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路,单纯用西方体育思想改造中国武术则只会毁灭中国武术。
其次,中国武术在与当今世界竞技体育相激相荡中,应坚持“异中求同,同中有异”的发展原则。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异”,正是武术吸引世界之所在。但决不能因其“优”与“异”而惟我独尊。固步自封,不求发展,只会导致武术自身的衰落。更何况,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奥运,整体上反映的是西方近代文化精神,对东方的体育运动总体上是排斥的。在当前西方体育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形下,竞技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武术要生存和发展,决不能游离于时代潮流的大环境之外。这就需要武术界作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努力,去挖掘传统武术中能够与西方竞技体育相融合的优秀项目,如已经不断尝试的中外散打比赛。但是,这种融合必须是在坚持民族特色、项目特点的前提下,“同中有异”的融合。作为推向世界的一种标志,武术向竞技大舞台——奥运会进军本无可厚非,但是从长久发展来看,我们应认识到武术进军奥运会,实质只是一种手段和途径,是为了更多的人认识武术,参与武术运动从而更好地发展、发扬中华武术,而不能错误地把武术进军奥运当成我们发展武术的目标指向,为奥运而奥运。
概而言之,中国武术在21世纪的发展,不能只着眼参与奥运会,而应以“超越奥运”为发展指向,在与西方强势体育的交流中,遵循“异中求同,同中有异”的原则,从武术自身特质出发,立足于东方体育文化的传统,以真正实现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相辉映,服务人类身心和谐、健康发展为终极追求。
[1]韩丹.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A].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论文集[C].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170-172.
[2]于志钧.解放后中国武术发展之检讨[J].武林,1998(2):7-9.
[3]李成银,宋爱真,于红梅,等.武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6(2):60-62.
[4]冯天瑜,何天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陈筠泉,刘奔.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A Reflection on the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Li Houzhi Shen Yue
(College of PhysicalEducation&Health,East China 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Chinese Wushu has both extensive modality and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the art of attack and defense can't reflect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Chinese Wushu can maintain evergreen life still owing to its ric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ently.To Chinese Wushu,in further the goal of its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o be the Olympic Games but also should beyond that. Key words:Chinese Wushuessencethe art of attack and defenseculture
G85
A
1004—5643(2011)01—0004—02
1.李厚芝(1974~),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武术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