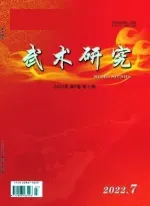论武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程大力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论武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程大力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文化是人类共通的、共同的创造或遗传,使人得以成其为人,并区别于其它生物。中国文化从来都以迥异于其它文化类型的鲜明的特征与广大的内涵,与其它民族和民族文化相区别开来,并独立存在。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武术以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特殊本质,却反映了一般意义上的、共通的、共同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武术文化形态包含有三个层次:道与理是核心层,礼与艺是中间层,技与术是外显层。
文化文化形态武术文化
1 文化、文化类型与中国文化的概念
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的术语,据说1920年以前只有六个不同的定义,而在1952年便已增加到160多个。现在则可能更多。一般而言,狭义的“文化”,专指与精神生产直接相关连的活动过程与产品;而广义的“文化”,则约略等于与自然物、自然界运动相区别的——既包括精神产品也包括物质产品在内的——人所创造的一切非自然物,以及这种创造活动过程本身。这就是文化。
文化是人类共通的、共同的创造或遗传,使人得以成其为人并区别于其它生物。但文化又形成为不同的模式或类型,以区分不同的种族、民族或部族。A·克罗伯肯定“不同质的文化可依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著名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更强调文比的这一特点,给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它任何民族的方式。”于是她又借鉴了尼采在古希腊悲剧的研究中所采用过的名称,将两种具有不同精神特征的文化称为“阿波罗型”文化和“狄奥尼索斯型”文化。
当然,文化既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另一个民族的方式,那么反过来说,不同的民族就会有不同的文化。所以又有人更具体地将世界文明划分为欧美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佛教文化拳、东亚儒教文化圈等四大文化类型。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世界历史上曾有过八个高级文化,它们分别是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则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过21种文化或文明,有趣的是他把中国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分列。后来在《历史研究》再版时,他的观点有了些变化,文化类型数目更多了,但中国文化则并为一种。无论是否必要,或许将一个族群的特征追踪得更细,文化类型与模式的划分也将更细。
中国文化从来都以迥异于其它文化类型的鲜明的特征与广大的内涵,与其它民族和民族文化相区别开来,并独立存在。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主要并不是种族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发达、深厚,也从来使面对它的异文化的拥有者们注目与震惊。
2 文化形态与武术文化形态的概念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柯亨指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的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是抽象的,概括的,又是具体的,类分的。克鲁柯亨所说的“各种符号”、“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各种具体形式”,事实上说的就是文化之下的各种具体文化形态。文化形态是文化巨系统中的子系统和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与文化形态的关系,是母体文化与分支文化的关系。武术文化,便是中国文化母体之下的一个分支文化——一种文化形态。
当然,文化形态也不是无限可分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否成立,关键是看其文化负载能力,或者说文化的灌注程度。让某一种小吃、一种陶壶也享受被冠以文化的殊荣,是文化一词的滥用,因为实际上这些物品的文化意义太小、太少、不够大。武术之所以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当做上升到文化层次的对象来对待和研究,能被称为“武术文化”,关键在于:第一,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武术文化自成完整体系;第三,武术文化这一完整体系全面贯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说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说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必然地会形成要形成武术。在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中,必不可少地要有武术。它不可能不存在,也不可能被排斥和忽略不计。正是这些诸多的具体的有机体,构成了中国文化本身。一种器械、一个拳种的出现和存在是偶然的,但武术文化的出现和存在是必然的;这犹如一种小吃、一种陶壶的出现和存在是偶然的,但饮食文化的出现和存在又是必然的。没有了武术文化(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等),中国文化就可能不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不是现在面貌的中国文化。
说武术文化自成完整体系,既是说它的内涵广大丰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千枝百蔓,同时也是说它的内涵足以独立,有着充分的自足的功能,和使武术文化形态同其它文化形态严格区分开来的质的规定性、确定性。虽然文化形态之间会有或多或少的渗透和影响,但武术却未因此与其它文化形态相混淆。少林寺与武术结缘,武术文化与宗教文化发生了碰撞和联系,但武术文化并未变成为宗教文化,就是一例。武术文化只是武术文化、就是武术文化。
说武术文化这一完整体系全面体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说武术有着足够的文化负载能力,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母体的一个侧面,具有着文化母体的核心本质特征,透过它,可以完整地折射文化母体基本精神的全部光芒。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在武术文化形态中都有集中的反映。“窥一斑而见全豹”,“一滴水可以照见整个太阳”,由武术文化形态的深入了解与研究,不仅可以把握武术文化形态本身,也可以更切入地观照复杂文化母体的主导与整体面貌。
是否能反映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文化形态是否确立的重要标志。但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基本精神有什么内容呢?
张岱年先生等在其著作《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提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许多要素的统一的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李泽厚先生则在《试淡中国人的智慧》中提出:中国人智慧的根基,实即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主要有四点,即所谓的“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汤一介先生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中则提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哲学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有三:解决人与自然(宇宙)之关系的“天人合一”;解决人与人(社会)之关系即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原则问题的“知行合一”;解决艺术创作中的人和反映对象之关系的“情景合一”。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个囊括世界而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深层结构。正是这一深层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若干表象,也形成了长久影响民族精神的四个方面:空想主义;实践的道德观念;求统一的思维方式;直观的理想主义。另外,庞朴先生则在《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缺乏神学宗教体系,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内容的观点。除了“天人合一”以外(中国文化中有着努力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所有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和大家的共识,但我的看法恰恰与之相反,因为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无法展开,我将另文阐述),综合这些看法,大致可以清晰全面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主要方面。
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武术中有着集中的反映,或者说,这种基本精神,深深渗透于武术文化形态之中。武术以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特殊本质,却反映了一般意义上的、共通的、共同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武术文化中反映的民族文化基本精神: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武术中反映的刚健有为、入世进取的精神。孔子提倡刚健有为的精神,强调并实践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易传》进一步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口号。历代儒家士人,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勉,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在此基础上,又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葆有“气节”,从来是中华民族崇尚的人生价值准则。中国武术从来赞扬锄暴安良、扶弱济贫的行为。专以惩恶扬善为己任,以高超武功作手段的侠客,更是中国人欣羡的对象,并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角色,由此,更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所仅见的武侠文学。忧国忧民、匡扶正义,始终是中国武林行为的座右铭,并蔚为爱国主义的传统。武林爱国英雄,代不乏人。明代少林僧兵抗击倭寇的事迹,更为武林平添了一分荣光。
(2)武术文化反映出的伦理型文化、重视人际关系的特殊人文精神。中国文化又被人称做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反对把人从社会人际关系中孤立抽象出来,强调人是社会的人,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和睦。武德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拳以德立,无德无拳”,“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武林重德,武德观念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武术和中国文化犹重人际关系这一特殊人文精神的联系。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推行中庸之道,谦虚恭敬,重视和合,是儒家人伦的基本要求,是儒家思想核心“仁”的基本内容,也是武德的核心。由武德出发,武术技术、武术方法也因之有了不少限制。武林有所渭“八打八不打”的说法,《罗汉行功短打·序言》竟称点穴术是为了“不得不打”,但又“不致伤人”才创立。内家拳的“后发制人”,套路之所以产生,中国武术家各式各样的间接比武方法,可以说都和遵循人际关系和谐的宗旨以及限制武术的暴力程度有关。
(3)武术中反映出的中国文化排斥神学宗教体系的世俗化精神。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文明的一种普遍文化形态。中国又是一个多宗教共存的国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在民族文化的其它文化形态中,宗教的影响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但始终显而易见。
然而一般而言,宗教的本质与武术的本质是截然对立的,成熟的、文明的、高素质的宗教的禁欲、原罪、非暴力等特征,与武术通常意义下的作为致伤、致残、致死的技术的特征,无论如何很难吻合与接近。中国宗教与中国武术的非同—般的结合,显然需要具备某种特殊的文化历史前提与条件。
孔子是不信神的,中国人对血缘亲情,现实社会、身体、生命、人生的重视,始终超过了天国与彼岸的设计。孔孟儒学始终是社会思想的主流与正统,并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延续数千年。外儒内法、儒道互补、三教合流,也始终没有突破这一以宗法和伦理为构架的社会文化基本模式,这就使得中国本土产生的以及外来的宗教,几乎无例外地变得非常世俗。要么始终未能出现高素质、成熟的宗教必然的天国福音的追求与设计,一如道教;要么一定程度上教律松动形成世俗化潮流,一如佛教。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武术和中国宗教才可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与结合。毫无疑问,禅宗的世俗化,及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的特殊地位,正是少林作为宗教组织,却能产生容忍武术乃至僧兵及种种武术行为的必须前提。宗教与武术的结合,其实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排斥神学宗教体系的世俗化精神。
(4)武术中反映出来的重视血缘关系、血缘团体的宗法精神。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宗法。宗法制是从氏族制下的血缘关系与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重本抑末”、“以农立国”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人民安土重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被束缚而依赖于土地。以土地为中心的人民,没有更多的选择,只可能以血缘纽带组合为群。农业经济的长期发达,应该说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没有脱离宗法轨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以后,宗法制度发生过一些变化,不再像殷周那样直接形成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但宗法制的一些基本原则几乎完整地留存下来。儒家“家国一体”的观念,是宗法制的反映,更是这种制度在思想领域的被论证肯定,宗法的网络,伸展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
作为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武林,作为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中诞生的武术本身,便不可避免地探深打上了宗法的印迹。武术门派的形成,与宗法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宗、门、家、派等名称,顾名思义,已足以说明宗法与武术的关系。所谓“正宗”“、名门”、“流派”“、嫡传”的极其讲究,无疑也是宗法习俗。武术承传的师徒制与武术神秘化的形成,亦都与宗法背景有关。
当然,武术文化形态所反映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用武术的而不是其它文化形态的方式表现的。
武术文化既是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又自成完整体系,能全面体现、反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这三点又是密不可分的。它只有既是母体文化的有机体,又自成完整体系,才可能全面体现、反映母体文化的基本精神。
3 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
3.1 武术的本质、功能、形式与源起
谈武术的本质,必须首先弄清“武术”二字的含义。
《说文解字》沿袭《左传》的说法,释“武”字为“止戈为武”,但这显然是后起的伦理意蕴上的曲解。而在殷商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中,武字显然都是手执武器的形状。
然而光拿起武器还不够,仅此尚不足以使武术确立,不会武术的人或一只动物拿起武器,仍然与武术无关。武术所以成为武术,重要的是还要有“术”。
“术”是什么呢?《说文解字》释为:“术”,邑中道也。段玉裁注云:“引申为技艺”。道路是通达目的地的,技艺则是方法技术之谓,都是手段,所以技艺也就被称为术。
那么,简言之,武术就是徒手或手执武器搏杀格斗的方法或技艺。可以说,这就是武术文化形态和其它文化形态的不移的质的差异。这种本质,是从它诞生起就被规定了的。无论时间如何推移,无论有多少文明的、后起的渗透、依附、派生,武术的本质都是确立无疑、确定无疑的,武术如果真正发生了质的变化变异,武术就不成其为武术了。
武术的本质确定了,那么武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很明确,武术的本质特征是攻防,即用徒手的或器械的方式方法,用于搏杀格斗中的攻击与防守。攻防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武术的本质特征,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武术的灵魂与核心。
将武术的本质与功能混淆可能会造成一些混乱,这也就是武术界长期为武术是“武”还是“舞”争论不清的原因。功能可能很多是后起的,而且呈渐趋增长之势。但武术功能的增减并不意味着武术本质的变化。虽然武术有着表演的功能,但武术并不是戏曲文化;虽然武术也能强身健体,也有内功养生内容,当武术绝不是养生文化;虽然武术也能自娱娱他,但武术肯定不同于娱乐文化;虽然武术也能部分抽出用于竞技,但武术整体而言也绝对不是竞技运动。武术只是武术,武术文化形态依然故我为武术文化形态。
武术本质的确定性一同于其它文化形态的本质的确定性。医学的本质是治病救人,但医学也可用于整形,在坏人手里也可用来犯罪。这就是说,医学在一定条件下又具备美容和杀人的功能。然而这并不等于医学的本质有了改变,医学的本质既不是美容也不是杀人,医学的本质只能是治病救人。
武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管是按门派流派划分,按刀、枪、棍、剑、拳划分,还是按功法、套路、散打划分,武术形式总是依武术本质而展开、存在。而武术的功能,并不直接依武术本质展开、存在,而是依武术的形式展开、存在,是武术的种种形式,具有了种种的功能。所谓武术的自卫格杀功能、体育健身功能、体育教育功能、娱乐自娱功能、表演娱他功能、运动竞技功能等等,其实都是直接由武术形式而展开,依武术形式而存在,都是对武术形式的利用和依附。其中,除了自卫格杀功能是武术的基本、直接功能从而与武术本质联系紧密外,武术的其它功能与武术本质的关系,则要间接得多。武术形式与武术本质,武术形式与武术功能的关系是不能脱节的,但武术本质与武术功能的关系却未必。例如:剑与剑法是武术形式,剑与剑法创制必须反映服务于武术本质;老太太玩剑,用来锻炼身体,则是利用了武术的体育健身功能。但老太太舞动的剑,却完全可以略去攻防,和武术本质不发生任何联系。
武术的本质特征是攻防,要形成为攻防和完整的攻防技术,前提是要有双方、而且双方角色可以互换,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是人。双方都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手段和技术,双方都既可以攻,也可以防。武术攻防又是一种循环,也就是说精妙的防守,是对对手精妙的进攻的反应;而精妙的攻击,往往又是对对手精妙的防守的反应。攻——防,再攻——再防,又攻——又防,武术技术正是在互以人为对手,互以对手的技术为对象,“见招拆招”,才可能产生并发展为如此博大精深。人与人角色可以互换,但人与兽角色是不能互换的,野兽不可能使用与人同样的技术攻防。如果说人兽角色可以互换,那实际上等于认为野兽也是智能生物,同样参与了一种文化——武术——的创造。
人狩猎活动产生的人捕杀野兽的技术是有的,但这种技术是单向的,因之肯定也非常简单,它不能和武术同日而语,它只是一种生产性技术,例如下套子、设陷阱之类。
今天的武术已经不再包括弓箭,但弓箭最早无疑是武术器械,弓箭射术无疑是武术技术。今天的武术剔除了弓箭,与弓箭作用被火器取代有关,与弓箭更适宜于战阵而不属于武术主体的民间武术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弓箭射术不具备武术攻防这一本质特征。射者的初射与被射者的防射,射者的再射与被射者的反射,射者的初射与再射,被射者的防射与反射等,并无一般武术格斗攻防那种有机的联系。又如:暗器是中国武术曾经具有的器械和内容,但暗器也逐渐在消亡。同样,这主要也不是它的使用价值消失的原因。暗器和射箭一样,也不具备武术的攻防的本质特征。而这两类遥击武器,倒的的确确是最早源于狩猎的。正因为弓箭与暗器的这一特殊性质,它们在武术的发展中不得不退出主流,乃至逐渐消失,不仅今天的武术运动员对弓箭茫然无所知,即使是硕果仅存的民间武术家,也往往对其知之甚少。
由发生学意义上对武术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对武术源起、本质、功能的明确,将有助于我们在文明日渐发达,武术文化形态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时,准确把握武术发展的方向,准确投入我们的努力。
3.2武术文化形态的三个层面
借用近年来流行的“文化三层次”说,亦可将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分为“物器技术层”、“制度习俗层”、“心理价值层”三个层次。
“物器技术层”是物质文化层面,它是武术文化形态的表层结构,它主要包括武术技术,武术器械,武术练功器具、场所、服装等内容。它表现和展开的,是一种人——物关系。
“制度习俗层”是相对隐形的中间层,它主要包括武术组织方式、武术承传方式、武术教授方式、武术礼仪规范、武德内容规范、武术竞赛方式等内涵。它表现和展开的,是一种人——人关系。
“心理价值层”是最内层或最深层的武术文化形态结构层,它主要包括武术文化形态所反映体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等内容。至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之源、超越之源,西方文化追到了彼岸的“福音”、“天国”和“上帝”,中国文化则追到了实际上藏于自身的“天”、“理”和“心”。中国文化的超越是一种“内在超越”,这种内在超越和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有着很大的不同。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的“人——神”关系,中国文化表现和展开的是内在超越的人——天关系、人——心关系、人——道关系。无怪乎,我们把武术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无怪乎,“求道”或“得道”是我们练武术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
或许我们还可以用另一套术语来表示这三个层面:道与理是核心层;礼与艺是中间层;技与术是外显层。
G85
A
1004—5643(2011)01—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