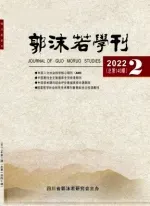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借镜
——以郭沫若与有岛武郎为中心的考察
王海涛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4)
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借镜
——以郭沫若与有岛武郎为中心的考察
王海涛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4)
郭沫若早年思想及新诗创作深受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通过有岛武郎,郭沫若接触到惠特曼的思想和诗歌;以有岛武郎为中介,郭沫若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将此种思想融入新诗创作中,故而其新诗体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有岛武郎的人格理想是郭沫若早年自我人格塑造的重要参照系,使郭沫若在灵肉冲突中获得精神慰藉。但由于自身浓烈的家国情怀,郭沫若逐渐疏离了有岛武郎。
郭沫若;有岛武郎;白桦派;无政府主义;人格理想
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1](P53-54)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来自日本的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这不仅因为日本充当了中国现代文学界了解欧美文学的中介,更在于日本近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许多现代文学的早期实践者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在日本现代文学变革的氛围中开始文学革新的探索的。诚如李怡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在传统中国文学的创作资源消耗殆尽、创造能力日渐枯竭时,是中国作家在日本对于西方文化的‘体验’首先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令他们在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郭沫若早年思想及新诗创作就深受日本白桦派(尤其是有岛武郎)影响。研究这种影响关系对郭沫若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为“郭沫若在这里也不仅仅是一个被关注的个体,而可能意味着创造社作家群体。再深入一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它又是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近代文学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切人点。”[3]
一
白桦派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主要活动时间是1910年至1923年,代表人物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被日本文学批评家本多秋五誉为“大正文学中浩大的水脉”“近代日本文学的精髓”。[4](P64)白桦派的文学主张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极力张扬个性的人道主义,推尊个性、强调发展自我,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其思想领袖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运动》一文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人类的意志、探讨个人应如何发挥自己的运动”,“不以个人为基础,则将一事无成”,所以“人类的发展,首先必须是个人的发展”。[5](P411)这种对个性自我的肯定是日本近代文学所需要的,也正契合郭沫若等中国新文学探索者的精神需要。因而,西乡信纲在总结白桦派的文学史价值时说:“白桦派运动的巨大功绩是恢复势将被自然主义抹煞的对人性的信赖,把近代的人道主义引进文学界,把它树立起来。”[6](P325)
白桦派不仅在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坛上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为人生派”和“创造社”的形成有推助作用:它的肯定人生,“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影响了“为人生派”;它的尊重个性、肯定自我,强调发挥人的创造力和表现自我的艺术主张影响了“创造社”。周作人是最早接触白桦派的中国文学家,他在《白桦》创刊初就购买了“罗丹70诞辰纪念号”,并且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保持着密切交往。他的“人的文学”观就是在白桦派的启发下形成的。创造社的领军人物郭沫若接触白桦派的时间也很早。他自述:“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7](P67)这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郭沫若明确提及白桦派对其直接影响的最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者经常提及的。自述中所说的“大学二年”即1919年。郭沫若在这一年关注到有岛武郎的《叛逆者》,并不是完全出于“无心”,而是与当时日本文学界的大环境有关。因为该年正值惠特曼的百年诞辰,日本文学界对惠特曼的研究与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加藤一夫、富田碎花、白鸟省吾等人组织了“惠特曼纪念会”,有岛武郎则在日本各地作了关于惠特曼的系列演讲,一度形成“惠特曼热”。这很自然地影响到留日的现代中国作家。田汉即于该年7月在《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肯定了惠特曼的“民主主义”“灵肉调和”思想和诗歌创作。对此,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信中称赞说:“他早那样地崇拜Whitman,要他才配做‘我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呢!”[8](P19)
当时的郭沫若与国内文学界较为隔绝,还处在探索文学创作走向的时期。他处在日本文学界大量引进西方文学的文化氛围中,很自然地接受了许多不同流派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很难说哪种文学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是,其早期诗作留下的惠特曼影响的烙印是鲜明的。而他之接受惠特曼正是以有岛武郎为中介的。日本学者秋吉久纪夫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形成过程》中甚而指出:“有岛武郎的《叛逆者》,可以说是决定郭沫若一生的主要因素。”[9](P346)但鉴于学界关于郭沫若与惠特曼的比较研究已有很多,故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主要探讨有岛武郎的思想影响郭沫若之数端。
二
有岛武郎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有岛武郎为中介,无政府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郭沫若及其新诗创作。
“无政府主义”一词系由日文转译而来。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欧洲,由德国学者麦克斯·施蒂纳首倡,后经由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发展完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论核心是“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反对一切组织纪律,倡导自由组合;反对“按劳分配”,主张“各取所需”。有岛武郎早期思想中即包蕴着无政府主义的因子。他早年结束留美生活途经英国时拜见了克鲁泡特金。通过克鲁泡特金的关系,有岛于1907年回国后结识了日本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并接触到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到晚年“他那种以强烈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厚了”。[10](P88)在短篇小说《除锈工》中,有岛武郎大胆地书写了底层民众对压迫的反抗,将他们视作抱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革命的自由人”。在《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中,有岛武郎极力推崇惠特曼的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即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为此,他大段摘译了惠特曼的长诗《自己之歌》。诗中追求自由、渴望摆脱一切束缚的观念“构成了有岛共鸣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政治立场的一种引力”。[11](P581)正是有岛武郎在文中表露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郭沫若。我们看到,郭沫若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好感。他于1923年翻译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序》(郭沫若译为《我的分内事不放在什么上面》)。同年10月18日,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大杉荣遇害,郭沫若有感而发写了《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他痛感:“在国家的历史渐渐演进以后,国家竟成为人类的监狱,人类的观念竟瘐死在这种制度之下了”,因而憧憬一种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并认为中国的传统精神就是世界主义的。[12](P139-140)可见,郭沫若这种“世界主义”思想正导源于无政府主义。正是秉持着“世界主义”思想,他后来又写了《马克思进文庙》。
他的这种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理想直接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在《棠棣之花》中,他借聂瑩之口说:“侬欲均贫富,侬欲茹强权,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他自言:“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过一些歌颂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诛除恶人的思想,很浓重地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7](P147)另如,在《巨炮之教训》中高呼:“我主张克己,无抗的信条。/也不要法庭:/也不要囚牢:/也不要军人;/也不要外交。/一切的人能如农民一样最好!”[13](P110)在《孤竹君之二子》中,他则借歌颂伯夷、叔齐表达了同样的理想社会诉求。对于其创作出发点,郭沫若在该诗剧《幕前序话》中也说得很明确:“我们考察他们的言论,综核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确是他们古代的非战主义者,无治主义者。他们的精神和我们近代人是深相契合的。我把他们拿来做题材,也犹如把Kropotkin,Bakunin(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拿来做题材一样”。[14](P239)
同时,郭沫若对有岛武郎所张扬的无政府主义的叛逆精神表现出极大认同,并将此种精神熔铸于其新诗中。
在《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中,有岛武郎写道:“我们面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态度: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所鼓舞,还是为哥特全盛时期的精神而讴歌。所有的人,都必须立即从中作出选择。选择前者,则将成为时代的宠儿;选择后者,则必勇当时代的叛逆者。而且,我深信这位温顺而谦和的罗丹,必将同易卜生、托尔斯泰、马奈、塞尚纳、惠特曼等现代文学艺术界的巨匠一起,甘愿充当叛逆者的首领。”“个性是艺术创作的核心。……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强大的个性,为萎靡不振的人民开拓新的世界。罗丹就是以这种态度来适应新的要求的。”[15]他极力推崇的是罗丹敢于颠覆古典艺术的清规戒律、努力探索富于个性的新艺术的叛逆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给予郭沫若极大鼓舞,激励其在诗歌创作中抛却传统规范的束缚,尝试采用新的诗体形式,融入个性化的自我精神。而经岛武郎译介的惠特曼作品正可成为他新诗创作的追摹对象。同时,有岛武郎是将确立主体价值作为创造新文化的重要途径的,深具文化忧患意识的郭沫若则通过包括新诗在内的一系列文艺创作践行了他的这一观念。
众所周知,郭沫若早年是个主情主义者,他曾反复申述诗歌的抒情本质。如果联系他接触有岛武郎《叛逆者》的时间,我们会发现:他的这类表述正集中见于其后的一段时间,尤其是他和宗白华、田汉的通信中。如,他在1920年2月给宗白华的信中说:“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而“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绪的)。”[8](P46-48)1923年,他在上海美专的演讲中也说:“艺术家总要先打破一切客观的束缚,在自己的内心中找寻出一个纯粹的自我来,再由这一点出发出去,如象一株大木从种子的胚芽发现出来以至于摩天,如象一场大火由一点星火燃烧起来以至于燎原,要这样才能成个伟大的艺术家,要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艺术出现。”[12](P123-124)这些观点都表露出他对艺术创作成规的反叛心理和对抒发主体情感的强烈吁求。1930年,他回顾创造社时就将其创作倾向概括为“个人主义”,并坦陈其所受日本之影响:“他们是在新兴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所陶养出来的人,他们的意识仍不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他们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他们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这内在的要求、自由的组织,无形之间便是他们的两个标语。这用一句话归总,便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19](P99)
有岛武郎的《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对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直接影响痕迹见于《匪徒颂》。该诗热情称颂了东西方18位不同领域的革命领袖,其中第五节称颂的是文艺界的革命者:
反抗古典三味的艺风,丑态百出的罗丹呀!
反抗王道堂皇的诗风,饕餮粗笨的惠特曼呀!
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诗中提及的“匪徒”与前述有岛武郎所说的“叛逆者”多有重合。只是,有岛武郎论文所述限于文艺领域,郭沫若则将对革命的呼唤扩展到政治、社会、思想、教育等各个领域。这是他在有岛武郎启发下结合中国现实思虑的结果。
在郭沫若的思想意识里,对传统的态度包含着破坏和创造两个层面,即破坏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像《匪徒颂》这样饱含反叛激情的诗歌在《女神》中是多见的。《女神之再生》《湘累》《天狗》《浴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胜利的死》等都彰显着同样的精神。它们抒情强度不一,抒情方式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富于反叛精神的抒情主体。试看《浴海》:“太阳的光威/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弟兄们!快快!/快也来戏弄波涛!/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全诗精力弥漫、激情澎湃,诗人在大海的鼓荡与淘洗中焕发出强烈的革新和创造冲动。那蝉虫的鸣叫正是诗人的心声,渴望改造旧我、旧社会,创造新我、新社会。该诗作于1919年10月14日,在郭沫若接触有岛武郎的《叛逆者》之后不久。可以说,正是有岛武郎所宣讲的叛逆精神给予郭沫若以强大的精神支撑。再如,佚诗《解剖室中》由解剖尸体联想到破坏后的新生,呼唤“新生命”“新少年”“新中华”。该诗洋溢着破坏的激情和重生的期盼,颇有《凤凰涅槃》中凤凰浴火重生的意味。诗中提及的罗当(即罗丹)、弥尔弈(即米勒)正是有岛武郎在《叛逆者》中论及的人物。
另外,在诗歌的抒情方式上,郭沫若也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几近喊叫式的抒情。《凤凰涅槃》《天狗》《日出》《晨安》《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等诗就是代表。这与千叶宣一在《诗的无政府主义系谱》中谈到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诗歌极为相似。[17]
三
有岛武郎的人格理想也对郭沫若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郭沫若早年自我人格塑造的重要参照系。
有岛武郎的人格理想是在惠特曼的影响下确立起来的。他在《不惜夺爱》中说:“人的生活的极至要求,就是自我的完成。完成社会,也就是自我完成。自我完成终究是社会的完成”。[18](P303)概而言之,他追求的是“灵肉合一”的人格理想,是“自由人”“自然人”。他不满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灵肉分离现象,致力探寻理想化的生存存在。在《关于惠特曼》一文中,他就盛赞惠特曼是典型的Loafer(自由人、自然人)。在收入《叛逆者》的《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一文中,他更是以惠特曼为镜坦陈心迹、勇敢自剖,表达了自己对“灵肉合一”的人格理想的渴求。所谓“灵肉合一”就是要兼顾灵与肉,在肯定灵的同时不舍弃肉,保持内在生命的完整性。为此,有岛武郎提出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我”,追求表里如一,反对人格分裂,提倡“灵魂伸展”,力求摆脱外部世界强加的各种束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反复申述灵魂的核心价值的同时,特别为肉身正名。他认为:肉是灵的一部分,二者并不对立,传统的陈腐观念必须根除。他引用惠特曼的《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为证。他的这一观点在长篇随笔《不惜夺爱》中有了更充分的发挥。他试图摆脱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二元矛盾困扰,营造一种没有二元对立的本能生活。为此,他引入爱的概念,希图通过爱的生活(本能的生活)获取完全的自由,甚至不惜将本能生活置于理性生活之上。这样,他就与追求“灵肉合一”的初衷逐渐背离了。但他的“灵肉合一”主张对同时及之后的一些日本文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影响了郭沫若(或者说使郭沫若获得了精神慰藉)。
彼时的郭沫若正处在与有岛武郎相似的矛盾纠缠中,困扰他最深的是因与安娜同居产生的负罪感。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如有岛武郎般自剖:“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8](P41)在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的信中,他说道:“能永不结婚,常保Purelove底心境,最是理想的。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这层倒还容易解决。有了生育更不自由。这层简直莫有解决的办法。”[8](P121)这流露出的都是因灵肉冲突导致的苦闷情绪。
恰在这时他接触到了有岛武郎的著作。除了《叛逆者》,他对有岛武郎的戏剧三部曲(《参孙与德利拉》《大洪水之前》《圣餐》)也颇感兴趣。在1920年3月6日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详细分析了《参孙与德利拉》一剧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该剧“描写的是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l与Reality底冲突,他把Samson作为灵底世界底表象,Delilah作为肉底世界底表象。”[8](P102)可见,郭沫若对有岛武郎的理论和创作都有较深入的了解。他处在灵肉冲突状态时找到的知音正是有岛武郎。但与同样被内心诸多矛盾所苦的郁达夫不同,郭沫若试图冲决各种桎梏,通过发挥创造的本能营造理想的人生。因而我们看到他特别认同有岛武郎文中译引的惠特曼的《大路之歌》(郭沫若译为《坦道行》),并且在前面提到的致宗白华的信中摘译了其中的两节:①
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底化身;
从今后我再不欷歔,再不踌躇,无所需要,
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大道。[8](P125)
我们看到在他的诗歌中就表现着与惠特曼相近的人生态度。在《梅花树下醉歌——游日本太宰府》中,他通过赞美梅花表达了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我赞美你!/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13](P95)这与惠特曼《自己之歌》中“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的诗句极为相似。
尽管有有岛武郎的精神支撑,郭沫若仍无法完全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对此,我们从收入《星空》的《苦味之杯》《黄海中的哀歌》《仰望》等诗歌中就可见出。正是为灵肉冲突、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所苦,郭沫若才会不知疲倦地咏唱破坏之歌,极力赞美太阳和大海。他希冀从苦闷与矛盾中挣脱出来,重获新生。但在探寻新生的道路上,郭沫若逐渐与有岛武郎疏离了。因为,他是一个有着浓烈家国情怀的人,父母之邦的苦难、民族的前途命运是他始终不能释怀的,他不能如有岛武郎般沿着单纯的思想心路走下去。这也是早期创造社成员共同的精神困惑。正如伊藤虎丸所说:“创造社的艺术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存在于这种艺术主义的根底的‘自我’的性质,一方面具有和这样的人道主义(按,指《白桦》和《三田文学》所张扬的人道主义)发生共鸣的‘条件’;另一方面还有中国人的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无法‘心安理得地写着人道主义的作品’。这两个方面,就规定了他们的文学上‘自我’的性质。”[19](P178)
(责任编辑:陈俐)
[1]郭沫若.桌子的跳舞 [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3]蔡震.“郭沫若与日本”在郭沫若研究中[J].新文学史料,2007,(4).
[4]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5]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6][日]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郭沫若.创造十年[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8]郭沫若等.三叶集[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9]吕元明.战后日本开展郭沫若研究概况[J].郭沫若研究·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10][日]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1][日]濑沼茂树等.有岛武郎研究[M].右文书院,1971.
[12]王锦厚等.郭沫若佚文集(上)[M].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13]郭沫若.女神[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4]郭沫若.星空[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5][日]有岛武郎.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J].郭沫若学刊,1988,(2).
[16]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7][日]千叶宣一.日本现代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8][日]吉田精一.明治大正文学史[M].同兴社,1984.
[19][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A
1003-7225(2011)01-0019-05
2010-12-13
王海涛(1976-),男,山东东营人,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四川省社科规划课题:郭沫若思想研究史论(SC10E019)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课题: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述评(GY2009L13)
注释:
①郭沫若漏译了第二节第三句“Donewithindoorcomplaints,libraries,querulouscriticisms”。该句意为:“消除了闷在屋里的晦气,放下了书本,摆脱了苛刻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