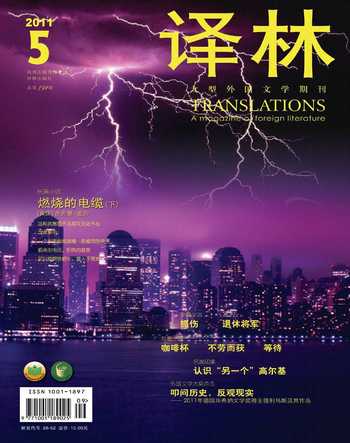纤笔一支的担当
庄建 虹飞
乔治•奥威尔不仅是20世纪最摄人心魄的对抗性作家,他的散文和评论随笔被很多人认为甚至比他的小说还要精彩。本书收录了奥威尔最有影响力的文学随笔共三十二篇,通过这些观点鞭辟入里、风格明晰简练的檄文,奥威尔想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如何思考的;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他还想让我们理解,我们到底是谁。TRANSLATIONS译林外国作家访谈录纤笔一支的担当
——华裔作家李彦访谈
无论是在北京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与记者就《红浮萍》中文版对谈,还是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故土历史呈现——加拿大与美国华人英语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李彦都更像我们中的一员。
十五年前,她用英文写作的小说《红浮萍》在加拿大出版。此后,再没有停歇。一位中国文学评论家这样评价她的作品:“李彦写了华人精神的离散,历史在她的作品中只是作为记忆出现,她的关注焦点是当代。离散中的人,会产生新的美学。”
李彦的作品,塑造出的是与以往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完全不同的移民形象,他们的生存状态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内心的思索不同,人生的追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此之外,李彦的作品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她是从内心写出去,不仅是写一个自我,而是写出了一个群体——“我们”,最终完成了新移民自画像的起笔和延续。
中国人在加拿大的移民史,由于李彦们的书写,得以续接,形成完整的链条。我们以为,这就是李彦和像她一样的新移民作家历史性的贡献。
李彦:1987年,我离开北京来加拿大求学。年轻的我,只想开拓视野,更多地了解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二十多年来,在海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忘不了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眷恋。
和不少国内同胞相比,去了海外的人,似乎对祖国的历史和今天的种种不足,更多了一份理解和体谅。这种感情,大概和上世纪80年代一位中国诗人米思及所表述的心情很类似吧。他在诗中写道:“被鞭打得越狠,对你的眷恋就越深。被驱赶得越远,越是痴痴地把你怀念。”无论时代是怎样地日新月异,历史是如何地变迁,中国传统的精髓,早已融化在我们的血肉之中,不可磨灭。
记者:在异国他乡,李彦们的生活起点与早期移民有了巨大的差异,受过的良好教育,为他们提供了观察与思考的新视角:更加关注的是自身与所处社会精神层面的流变。
李彦:来加拿大一年后,我开始创作小说《红浮萍》。写作的直接动因,是有感于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了解的肤浅。由于文化、历史、社会、信仰、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长期“冷战”隔绝的结果,二十多年前,普通西方民众对中国缺乏了解。加拿大图书馆里有关中国的书籍铺天盖地,但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写的。在他们笔下,无论是描写历史事件,还是政治运动,中国人基本上都被塑造为思想简单,没有信仰,缺乏正义感,或是懦弱得任人宰割,或是热衷于暴力行为的冷血动物。这种偏见与误解,根深蒂固。
我决定自己动手,用英语来讲故事,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反映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历史,写出中国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写出他们在动荡不安的历史状态下坚忍不拔,顽强的奋斗。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接受的英文采编专业训练,此时派上了用场。
《红浮萍》对历史的把握和对人性力量的挖掘,得到了读者认同。一位住在多伦多的中年女教师写信说,“读了你的小说,我体会到,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女性,情感上原来十分相似。女主人公的许多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们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一封温哥华女读者的来信更是在我的内心掀起涟漪:“读了你的小说,当我再次走入唐人街的中餐馆,仔细端详在那里遇见的华人时,我已经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不再是头脑简单,表情麻木的群体,每张脸上,都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他们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心灵。”
这本书被美加不少学校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辅助教材,它成为一个通道,虽不宽广,却很独特,可以让读到它的人走进中国人曾经历过的那段路程。
几年后,我又用中文创作了《嫁得西风》。动笔前,脑中已充盈新一代移民在海外生活与奋斗的故事,我希望我的创作是一座桥梁,让新一代华人的生活镜像从这座桥回归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故土。我的第一部中文作品,就这样以长篇小说开始。
记者:母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创作,带给李彦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与状态。
李彦:当我想表达对生命更深层次上最真切的心灵体验时,似乎用英文更直接。也许因为它只有26个字母,是一种很简洁的语言,在使用时似乎更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事情的实质层面上,因而能抛开一些虚浮的东西,使思绪朝纵深发展,不太受文字表象的诱惑和干扰。英文作品让西方读者直接进入你的故事,体会你想通过文字传达的思想和生活, 作家由此获得了话语权。绝大多数居住在海外的华裔作家是用母语创作。我决定采用双语写作,是希望我们华裔移民的声音能够被主流社会听到。因为华裔在加拿大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是绝对的少数民族。仅用中文创作,便只能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自拉自唱,自娱自乐。
《雪百合》出版后,《加拿大文学评论》载文说:“李彦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写作所产生的神奇的炼丹术般的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书中的意象群和节奏韵律感。毫无疑问,她那带有共鸣的声音,是属于中国韵味的,即便她是用英文写作,也充盈着那种古老语言所携带的胆识、生机与美丽。”
记者:写自己的故事,写新一代华人移民正在“进行时”的生存状态,李彦找到了生活的富矿。她身在其中,将生活凝炼成文学,文学中便带有了生活的体温。
李彦:人们在陷入困境时,往往会希望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协助自己得以解脱;而人们在物质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也往往会把兴趣转移到生命的终极意义这些抽象的思考上来。我很早就观察到新一代移民在海外生存的特点,并开始思索这一领域的问题。我以局内人的身份进行的创作,更像是在完成一幅“自画像”,心对着手,挥洒自如,完全进入了“得心应手”的境界。
《嫁得西风》与 2001年在北美《世界日报》小说版上连载的中篇小说《羊群》是开端。过去的十年里,我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例如《毛太和她的同学们》、《地久天长》、《忘年》、《白喜》、《罗莎琳的中国》,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探索的作品。
评论家白烨说,“《羊群》这部中篇小说,以一个加拿大小城华人基督堂发展教徒和争夺教职的经过,揭去了罩在这个场所的神圣面纱,让人看到了冠冕堂皇背后的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也揭示了一些共产党人在出国移民之后皈依基督教的内在隐秘。一些人是寻求帮助,一些人是寻找组织,基督教就如此这般地在一些人那里成了党组织的替代品。这像是在讲述信仰的异变,又像是在描述信仰的不变,像是讴歌信仰的力量,又像是在诘问信仰的意义。牵扯出有关人的精神世界现状的大问题,很让人为之惊醒,为之思索。”
近二十多年来,华裔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不断进入加拿大,在各行各业为加拿大社会做出贡献。但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华裔移民的社交圈子往往限制在自己的族裔之内,主流社会对我们这个群体的生活和思想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媒体上出现的有关华裔新移民的报道,很多是与犯罪行为相关的浅表且负面的消息。因此,我决定用英文写一部长篇小说,为我们华裔移民画“自画像”,从心灵层面真实地展现身为第一代移民在新世界里的喜怒哀乐、彷徨求索,以增强主流社会群体对我们华裔新移民的理解,促进族裔间的和谐共处。
2010年1月,我的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在加拿大出版。几十年来我对人生、对信仰、对女性角色的思考都融汇其中。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一个小城,描述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寻找心灵归属感的历程。小说主人公百合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很多篇幅都用来描写她面对现实和理想冲突时的困惑以及对生活价值观的反思,在应付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完成了精神和心灵上的转变。我期望这部作品能够促进西方民众与新一代华人移民相互间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加拿大评论家说,“《雪百合》为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信仰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并通过幽默的语言与出色的观察力探索了移居到加拿大的华人的体验。”
“贯穿小说始终的还有其他一些主题:宗教对新移民的作用,华人家庭的期望,以及人类在精神追求上有时必须面对的不可承受之重。小说的文笔与风格非常出色,描述了华人新移民奋斗不息的意志,提供了他们在加拿大追求理想生活的生动写照。”
《加拿大文学评论》发表评论说: 当今之世,新闻报道里出现中国的消息越来越多,中国的形象也总是被描绘成对西方构成的新威胁。恰在此时,对中国和西方世界都了如指掌的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在她最近出版的这部新小说中,李彦通过坦率与微妙、悲伤与喜剧交替出现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移民在安大略一座小城里新生活中的阵痛。小说的开端,在表面上给读者的印象是简单的平铺直叙,但很快就揭开了一层层深深埋藏的复杂的内涵。随着故事的逐步展开,读者越来越被吸引,涉足于一个隐秘的世界中,在那里,无言的疼痛交织着沉静的希望,流畅、清晰的笔触绘制出一幅幅精致紧凑、充满生机的、来自心灵世界以及自然环境的一道道迷人风光。
“百合”在英文中,象征着纯洁,隐喻着主人公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中文里则有更加丰富的含义,象征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以及作者对人类社会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望。雪,不但代表了冰雪之乡加拿大,也象征着新移民来到陌生的土地上时最初的感受。“雪中的百合”,更深一层意义是:从富饶古老的家乡移植到一片冷冰冰的新土地上,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们为这种选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新移民过去的经历和背景如何,在新的环境里,一切都被淹没掉,无法凸现出来。他们所受过的高等教育如今都变成了过时的沉重包袱。人们憧憬着成功与辉煌,常年累月地在渴望与企盼中挣扎与煎熬着,直到最后,绚丽的梦想在现实面前变得支离破碎,烟消云散。在移民地,人们只能白手起家,从零做起,重新打造新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社会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融入西方的现代生活是一桩举步维艰的难事。
有趣的是,如今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作家哈金,也写了一本和《雪百合》主题相似的小说,《自由的生活》(A Free Life)。我们都是在来到北美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不约而同地,发表了这部由新移民作家的目光来打量我们身处的新环境的小说。这种经过沉淀的观察和描写,是我们从初来者的兴奋冷静下来后,经过长期痛苦的摸索,灵魂深处最真切的体验,所以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这个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不足。
加拿大有一批第三代、第四代华裔作家,非常优秀,他们有良好的英文功底,但中文水平却相对较低,有些甚至不懂中文,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几代华人在加拿大奋斗求生的历史,书写了华裔移民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环境下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异域经验,对于白人世界的种族歧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也都给予了批判性的呈现。
在过去二十几年里,这些华裔作家的作品屡屡获得加拿大国家级文学奖, 2010年刚刚又有一位新秀获总督文学奖提名,对提升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华人祖先海外奋斗的主题下,影响较大的华裔英文作家和作品有:
郑蔼龄的自传体小说《妾的儿女》,1994年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小说类提名。
李群英的小说《残月楼》,1990年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小说类提名,温哥华城市奖等。
余兆昌的二十几部文学作品,如《金山传说》、《列车鬼魂》、《唐人街》、《收骨人的儿子》、《亡者的金子》等,很多都是获奖作品。
崔维新以他的《玉牡丹》为代表作的四部长篇小说也是连续得奖,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热捧的杰出作家。
黎喜年(Larissa Lai)的 《千年狐仙》(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刘绮芬(Evelyn Lau)1989年出版的《逃离家庭的少女》获总督文学提名奖;
方曼俏的小说《午夜龙记》、《中国狗》,也得过奖。
除了小说,华裔作家中较为著名的还有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朱蔼信(Fred Wah),歌剧作家陈嘉年等等。
2001年,在多伦多上演的歌剧《铁路》,是一批华人作家集体创作的结晶。讲述了一百多年前华人离乡背井到北美修铁路的悲惨生活和艰辛工作。
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第三代华裔英文作家创作有几个特点: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兼之一百多年来语言和文化的变迁,第三代华裔作家在表现他们的父祖辈华人移民的生活时,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隔膜,致使有些作品呈现的第一代华人形象失之刻板,他们显得头脑简单、思维粗浅、语言贫乏,叙述祖先故事时信息逐代递减的情况很明显。但是,也有少数几个具备了一定中文水平的华裔作家的作品,却没有这种缺陷,如余兆昌(幼时读过中文学校,大学时也选修过两年中文课程)、方曼俏(5岁从香港移民来加,可以与父母良好沟通), 他们在作品中展现的华人形象就显得有血有肉、情感丰富。不少北美土生的华裔作家用英语写了很多有关“金山”题材的作品。由于他们的父辈往往就是当年的华工, 与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当我读他们这种源于真实生活, 而非二手资料的作品时, 经常会有那种置身其中的颤栗和真切感。他们成功地将华裔移民祖先的历史生动深刻地介绍给广大的西方人,在主流文学中为华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 历史和文学已被密不可分地融会在一起。
之前的华裔作家除了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批判外,对自己族群的黑暗面也有所表现和批判,但这种表现存在着比较微妙的尺度。华裔作家所表现的华人族群的黑暗面大多集中在赌博、纳妾、重男轻女、不讲卫生、过分节俭、不诚实、弄虚作假等方面。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描述灵异现象,表现鬼怪和灵魂的存在的文字,例如崔维新、余兆昌、方曼俏等作家都在作品中描写过祖先的灵魂,这种对讲述灵异事件的热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第三代华裔作家身处异国他乡的强烈孤独感。也许,通过鬼魂灵异的故事,可以为这些无根的移民提供一种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归属感。
除了第三、第四代华裔作家,加拿大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用英文写作的新移民华人作家,除了我的《红浮萍》、《雪百合》之外,还有《虎女》的作者赵廉,《苦风孤叶》的作者叶婷行,黄俊雄的短篇小说集等。如果包括北美整个范围,比较突出的还有《红杜鹃》、《野姜花》、《成为毛夫人》的作者闵安琪,还有哈金,写了《等待》、《战废品》、《自由的生活》等。但是,这个群体的作品,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语言上的隔膜是首要的因素,但英文创作的中国题材的作品没有进入华文文学研究的范畴,也不失为一个原因。所以,这个群体,成为了一个在祖国被忽视的角落。
与第三代华裔英文作家不同的是,新移民作家大都中文水平较高,具备双语写作的能力。无论是在华人社会中还是在西方社会中,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都比第三代华裔作家的祖、父辈相对宽松多了,因此在我们的作品中,几乎很少看到关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和屈辱历史的呈现,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如评论家白烨所指出的,“关注点已经扩展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精神信仰的诘问与追求。”
我是以“insider”(局内人)的身份来讲述中国的故事的。一个“insider”的注意力是内倾式的,她来自于那里, 生活和成长于那里, 便自然会更多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人性中更具深度的东西,更多关注精神层面那些真切的体验,而一个“outsider”则较多关注表层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有时难免给人以走马观花,猎奇甚至误解之感。中国人写中国和外国人写中国,出发点和感受当然不同。我的作品,很少涉及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内容,而是更多地将着眼点放在对人类精神世界层面的关注上,很多都是内省式的思索,包括对不同文化和信仰之间的认真比较。这也许是受益于我过去十几年来在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课程的经历。另外,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们,多属加拿大的知识阶层。大家在一起关注和谈论的话题也间接地影响了我创作的内容和主题。
不但加拿大主流文学评论界注意到并且欣赏我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精神层面的意义,有些中国评论家也注意到了我的创作有别于很多海外华裔作家的这一特点。
记者:第三代华裔作家和近年来崛起的新移民作家的中英文作品,为西方世界的读者呈现了华人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气象,对重塑华人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意义深远,但这两个群体作家的创作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李彦的一句话,让我们无法忘记。她说,在我的心目中,一个好作家应当关注人类的命运,并能用手中的笔推动和影响社会的变革。“纤笔一支,三千毛瑟”。
“有意味地发现生活,有想法地表现生活,看似平实的字里行间却闪动着一种渗透人心的力量,那种感染力会让你久久地回味,感觉到作者已将自己融化在作品中,是在用心灵去阐述故事……她对别人如何应对生活,以及如何艰难,并不是很有兴趣,她更感兴味的,是那些隐藏在内里和背后的东西,比如,人生遭际中的心路历程,生活事项里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别人喜于描述新老移民的生活状态的话,那她更乐于表现移民男女的内在心态。正是这种内倾式的写作姿态,使得李彦的小说以‘不求新而自新和‘不求深而自深,别具韵致,并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思想性特征来。她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都是这种探求的硕果,这种风格的产物。”
——这是评论家白烨说的。我们以为,是画龙点睛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