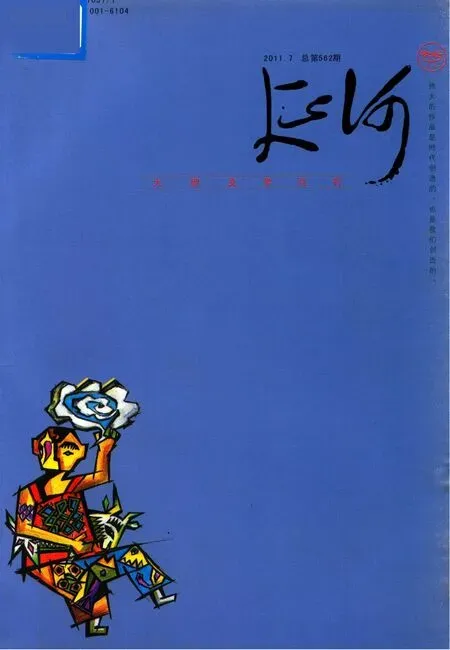我与母亲
祁玉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情真意切,真挚感人,将母爱和母子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可谓千古绝唱。多少年来,我百读不厌,刻骨铭心。
我的母亲一九二四年正月十一出生于子洲县水地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5岁丧父,遭到有钱人家的百般歧视,受尽了种种磨难,靠我的外婆含辛茹苦将她和我的大舅、二舅、大姨、二姨、四姨抚养成人。由于家庭生活所迫,14岁就嫁给了我的父亲。从此,便操持起了我家繁重的家务。她虽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极普通的农家妇女,但贤淑明理,勤劳善良,思想进步,早在建国前就加入了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各项活动,成为当地有影响的妇女代表之一。村里和方圆十多华里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人们都爱找她商量,渐渐地她便无形中成了一名义务调解员,化解和处理了不少家庭纠纷和社会矛盾。解放后,她还曾担任过大队妇女主任,带领全村妇女积极投身生产建设,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县、乡的表彰奖励。从懂事起,我就对母亲十分敬重,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我小的时候,我家很穷,孩子又多,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每逢吃饭,母亲总是先招乎孩子们吃。年幼无知的我们,你一碗我一碗抢着吃,尤其是我的大哥和四弟,饭量又大,好像永远吃远吃不饱。每当这时,我常常催促母亲快吃,可她总是说“我不饿,你们尽管放开吃吧。”等最后轮到母亲时,已所剩无几,她只好将锅底残余的些许饭菜掺上开水充饥,有时竟空着肚子。
那时候,我们兄弟几个非常贪玩,衣服和鞋袜往往穿不了几天就破烂不堪,这就更加加重了母亲的负担。白天,母亲还要下地干活,针线活只好靠晚上来做。多少个夜晚,当我一觉醒来,母亲还在昏暗的油灯下飞针走线,挑灯夜战,聚精会神地为我们缝补衣衫。上初中的时候,家里拿不出上灶的口粮,我只好“跑灶”。家里距学校有十多华里,而且全是山路。为了不耽误我上课,每天鸡不叫母亲就起床做饭。等我吃完饭后天还不明,她担心我一个人不敢行走,就提了马灯送我爬上高高的山巅,直至天亮。有时怕我迟到,她担心的一夜都睡不好觉。恢复高考那年,我参加应试被延安农校录取,学习畜牧兽医专业。由于我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便产生了不想上学的念头。母亲察觉后,耐心地开导教育我,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曾医也是一门技术,山里缺医少药,只要学会这门技术是不愁派不上用场的,再不要这山望见那山高”。在母亲的开导下,我终于下定决心,上了延安农校,圆满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任务,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上学那阵,家中经济十分拮据,母亲在花钱上特别仔细,不允许子女乱花一分钱。但是对我学习上的花钱,却放得比较宽,从不吝啬。尤其是我上中专时,学校花费比较大,每次当我写信向家里要钱时,母亲总是东拼西凑,按时给我寄来。当我捧着母亲寄来的钱和信时,仿佛又看到了她老人家辛勤劳作的身影,禁不住心旌颤动,热泪涟涟。
我参加工作后,有了妻室儿女,可母亲对我的工作、生活仍不放心,仍把我当作小孩子来呵护。每次回家临行前,母亲总要把我送上大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注意身体,努力工作,做一个正正派派的人。那年夏天,母亲突然来信提出想来延安看看火车。我便按照母亲的意愿把她从老家接到延安。百忙中我抽出时间,陪母亲登宝塔,上清凉,参观王家坪,看火车站。每到一处,母亲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下她是真正见了大世面,死了也不后悔了。在延安,她一连住了四个多月,后来她却怎么也不住了,说她在城里住不惯,提出要回老家。我以为这是她的本意,只好将她送回家。从老家归来,我才听爱人讲起,母亲当时觉得身体不舒服,怕老溘在延安给我添麻烦。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母亲要回老家的真正原因。
母亲由于辛劳过度,一辈子疾病缠身。今年又苍老了许多,加之近年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过敏性肠炎等疾病,使她的行动更加不便。春节前夕,她一病不起,生命垂危。我得知情况后,专程从延安请了最好的的医生匆匆赶回老家去救治。总算命大,母亲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临行前,我想再次领她到延安居住,她说她住不惯城里,让我好好把公家的事干好,再不要牵挂她了。
在乡下老家过罢年有好几个年头了。今年,因母亲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和爱人、儿子商量,无论怎么忙也要回家陪母亲过年。
从市里到县城再到镇上,一路上冰雪已经融化,行走方便;而镇上至老家一带积雪仍未清除,行走极为困难。回到家中后,我生气地问当支书的大哥为什么不铲雪?大哥很难为情地说:“没有强壮劳力,不好组织。”是呀!我怎能埋怨大哥呢?近年来,偏远山村不少强壮劳力,尤其是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有的甚至举家搬到了县城、市里去住,农村人口急剧下降,遇到公益性的事和婚丧嫁娶,连相互帮忙的人都找不下。
在镇上和老家之间有一座名山,称三郎山。这座山,山势较高,山巅上长满了茂密的柏树。在方圆百十里馒头似的光秃秃的荒山当中,突兀出这样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峦,很是奇特。小时候,我常常站在老家的山巅,遥望这座山峦,十分好奇和向往。便常常想走近它,亲身感受一下它其中的奥妙。然而一直未能如愿。这次回家路过此地,趁天色尚早,遂绕道前往观赏。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巅,瞭望老家时,因四周树冠遮挡,什么也看不见。山巅中央还有几间庙宇,从庙宇内外现状和前些年维修的碑记判断,建庙已有很长年代了。香火虽比不上那些名家庙宇,然而在这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香火还是不断的。多年来,父老乡亲们那颗颗祈盼天遂人愿的虔诚心灵,依然没变。
为了急于看到家乡熟悉的山峦,在儿子的引领下,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绕过山巅,避开树冠,站在山巅一侧仔细端祥。终因距离较远,加之积雪和阳光相互反射,影响了视线,怎么也辨别不清。在下山的路上,碰见了49岁的守庙人张生前。问他山上的柏树树龄多长?庙宇是什么朝代修建的?“不知道!”他摇摇头说,“就连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不清楚”。末了,便模棱两可地甩了一句:“反正历史已经很久远了”。
年卅上午,我和大哥、儿子、侄儿等一起踏着积雪给已故的父亲上坟。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我父亲已经去世14年了。但父亲的音容仿佛还在眼前,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清晰。如今,父亲的坟头已长满了枯草,坟的周围前些年栽下的柏树、松树大部分已经成活。我在父亲坟前献祭、上香、烧纸、叩头,默默地祝福他老人家九泉之下幸福安宁。

贾平凹书画作品
我大姐家住在高新庄村。这个村子是我们行政村所在地,距我们高家峁自然村只有5华里。小时候,我家姊妹多,父亲残疾,母亲多病,生活很是困苦。大姐家人口少一些,在当时来讲,光景相对好一些。为此,我多半是在姐姐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成长进步,大姐和姐夫给过不少关爱和帮助,这在我一生当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再加上我曾在高新庄小学上过学,高中毕业回到村上后,在那里的代帽初中教过一年半书,对高新庄很有感情。每次回家,我总要到那里走一走。这次回家,自然也不例外。从父亲坟上下来,便转身向高新庄村赶去。当年年轻、英俊、干净卫生的姐姐、姐夫已年过六旬,儿女们也长大成家,都南下延安去住了,而他们老俩口却怎么也撂不下这穷山沟沟,依然住在自家村上。眼下,姐夫满脸污垢,穿着邋遢,苍老了许多,见了人自觉地躲在一边,一言不发;大姐也老态龙钟,加之得了糠尿病,面容浮肿,手脚溃烂。看到他们的模样,我很是伤心。便一再劝他们到城里去住,特别嘱咐大姐很快到大医院去诊治一下。而大姐却苦笑着说:“没事,没事!”我知道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只好好说歹说丢下2000元钱,掩面而去。
年卅晚上,我特意让大嫂给我做了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猪肉绘洋芋、粉条和小米捞饭,吃起来是那样的香美可口,好像又回到了孩提时代。晚八点,央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如期播出,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的耍牌,有的看电视,有的聊天,其乐融融。深夜零点,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后,年长的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又长了一岁!”孩子们却沉浸在欢乐喜悦的气氛之中,至于年龄问题对他们来讲,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头脑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概念。在儿子的提议下,我们走出院子燃放烟花。山村的夜晚异常宁静,天上的星星繁密而明亮,大地一片漆黑。束束礼花在深邃的苍穹中不断爆炸,绘成各种美丽的图案,映的半空一片通明,打破了山村宁静的夜晚。
为使我们在老家短暂的逗留住的舒适,大嫂精心打扫了房窑,准备了被褥,并且将土炕烧了又烧,生怕我们受冻。夜里,我和妻子与母亲睡在一起。母亲过年已达85岁高龄了,身子虽然不怎么硬朗,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头脑还较为清楚。她一觉醒来,却再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坐起,一会儿躺下,一会儿不知胡乱地翻着什么,一会儿又唠唠叨叨,尽给我们说些宽心和祝福的话,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照管好,不要担心她。我无言以对。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下面烫的要命,上面却阴森刺骨,很不舒服。不知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记得2008年的中秋节。与往年一样,我照例赶回乡下老家探望老母。
说来倒也顺利。因故乡通了柏油路,从延安驱车动身,三个小时就到家了。令人高兴的是,今年雨水较好,基本没有受旱,视野所及,满目苍翠。前些年实施的退耕还林栽下的树、种下的草,大部分已经成活、长大,几乎覆盖了裸露的地块,包括过去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我的老家村子附近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也都焕然一新,一片翠绿;羊子也全部圈养起来,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山野里的玉米、洋芋、糜谷、豆子长势喜人,绿油油的一片,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景。进了村子,已达中午1时。本来就人口不多的村里,十几位男女老少的村民正围坐在我家硷畔上,他们一方面为的是聚在一起拉拉家常,凑凑热闹。母亲也在等待着我的回来。
没见母亲又有好几个月了。我问母亲:“身体怎样,有没有病?”母亲有气无力地说:“还算可以!”坐在一旁的大嫂接着说:“母亲近来身体越发没有先前硬朗了,时不时感冒、闹肚子,全凭村里赤脚医生二娃打滴治疗,才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仔细端详着母亲,她的身子更加清瘦了,头发愈发花白、稀疏;许是乡下太阳光强烈,母亲脸色晒的黝黑,思维也变得不如从前,显得有些呆滞,而且走路也大不如过去了,拄着拐仗,颤颤巍巍,需要人扶才行。看到母亲这个模样,我无限惆怅。父母一生共养育了我们七个儿女,四男三女,可以说费尽了心血和劳苦,母亲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父亲在十几年前已经先走了,撂下了母亲。按理说我们7个儿女一定能够照顾好母亲的,但前些年,我们姊妹6人都到了延安谋生,只有大哥在乡下老家守望着那份家产和田地。为了报答母亲,让她老人家能够享受天伦之乐,我曾将母亲接到延安居住,还特意安排让母亲坐了一趟飞机和火车。母亲自然很是高兴。但是随着她老人家年岁的增加,愈发愈怀念老家,怎么也不想在城里居住。再加之我的工作变动,和妻一道离开了延安,到保安工作。无奈,只好将母亲送回了老家,由大哥代我们姊妹6人尽孝。大哥的儿女们也到了延安,家中只留下他们两口子,既要生产,又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喂吃喂喝,端屎送尿,寻医看病,悉心照顾,其操劳和负担不言而喻。我和爱妻商量,几次提出想把母亲接到延安或保安居住,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可一次一次都被大哥和大嫂拒绝了。原因有二:一是怕加重我的工作和生活负担,不想拖累我;二是怕母亲老在外面,以后不好回家安葬。我只好作罢。
按照原来的打算,当日我要离开老家,赶往山西吕梁寻访民国18年卖到黄河东岸吕梁山区且早已去逝的我的可怜的二姑。然而看到母亲的模样,看到我亲爱的大哥、大嫂和先期回来的我的大姐,以及那些热情纯朴的乡亲们,我便打消了心中的念头,在家留宿一夜。不知不觉,天已向晚。刚刚吃了午饭,大嫂和大姐又忙活着做起了晚饭。那全是我小时候爱吃的东西:蒸洋芋、洋芋擦擦、煮玉米、熬豆角、炖羊肉。我吃了一样又一样,每一样都是那么可口、香美,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
大哥担任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眼下,县上正安排乡村搞人畜饮水工程。他领着村民忙前跑后,分卸分送着由三轮车从60多公里外的县城拉回的水泥套圈。那套圈是非常沉重的,一辆大型三轮车顶多能拉20多件,卸起来难度较大。为了安全起见,大哥明确了各方的责任,还与卸货的村民签订了安全协议。晚上,我想和大哥拉拉家常,可他仍闲不下来,不断地给几个村民小组长打电话,要求他们抓紧卸完货后,连夜赶到虎头峁村开会,商量饮水工程实施问题。不一会儿,他便拿着手电,摸着黑,匆匆离开了家。
夜里,我和妻子一同睡在母亲的炕头。我尽可能地和母亲多说几句话,拉拉家常。可是,劳累了一天的爱妻早已睡着了,随后母亲也渐渐地打起了鼾声。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我的孩提时代,想着故乡的山山峁峁,想着入土为安的父亲和早些时候逝去的纯朴憨厚的乡亲们,想着远在延安的儿子和亲人们,想着他们忙碌而短暂的一生……大脑异常纷乱和昏闷,愈睡愈难入眠,只好再服药安定。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太阳升起了好几杆子高。我洗了脸,刷了牙,顾不得吃饭,就叫了侄儿和外甥与我一起给我的父亲上坟。父亲坟头周围林草茂密。我知道,躺在坟茔下的父亲早与大地融为了一体,一股凄凉悲怆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我在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不停地给他老人家上香、烧纸,献上我给他带的苹果、红枣、月饼、肉食,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和爱戴之情……
终于要走了。母亲不顾众人劝说,挣扎着从炕头上下来,柱着拐仗,颤颤巍巍地走出院子,来到硷畔上照样送我。我回过头,也照样说一声:“妈,我走了!”可是母亲并不言语,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我明白,此时的母亲极度伤心,她害怕和担心日后再见不上我。望着秋风中站立着的我那瘦小而弱不禁风的母亲,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野。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母亲已去世一周年了,元旦前夕,我回乡下老家给母亲举办祭奠活动。
为少惹麻烦,事先很是保密,并且一再给大哥、侄儿、外甥们交待,一定要从简从快。这也是母亲生前多次嘱咐的。
可是,当我风尘仆仆赶回老家时,硷畔上早已站满了黑压压的人。当然,绝大多数是亲属和村里的人,也有少许外村人和延安等地来的人。走回院子,窑里窑外忙得不亦乐乎。烧水的,备菜的,做饭的,乱作一团。
还没等我坐定,村里和外村几个人就围了上来。依旧和过去一样,安排子女的,调动工作的,需要升迁的,打官司的……就你一言我一语给我说起情来。我不停地应付着。他(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叙述着,生怕我听不懂、记不清、记不住。
说情人当中,有一位身材高大、衣着陈旧、满脸污垢、面容苍老的人,显得很是激动。他不时地打断别人的话,争着要和我说话。见别人不答应,他便大喊大叫起来,就说他与我是小学和初中同学,从小患难与共,当年曾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末了,又说:“别看他官当的多大,我才不怕他哩!你们信不信,我就敢扯他的脖领子,你们敢吗?”还没等我反映过来,他就一把扯住我的领口,使劲地前后摇了几下。
我这才看清楚,他真的是我当年的老同学,小名叫眼明,大名称郭鼎才,我们曾在小学、初中一起念过书。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比我大4岁,十五、六岁时,个子就长得很高,足有一米七、八。他爷爷郭志忠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懂些书文,礼贤下士,在方圆几十里是有名的说理之人。再加上家里光景殷实,尤其是一大家子十多口人同家生活,很是受到外人的羡慕和尊重。眼明是他爷爷郭志忠的长孙,所以在家里的地位很高。他的爷爷和父亲早早就将他送进了学校。然而,不知为什么,老师讲的眼明一点都记不下,学习一塌糊涂,就连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常常受到老师的惩罚。再加之眼明性情善良,嘴舌笨拙,也往往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辱。可是,我与他关系一直较好,所以,眼明常常给我吃干粮,我也常常帮助他写作业。考入初中后,我和眼明一起又度过了两年半的初中学习生涯。在新的学校,眼明和我同样忍饥挨饿,受尽了人间疾苦。由于眼明个头大、饭量重,更是吃不饱饭。有一次竟然饿昏在教室里。那墙倒似的栽倒在地的情景,至今都历历在目,令人心酸。可就这,眼明都没有忘记帮助我。后来,我初中毕业升上了高中,而眼明名落孙山,回家务农。之后,几十年很少谋面。没想到,眼下的眼明竟变成了这般模样。
就在我沉浸于对往日友情回忆的时候,眼明一把将我从人堆中拉出,拉到一个避静处,语无伦次地给我诉说了这些年来他和家人的遭遇,并一再请求我给乡上和县上说说,让给他办个低保。末了,便将两块饷洋塞给我。我一下子傻了眼,怎么都不要,我就让他变卖些钱,以弥补家庭的生活不足。眼明急了,竟然流下了眼泪,说:“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现在这东西也不值几个钱,我留下没用,还是送给你儿子作个纪念吧。我又不是行贿,如果你不收,就是小看我鼎才!”见我还是不收,他只好硬塞在我儿子的手中。
面对我的老同学眼明,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央求担任村支部书记的我的大哥和乡上、县上的同志,今后多多照顾他。
儿子、侄儿、外甥们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家中的事情再也不要我过多的忙碌、操心,他们将一切都商量、安排和办理得井井有条,我很是高兴。
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自有后来人”,的确年龄不饶人。夜里,晚辈们又放起花炮来,并且非要拉我到硷畔上观看,多么美好的夜色呀,天空深邃,星星稠密而闪烁,大地一片漆黑,格外静寂。这么美好的夜色,只有在乡下才能够看到。几百束花炮在窑背上“咚咚咚”地响了起来,火焰窜上脑畔,直刺苍穹,然后在半空爆炸,形成各种五彩缤纷的图案,将天地映得一片通红。呐喊声、欢呼声、花炮声融为一体,响彻山谷。我像小孩子似的,站在人群中,和大伙儿一起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刻。
第二天,一家人早早起床,吃了早饭,便一起给父亲和母亲上坟,献祭献花,烧纸叩头。二老的坟墓前跪下黑压压的一片人,送上亲朋们的哀思。这里边也有我。

黎明喊我起床 贾平凹
堂哥玉亮才刚过60岁。他一辈子争强好胜,吃苦耐劳,光景过得很是富裕。没想到,两年前突然患了脑梗,久治不愈,后来便发展成偏瘫,不能言语。可怜的他前几天竟然撒手而去。办完母亲的祭奠后,我便携妻和儿子、侄儿、外甥们及时赶到八、九华里外的祁家土焉村,送上我们的慰藉,寄托我们的哀思。当我打开装殓着玉亮哥的棺椁时,玉亮哥穿着崭新的衣服,身上盖着红被面,头上戴着蓝帽子,满脸的大胡子已剔刮得干干净净,双目紧闭,微张的嘴巴噙着银圆,只是脸颊有些消瘦,看上去十分安祥,像熟睡一般,一点儿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似乎比生前英俊了许多。我紧紧地盯着他熟睡的面容,久久不愿合上棺盖。
死了好,死了再也不要受罪了。最起码对玉亮哥是这样。我不知是怎样离开玉亮哥家的,一边喃喃地说,一边又跌跌撞撞来到我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妈,三伯、三妈和玉明哥的坟前,给他们一一烧了纸,献了祭,叩了头,这才算返回生我养我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山村——高家峁。
母亲,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就要来到了。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您老人家,想起了您慈祥的面容,想起了您瘦弱的身影,想起了您絮絮叨叨的神态……我多么想急切地来到您的床前,再给您递上一碗热烫烫的饭菜,问问您的病痛,陪陪您拉拉家常,听听您亲切的教导……可是,当我下意识地跑回家中后,屋子里空荡荡、静悄悄的,再也看不到您的面容,听不到您的声音。我忽然明白,您老人家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且离开整整100天了。现在,我们母子已是阴阳两隔,今生今世再也不能重逢了,孝敬您老人家只能是一种痴想,这是多么残酷的人生轨迹和现实生活呀!
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清明是祭奠亡灵的时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尽管我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我还是抽出时间,与妻儿一起回到家乡,来到您和父亲并葬的墓地,给您们二老上香、烧纸、叩头、添土,并且深情地问一声:“母亲,您现在还好吗?”
2008年农历11月24日,对您的儿女和亲人来讲,是一个灰色的日子。这天凌晨2时10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熟睡中的我和妻子惊醒。深更半夜来电话,十有八九是不祥之兆!要么是工作方面有什么紧事,要么是家中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我急切地拿起电话,里边传来了远在子长乡下老家的四弟低沉而沙哑的声音。他告诉我,母亲于今日凌晨2时零4分去世了,要我节哀!
放下电话,我很是悲伤,心早已乱了,一时竟茫然不知所措;坐在一旁的妻子,也已泪流满面。尽管这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事情,尽管母亲年事已高,但是作为儿女的我们,依然舍不得她老人家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人世。
我和妻子半倚半躺在床头上,默默相对无言,急切地等待着天亮,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母亲这些年来的生活状况来。
81岁的父亲于1994年农历2月4日去世时,母亲已经71岁。父亲去世后,一生多病的母亲一直在乡下老家,与大哥、四弟共同生活。后来,我觉得乡下条件较差,不利于母亲的健康,于是便和妻子商量,曾几次接母亲来延安居住。但每次住上一段后,母亲怎么也住不惯,人在延安,心却早已飞回了老家!她担心远在乡下的大哥、四弟光景过的如何?与邻里关系处的怎样?天年好不好?几个心爱的孙子是否茁壮成长?并时不时嚷着要回家。无奈,我和妻子只得几次将她送回老家。可是在老家住上没几天,母亲又思念和担心起我们来了。最使她放心不下的是,我在工作中会不会跟人家闹矛盾,有没有人在陷害我?多病的妻子的身体还好吗?她的爱孙、我唯一的儿子婚姻大事定了没有……她不停地嘟囔着让我的大哥、四弟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母亲呀,您老人家一生从来不考虑自己,总是把儿女们的事情放在心上,担心了这个,又怕伤了那个;在您老人家的心目中,子孙们的地位至高无上,而且是那么神圣,永远不可侵犯。
随着母亲年事的不断增高,前些年,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又将母亲接来延安居住。期间,无论她怎么唠叨,我就是不答应她回乡下老家!母亲感觉到我已经铁了心,从此再很少嚷着要回家。为更好地侍候母亲,我和妻子特意雇了一个保姆,昼夜不离她老人家,给她做饭、洗衣、吃药,陪她拉话。妻子时不时将牛奶、面包、肉食、水果等送给她食用,并且一有病,就找来大夫去诊治,有好几次还送到了医院治疗。母亲几次生命垂危,我们已做好了后事准备。但刚强的她老人家,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挣脱回来,渐渐康复出院。对此,我们是多么地高兴呀!
母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那种小脚女人,但她的思想较为开化,对新生事物很感兴趣。于是妻子和儿子就买了《陕北道清》、《陕北说书》、《情深深,雨朦朦》、《兰花花》、《走西口》,以及小品《东北二人台》、《赵满屯》等一些影视碟片,播放给她听、给她看。她听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一次又一次,似乎永远听不够,永远看不够,而且思想情绪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常常为剧情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黯然伤心。就这样,母亲最后一次与我们在延安一住就是三年。中途,为了让母亲感受一下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和妻子特意在延安买了飞机票,陪母亲和大姐、二姐、小妹坐飞机到了西安,住进了钟楼饭店;第二天又逛了大街和商场,与她老人家在钟楼合影留念;下午又买了火车票,当晚乘火车返回了延安。一路上,我的大姐、二姐既晕飞机又晕火车,呕吐不止,萎靡不振;而母亲却一点儿都不晕,而且面带笑容,精神矍铄,问这问那,时时沉浸在无比幸福喜悦之中。之后,她多次给家人和邻居讲,她既坐了飞机,又乘了火车,而且还看了省城西安,真正是见了大世面。而作为儿女的我们,也如愿以偿,总算对母亲尽了一点孝心,心中感到一丝的快慰。
2006年仲夏,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动,由宝塔区调往志丹县工作。就在我赴任的前夕,母亲怎么也不住了,急着嚷着要回老家。她说我到县上工作,生活一定不便,肯定会有诸多困难,要求妻子一同前往侍候我。就这样,看到母亲态度坚决,同时也考虑到她老人家说的多少有些道理,我便和妻子又将母亲送回了老家,便愉快地投身到新的工作岗位。
母亲在乡下老家一住又是两年。期间,每逢过年和重大节日,我和妻子老是放心不下母亲,总要抽出时间回家探望。夜晚,我和妻子与母亲睡在一起,听着她老人家唠唠叨叨的叙说,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半夜后母亲打起了鼾声。可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不由地想起了童年,想起了过去在乡下的生活,想起了年少时母亲给过我的爱……第二天早饭后,我们要走了,母亲摇晃着身子,慢慢地从炕上溜了下来,柱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出家门,走出院子,走到硷畔上,走到大路口,像当年送我去外地上学一样目送我远离。看到苍老瘦小、风烛残年的母亲,我的心一阵阵痛楚。然而却毫无办法!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血肉之驱的我岂能加以改变?
去年国庆节前夕,考虑到亲人们都已前往延安居住,年迈的母亲只有靠在乡下老家50多岁的大哥和大嫂侍候。他们既要劳动又要侍候母亲,负担很是繁重。为了减轻大哥和大嫂的负担,尽尽做儿子的最后一点孝心,我和妻子商量,干脆将母亲接到志丹县城居住。来到县上的前30天,由于住宿条件较好,饭菜营养丰富,母亲的体重增加了,肤色变白了,身体硬朗了,走起路来也不需要人搀扶了。我心里暗暗高兴,就想,母亲再活几年是不成问题的,便打算陪母亲在县上好好过个年,让她老人家健康长寿,享受天伦之乐。可是万万没有料到,一月后,母亲旧病复发,精神萎靡,寡言少语,饭量大减,行走十分困难,有时靠人搀扶都站不起来。妻子先后两次将母亲送进医院医治,但效果不佳。母亲一生多病,尤其到了晚年,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时时折磨着她老人家。经过医生的认真诊断,这次犯病,除了上述疾病有增无减外,要命的是脑干部分出现了严重的梗塞。医生建议,这么大的年龄,这么严重的疾病,靠药物彻底治好是不现实的;如果用手术治疗,难度却很大,效果也不是十分理想。当时,我正在省城西安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妻子打来电话告诉我,母亲拒绝治疗,而且一个劲地嚷着要回老家;医生也建议,回家静养比较妥当。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便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让妻子多带些药品,立即送母亲回老家一边静养,一边治疗。
省上会议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返回老家看望母亲。此时的母亲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已经不会说话了,而且水米不进。我坐在她的身旁,给她饮水、擦汗,想为她最后送终。可是她老人家的病情时好时坏,反复无常。等了两天后,由于县上工作较忙,我只好决定离开她老人家返回县上。此时的母亲虽然不会言语,但有时还能听懂我们的一些话语。当她听到我要离开老家返回县上的时候,两眼死死地盯着我,竟然流下了泪水。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我只好哄骗她老人家说我不走,然后掩面忍痛离开了她,由哥嫂、二姐、小妹等代我尽孝。就这样母亲又苦撑了20天,这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我和妻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匆匆赶回了老家。而母亲早已躺在了冰冷的脚地上,身下铺着干草,身上穿上了老衣,脸上盖着一张白麻纸。我默默地走上前去,跪倒在她老人家面前,给她上了香、烧了纸、叩了头,然后轻轻地揭开盖在她脸上的麻纸,母亲的面容竟是那样的安祥、好看,仿佛熟睡一般。一股悲怆之情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但是无论如何怎么也封锁不住母亲去世的消息。几天来,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我曾经工作过单位的同事及朋友们,纷纷前来吊唁。我知道,这既是对我敬爱的母亲的深切悼念,也是对我们做儿女的最大安慰。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出殡的那一天,我们早早起来,将灵棚拆卸干净,收拾完花圈,将母亲送到了墓地,下葬到早已准备好的墓穴里。我和大哥不顾一切地跳下墓坑,把墓穴打扫的干干净净,将母亲的遗像摆放端正。此时此刻,我突然明白,母亲和我们永别了。我紧紧地盯着她老人家的遗容,足足看了几分钟,久久不愿离去。
无情的黄土将母亲深深地掩埋了。从此,我们母子阴阳相隔,永远不能相见。我在母亲坟前长跪不起,把对她老人家的无尽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在这清明佳节到来之际,让我深深地向您再鞠一躬,并且再道上一句:“母亲,您现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