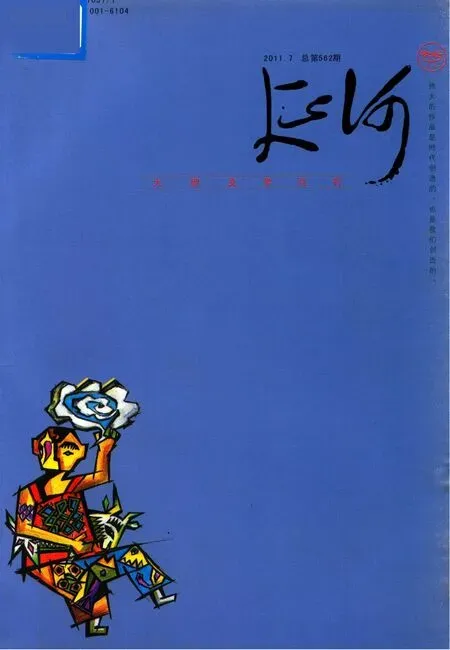一个作家的证词——略 萨
时间:2011年6月14日上午
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
主办方:上海外国语大学
合作组织: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上海99网上书城
尊敬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先生,尊敬的老师们,非常尊敬的易玛•冈萨雷斯女士,各位外交官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我首先想讲的话,当然是感谢上外能够有这样的热情来接待我,能够给我顾问教授这样的名义。当然,我希望能尽力,对得起这份尊重。在这里,我要向老师、院长以及我的各位同事表达感谢之词。
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到一所培养老师和未来笔译、口译以及专业人员的学校,这对一位西班牙作家来说,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这里所用的西班牙语,就是我写作的语言。而且,西班牙语国家的人是非常以这种语言为自豪的。它不但是能在五个大洲进行传播的语言,而且是全世界5亿人正在讲的语言。西班牙语就像一个传播器一样,传播了现代、现代化,而且传播传统非常悠久的文学、文化。在上百个作家中,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以西班牙语进行创作的作家的故事,使得我们当代文学更加丰富。通过(这种)文化、文学(的传播),使得读者能面对现实的残酷以及梦想。在今天的讲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中一位作家的故事。
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城市了,后来搬到玻利维亚去,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非常棒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方式。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在时空进行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惊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阅读,这些冒险的故事,我可能不记得了,不过,可能是天生的对文学的爱好吧,我看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对文学的爱好、天赋体现得这样早,可能是因为我还是很早熟的吧。我记得,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给人感觉像阳光前来照亮了我的青年、少年时代。阅读对我来说,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生活,使得我产生一些想法,(设想着)能够成为一个作家。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吃饭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只是在一些节假日、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比较自由的职业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工作时间之外,他留出一些时间进行写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新闻专业。但我的天赋给我的这种爱好,是文学。所以我做了不少工作,从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当时我只是利用空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他们中的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我也不例外。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等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卓越的事,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这种完美的境界,这种纯洁、连贯。
50年代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一个戏剧《一个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但在当时的秘鲁,戏剧表现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就改而写一些故事、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统一的,分割的,特别是从文化角度来讲,在秘鲁我们不知道在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诗人或者小说家、戏剧家,有些什么创作。我们所读的,都是从欧洲过去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自己还是秘鲁人,是哥伦比亚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集体。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感觉是艺术、文学的殿堂。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学天赋、有艺术才能的人,都有那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生活。因为在那里能够变成艺术家,变成作家。
大学完成后我有幸在西班牙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住了7年。这7年对我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我欠了巴黎很多东西。但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秘鲁只是一个省,拉丁美洲社区一个非常大的省。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都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过。在那个时代,那里住过阿根廷的胡里奥•阿里特萨,还有卡彭铁尔、聂鲁达等。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个拉丁美洲作家了。我发现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化上的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同时,在那些年里,有很多的小说进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术、叙述的方式都发生了革新。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军官在学校的经历。
很久以后我发现,我从那时开始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的不同。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一个你想象中的过程,但对我来说,写作一直都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的。你有一些经历、有一些记忆,可能有些东西还是很神秘的,能激起我的想象、幻想,给我一些暗示、想法。有些影像、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情感丰富。我在军官学校待了两年。秘鲁是一个分割得很厉害的国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区、热带雨林地区,分割得非常清晰。另外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区非常繁荣,但更大一部分是和西方化的秘鲁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个时候(整个)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像秘鲁一样非常分割化。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最初的时候)我对秘鲁的印象是非常片面的。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个国家里发生的很多事。我小的时候在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呆过,当时(那所学校)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包括了各个阶层。有比较优越阶层的,让很反叛的孩子去受军训,希望他们成为军人。还有一些是农民。当时奖学金比较广,能使比较贫困的人进入这个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型的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不管你对它)有偏见也好,有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并不是很好的回忆,并不开心,但给我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秘鲁社会的暴力情况、分割情况。对我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那里的生活)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我在那里就梦想着哪天我写一部小说,利用我那种经历。所以《城市与狗》就是根据在那里的真实经历写成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可能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有的影像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对我来说,有些神秘的影像能够激励我来做这些文学的创作,进行幻想、想象。当然,还要通过很多的工作——修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成形了。
其实,我写小说还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开头部分,每次都要(重新努力),努力使我自己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非常敬佩一些作家,不光他们的天才、他们独特的创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但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记录了一天天发生的事情,在福楼拜每天写的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使人感觉到通过书信可以了解他如何构建他的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天才的作家。他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建造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执着的,而且是自我批判的。通过这种努力,一部作品刚开始可能非常贫乏,没有什么色彩,但你逐渐将它完善,直到成为一部杰作,天才之作。福楼拜的(这些书信)作品对我非常重要,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中了解到),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天才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对我来说,福楼拜(确认过)的这一点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大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还有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威廉•福克纳,就是他,把我迷住了。他的散文、故事的影响面、力量感,他的作品的聪明的建构,那是能让人感知到它的真实性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热带雨林,去亚马逊河印第安人部落,在那里旅行了几个星期。那儿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面孔,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还在石器时代,只有很少的现代化的特征。但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棒。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我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之后,《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那个经历相关的。和《城市与狗》非常客观的情景不一样,《绿房子》都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一个一个(层级式的)厚度。有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还讲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包括北部沙漠地区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让人感受到秘鲁),了解(它的)多样性、复杂性,秘鲁这个国家非常多样的分割化。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的所有小说中最花我工夫的。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所以这8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到那个学校去,也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后三年。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大学中有抵抗的运动,有些地下的组织。因河拉不拉党(音译)是中左派的一个党,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做那些事)。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古宅大院图 贾平凹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奥德利亚,安全局的局长。我就认识他几分钟。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的看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做的一个秘密报纸,他说,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拿着报纸,给我看。有这么多人在他手里被捕了。他给人感觉非常可怕,也感觉到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我想哪一天要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利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他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一些小的故事。但怎么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我选择了)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它能引出一个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变成了复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
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很多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前三部小说一样,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作。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那里几个小时的书房写作。逐渐的,你把它包裹起来,哪怕几个小时写作之外你都把自己卷进去了。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整个故事开始成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草稿出来。草稿出来,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只是比较混乱罢了。但我确定,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开始令人愉快了,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是再次写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写。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努力,比起你所要达到的目标,(已有成果)总是处在(目标刻度线)下方。但你要意识到,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再写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补充什么东西了,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改变它的时候,不能让它太频繁。我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要下降了(就赶紧收手)。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写两年、三年,(当它)已经和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完全联系起来,你要和它分割开就是非常难的。所以一本小说写完的时候,你会怀念,你生活的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小说结束,为了让真空的感觉消失,我会马上进行创作。在做最后的修改时,我已经在想下一部作品了。
为什么你会有些生活的经历成为动力?成为非常强的动力来写作?其他的经历,就没有这样的激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谈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很迷惑。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都有中心的思想,有些可能是对你人生产生创伤的东西。你无意识的藏在内心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写一些东西,因为我发生过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蓄意的去找一个经历,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我的故事。从来没有。有些事情在我生活中发生过了,产生了这种进程,不能抗拒的动力促使我去写。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比如,我从来没想过要写不是发生在秘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有民族情结,只能写自己国家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秘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年轻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这种取向)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要在我的故事中出现。有一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棒的书,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想了解拉丁美洲的人都该看看这本书,是巴西作家达•库尼亚的纪实文学《腹地》,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写的是巴西东北部20世纪卡奴杜斯内战。当时的历史背景非常令人惊喜。没有什么暴力,就变成共和制了。君主制已经不能再流行下去了。人们有这种情节,爱祖国,相信新的制度会带来公正,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的这样的改变。东北部地区一些农民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但是怎么可能呢?这个共和国建立就是为了穷人谋福利的。国家派了一个连去镇压,但是失败了。巴西这时感觉很不安了。政府不知道为什么穷人会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理论:并不是穷人开始反对共和国,而是阿根廷在葡萄牙流亡的君主派的人在引导,他们到东北部,引起叛乱。因为原先英国和巴西在君主时代很有关系。接着就派过去一个军团镇压叛乱,最后打败了(对方)。共和国的英雄在那里死掉了。这个军队到前线,还写了报告,能把真实的事件搞混乱。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讲到蓝眼睛的农民,就说是英国人假扮的。幻觉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掺和到一起。叛乱最后以很多农民死亡而结束。达•库尼亚讲到,我们做了什么?他告诉大家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变成了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是非常狂热的,两个世界互不相容,更不能互相理解,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这让我非常惊异,了解到什么是拉丁美洲,什么不是拉丁美洲。突然之间,我觉得要写一部小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写不了解的国家,没有去过的国家,而且是历史的史实中的事件。这个国家讲的语言并不是我所写的语言。但我有一种必须要去做的感觉,我急着去写了另外一部小说,就是《世界末日之战》,是幻想的。达•库尼亚已经变成了主人公,他在书中是随军记者。我也写到拉丁美洲一个标志性的元帅,31年,他通过铁腕统治国家。1974年我到巴西去工作了8个月,我听了很多有关土米西列(音译)的故事,而且好像是不真实的故事——他的残酷、他的腐败——给人感觉他好像一个小丑一样,把整个国家完全变成一出闹剧。我需要把他讲出来。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戏剧性的。总统府里做的事情,都是戏剧。这些事情,我感觉到必须写一部小说。有很多我听到的轶事,我将之写入了《公羊的节日》,一个有关独裁者的故事。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我不了解的另外两个国家:刚果和爱尔兰。也是阅读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有个人物约瑟夫•康拉德(音译),也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写的是冒险家的故事。我几年前看了他的传记。他到刚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尔兰人,(那人)在那里已经住了8年,带他大开了眼界。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刚果人)就像欧洲人一样,有商业,有现代化,这些在殖民地(诱发了)很热情的想法,认为殖民是好事。罗杰•凯斯曼,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在刚果的橡胶园里。欧洲人在那个世界完全无法无天。康拉德的小说我读了很多次,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也曾经到亚马逊哥伦比亚、秘鲁研究过,他控诉的,最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橡胶园做的一些暴行。因为他20年的努力,在欧洲乃至整个全世界都掀起一个潮流,就是开始控诉殖民主义对橡胶园的这种暴行。我开始对他进行研究。我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并不是光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他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并不是在秘鲁发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今天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我的这些经历。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进入世界),你发现了一个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东西使你能让他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复活,让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给人感觉像是传奇。(经过)这么大的努力后,你得到你的回报。这就是写作给我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讲福楼拜的一句话。他在书信集里讲到: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计算机,或者用电脑写作。而是根据你的写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节奏。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封闭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内。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我希望)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续性、连续性,仅只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社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道德方面的力量(这样要求的)。你对城市情况有兴趣,对国家情状有兴趣,你就应该发出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你作为一个作家,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个人,但可以给语言或者政治贡献出更大的精确性、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往往会)使得事实混淆了。这个时候,作家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的工作),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我们(作家)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适当)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这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参与到)整个生活、政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地度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在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了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有很深的痕迹留下。不但能增进对一些事实的经验的了解,还有一些也很重要的,我称之为“后遗症”——在历史上会产生的一些影响。这些后遗症、影响是什么呢?这就是好的文学作品无可回避的一种感觉,它说服一个人逼视他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他想的这样,并不是他想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看过《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再回到现实世界一看,我们的真实世界多小啊!和我们现实的那个世界比起来。(文学)作品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这种痕迹,是一种不满足。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
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培养人才、培养公民来说,我们的学习中,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学科序列)。而且,(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能用很多时间去看诗歌、小说或者戏剧作品,当然,是很享受的,有些情况下幸福感很强烈。(在这方面,文学)也是做出贡献的。你有了这种思想,(就能)让社会流动起来,做出贡献,让社会不断进步。
非常感谢你们的倾听。
相关链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主持人:非常感谢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博士的演讲。您的博学让我们所有人获益匪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您本人以及您的文学创作,请允许我们的学生占用您一点宝贵的时间。接下来,请同学们跟略萨博士互相交流一下。
提问:首先,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演讲。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机会来认识您的个人生活、思想。我是上外的学生。我是学习西班牙语的硕士。我的问题和您的作品有关。您的作品的特点,就是宏大和复杂的结构。您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结构大师。我想知道的是,您构筑和设计这些结构,是因为个人的喜好,还是为了表达和内容组织的需要?谢谢。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如果上外的学生都像你一样,西班牙语讲得这么好,那可太了不起了。每个作品的结构建筑,非常重要,因为形式方式、语言我都非常感兴趣。但所有这些都是为所讲的故事服务的。有些作家喜欢一种形式,他把讲的形式看得比故事重要。但我不是的。我觉得在文学中最难的,就是你很好的把故事讲出来。也就是这个故事能有说服力,我们看到它的时候,不像是我们在看它,而就像我们正身临其境,因为它的这种能量、令人信服的能力、力量,这部作品把你吸收了,给人感觉它就是生活中的。这非常重要。形式也好,技术、组织、结构、时空等,最重要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得我的故事能有说服力。你感觉不是看一个作品,而是你就生活在这个作品中。当然,你要有草稿,你要叙述它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是很混乱的。对发生什么并不清楚。有时候,有些东西你要把它去除,其实这也很重要。打个比方,有些东西我们称之为省略性的叙述,让你有好奇心去了解,这些地方给它留白是很重要的。叙述者也是很重要的,让谁来叙述,还是干脆用旁白。你也许会认为旁白叙事和作者是同一人,但你要明白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有时候人物就是作者的自称,但并不代表他就不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很重要的就是创造叙述者,谁是叙述者。时间和叙述者一样,也是创作出来的。你要在形式上给他感觉出来。我要根据我所讲的故事来服务,给它力量,你要给人感觉不是写出来,而是你自己经历过的。每个故事,叙述者都会换,看你讲的什么故事。比如说,《凯尔特之梦》的梦想,刚果人、爱尔兰人独立的梦想,在这里我们用的是叙述体、编年体。编年体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好像是古代用的,已经不流行了。有很多的故事、片断通过编年体的形式给写出来。我讲的故事,是需要用这种叙述方式的。只有一个情况下,就是《崽子们》这部小说,结构我刚开始就有了,讲的是主人公几岁时生殖器被狗吃掉了,是非常悲伤的故事,然后从他的视觉给他看出来。整个事实能够有一点变化,模糊化,所以我感觉他应该被创出来,应该让大家分散出去注意力。没有时间来拒绝它,拒绝这种现实性、残酷性。用音乐性的语言来让你分散这种注意力。不光是它的内容重要,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发音是什么样也很重要。每个故事,每个情况,讲的形式都不一样,结构都不一样。
提问:我也是上外的学生,我是三年级的。我的问题很简单。最近几年,中国和西语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北京开了塞万提斯学院,在西班牙和秘鲁也开了孔子学院,每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但秘鲁还是很遥远和神秘的国家。我的问题是,您认为我们年轻人应该做什么来加强中国和西语世界的认识和了解?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我们现在是非常棒的时代。
提问:文化交流是必须的。特别是在现在的时候。我今后想成为翻译。您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做什么来促进双方的理解和交流,中国和西班牙语世界的交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我们现在有了交流,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小了,疆界已经开始消失了。科技的革命这么大,使得我们可以瞬间交流,距离感已经消失了。这个确实很好。我们认识更多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这样你呆板的东西、成见就更少了。尽管我们有文化差异,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其实我们的共同点比差异重要得多。所有可以增进文化理解的交流、对话我们都应该去做。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让你了解更多世界的文化。你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了解自己国家文化的方式。如果我们能更了解对方的话,我们文化交流更多,可能暴力会更少,冲突会更少。所以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任务。在你的肩上有这样的任务,加强交流,相互了解。确实这些在中国也在发生。我年轻的时候,认为中国是很遥远的国家,完全要去想象他的。(以前)我们没有机会去向来秘鲁的中国人了解中国。那时的感觉,到中国就像到火星去。因为工业的关系,商业的联系,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到秘鲁来了。中国也逐渐因为商业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工作的原因,和秘鲁走得越来越近了。这样交流起来,桥梁就更多了。很多西班牙语世界的书能翻成中文,而中国的书也能翻成西班牙语。这样的交流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成见、偏见就消失了。因为如果不太了解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些偏见。语言的学习,是非常基本的。了解一个语言后,不光可以作为交流的工具,而且能吸收不同的文化,这是最好的。然后再了解自己的文化。这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非常好了。
主持人:谢谢略萨博士和各位同学。亲爱的朋友们,同学们,女士们、先生们,在今天结束这个活动之际,请允许我引用伟大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文学是人类在现实与梦想之间跨出的一步”。今天这个活动,就是中国和西语世界的语言、文化相互交流跨出的重要一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