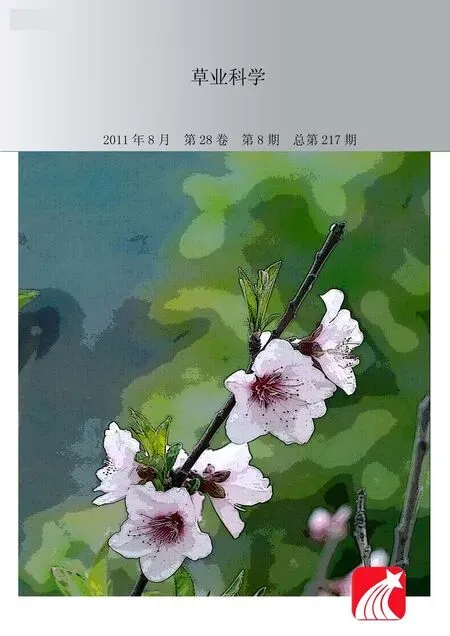祁连山北坡草地生物量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黄德青,于 兰,张耀生,赵新全
(1.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高原生物适应与进化重点实验室,青海 西宁 810001; 2.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化工系, 广西 桂林 541002; 3.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生物量是草地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数量特征,是认识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1],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是草地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重要内容之一[2]。研究草地生物量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有助于了解草地生物量积累过程和揭示环境因素对草地生物量的影响机制,对草地资源管理和合理利用、退化草地的恢复与重建以及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3]。鉴于此,围绕草地生物量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广泛的研究[2-9]。
对于草地生物量的估算,主要通过样地调查、定位观测、遥感反演及模型模拟等途径获得[3,10-12]。其中,以野外实测调查最为常见,虽然野外调查在时间、尺度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性等方面存在众多不足,但遥感和模型模拟估算的可靠性程度,需要实测数据的验证和支持[11],因此地面大量实测数据对准确估算草地生物量具有重要意义。在环境因子对草地生物量影响的研究方面,一般认为气候因子的影响最为显著[11]。在众多影响植被的气候因子中,以表征热量的温度、表征水分条件的降水以及表征水热组合状况的可能蒸散及干燥度和湿润度来研究的报道较多[13]。
祁连山北坡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带,由于受青藏高原气候和蒙新荒漠气候的双重影响,气候具有明显的垂直梯度和水平差异[14],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植被类型,这里发育的山地草原、山地草甸以及草甸化草原等植被类型是发展草畜产业的基础,不同的草地类型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生态作用。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气候等环境条件的改变,天然草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其生态功能的发挥。因此,不少学者对该区草地资源状况、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及退化草地的资源利用进行了研究[14-16],但有关祁连山北坡天然草地生物量及其与环境因子关系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以2004年祁连山北坡5类天然草地的实测数据和同期的气象资料为依据,初步分析该区草地生物量状况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定量关系。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设在黑河上游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处祁连山北坡中段、河西走廊南侧,位于97°20′~102°13′ E、37°28′~39°49′ N,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本研究以占肃南县草地总面积的63.2%的5类主要的天然草地类型,即高寒草原、山地草甸、山地草甸草原、山地草原和山地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在各草地类型设立相应观测点,各草地类型立地条件的基本概况和群落主要植物分别见表1和表2。

表1 5类草地的基本概况

表2 5类草地的主要植物种组成
2 研究方法
2.1生物量调查 为了揭示气象因子与生物量的关系,试验样地均选择相对开阔和人为干扰相对较少的天然草地群落。于2004年5月(牧草返青)-10月下旬(生长末期),即每月下旬在所选样地内随机设置面积0.25 m×0.25 m的样方5个,3次重复,每次每草地类型共计15个样方。采用收获法(齐地刈割)[17]测定各样方的地上生物量,然后带回室内在80 ℃恒温下烘干称量(精度0.01 g),同时,记录各样方的植物种类和群落盖度(目测法[18]);在收割后的样方内采用挖土块法[19]取样,测深为30 cm的地下生物量,每10 cm一层,样品按层装入布袋中,将带根的土样置于沙网(0.5 mm)中用水冲洗后带回室内,在80 ℃恒温下烘干称量(精度0.01 g)。地下生物量指地面以下0~30 cm全部生物量(包括植物的活根和死根)。
2.2气象因子的测定
2.2.1土壤水分和降水量测定 与生物量同时测定。于2004年5-10月每月下旬测定1次,采用土钻法[18]分层取样。测深为120 cm,各层分别为0~10、10~20、20~40、40~60、60~80、80~100和100~120 cm,共7层,每层重复取样5次,然后带回室内用烘干法(105 ℃)烘干称量,取其平均值为该层的土壤水分含量。土壤含水量的计算公式为:
(1)
降水量采用气象站用常规雨量筒测定。
2.2.2气象要素观测与计算 在5类天然草地定位试验区设立小型自动气象站观测点,按照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要求和试验研究的需要设置。观测要素包括大气温度、土壤温度、相对湿度、气压、太阳辐射、风速等,观测步长为30 min,观测方法是小气候自动观测系统自动记录。提取2004年生长季观测的数据,取其平均值用于数据分析。
干燥度指数(aridity index,AI)采用月潜在蒸散量(ET0,mm)与月降水量(P,mm)之比[20]来计算:
AI=ET0/P。
(2)
潜在蒸散量(ET0, mm/d)选取标准化、统一化后FAO推荐的P-M公式[21]来计算:
(3)
式中,Δ为饱和水汽压曲线对温度的斜率(kPa/℃);Rn为净辐射(MJ/m2·h);G为地热通量(MJ/m2·h);γ为干湿表常数(kPa/℃);T为日平均气温(℃);μs为风速(m/s);es和ea分别为饱和水汽压和实际水汽压。
2.3数据处理 用Excel进行数据的初步处理和作图;用SPSS 17.0统计分析软件对生物量与各气象因子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及显著性检验;潜在蒸散量的计算通过SAS 8.1统计软件进行,在估算过程中,需要进行若干次复杂的各类量纲换算[22]。
3 结果与分析
3.1生物量与植被盖度 祁连山北坡5类草地的生物量如表3所示。不同类型草地的生物量变化在130.3~926.2 g/m2,变异系数为58.2%。其中,山地草甸的生物量最大,为926.2 g/m2,占总量的37.8%,这与该草地类型的拥有丰富的植物种类、较高的植被盖度和密度以及降水量等因素有关;其次是山地草原、山地草甸草原和高寒草原,分别占总量的20.7%、19.4%和16.8%,山地荒漠草原的生物量最小,为130.3 g/m2,仅占总量的5.3%,这与荒漠草原较干旱的气候有关。总体上,祁连山北坡草地生物量为490.4 g/m2,其中地上、地下生物量分别为42.1、448.3 g/m2,地下生物量约为地上生物量的10倍,因此地下生物量对总生物量的贡献远远大于地上生物量。

表3 5类草地的生物量
相关分析表明,5类草地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关(F=120.61,P=0.002<0.01)(图1),二者存在极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即地上生物量较小时,地下生物量积累缓慢,地上生物量增大时,地下生物量呈线性快速增长。植物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呈正相关的普遍结论已在不同区域的不同类型草地中得到证实[1-3]。基于二者的相关性,为准确估算该区草地地下生物量提供了依据。
植被盖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吸收资源面积的范围,植物所能利用的空间最终反映在植物的生产量,即生产力的大小上,植物种群盖度越大,同化面积越大,生产力也就越高[23]。分析表明,5类草地的生物量与植被盖度呈显著的正指数关系(F=23.92,P=0.02<0.05)(图2),随植被盖度的增大,生物量呈指数形式显著增加。这与以往的研究[2,23]是一致的。分析还发现,土壤表层(0~20 cm)的含水量与植被盖度亦呈显著的正指数关系(P=0.012<0.05),而20 cm以下土层土壤含水量与植被盖度的关系不显著,这表明植被盖度与表层土壤含水量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定量关系,即随植被盖度的增大,表层土壤含水量显著增加。这与王根绪等[24]在高寒草地的研究工作相似。

图1 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的关系

图2 生物量、土壤含水量与植被盖度的关系
3.2生物量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3.2.1生物量与水分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热条件是制约草地植物生长的重要因子[25]。生物量与土壤含水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图3),土壤含水量可以解释生物量变异的86.7%,表明土壤中的水分越多,越有利于草地植物的生长发育,使生物量增加。可见,土壤中水分的多少是影响祁连山北坡天然草地生物量的重要因素。
分析还表明,生物量与降水量、相对湿度呈正相关关系,但均没达到显著水平(P>0.05),与土壤含水量相比,这种相关性较小,说明生物量对降水量和相对湿度的敏感性较弱。然而,5类草地生长季土壤含水量与降水量的关系均达极显著水平(P<0.01)[26],即土壤含水量随降水量的多少而增减,因此,可以说降水是通过土壤水分对生物量产生影响的。
3.2.2生物量与温度 生物量与大气温度、土壤温度均呈负相关关系(图3)但不显著(P>0.05),即生物量随大气温度、土壤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这种关系似乎并不能反映真实现象,因为在生长季,随降水的增多和气温的升高,生物量在逐渐增大。有研究表明[11],在降水充足的情况下,大气温度和土壤温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牧草的生长发育,但在降水较少的情况下,高温将导致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的加剧,造成土壤中供给牧草生长发育的水分不足,影响植被的生长。所以,有必要分析水分与温度的协同对生物量的影响。
3.2.3生物量与干燥度 干燥度作为水热因子的综合指标更能反映生物量与水热因子的关系[20]。如图3所示,本区的干燥度较大,为1.5~6.9,体现了该区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特征。分析发现,生物量与干燥度呈负相关关系,表明生物量随干燥度的升高而降低,当干燥度介于1.5~3.0时,生物量随干燥度的上升而迅速下降。干燥度能解释生物量变异的70.6%,高于大气温度的25.7%和土壤温度的63.8%,但没有达到显著相关水平,这与郑晓翾等[27]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研究相一致。
4 讨论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的草地类型因其气候条件、植被组成和土壤性质等存在较大差异,草地生物量会有很大的不同。如马文红等[28]在内蒙古温带草原测定的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的地上生物量分别为56.6、133.4 和196.7 g/m2、地下生物量分别为301.0、688.9 和1 385.2 g/m2,安尼瓦尔·买买提等[29]对新疆荒漠草原、草甸草原、高寒草原、典型草原和山地草甸地上生物量测得的结果分别为77.56、194.00、106.00、118.22和260.89 g/m2,均高于本研究测定的同类草地生物量。其原因可能有:我国北方草地生物量空间分布格局至东向西呈递减趋势[30],马文红等[28]研究也表明,内蒙古西部的地上、地下生物量分别小于100和500 g/m2,由此推断,祁连山北坡草地因受干旱、低温等恶劣气候的影响,其草地生物量总量处于较低水平;研究区长期的人类活动(如放牧)也不利于草地生物量的积累;马文红等[28]对地下生物量取样深度为50~60 cm,而本研究的取样深度为30 cm,可能低估了地下生物量。因此,还需要更多的调查数据以获取更为准确的生物量数据。

图3 生物量与土壤含水量、降水量、相对湿度、大气温度、土壤温度和干燥度的关系
准确认识生物量时空变化的控制因子对于预测草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29]。已有研究显示,水热条件是影响草地生态系统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降水是中国北方温带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最主要的限制因子[10,25]。但在本研究中,生物量与降水量、相对湿度、大气温度、土壤温度和干燥度均未达到显著相关水平(P>0.05),而与土壤含水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
植被盖度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较大[24,31],本研究中,0~20 cm土层的土壤含水量与植被盖度呈显著的正指数相关关系(P<0.05),说明植被盖度增加,有利于提高土壤水分含量。这是因为植被盖度较高时,植被截留能有效减小降水径流发生,有利于降水向土壤渗入,能有效增加水源涵养的功能;反之,当植被盖度较低时,降水径流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不利于土壤水的补给和植物的生长。由此可知,较高的植被盖度有利于降水对土壤水分的补给,而较高的土壤含水量则有利于草地生物量的积累和增加。因此,退化草地的恢复和重建不仅能提高植被盖度和生产力,更能提高草地的水源涵养和气候调节能力,这为该区实施还林还草工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1]李士美,谢高地,张彩霞.典型草地地上现存生物量资产动态[J].草业学报,2009,18(4):1-8.
[2]陈生云,赵林,秦大河,等.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高寒草地生物量与环境因子关系的初步分析[J].冰川冻土,2010,32(2):405-413.
[3]马文红,方精云,杨元合,等.中国北方草地生物量动态及其与气候因子的关系[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0,40(7):632-641.
[4]Dwire K A,Kauffman J B,Brookshire E N J,etal.Plant biomass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along an environmental gradient in montane riparian meadows[J].Oecologia,2004,139:309-317.
[5]Hui D F,Jackson R B.Geographical and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in biomass partitioning in grassland ecosystems:a synthesis of field data[J].New Phytologist,2006,169:85-93.
[6]Bai Y F,Wu J G,Pan Q M,etal.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diversity:evidence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J].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07,44(5):1023-1034.
[7]普宗朝,张山清.气候变化对新疆天山山区自然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的影响[J].草业科学,2009,26(2):11-18.
[8]Fan J W,Wang K,Harris W,etal.Allocation of vegetation biomass across a climate-related gradient in th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J].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2009,73:521-528.
[9]Yang Y H,Fang J Y,Ma W H,etal.Large-scale pattern of biomass partitioning across China’s grasslands[J].Global Ecology Biogeography,2010,19:268-277.
[10]Ni J.Estimating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of grasslands from field biomass measurements in temperate northern China[J].Plant Ecology,2004,174(2):217-234.
[11]陈效逑,郑婷.内蒙古典型草原地上生物量的空间格局及其气候成因分析[J].地理科学,2008,28(3):369-374.
[12]米兆荣,张耀生,赵新全,等.NDVI和EVI在高寒草地牧草鲜质量估算和植被动态监测中的比较[J].草业科学,2010,27(6):13-19.
[13]李镇清,刘振国,陈佐忠,等.中国典型草原区气候变化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J].草业学报,2003,12(1):4-10.
[14]常学向,赵文智,赵爱芬.祁连山区不同海拔草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9):1599-1603.
[15]赵成章,樊胜岳,殷翠琴,等.祁连山区退化草地植被群落结构特征的研究[J].中国草地,2004,26(2):26-30.
[16]闫月娥,王建宏,石建忠,等.祁连山北坡草地资源及退化现状分析[J].草业科学,2010,27(7):24-29.
[17]刘国彬.草地植物生物量研究概述[J].草原与草坪,1986(2):9-15.
[18]白永飞,徐志信.典型草原9种牧草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J].中国草地,1994,16(6):21-27.
[19]宇万太,于永强.植物地下生物量研究进展[J].应用生态学报,2001,12(6):927-932.
[20]孟猛,倪健,张治国.地理生态学的干燥度指数及其应用评述[J].植物生态学报,2004,28(6):853-861.
[21]Allen R G,Smith M,Perrier A.An updat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reference evapotranspiration[J].ICID Bulletin,1994,43(2):35-92.
[22]张耀生,黄德青,赵新全,等.祁连山北坡草地潜在蒸散量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0):8403-8405,8435.
[23]张国辉,赵成章,李兴福,等.石羊河上游草地植物种群特征与生产力关系研究[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9,44(5):116-120.
[24]王根绪,沈永平,钱鞠,等.高寒草地植被覆盖变化对土壤水分循环影响研究[J].冰川冻土,2003,25(6):653-659.
[25]Bai Y F,Han X G,Wu J G,etal.Ecosystem stability and compensatory effects in the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J].Nature,2004,431:181-184.
[26]黄德青,张耀生,赵新全,等.祁连山北坡主要草地类型土壤水分动态研究[J].草业科学,2005,22(8):6-11.
[27]郑晓翾,赵家明,张玉刚,等.呼伦贝尔草原生物量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J].生态学杂志,2007,26(4):533-538.
[28]马文红,杨元合,贺金生,等.内蒙古温带草地生物量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08,38(1):84-92.
[29]安尼瓦尔·买买提,杨元合,郭兆迪,等.新疆草地植被的地上生物量[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2(4):521-526.
[30]朴世龙,方精云,贺金生,等.中国草地植被生物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J].植物生态学报,2004,28(4):491-498.
[31]Hutjes R W A,Kabat P,Running S W,etal.Biospheric aspects of the hydrological cycle[J].Journal of Hydrology,1998,212-21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