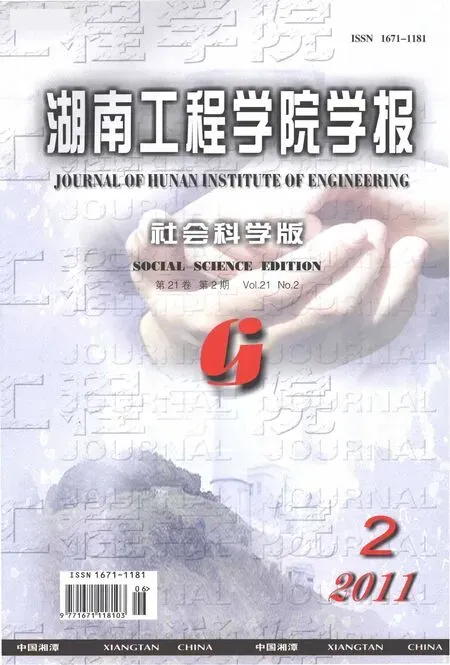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重的思想
马汉钦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论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重的思想
马汉钦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衡阳 421001)
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重的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汉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提出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发展时期,唐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深化时期。
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重;汉朝;魏晋南北朝;唐朝
中国古代绘画“形”“神”兼重的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汉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提出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发展时期,唐朝时期为“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深化时期。试申论之。
一 “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提出——汉朝时期
既提到了作形状解释的“形”,又最先提出绘画反映现实必须重传“神”这么一种观点的,是汉朝刘安与其门客们所编著的《淮南子》。《淮南子》在宇宙观方面提出了“形体”与“精气”并重说,认为“夫形者神之舍也;气者,神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淮南子·原道训》)这种思想也贯穿在他们的绘画美学思想中。他们表示反对作画、特别是作“寻常之外”的大画“画者谨毛而失貌”(《淮南子·说林训》),反对“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说山训》)这就是说,绘画反映现实,特别重要的是须反映出主宰“形”的那种“神”。只不过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出“神”这个概念,而是以“君形者”和“貌”这样的概念代替着“神”这个概念。
汉朝王逸之子王延寿在作于公元150年前后的《鲁灵光殿赋》中,对于“图画天地”,进一步提出了“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和“随色象类,曲得其情”的要求(见《文选》)。这里虽然没有“形”与“神”的字样,但是,很明显,“写载其状”,正是求的形似;而“曲得其情”,正是求的“神似”。他实质上提出了“形”“神”兼备的要求。
二 “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是顾恺之的人物画论,再就是宗炳和王微的山水画论,最后则是谢赫的宫体画论,对“形”“神”兼重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在我国绘画史上,是对“形”“神”兼重观点的重要发展。试以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和谢赫的“气韵生动”说为例,予以说明。
(一)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
顾恺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他的绘画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三篇画论之中:《魏晋胜流画赞》、《论画》和《画云台山记》。除此之外,《世说新语》、《晋书·顾恺之传》、《宣和画谱》等书中也记载了一些顾恺之的论画语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恺之的绘画思想主要集中于对人物画的探讨,兼及山水画。开辟了中国绘画新纪元的“以形写神”说,就是他提出来的。那么,顾恺之提出的“形”与“神”是指哪些内容、对“形”与“神”关系的认识又是怎样呢?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
一般地来说,“形”就是被描绘对象的外部形象,它包括对象的形状、特征、结构、习性、质地。然顾恺之所说的“形”,依据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以及顾恺之本人的论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形”当指人的物质意义上的形体,包括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具体器官。但同属形体中的一分子,各种器官受重视的程度并不相同。试看《世说新语》中的两段话: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座,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乎神明?”(《世说新语·排调》)[1]434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哪可便与人隔?”(《世说新语·贤媛》)[1]378-379
可见,在时人的心目中,人的身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乎形骸”的,如须发牙齿;一类是“关乎神明”的,如眼睛耳朵。顾恺之本人的认识也是这样的,有《世说新语·巧艺》为证: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点明瞳子,飞白拂其上,使如青云之蔽日。”[1]387
除此之外,“形”还有第二层的含义,就是指与人物精神气质相近的背景和环境。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他必然与他周围的环境和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并与之形成一种相互发明的共生氛围与情境。如此一来,环境和外物也就成了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正如顾恺之在他的《魏晋胜流画赞》中所说:
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
也。[2]174-176
这就是说,画家必须多方体察所要表现的对象的外在环境,合理地布置画面,才能曲尽人物之妙。我们从《世说新语·巧艺》中的另一处例子,也可看到顾恺之的这种认识:
顾长康画谢幼舆于一岩石里。人问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岩壑中。”[2]388
顾恺之在这里把谢幼舆置于丘壑之中的安排,也就是合乎人物风神气韵的“置陈布势”。
那么,“神”,又是什么呢?《世说新语·巧艺》有这么一段记载: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1]388
所谓“阿堵”,就是人的眼睛。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人的眼睛是人身体中最能够体现人物风神气质的部位。由此可见,顾氏所指的“神”,即是人的精神、情态、性格、气色。
那么,“形”“神”的关系怎样呢?顾恺之在其《论画》中提出了“以形写神”的重要思想: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嘱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晤对之通神也。[2]174-176
在当时人们习惯于把“神”高高地凌驾于“形”之上的气氛下,顾恺之明确地指出,绘画当走的路是“以形传神”。顾恺之认为,人物画要想获得传神的艺术效果,抛开所描绘的对象的“形”,那就是“空其实对”,是绝对不行的;当然,如果不去深入观察所要描绘的对象,抓不住它的“神”,只是对着实际的东西依葫芦画瓢,这样虽然“形”是有了,不过是无“神”之“形”而已,乃是“对而不正”的偏颇。可见,在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里面,“形”与“神”有依附和统一的直接关系,但又有它们的独立性。“形”不等于“神”,“神”也不等于“形”。“神”,固然要通过具体可视的笔墨形象来表现,然而不是任何形象都可以体现对象的“神”的。只有符合传神要求的“形”,才能体现其“神”。所以,顾恺之肯定了“神”是可以感受、捕捉的,而“神”的再现于画面,则是靠“形”为基础。无“形”,即无“神”;有“神”,必有“形”。要使“形”传“神”,关键在于对象各个有助于“神”的因素,并且根据对象情态的特点加以塑造。塑造形象的全过程;应当以传对象之“神”为核心,画家运用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把握感觉捕捉情态,并把感觉到的情态用笔墨形象地绘制出来。否则,纵使有“形”,“形”却不能传“神”。这种“形”,就不具有生命力,徒为对象的驱壳。显然,这正是“形”“神”兼重的思想。
顾恺之对“形”与“神”的认识是十分全面和深透的,并具有一定的辩证性。他认为绘声绘色画艺术所要取的“形”,不是死板地照抄对象轮廓的一毫一厘。应当根据表现对象特定的、具体的神情态度需要,对原形进行变化。这种变化是画家在充分了解、熟悉、感受对象的基础上,运用形象思维对原形进行取舍、提炼、夸张的艺术加工。他在为裴楷画像时,额上加画了三毛,并解释说:“楷俊朗有识具,观者说之,定觉神明殊胜。”为什么顾恺之要在裴楷的额头上加画三毛呢?裴楷是晋朝人,精通《老》《易》,学问渊博。大凡研究学问的人,其精力全然集中在事业上,无暇修饰自己,故而在形象上,常常显示出一种自然而不做作的神情。顾恺之为在形象上表现裴楷的气质素养,于是抓住这一点,运用形象思维加以造想妙得加画了三毛。达到可视、可感,形象生动的妙境。他为了揭示人物内在本质,大胆地改变原形,这一成功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他对“形”的看法不是静止不变的,更不是自然主义的。
在传人物之“神”的追求过程中,创作者主体之“神”的作用,顾恺之也有论及,在此略提一笔。《魏晋胜流画赞》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2]174-176
“迁想妙得”,就是顾恺之对创作者在绘画创作中其主体之“神”与所描绘的客观对象之“神”相融和过程的描述,指的就是创作者将自己的主体之“神”“迁”入对象之中,使客观对象的身份实现主体化,达到物我混一的境界,如此,就能够妙得其真,从而在创作实践中达到“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地步。
从上所述,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与韩非子要求“形”的“类之”,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他揭开了中国绘画的真谛,这是我国绘画及美学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
(二)谢赫的“气韵生动”说
谢赫是南朝齐代的著名画家,其《古画品录》表现了他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的宫体画的形神观。他的“气韵生动”说,就表现了他兼重“形”“神”的绘画思想: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2]190
那就先说位居“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吧。
“气韵”这一概念,来自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这在《世说新语》是有大量证明的。如《言语》中的“拔俗之韵”、“天韵”、“风韵”;《任诞》中的“风气韵度”、“大韵”;《识鉴》中的“雅正之韵”;《雅量》中的“思韵”;《品藻》中的“高韵”;《贤媛》中的“性韵”,等等。我们知道,《世说新语》是魏晋玄学“重神轻形”的忠实体现,所以,谢赫使用“气韵生动”这一说法本身,也就表明了他在绘画中的重“神”思想倾向。
不过,作为一个宫体画家[3],且生活在齐、梁那个非常特别的时代,谢赫所说的“气韵”已经与魏晋玄学时所说的“气韵”有了很大的区别。魏晋玄学所推崇的“气韵”,是来自悟“道”者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体验,它的基调是清、淡、静、远、逸;而谢赫所说的“气韵”已经不再有这些哲学方面的旋韵了,而是一种宫廷奢靡的审美情调,是以表现宫廷美女的风姿韵味为特色的一种世俗化的审美追求,谢赫曾经称之为“雅媚”。这就是说,谢赫的“气韵”是有着极大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的,尽管他也是以表现人物之“神”为己任的,也是要求以绘画之“形”来表现人物的内在之“神”。
所谓“生动”,就是对作品“气韵”在表现方式上面的整体要求,“生动”也就是“气韵”的活的形象。如果说“气韵”是描绘人物之“神”的要求,那么“生动”也就是对人物之“形”特别强调,这是谢赫作为一个“宫体”画家稍稍不同于顾恺之的地方。谢赫的确不忽视“神”的表现,但更为强调对形体动作、姿态的精细描绘,应该说,这和宫体画的庸俗追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特别赞赏一些能够逼真地描写对象的画家。如他评顾骏之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就构成谢赫绘画形神思想的重要特征。从姚最《续画品》对谢赫绘画的评论,也可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地着力于对人物形体姿态的逼真生动的描写。可见,较之顾恺之,谢赫对绘画之“形”的重视更多一些,这和他作为一个“宫体”画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其余的五法中在“形似”方面那细而又细的孜孜之求了。
三 “形”“神”兼重绘画思想的深化——唐朝时期
到了唐朝,画论家张璪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2]281的艺术主张。这一主张在绘画形神理论上史有着不可抹杀的理论意义,因为他不仅要求画家以自然为师,注意绘画上的“形似”,并进行创作时去发觉和迷惑出对象的客体之“神”,而且特别强调了画家在绘画创作时的“心源”问题,即画家主体之“神”在绘画创作中的体现。所以,他这句简简单单的话,在某种意义上看,是对此后绘画重“意”倾向的开启,在此特别一提唐朝张彦远则更明确提出“意在笔先,画尽意存”这就把“意”给突出出来了:
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2]308
他进一步强调画家的“意”在绘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作画应当要立“意”,并以此为绘画之本。所谓“立意”,其实就是就是确保画家的主体之“神”在绘画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并在此基础上使得自己的主体之“神”与客观景物形成契合,达到主客体之“神”在绘画中的融合统一,从而以我之“意”造境,以我之情造“形”。
很显然,这仍然是“形”“神”兼重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将他的思想和顾恺之、谢赫等人的理论进行一下对比,我们会看到这一思想的发展在于:顾恺之、谢赫等人对画家主观的心意活动尚无涉及,而张彦远就明确提出在描绘对象时,不仅要注重对客观实体的体察,更重要的是要画家主观心意的参与,在对客观实体的描写中,使之与画家自我心意的逐步靠近,并达到主客观的融合、主客之“神”的统一,使画中有我意,画中我有情。这实际上就更加接近了艺术创作的本质。
[1] 徐震堮.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G].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813.
Equal Stress on“Shape”and“Spirit”in China’s Ancient Painting
MA Han-q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 College,Nanhua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0,China)
The thought of equal stress on“shape”and“spirit”in China’s ancient paint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such a thought was put forward in the Han Dynasty,developed in the Wei Jin as well a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nd promoted in the Tang Dynasty.
China’s ancient painting;equal stress on“shape”and“ spirit”;Han Dynasty;Wei Jin as well a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ang Dynasty
I01;J202
A
1671-1181(2011)02-0042-03
2011-02-10
马汉钦(1966-),男,湖北洪湖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周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