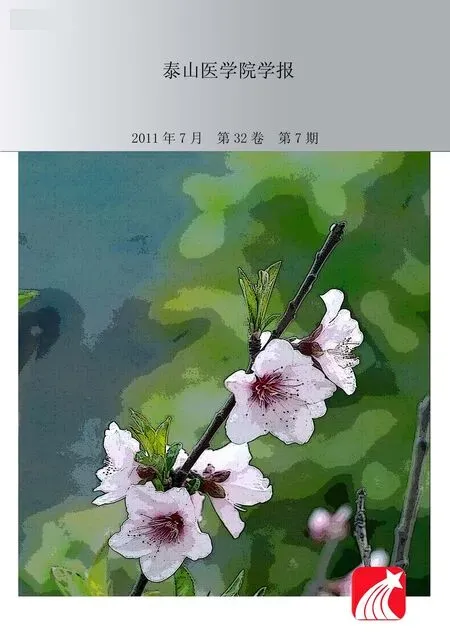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高危因素及诊治的研究进展*
朱燕霞 侯洪春
(1.泰山医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6; 2.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山东 济南 250001)
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是与宫颈浸润癌相关的一组癌前病变,它能反映宫颈癌发生发展的连续过程。一般情况下,由CIN发展为宫颈浸润癌需经历8~10年的时间,因而发现和治疗宫颈癌前病变即CIN对宫颈癌的预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对CIN和宫颈癌的流行病学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逐渐认识到CIN和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宫颈癌筛查的广泛普及以及筛查技术的提高,临床上浸润性癌已相对少见,而CIN的检出不断增多,因此,正确认识CIN的发病因素并进行正确的诊断及规范的处理是降低CIN及宫颈癌发病率的关键。现就近年来CIN及宫颈癌的高危因素、筛查及治疗方面做一综述。
1 病 因
1.1 HPV与CIN、宫颈癌
目前,已分离出100余种HPV亚型。依其致癌性可分为2类:①低危型: 如HPV 6、11型,可引起外阴湿疣和CINⅠ;②高危型:如HPV16、18、45、56等,可引起CINⅡ-Ⅲ和宫颈浸润癌。在宫颈浸润癌中HPVl6型及18型阳性率最高;CIN次之。
在CIN病变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中,HPV感染最为重要。CIN组织中HPV-DNA的阳性检出率可达88%,而正常宫颈组织中仅4%,CINⅠ组织中多为低危型HPV(HPV6、11等)感染,而CINⅡ及CINⅢ组织中多为高危型HPV(HPV16、18、31等)感染。随着CIN级别的增高,高危型HPV感染率也增高。表明高危型HPV感染与CIN病变进展的关系密切,高危型HPV感染既是CIN的重要原因,又是病变发展的高危因素。
1.2 性行为、生殖状况与CIN、宫颈癌
随着对宫颈癌流行病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宫颈癌的发生与性行为和妇女的生殖状况密切相关。Rostad等[1]研究显示,初次性交年龄在16~19岁时风险度为1.8,<15岁时风险度明显增加至4.8(P=0.00)。且宫颈癌的患病危险性与性伴侣个数及分娩次数呈正比,当性伴侣个数为>6时,其相应风险度比1~5个增加5.7倍(P=0.00)。分娩次数>5次比分娩次数为0~1次的风险度增加4倍(P=0.00)。多项研究也进一步证实宫颈癌的发病风险与初次性交年龄、多个性伴侣、分娩次数相关[2]。此外男性性行为也被认为是宫颈癌的重要风险因素,当丈夫有婚外伴侣时,妻子患宫颈癌的危险性可增加8.1倍[3]。
1.3 吸烟与CIN、宫颈癌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吸烟与宫颈癌的关系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研究认为宫颈黏膜具有一张Langerhan细胞和T淋巴细胞组成的广泛的免疫细胞介导网络,宫颈黏液中的尼古丁和可铁宁高含量可降低宫颈的免疫防护,使其更容易感染HPV病毒,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另外一种学说[4]认为致癌性烟草代谢物可随尼古丁和可铁宁一起进入宫颈组织中,使宫颈黏液的致突变性增加,从而导致宫颈癌变。不同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吸烟在排除了性行为影响后仍然是宫颈癌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5]。Nunez等[6]研究表明吸烟的量和年限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当每日吸烟≥20支,吸烟年限≥5年时,CIN及宫颈浸润癌发生的风险度明显增加(P=0.02)。在农村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吸烟妇女所占比例较少,大多数为被动吸烟。在Sun-Kuie等[7]研究中排除了年龄、初次性交年龄、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妇女自身吸烟等因素后,配偶的吸烟量与妇女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的发病风险成正比,说明被动吸烟同样可以增加CIN及宫颈癌的危险性[8]。
1.4 口服避孕药与CIN、宫颈癌
有研究[9]显示口服避孕药(OC)可通过病毒基因组中的激素效应元件增加HPV病毒表达,从而增加CIN及宫颈癌的发病风险。目前对口服避孕药使用的研究很多,但报道结果并不一致。Smith[10]对1986~2002年发表的有关口服避孕药使用的研究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OC使用<5年者总风险度为1.1;OC使用5~9年者总风险度为1.6;长期使用OC者(>10年)总风险度为2.2,并且指出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者即使停药后宫颈癌的危险性有所下降,但并不能消除其增加的风险。在Phillip等[11]对激素类避孕药使用的研究中却发现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并不增加CINⅢ形成的风险,只有注射激素类避孕者才可增加CINⅢ的风险度。
1.5 卫生状况与CIN、宫颈癌
在排除了早婚、多产等因素影响后,卫生状况与宫颈癌的发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尤其是农村妇女不良卫生状况是诱发宫颈癌的最强风险因素[3]。由于缺乏相应的卫生知识和卫生条件,共用舆洗器具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又存在着不良的性卫生习惯,增加HPV感染的风险,最终导致CIN及宫颈癌的发病危险度上升。在Silvia[12]的研究中对照组妇女无室内卫生间者HPV感染风险是有室内卫生间者的4.8倍, 缺乏流水HPV感染风险度为2.0,性生活后很少清洗生殖器官者风险度是常清洗者的4.5倍。
1.6 社会经济状况与CIN、宫颈癌
目前有关宫颈癌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营养、卫生服务资源等。多项研究[13-17]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是CIN及宫颈癌的重要风险因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许多妇女健康预防意识差,很少主动参加宫颈筛查和妇科检查。此外经济收入低、早婚、多产现象更容易出现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中。营养状况同样也在CIN及宫颈癌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项最新的研究[18]表明机体的叶酸水平降低可增加CIN及宫颈癌的危险性。这可能是因为叶酸缺乏可干扰DNA的合成、修复以及甲基化,或改变细胞对致癌基因或化学致癌物的易感性,最终导致肿瘤形成,而正常水平的叶酸盐则可减少这些因素的风险,起到预防CIN的作用[19]。
1.7 家族史与CIN、宫颈癌
有关宫颈癌家族史的研究报道较少,一项对印度病例对照研究中的宫颈癌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的研究显示,有宫颈癌家族史的妇女总发病风险是无宫颈癌家族史妇女的2倍,由此可见相关癌症家族史也是CIN及宫颈癌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
2 宫颈癌的筛查
2.1 细胞学检查
在我国大多数基层医院仍采用传统的制片法和巴氏诊断系统,该方法虽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巴氏分级范围过宽,没有与组织病理学相对应的术语,对临床缺乏明确的指导意义。自1988年美国的50名细胞病理学家提出the bethesda system(TBS)这一描述性的宫颈细胞学诊断报告方式之后,1998年液基薄层细胞学制片技术(thin-prep cytology test,TCT)引入我国,TBS与TCT两者的结合提高了细胞学检查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且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细胞学检查方法。对符合以下条件的妇女应进行脱落细胞学检查:①初次性生活3年左右开始,每年接受一次检查。②30岁以后连续3次脱落细胞学检查正常者,每2~3年复查一次。③大于65岁的,在10年内有3次正常者可停止筛查。④对高危人群,检查的间隔和终止年龄要结合HPV结果。
2.2 HPV-DNA检测
现已明确,CIN和宫颈癌的发病与HPV的感染有关,特别是处于持续感染状态的妇女,其患病风险更高。研究[20]表明,高危型的HPV16、HPV18与CIN关系密切,两者在CINⅡ、Ⅲ患者的感染率(分别为55%、65%)要明显高于CINⅠ的患者(30%)。新近研究[21]发现,随着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的升高,其高危型HPV感染率也逐渐升高而且病毒负荷量与CIN分级具有显著相关性[22]。因此,HPV-DNA检测有助于CIN和宫颈癌的筛查。目前世界范围内认可的检测方法是杂交捕获法(hybrid capture 2,HC2),其检测高度病变(HSIL)的敏感度高于TCT,而特异性略低。HPV-DNA检测联合液基细胞学检查对宫颈癌及CIN是目前最好的筛查方法。
2.3 阴道镜检查
在宫颈细胞学检查和HPV-DNA联合筛查后,按上述处理方法,大部分应进行阴道镜检查。在镜下先全面观察宫颈阴道部、转化区和阴道穹窿周围,满意的阴道镜活检的诊断标准为“转化区的内外边界均清晰可见”。而后在宫颈表面涂布3%的冰醋酸,进一步系统地观察转化区,再用Lugol碘溶液涂抹宫颈,可出现不着色区域,即碘阴性区。出现以下异常的图像时可考虑有CIN或更高级别的病变:白色上皮、点状血管、镶嵌、异型血管,尤其是厚的白色上皮、粗镶嵌、粗点状血管。当需要活检时,在以上部位进行多点活检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近几年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满意的阴道镜检查及镜下活检后的病理诊断可以作为一部分的CIN诊断标准,是诊断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23]。但是镜下检查代表的只是有限的宫颈取材的标本,可能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阴道镜医师的技术水平,取材部位的深浅、大小以及病变的部位和范围等,有的学者[24]认为CINⅢ及早期宫颈癌病变多为多中心性,阴道镜取材有限,且无法取得宫颈管内的病变,若病变深入宫颈内则容易造成漏诊,故阴道镜检查不满意时需结合宫颈管搔刮术(endocervical curettage,ECC)或进一步做CKC或宫颈环形电切术(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procedure,LEEP)进行诊断。
2.4 宫颈活检
阴道镜下多点活检及其病理报告是诊断宫颈病变的金标准,正确取材应在转化区内的病变部位。对不满意阴道图像,行ECC尤为重要。
3 诊 断
CIN的确诊和级别的划分需以活组织病理为标准。
3.1 宫颈多点活检
由于直视下宫颈多点活检取材难以明确定位,在有条件的地区或医院,这种方法已被阴道镜下活检取代。
3.2 宫颈管搔刮术(endocervical curettage,ECC)
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应进行宫颈管搔刮术:①TCT筛查提示为非典型腺细胞(AGC);②阴道镜下未见转化区;③CIN自转化区延伸至宫颈管内;④检查者不是专业阴道镜医师。
3.3 宫颈环形电切术(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procedure,LEEP)
LEEP手术是采用超高频电波刀,通过Loop金属丝传导高频交流电(3.8 mHz),组织吸收热量后快速切割组织,而不影响切出组织及其切口边缘的组织特征,切除的组织完全可用于病理学检查。LEEP作为诊断方法,其应用指征[25]为:①阴道镜检查无明显异常,而TCT为ASC-US或AGC-US;②TCT或阴道镜检查均为HSIL;③阴道镜检查不满意的TCT异常者。而LEEP作为治疗的指征[25]为:①阴道镜和活检证实的CIN I级呈持续状态,无随诊条件;②CIN I级伴高危型HPV感染者;③CIN II级患者;④部分CINⅢ级中的重度不典型增生者,但不包括原位癌。
3.4 冷刀锥切术(cold-knife conization,CKC)
随着阴道镜的逐步开展和应用,CKC用于诊断已经大为减少。与锥切相比,阴道镜虽然具有简单,经济,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患者痛苦小和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但它并不能完全代替锥切宫颈病变,尤其是宫颈原位癌,多为多中心性,而阴道镜取材有限,易造成漏诊。CKC在诊断方面的应用,除与LEEP的3条指征相同外,还包括:①细胞学、阴道镜和活检检查结果不同。②细胞学、阴道镜和活检可疑浸润癌。③疑为子宫颈腺癌。只要有以上六者其一,都应做宫颈锥切来进一步明确诊断。
4 治 疗
4.1 CINⅠ的治疗
很多研究表明CINⅠ不经治疗有60%左右可以自行消退,仅有11%的患者进展为更高级别的病变,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对于具有随访条件,依从性好的CINⅠ患者可以进行密切的随诊,在第6、12个月时进行TCT检查,结果为ASC-US或更高级别时做阴道镜活检;或随访12个月,对持续或新发高危型HPV-DNA(+)者行阴道镜下活检;连续两次TCT检查为阴性或HPV阴性,就可改为每年随诊。行阴道镜检查后,如果患者不具备良好的随访条件,应进行宫颈病变破坏治疗或切除治疗。一些学者应用LEEP对阴道镜活检的结果进行重新评估,发现有18.8%~23.1%的CINⅠ患者其病变级别升高[26-28],同时因为破坏治疗不能取得标本送病理,因此在治疗方法的选择上,仅有阴道镜检查满意的患者可以进行宫颈病变破坏治疗,其方法有:激光治疗,电凝治疗和冷冻治疗。对宫颈切除方法的选择最佳为LEEP,这是因为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费用及住院时间均优于CKC[28],尤其可以在门诊一次性完成诊断与治疗[28],而且LEEP后的宫颈粘连或颈管狭窄的发生率要低于CKC。其缺点是对标本边缘的热损伤可能影响病理诊断,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有的学者提出LEEP时病变部位点龙胆紫,可以提高CIN的诊断[24],因而LEEP可以作为最优术式。
4.2 CINⅡ的治疗
由于CINⅡ病变进一步发展为CINⅢ者或癌变的可能性较高,同时高危型HPV-DNA的感染率要明显高于CINⅠ患者,而且持续感染者较CINⅠ多,因此最好选择宫颈切除治疗,尤其是对于阴道镜检查不满意的患者。
4.3 CINⅢ的治疗
CINⅢ包括重度不典型增生和原位癌。以往认为对无生育要求者应当直接行子宫切除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与证据表明,子宫切除术属于过度治疗,应首选宫颈冷刀锥切术(CKC),其指征为[25]:①CINⅢ级;②宫颈原位鳞癌;③宫颈原位腺癌;④Ⅰa期宫颈癌。部分CINⅢ级中的重度不典型增生者(除外原位癌)可以用LEEP治疗。对于重度不典型增生的患者,CKC和LEEP的疗效是肯定的,而且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同时CIN患者经LEEP或宫颈冷刀锥切术治疗后HPV-DNA平均负荷量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29],LEEP后宫颈可恢复正常的鳞柱交界,便于用阴道镜、宫颈细胞学及病理学检查随诊,对有生育要求的CINⅢ患者,在有条件随诊时行LEEP是较理想的治疗方法[30]。由于CINⅢ及早期宫颈癌病变多为多中心性,阴道镜取材有限,且无法取得宫颈管内的病变,若病变深入宫颈内则容易造成漏诊,故一些学者认为对切缘有CINIII残留的宫颈原位癌及宫颈癌Ia1期者,锥切后仅行随诊的风险较大,宜进一步处理[31],行全子宫切除或范围更大的术式。对于锥切术的范围,国内目前认定为,切除宽度应在病灶外5 mm(宫颈癌Ia2期),锥高延至颈管2~2.5 cm,锥切时要将鳞柱交界一并切除[25]。而国外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在异常转化区周围3 mm,高度达到1.5 cm即可[32]。这是由于在微小浸润癌(宫颈癌Ia1期,深度<3 mm)的情况下,淋巴血管间质的浸润的受累程度比浸润深度更容易影响预后,也就是说,切缘阳性者并不是决定预后的主要因素。当然无论锥切后的结果如何,大部分学者认为均必须进行密切随访,以便早期发现复发,及早治疗。
4.4 妊娠期CIN的治疗
妊娠期间雌激素过多使柱状上皮外移到子宫颈阴道部,移行带区的基底细胞出现不典型增生,可类似原位癌病变,也易患病毒感染。妊娠合并子宫颈鳞状上皮内瘤样病变常由HPV感染所致。研究[33]表明,在妊娠期CINⅡ和CINⅢ发展成为浸润癌的危险性较小,产褥期病变自然消退的比例相对较高,产后随访未发现病变有进展,且妊娠期手术有出血多及流产率增加等风险,因此建议对妊娠期发现的CIN可观察并产后随访,妊娠期采用诊断性宫颈锥切术仅限于未排除浸润性癌的妇女。
5 随 访
应当包括TCT、HPV-DNA、阴道镜下活检。CINⅠ的随访如上所述。CINⅡ、CINⅢ的患者应在3个月内复诊。复诊后若TCT提示为正常,则每年随访一次TCT检查;如果复诊后TCT结果提示HSIL,应在一个月内进行阴道镜检查取活检并进行宫颈管搔刮术,如果阴道镜活检证实仍为HSIL应进行LEEP,如果活检结果低于HSIL而ECC为阳性,建议行宫颈锥切术。随访过程中任何细胞学或病理学诊断为浸润癌者应在1周内进行阴道镜下活检,活检结果低于浸润癌要立即做CKC或根据患者情况行更高级别的手术。而后继续每4~6个月复查一次TCT,直至连续两次转阴后改为每年一次TCT。随访时可同时进行或仅做HPV-DNA检测,高危型HPV-DNA阳性者其病变持续存在或进展的可能性明显增高,可按照复查结果为HSIL的随诊方法处理。
综上所述,CIN和宫颈癌的高危因素多且复杂,多种因素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间有无协同或拮抗作用,是否还有新的更重要的危险流行因素,尚待进一步研究。CIN和宫颈癌的筛查是降低宫颈癌发病率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如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宫颈癌前病变的发生,以及如何在现有方法基础上更好地治疗及检测已发生的、正在进展的或复发的宫颈病变,依然是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对CIN患者应遵循个体化原则,根据其分级不同、病变范围、患者年龄、生育愿望、健康状况和医疗条件及技术水平等因素合理施治,以避免治疗不足和治疗过度。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手段,术后的随访都是十分必要的。
[1] Rostad B,Sehei B,da Costa F.Risk factors for cervical cancer in Mozambican women[J].Gynecology Obstetrics,2003,80(1):63.
[2] Sean F Ahekruse,James V Lacey Jr,Louise A Brin-ton.Comparis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genotypes,sexual,and reproductive risk factors of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J].Am J Obstet Gyne-col,2008,188(3):657.
[3] Doudja Hammouda,Nubia Muiioz,Rolando Herrero.Cervical carcinoma in Algiers,Algeria: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lifestyle risk factors [J].Int J Cancer,2005,113(3):483.
[4] Holly EA,Petrakis NL,Friend NE.Mutagenic mucus in the cervix of smokers[J].J Natl Cancer Ins,2008,76(6):983.
[5] Hellberg D,Nilsson S,Haley NJ.Smoking and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nicotine and cotinine in serum and cervical mucus in smokers and nonsmokers[J].Am J Obstet Gynecol,2006,158(4):910.
[6] Nunez JT,Delgado M,Pino G.Smoking as a risk factor for preinvasive and invasive cervical lesions in female sex workers in Venezuela[J].Int J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2002,79:57.
[7] Sun-Kuie Taya,Kae-Jack Tay.Passive cigarette smoking is a risk factor in cervical neoplasia[J].Gynecologic Oncology,2004,93(1):116.
[8] Carlos H Sierra -Ton'es,William W Au,Concepcion D Ar- rastia.Polymorphisms for chemical metabolizing genes and risk for cervical neoplasia[J].Environmental and Molecular Mutagenesis,
[9] de Villiers EM.Relationship between steroid hormone con -traceptives and HPV,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and cervical carcinoma[J].Int J Cancer,2003,103(6):705.
[10] Smth JS,GreenJ,Berrington de Gonzalez A,etba1.Cervi-cal cancer and use of hormonal contraceptives:a systematic review[J].Lancet,2003 361(9364):1159.
[11] Philip E Castle,Joan L Walker,Mark Schiffman.Hormonalcontraceptiveuse,pregnancy and parity,and the risk of cervical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3 among oncogenic HPV-DNA-positive Women with equivocal or mildly abnomral cytology[J].Int J Cane-er,2005,17(6):1007.
[12] Silvia Franceschi,Thangarajan Rajkumar,Salvatore Vac-carella.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risk factors for cervical cancer in Chennai India:a case-controlstudy[J].Int J Cancer,2008,107(1):127.
[13] Dudia Hammouda,Nubia Muiioz.Rolando Herrero.Cevical carcinoma in A1gier,Algeria: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lifestyle risk factors[J].Int J Cancer,2005,113(3):483-489.
[14] Silvia Franceschi.Thangarajan Rajkumar,Salvatore Vaccarella.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risk factors for cervical cancer in Chennai India:a case-control study[J].Int J Cancer,2003,107(1):127-133.
[15] Rostad B, Schei B, da Costa F.Risk factors for cervical cancer in Mozambican women[J].Gynecology Obstetrics,2003,80(1):63—65.
[16] Fang-hui Zhao,Michele R Forman,Jerome Belinson.Risk actors for HPV infection and cervieal cancer among un-creened women in a high-risk rural area of China[J].Int Jancer,2006,1l 8(2):442-448.
[17] Michelle J Khan,Edward E Partridge,Sophia S Wang.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risk of e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grade 3 among oncogenic human papillomavimDNA-positive wolnen with equivocal or mildly abnermal cytology[J].Cancer,2005,104(1):6l-70.
[18] Karunee Kwanbunian,Phimonsri Saengkar,Cheeraratana Cheeramakara.Low folate status as a risk factor forcervi-cal dysplasia in Thai women[J].Nutrition Research,2005,25(7):641—654.
[19] Butterworth CE Jr,Hatch KD,MacalusoM.Folate deftieney and cervical dysplasia[J].JAMA,1 992,267(4)8-533.
[20] 王莹,卞美璐.液基薄层宫颈细胞学图谱[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14.
[21] 汤惠茹,吴瑞芳,周艳秋,等.不同程度宫颈病变感染人乳头瘤病毒的亚型种类[J].实用医学杂志,2007,23(9):1334-1336/
[22] 金力,郎景和,王友芳,等.高危人类乳头状病毒负荷与宫颈上皮内瘤变的分级关系[J].生殖与避孕,2006,25(7):422-425.
[23] 王静,刘汉萍,罗小平.阴道镜下宫颈多点活检结合颈管搔刮术在宫颈病变诊断中的价值[J].中国妇幼保健,2008,20(1):128-129.
[24] 张久存,刘芳,翟建英.100例宫颈上皮内瘤变电切术前术后的病理对比[J].宁夏医学院学报,2008,20(2):221-223.
[25] 沈铿.宫颈上皮内瘤变治疗方法的选择[J].中华医学杂志,2006,86(5):291-294.
[26] 李巍,马慧娟.宫颈环形电切术对阴道镜活检诊断为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重新评估[J].中国社区医师,2007,20(4):27.
[27] 杨洁萍.宫颈锥切术后与阴道镜下活检对宫颈上皮内瘤变诊断价值的探讨[J].中国医药导报,2008,28:167-168.
[28] 李青华,吴湘.三种术式治疗子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183例疗效观察[J].医学临床研究,2007,24(7):1135-1137.
[29] 胡海燕,徐瑾.宫颈上皮内瘤变治疗前后人乳头状瘤病毒负荷与疾病预后的关系[J].实用医学杂志,2008,24(2):199-220.
[30] 代淑兰.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73例手术治疗探讨[J].华中医学杂志,2005,29(6):435-436.
[31] 朱之玲.高频电波刀电圈切除术在宫颈CIN Ill及宫颈癌I A诊治中的应用价值[J].中国癌症杂志,2007,17(6):476-478.
[32] Michael S Baggish,夏恩兰,卞美璐.Colposcopy of the Cervix Vagina and Vulva[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6:263-264.
[33] Kyrgiou M,Koliopupos G,Martin-Hirsch P,etal.Obstetric outcomes Afte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for intraepithelial or early invasive cervical lesions: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J[J].Lancet,2006,367 9509 :489-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