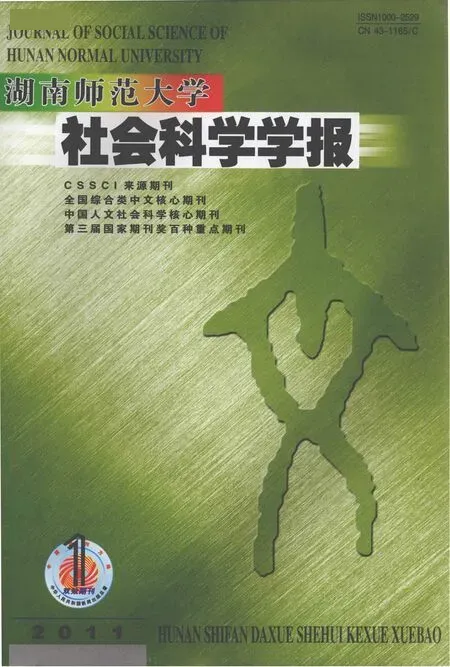论威廉斯早期诗学中的女性观和诗歌创作
武新玉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2)
论威廉斯早期诗学中的女性观和诗歌创作
武新玉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2)
威廉斯早期诗学中女性观有一个孕育和发展过程;赞同女权主义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立场是其诗学女性观的核心和本质;其诗歌创作实践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逐渐走向后现代主义开启了新的途径。
威廉斯;庞德;女性观;女性形象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在早期的写作中全面地对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进行抵制批判,终于建构了独树一帜的诗学和诗歌创作实践,为20世纪美国诗歌独立健全地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我们把威廉斯的诗学分成早晚两期的话,那末早期是他诗学的孕育发展期,后期是他诗学的成熟光大期。本文旨在研究他早期(20世纪初至30年代)诗学中女性观的形成与其在诗作中的体现。
一、威廉斯早期诗学中女性观的孕育和发展
威廉斯早期的生涯正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1880-1920)相契合。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标志性的女权主义诗学产生,但英国的弗吉尼娅·沃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法国的西蒙·德·波娃的《第二性》的出版开启促进了对男性文学文本中的性别歧视及女性文学传统和女权主义文学的研究。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威廉斯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威廉斯早期诗学中的女性观的孕育和发展也有其内在的成因。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没有姐妹,婶婶,堂姐妹。至少在近亲范围内。所以,除了母亲和祖母外,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从没亲密地了解过一位女性。这很重要,这在我心中燃起足够烧死五十个成长中的少年的好奇之火。”[1](P5)精神分析批评认为,文学创作就如同作家做白日梦,作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往往在写作中得到某种象征性的满足和替代。由于威廉斯本人的经历,他对女性的强烈迷惑和好奇心激发了他对女性世界的探索,促使他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刻画了19、20世纪之交的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
女性历来是诗歌的重要题材和主题,但她们大多是男性观笔下的女性,是他者、物体、附属品,这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直至尼采、魏宁格等,大抵如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男子“在各方面都超过妇女”,女人、奴隶和下等人都不应该为高等人所模仿,怯懦的或者不义的人在来生就要变成女人(见罗素《欧洲哲学史》上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妇女是发育不全的人,丈夫该“像一个国君一样统治着妻子,像一个皇帝一样统治着孩子”,他甚至武断地宣称女人要比男人少两颗牙齿,为此罗素曾讽刺亚里士多德应该让其夫人张嘴自己来数一下。古希腊诗人希摩尼德斯曾把女性比作狐狸、猪、狗、泥浆、无尾猴。就连后来的激进的思想家卢梭,在谈到妇女时也认为“妇女的第一个品质,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温顺”,“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至于近代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等人,对妇女简直有一种病态的仇视心理,尼采甚至向男人们大叫:“是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另一个悲观主义者魏宁格也附和道:“不论某个男子何等卑贱,他总是大大超过最高尚的妇女,而且大到无法比拟的程度。”这些一向被视为文化巨人的言行,充分暴露了西方文化传统对女性的虚伪态度:表面上把女性赞美为弘扬文明的“缪斯”,实质上将她们贬损为导致文明堕落的“魔鬼”。威廉斯生长于此传统中,却因时代变迁、女性主义的勃起和自身经历的影响,对此男性观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样,人们虽然在他的诗中仿佛看到男性诗歌传统的影子,但实际上他的诗歌蕴涵了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并且这样一种色彩是在不断变动和深化的。试比较威廉斯的诗歌《启示》(“The Revelation”)1914年版和 1934年改编版的不同即可明了。从威廉斯对这首诗歌的前后修改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这两首诗的前面几行都一样,说一个姑娘来到跟前停下,向我伸出手,她的出现使我欣喜,使我记住了我所做的梦。这些诗行的象征意义是女性形象为男性诗人的创作带来灵感,但在1914年的诗中,那姑娘“向我伸出手/一言不发”,似乎被剥夺了发言权或失去了话语能力,形象并不完整。而在1934年的诗中,“一言不发”这一行消失了,上一行改为“向我伸出手——”,这破折号含义很多,可能表示那姑娘伸出手的同时说了话,也可能表示那姑娘虽未说话,但她来到跟前伸出手的形象已足够雄辩,足以说明一切。通过这样的改动,1934年诗中姑娘的形象比1914年诗中的形象来得更高大和完整,这也表明经过20年后威廉斯对女性更尊重,对她们的看法更全面更深刻更接近本质了。第二,经过改写后这首诗变得更为客体化,少却了诗人的主观感受的表述,语言更简洁,特别是关于女性性别方面删减了传统的描写,没有了“她的灵魂/从她安宁的眼神里流向了我”这句子,也没有了“美丽”这字眼,这显示了威廉斯对传统女性描写手法的改革和扬弃。第三,诗歌中采用了不少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式的“破折号”①,反映了女性思维特有的敏感、细腻和跃动的风格,突破了传统书写中陈旧规范的局限,颠覆了逗号、句号这些传统逻辑及理智符号的束缚,将原有的封闭诗行打开,使之更具开放性和灵动性。威廉斯敢于、肯于采纳狄金森式的句法与标点正表明他对女性书写风格的肯定、赏识和吸纳。无论从词藻到句式,可以说威廉斯1914年原诗的创作是基于男性传统对女性进行书写的,但他1934年对这首诗歌的修改使之从视觉外形到内容本身都比原诗更为突破传统的禁锢,更反映了他作为男性作家对于传统男性权威的自觉抵制和对女性形象及其书写的认可和赏识。作为传统男性世界中的“边缘人物”,威廉斯善于立身于传统之中而颠覆之,做到脱胎而出。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说:“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2](P8)。
威廉斯早期在庞德的影响下加入了意象主义诗歌的写作,为杂志“Egoist”撰稿。“Egoist”原是一本女性主义刊物,却在庞德的影响和操纵下渐渐认同男权诗学了。但从这一时期威廉斯的诗作与信件已可看出他对庞德所倡导的男权诗学的抵制,可以说此时的威廉斯一脚尚在男性传统领域内,一脚已迈向女性主义这一边。如诗歌《过渡》(“Transitional”,1914)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威廉斯对女性所持态度的一种过渡性的变化:“首先,他这样说:/是我们心中的女人/使我们笔耕不辍——/让我们承认这一点——/男人将会沉默。/我们不是男人/所以我们能够言说/并能有意识/(两方面都顾及)/既在感官上放松自在/又在准确上得体适切。/接着我说/你敢宣传/你这观点么?/他这样回答:/是我,非我——此时此地?”整首诗歌的语言和性别书写充满着具有张力的内在矛盾。诗歌以“he said”表达了主体的存在和性别定位,但诗歌的结尾“Am I not I—Here?”却表达了主体对自己存在的反诘或不确信。破折号和问号的使用使整首诗歌的意义波折起伏并具有开放性。如果说诗歌的第一诗节有一个明确的逻辑意义,那末第二、三诗节似乎是对它的质疑和颠覆。“我们不是男人”是指我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是因为我们承认“是我们心中的女人/使我们笔耕不辍”。传统对“诗人”的理解是彻底男性化的,爱默生曾在他的散文《诗人》中,把诗人定义为“芸芸众生中的男士”[3](P296),本诗的第一节对此显然持有异议,然而诗歌的末行这不确定的句式又仿佛是一个自我否定,反映了20世纪初期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与日渐汹涌的妇女运动的碰撞与交汇:在女权运动及其它现代思潮的冲击之下,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两性观念的剧烈变革。这一变革也波及文学领域,种种旧的美学观念遭到挑战或解构,新的观念在破土而出,包括给女性以独立、平等、自由的地位和强调男女两性和谐相处互生互惠的诗学观。
在这大背景下,这首名为《过渡》的诗表明威廉斯在其早期的诗作中已开始有意识地涉及性别政治和权力话语。他在1917年的《致需要者》(Al Que Quiere!)中表明了自己的美学观:诗歌的权威不在于“男性的喧嚣和咆哮”,而在于“女性歌唱连接一切”[4](P20),青年诗人的缪斯该是“可怕的老妇”,这老妇的力量足以剥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此后威廉斯的诗歌常以女性为题材,突出女性形象对改造诗歌艺术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一切很清楚地勾勒出威廉斯早期诗学中女性观的触发、孕育和发展。
二、威廉斯早期诗学中女性观的核心与本质
威廉斯诗学中的女性观是在他与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男性诗学观的交锋和抵牾中逐渐明朗、完整和系统起来的。庞德是美国20世纪意象派运动的奠基人和旗手,也是整个英美现代派文学运动的主将。与庞德相比,威廉斯在20世纪初期很不起眼,只闻名于很小的范围内,可谓文运冷落。但威廉斯是一位敢于打破创作常规的诗人,一位试图在诗歌领域中捍卫“自我”、革新传统的诗人。在当时奉行“人性就是男性”[5](P136)的人文环境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诗人要想成功便常常意味着必须先屈服,即只能作为“妻子”或“女儿”而存在,直到日后熬出头,归化为男性社会的一员,就像布鲁姆认为后来者“遂重新评价他的先驱,最终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塑造他(修正)”[6](P5),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弑父”或本我的“升华”。因此,威廉斯若想保存自己的本真,则只有违抗传统的规范与父权制的束缚,自由充分地表达他的“自我”。他努力从男性主义的创作模式和陈规中逃离出来,运用书写“女性的自我”的美学策略来打破常规抵制权威,最终以独特的诗风和格调唱出了自己的歌。他的“自我流放”实际上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房间”。
庞德在其诗歌创作中几乎没有一位女性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正面的形象:她们或纵欲,或空虚,或迷信,或脆弱,有的甚至因被诗人“道具化”处理而成为失去人性的木偶。诗人对她们的态度则无外乎斥责、鄙夷、嘲讽、忽视,至多也只是居高临下、无关痛痒的怜悯。这与他诗中的正面男性形象如圣杯骑士等形成鲜明的反差,暴露了他与女权主义宗旨相悖的反女性主义倾向,反映了他传统的男权主义视角。庞德这一诗歌特点从本质上讲源于他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性别观。
与此相反,威廉斯的诗歌平视女性,尊重女性,让女性有自己的声音,如诗歌《一个黑人妇女》:“带着一束金盏花/包在/一张旧报纸里/她捧着它们/光着头/两条/肥厚的大腿/使她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她行走时/瞧着/路上经过的/商店橱窗/她是什么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大使/来自一个长满美丽的/双色金盏花的世界/她声称/除了/在街上行走/就不知道干什么/她捧着那束花/像清晨的/一支火炬。”
与庞德的诗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廉斯这首诗歌中的主人翁是个真实的女性,她有着肥厚的大腿,显然不是少女;她光着头,她的花用旧报纸包着,显然不是传统作品中的美女或女神。她是村妇老妪,来自长满美丽金盏花的另一个世界。她来到了城市,瞧着路边的商店橱窗而不屑再顾,代表文明的旧报纸遮不住来自大地的金盏花的美丽。她不知道干什么,只知道在街上行走,而这行走本身就已足够,已具有非凡的意义。她有勃勃的真气,她的行走是生命力的流动,她手中的花束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为这苍白无力、了无生气的城市驱除了黑暗,迎来了黎明。这样一个村妇老妪式的黑人妇女形象比庞德的月桂女神的少女形象远为现实、真实,词朴而意诚。
从本质意义上讲威廉斯这首诗完全抛弃了男权主义诗歌的传统主旨和格调,他让母性的、泥土气的、粗俗的女性形象直接发声,拥有权力,决绝地否定以男性为主宰的文明将女性有违人性地物化的做法,而对真实饱满的女性的回归表达了殷切的期待,发出了深沉的呼唤。
威廉斯认为真正的女性象大地母亲,是生命的源泉,富有活力的创造者,而非男性欲望和意志的被动接受者。这种女性既有精神性,又有物质性。威廉斯的诗歌刻画女性形象时总是将之现实化、客体化,而拒绝将之抽象化。在诗歌创作中威廉斯通过认同和赞美历来无权势的、被贬低的、被凌辱的女性来表达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解构。正如女权主义者伊莱恩·肖华尔特所说:“女权主义批评就是要重新确立经验的权威。”[7]现实的生活经验的世界是男性女性共有的,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应该终结,女性也顶半边天的社会新秩序应该建立。威廉斯所创造的女性形象能坚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充满着反抗精神,追求幸福和平等权利,他对女权主义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立场表达了由衷的同情、理解、支持和赞赏,这是威廉斯诗学中女性观的核心和本质。
三、威廉斯早期诗歌中的女性观诗学实践
威廉斯早期诗学中女性观的孕育和发展与其相关的诗歌创作是相互促成、互为因果的:他的女性观的孕育和发展指导引领了他的关于女性诗歌的写作,而后者的写作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充实和完善。于是威廉斯早期诗学中的女性观的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他有关女性的独树一帜的诗歌渐成大观的过程。他的女性观诗学的具体实践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诗歌的题材:脚踏大地的底层女性
威廉斯常常选择自然生活中的女性作为其诗歌的母题。威廉斯曾经说过,他“试图尽量准确地、有节奏地描写所发生的事情,但不是丁尼生式的诗歌形式,不是普罗旺斯的女性,而是与我同时同地的女性”[8](P48)。《一个穷苦的老妇人》(“To a poor old Woman”)[9](P275)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女性。
《一个穷苦的老妇人》呈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老妇人的意象。一个在街头专心吃李子的穷苦老妇景象深深触动了诗人的心,诗里渗透着作者对穷苦老妇的理解和认同,但他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通过描写老妇人吃李子的神态与感受来表达。其角度从远到近,从轮廓到细节,一直深入到老妇人的内心。第二诗节三句平淡重复的口语“她觉得它们味道真好/她觉得它们味道/真好,她觉得它们/味道真好”通过跨行处理,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效果。诗句的节奏与老妇人的脚步节奏刚好合拍,这种节奏的重合使读者内心受到感应,似乎进入到老妇人的内心,与她一同体验简单的快乐。在第三、第四诗节,作者使用嗅觉意象来描写这位老妇人,沉醉其中的熟李子味道——“熟李子的慰藉,似乎弥漫在空中”,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首诗的人物形象很简单,通篇采用客观描述,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刻画吃李子的老妇人,使其在诗里成为审美意象,成为打动读者心灵、体验作者感情的富有美感的意象符号。“美感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情感,是一种以净化了的情感为特色的包括领悟、认识、向往、意志在内的综合反应”。[10](P128)这首诗的意象带给读者的美感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和真挚的情感,读这首诗能促使读者更加热爱生活,同情与关注女性,并根据自己的经历见闻来补充新的认识,使女性理所应得的地位与真切自然的形象得以彰显。
仔细揣摩,我们发现威廉斯笔下这样的女性常常是不被社会所包容的、男人们正眼“看不见的”那些边缘人物。她们孤立无援,“与主流社会和精英意识相对疏离”,在生存的夹缝中惘然四顾,缺乏归属感,经历着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磨难,成为男性社会中的“畸零人”[11]。然而威廉斯能将这样平常的老妇作为歌唱的对象,对她倾注真诚的关怀,理解她,尊重她,描绘中绝无揶揄的成分,这就使他与众不同,有别于其他男性诗人,尤其与庞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庞德认为艺术家应是精英分子,艺术家所讴歌的应该是精英主义,而非无知识的平民,特别是女性。
庞德的诗作的女性形象与威廉斯的迥然不同,它们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精英分子眼中的女性形象。[4](P27)如庞德在他的《白罂粟》中,将女人比作罂粟花,认为女人是娇美靓丽的,也是神秘而充满诱惑的:白色的罂粟花,沉重地负载着梦,/我渴望着它们的唇瓣。/当我瞧见它们隐匿/出没在阴影之中/它们是白色的。/如果有人用她眼中古老的渴望瞧我,/我将如何回答她的眼色?/我已经追随森林中的白人。/是的,这是一次长的追寻,/这是一次焦渴,当我看到它们/在挺立的树丛中消逝,忽隐忽现。/呵,当爱情在心中熄灭,/人们何等悲痛。[12](P37)
白罂粟代表着令人迷惘的诱惑,它“沉重地负载着梦”,诗中“隐匿”,“出没在阴影之中”,“忽隐忽现”,“消逝”,都暗示了女性的神秘,难以捉摸,不能企及。这形象与前所提及的月桂女神不是如出一辙么?庞德在另一首诗歌《咏叹调》中也这样描写女性:我的爱人是深深藏在/水底的火焰。/我的爱人是欢乐的亲切的/我的爱人象水底的火焰/难寻踪影。火焰是炽热而灼人的,水底的水是冰冷和幽暗的,“水底的火焰”是一个悖论式的超越生活本身的意象——水的冰冷和火的炽烈并置在一起,跳动的火焰是美丽的,却置身于水底,让人无法接近,其情何堪。因此庞德诗歌中的女性是美丽的、神秘的,同时又是缥缈虚幻、非现实的。从本质上讲,这种女性形象其实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女性的否定。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将女性升华为男性以及整个人类的月桂女神②,还是将其幻化为引诱人类沉湎于情欲的“罂粟”,都是对现实女性的贬低、扭曲和排斥,都是把女性视为他者的男权传统的表现。庞德无疑是这种传统的秉承者和推波助澜者。
威廉斯选用脚踏大地的底层女性作为他诗歌的题材,把她们的形象具体化、现实化、客体化,而拒绝将之理想化和抽象化,他认同无权势的、被鄙视的、被凌辱的女性,实质上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的美国诗坛起到了发聋振聩、引导潮流、另辟天地的作用,其更新性别观念的意义不可低估。
2.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丰硕、健康的劳动者
威廉斯认为现实生活中纯朴普通的女性,有着无须粉饰雕琢的美,有着无穷的超越平凡的诗意:不事张扬,没有崇论宏议,原汁原味,引人入胜。威廉斯将这些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以白描手法铺陈,对细节的落笔也更精致入微,如诗歌 《下层人的肖像》(“Proletarian Portrait”):“一个高大粗壮、没戴帽子的年轻女人/腰系围裙/脑后头发溜光/站在街旁/一只套着长筒袜的脚/踮在人行道上/手里拎着一只鞋。她/朝鞋内细瞅/抽出硬纸鞋垫/寻找那颗/扎痛她脚的钉。/”这首诗歌描写的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按传统的标准,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大街上脱鞋寻找扎痛脚的钉子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场景进不了诗歌的圣殿,但威廉斯把它请了进来,因为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美国下层劳动妇女的内在和外在形象。这个没戴帽子、腰系围裙的青年女子,尽管生活困苦,却健康、自在、率性、可亲,全然没有男性主义熏陶下有产阶级女子的那种扭捏作态和矫揉造作。这样的女子是真实可敬的,这种女子形象只能出自摆脱了男权主义的束缚、能平视女性的诗人笔下。
正如艾伦·奥斯特罗姆(Alan Ostrom)所评述那样,威廉斯的诗歌描写的都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如普通的花朵一样的事物”[13](P3)。因为专注于事物本身,威廉斯的诗歌又常被称为“事物的诗歌”(the poetry of things)③。很多批评家认为威廉斯的诗歌具有“反诗歌性”(antipoetic)[14](P76),这也就意味着威廉斯抛开了那些不必要的文学隐喻,而通过常人的眼和笔去发现和表达现实社会与自然环境中日常的男男女女和他们诗意生活的美。
3.诗歌创作的视角:女性感官和经验模式
威廉斯认为人类感知世界的模式有性别的区别:男性强调理智和逻辑,追求完美的结局,采用因果关系、单向线性的思维模式;女性强调情感官能,追求愉悦的过程,采用网状关联、多点交叉的思维模式。在父权制的社会中,长期以来,男性模式得到推崇和倡导,占有主导地位,女性模式遭到贬低和拒斥,处于受压制的境地,结果导致男性趾高气扬,女性俯首帖耳,以至于当今某些女权主义者为了求取男女平等,竟然主张女性消除自己的性别特点,放弃自己的思维模式,完全认同男性,希翼在男权主义的世界里谋得一席之地。威廉斯坚决反对这种饮鸠止渴的做法,主张男女有别,两者平等互补,而在当今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尤其要发挥女性模式的特殊功效,以弥补男性模式的僵化和局限。如果说男性是原动力,女性则是原动力的基点。男性不断地追求,其后果是远离大地去凝视星空,耽于抽象的遐想,而女性则立足于大地,拥抱具体的事物,延续物质的生命,倘无女性基点的维系,男性只怕都成为随风而逝的无根的飞蓬。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女性的认知模式更浑朴自然、切合实际、亲切灵动。威廉斯在早期诗歌的创作中抛弃了强烈的主观抒情的浪漫派诗风,又避开了冷静理智的形而上的玄思,而致力于构写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客体主义的意象诗,这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即是对女性认知模式的认可、接受和实践。
在《伟大的性螺旋》(“The Great Sex Spiral”)一文中威廉斯还提出以富有活力和研究成果的女性心理学来充实、纠正或取代男性心理学中的陈旧和错误的观点。[4](P36)他用与身体有关的语言来表达男女生理上的差异所造成男女身体体验、心理认知和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女性能孕育多产,故而愿意宽容接纳,善于多元相谐;男性以进入霸占为旨,因此重在征服称雄,两元对立。要破解二元对立,完整地看待世界,合理地处理生活,男性必须克服自我中心的偏执性和独裁性。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理性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统治正是遵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重理性,轻情感,重精神,轻肉体、以男性压女性来确立其优势地位的,因而书写女性,包括她们的身体,也就成了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男性传统、缓和二元对立、反对形而上的一项重要的写作策略。威廉斯在他的诗歌中真诚地歌颂女性和母性,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叙写女性的感官经验,客观切实地描绘女性的容貌举止,正是对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热情呼应。作为男性诗人而采用女性的视角和感官经验创作,威廉斯的诗歌不仅是对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的冲击和纠偏,也是对女性主义书写的充实和丰富。诚如威廉斯所说,男性是含糊的一般论者,女性是具体的思想者。男性的理智逻辑模式只有与女性的感官经验模式相结合,我们眼中的世界才富有立体感,生活才五彩斑斓。
4.诗歌的语言:感官性,经验性,片断性,多元性,触摸性
威廉斯的诗学包含平正公允的女性观,他诗歌创作的大量题材是底层女性,他的女性形象是丰硕、健康的劳动者,他的视角常是女性感官经验模式,那么他的诗歌语言具有强烈的感官性、经验性、片断性、多元性和触摸性等特征也就是循理顺章的事了。事实上威廉斯采纳这种语言风格是有意为之,他要用这种与女性相关联的具体、质感的语言来摧毁男性语言的逻辑形式和思维结构的束缚,实现包容的、民主的、多元的创作空间。
威廉斯描写女性的诗歌拥有大量新鲜独特的感官性的意象,其中多为视觉意象,也有不少能唤起读者丰富联想的其它感官意象,如触觉意象,譬如在《寡妇春怨》开首有这样的诗句:“我的院子是悲伤的海洋/新草遍地/火焰般闪耀/一如既往/今年凄清的火焰/……”这里“海洋”、“新草”、“火焰”都是视觉形象,但同时也是触觉意象:海浪起伏给人以悲伤的感觉;新草似火,过去使人感到温暖,今年却让人觉得凄清。
威廉斯在《女士肖像》[18](P129)(“Portrait of a Lady”)中将妇人的“双膝”比作“温煦的南风”,这是纯粹的触觉意象。南风无影无踪,肉眼无法见到,但它吹拂在身上,给人温软的感觉,以它形容贵妇人的双膝,确是比较奇特的意象,但也不失为贴切。在这首诗中,诗人把“你的大腿”、“拖鞋”、“膝盖”等细节放大,赋予它们不平凡的意义,以吸引人们注意,启发人们深思。可以说正是这种诗性语言意识的觉醒——这种在女性、身体和诗歌、语言之间统一和谐意识的加强,不仅使女性在性别意识上获得了一种诗性的彻悟和回归,而且大大提高了20世纪早期美国关于女性诗歌写作的艺术品质。这种女性特征的语言是对男性理性语言的有限性的突破,只要它存在并与男性语言相结合,诗歌语言的诗性便进入了无限、统一、圆融之境。
威廉斯想象一个全面的生成于和发展于女性的物质经验的敏感性。虽然男人不可能感受女性的意识,但这种敏感性可以通过艺术,通过追求具体、客观、确实的努力来获得,专注的想象和创作可以使诗人置于女性和母性的境地。
女性是性、灵魂和物质的结合,她们能体现存在和事实的真实性,因而她们的语言构成了威廉斯诗性语言的重要部分:诗歌的语言应该有女性化的成分,女性的语言表达是具体的,肉质的。对女性主体性和语言的肯定是对鄙视女性为“无本质”“无灵魂”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批判。作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男性诗人,威廉斯在他的早期作品里积极探索“走进”女性世界的可能性及其含义,他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语言的尝试本身也表现了男性性别的模糊化:不再是逻辑的、理性的、逻各斯中心的,而是含糊的、多元的、不连贯和颠覆的,意义不再确定无疑。这种语言具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气息,既是从语言和性别关系上对传统的男性权威的解构,又是对健康新鲜、富有活力的一种新型诗歌语言的建构。以历史的眼光看威廉斯的语言革新和实践上的方向是正确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对同时代的人及后来者是有启迪意义的。
四、结 语
威廉斯是个男性诗人,但是他具有开明的女性意识;他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对男权主义的批判和与女权主义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女性观,并通过诗歌实践予以检验和充实。他诗歌美学的弃月桂女神、取村妇老妪的倾向,他诗歌题材的女性形象,他诗歌视角的感性经验模式,他诗歌语言的直观性和质感性,都是20世纪早期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碰撞搏击的产物。威廉斯和他的诗歌本身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在女权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两性关系的剧烈的变革,从更广泛的层次上说,这一变革是一战之后整个西方文化体系重大调整的一部分。在这调整中,种种旧的价值观念,包括“月桂女神”所代表的“天使”理想在内,都遭到现代观念的坚决挑战。作为文化斗士和诗人,威廉斯热情地参与了反对权威的文化批判,在其早期的诗歌中抵制了以庞德为代表的男性传统,探索了文化建构的性别融洽问题。他在女性与文学之间关系上的独到见解与今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旨是一脉相通的,无论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或一桩文学事件,威廉斯早期诗学中的女性观和相关诗歌创作所做出的开拓性的贡献都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向后现代主义发展开辟了途径,值得我们研究和铭记。
注释:
① 狄金森的诗作大量采用了破折号和大写首字母,当时的编辑认为这不符合规范,要求狄金森予以改正后才能刊出,而狄金森坚持己见,这也许是她绝大部分作品生前未能发表的缘故之一。
② 事实上,“月桂女神”只是男性心目中“天使”理想的化身。
③ 之后发展成威廉斯的诗学观念“思想只在事物之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
[1]Kerry Driscoll,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d the Maternal Muse,UMI Research Press,1987.
[2]Elaine Showalter,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women,Literature,and Theory.New York:Random House,1985.
[3]R.Emerson,Emerson’s essays,New York:Contin uum,1982.
[4]Linda A.Kinnahan,Poetics of the feminine:authority and literary tradition in William Carlos Williams,Mina Loy,Denise Levertov,and Kathleen Fras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5]W.Martin,TheCambridgeCompaniontoEmily Dickins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6]哈德罗·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7]Showalter,“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Critical Inquiry,Special Issue on Writ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1981,(8):181.
[8]Litz A.Walton and Christopher MacGowam,eds.,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Vol.I,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6.
[9]William Carlos Williams,Collected Earlier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6.
[10] 夏之放.文学意象论[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11] 周丽华. 寂寞将何言[J].外国文学,1998,(4):114.
[12] 申 奥.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3]Alan Ostrom,The Poetic World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6.
[14]Charles Doyle,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
Abstract:The view of female gender in Williams’early Poetics ha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breeds,it is the core and essence to agree feminism to establish a new social order;his poetry creating open a new way for American modern poetry to postmodern poetry gradually.
Keywords:W.C.Williams;Pound;view of female gender;image of female gender
(责任编校:文 一)
On the View of Female Gender and Poetry Creating in W.C.William’s Early Poetics
WU Xin-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I106.2
A
1000-2529(2011)01-0112-06
2010-05-03
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11YS104)
武新玉(1979-),女,江苏镇江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