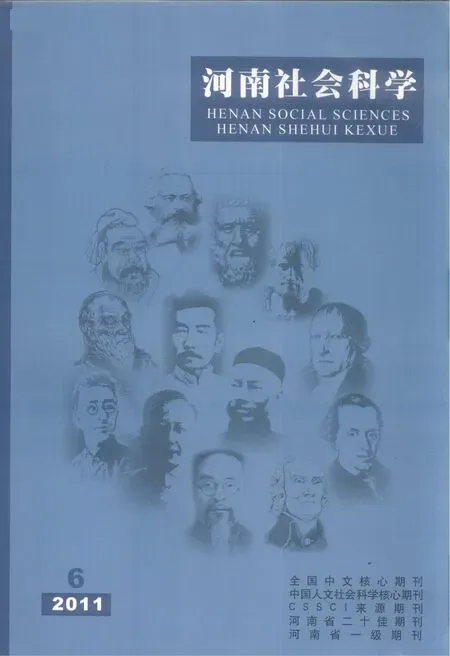《诗经·关雎》主旨近当代歧说之辨正
王书才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诗经·关雎》主旨近当代歧说之辨正
王书才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近当代学术界在阐释《诗经·关雎》主旨方面,“恋歌说”和“贺婚说”颇为流行。依据周代金文文献和先秦礼仪制度,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辩驳,主张此篇当为歌颂夫妻和谐相处、婚姻幸福的颂歌,本是专属于天子诸侯和其他特殊贵族的“房中之乐”。
《诗经》;《关雎》;主旨;辨正
《关雎》一诗的阐释,如果从孔子赞叹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算起,已经有两千六百多年;即使从西汉四家诗说算起,也已经历时两千来年。对于《关雎》的研究,按照学者观点的重大转变程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汉唐阶段、宋元明清阶段和近代当代阶段。其实无论是汉唐还是宋元明清,当时的学者都很重视文献学方面的基础,重视“知人论世”,即使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也不像近代一些学者那样不顾当时的文化背景从而强为新解。
汉代四家说《诗》者中,毛诗学派坚持认为《关雎》是颂诗,是赞美“后妃之德”(《毛诗序》)的。齐鲁韩三家则一致认为《关雎》是篇“刺诗”,是用来讽劝和提醒周康王不得贪于女色而要勤于政事的,“韩、齐、鲁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故司马迁、刘向、扬雄、范晔并祖其说”[1]。
四家对于《关雎》主旨的解释,在讲究创新的宋代就受到了辩驳和否定,因为齐鲁韩三家所讲的讽劝周康王一事,只是属于用诗而非作诗,无法用来揭示《关雎》创作本旨:“若曰关雎止刺康王,非咏文王之事,则不得为正风;圣人删诗岂以刺诗为一经之首耶?”[1]而毛诗所谓赞颂王妃美德之说,也得到了后人的指正和补充,补充者认为此篇不是赞叹王妃心怀阔达、毫不嫉妒、诚心诚意为天子物色辅佐事业的淑女与自己一起相夫教子的,而是赞叹周文王与太姒二人夫妻相处和睦,犹如琴瑟般和谐、钟鼓般唱和,从而歌颂天子和后妃能够修身齐家以作天下士大夫们的优秀楷模的。欧阳修《关雎论》力驳《毛诗序》,批评汉宋解释者错会大义:“为关雎之说者,既差其时世,至于大义亦已失之。盖关雎之作,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然雄雌和鸣,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毛、郑则不然,谓诗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妒忌之行,而幽闺深宫之善女,皆得进御于文王,所谓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众宫人尔。然则上言雎鸠方取物以为比兴,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则终篇更无一语以及太姒。且关雎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于人情。古之人简质,不如是之迂也。”[2]元明清三代作为官方经学定说的朱熹《诗集传》,也接受欧阳修等时人新说,认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3],指出诗中男女乃是周文王和妻子太姒:“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3]直到清代,说《诗》之家,仍旧判断《关雎》乃书写文王与其后妃之事之情,如陈启源虽主张“淑女不得指后妃也”,然而沿袭毛郑汉人旧说,云《关雎》乃“文王后妃所自作也”,“古者朝有外职,宫有内职。外职旷而天工不举矣,内职缺而阴教不修矣。故天则播五行于四时,而月生焉;王则齐家以治国而后妃主焉。嫔御以下,皆所以佐内理者,如星之助月光也。后妃无妒害之私,极诚求之切,可以章文王刑于之化周之兴也,有自来已。故关雎者,后妃求贤于内也”[4]。
清代以喜好创设新说最为著名的学者毛奇龄,也极力论证“淑女”即是“后妃”,思淑女就是文王思慕后妃,不是后妃之外另有淑女,其说对于拨开汉儒所散布的解经迷雾颇有力度:“《小序》所云‘思得淑女’者,是思得后妃,不是后妃又思得淑女。此系毛、郑误解小序。”[5]
古代诸多学者在此诗作者的身份认定上很不一致,或言系后宫女子所撰,或言周初贵族毕公所撰,或言后妃自撰;对于诗的主旨,或言赞美后妃不嫉妒的美德,或言称扬后妃积极进贤,或言借后妃之德歌颂文王善于教化,或者认为是咏叹此诗以讽劝好色惰政的周康王。可是有一点是古代学者并无分歧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诗里的男女主人公,是天子与其妻子,绝非一般士大夫,更非平民百姓。古代学者之所以如此一致,是因为他们知道,从诗末最后两句“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来看,诗里的男女主人公只能够是天子、诸侯与公卿贵族。而在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上属于周南的受到歌颂的又只能是文王等诸侯甚至天子,正如郑玄《周南召南谱》所谓:“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6]此一封地属于周公、召公及其后人,一直到西周东迁。
而从《诗经》本文来看,一共7篇16次提及“钟”字,“钟鼓”二字作为名词一起出现的有8次,均是天子和国君在场而铺设如此大乐。《唐风·山有枢》“尔有钟鼓,弗鼓弗考”,《小序》云其“刺晋昭公也……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6]。《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小序》云其“刺幽王也”[6]。《小雅·楚茨》:“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虽从全诗字面看不出《小序》所谓“刺幽王”之意,但全部所写乃是周天子祭祀祖先神灵的过程和场面,是没有疑义的。《小雅·宾之初筵》:“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小序》云,此诗乃卫武公所撰,讥刺周幽王治下的朝廷风气:“幽王荒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6]大雅·白华》:“鼓钟于宫,声闻于外。”毛亨认为全诗意在讥刺周幽王之后褒姒,郑玄认为此句比喻“王失礼于外,而下国闻知而化之”[6]。《大雅·灵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孟子曾经引用过它以强调与民同乐的意义和价值。《小序》称其是“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6]。郑玄认为周文王当时以天子身份建此灵台,万民欢庆。
在先秦,拥有贵重的乐器和享受某种音乐是有等级限制的。鼓乐,士庶皆可有之,《论语》里已言“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以不论。可是钟器,就非特权人物不得拥有的。在西周春秋时期,一般大夫没有天子和国君的赏赐,还是不能享用击钟之乐的。晋国大夫魏绛媾和戎狄,强盛晋国,为晋国立了大功,晋君赐予钟磬“,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7]。孔颖达云:“以魏绛蒙赐,始有金石之乐,知未赐不得有也。”[7]
再从出土文献来看,《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了359件青铜钟器,属于西周中晚期的有119件,其主人可分三类:一是天子诸侯,如周厉王、鲁君、纪侯、秦君、邢侯、齐侯、邾君、楚王、虢叔等。二是公卿,如周朝的南宫乎、芮公、毕公、单伯等。这两类占了钟器主人的绝大多数,铸钟是为了祭祀、自娱和娱宾。三是天子诸侯有所重赏的贵族,他们铸钟是为了纪恩。春秋时期的钟器有117件,绝大多数属于诸侯所有,其主人有宋公、秦公、邾君、齐公、楚王、许子、莒君、蔡侯等,其余主人为公卿和王子,如邾国太宰、齐国鲍卿、徐王之子等[8]。
综上所述,可见一直到春秋末期,钟鼓齐鸣仍是天子、诸侯和特殊贵族才能享受的器乐,非一般贵族所能够僭越享用。一直到战国时期,打造乐钟仍是万乘之国的君主需要慎重思量的大事。《殷周金文集成》所录战国钟器的主人如曾侯乙、越王、楚王也皆是王侯。
所以可以说,《关雎》诗尾所谓“钟鼓乐之”,绝非夸张性的临时取悦女方之言,而是一位天子诸侯至少是公卿贵族对新婚妻子表示亲爱的由衷举动。
而自从民国年间起始,某些学者未能认真考察古人礼仪规范,也未能深入了解先秦人们所生活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便以后世礼崩乐坏、不再讲究君臣礼仪的今人风俗去臆断二三千年前的文学作品的主旨,往往所得观点初看去头头是道,细究起来却颇有破绽。
自从“五四”以来,学者所创立的新说,大致有以下两项:一是认为《关雎》是书写自由恋爱的歌曲,证据是开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数句;一是认为《关雎》是婚礼上的祝贺歌曲。其实这二说都与此诗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大相矛盾。
先看“恋歌”之说能否成立。诗里是写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等情形和心态,可是能否根据诗里有男子思女就一定可以断言它就是一首恋诗呢?诗里歌里有一男一女就算是恋诗恋歌吗?恐怕未必。所谓的恋爱,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应当是“男女互相爱慕”和“男女互相爱慕的行动表现”[9];按照《韦氏高阶英语词典》的定义,“恋爱”是“attractionthatincludes sexualdesire”,“Whenpeoplebegintofeelromanticlove foreachother,theyfallinlove”[10]。可是诗的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然后才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于异性的思慕没有具体明晰的对象,是见到动物双双对对,想到君子应当娶得一位淑女。后面也没有详细叙说男子如何去追求“淑女”,只讲他“求女”未成之前的担心和“求女”成功之后的欣悦。作为一位拥有琴瑟特别是钟鼓之类高档乐器的贵族甚至是诸侯或者国君,难以想象他会像《郑风》、《卫风》里那样“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卫风·氓》)或者“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一样亲自出马当面向女子求婚;再者《郑风》、《卫风》这些诗篇是在那些男女当事人已经超出以礼相婚的年龄,官方准许其“奔者不禁”情况下产生的。贵族男女还不至于男方老大难娶、女方老大难嫁吧。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一般贵族还是要有贵族的做派的,《诗经》里两次强调男女婚姻当有媒氏作为中介加以说合才算合礼:“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豳风·伐柯》)“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直到曹魏时期,曹植《求自试表》还提到:“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所以很难想象,《关雎》是一首书写恋爱的诗篇。如果是一首恋爱诗歌,它和孔子深恶痛疾的“郑卫之音”还有什么区别呢?孔子对《关雎》赞不绝口,对《郑风》、《卫风》连连诋毁,恐怕更是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古人的“求女”就是派媒人向女方求婚,对于自己将来结婚的对象,在求婚之前自然也要到处搜集信息,访探哪家女子贤惠美貌,然后征求父母之命,再派媒氏前去代男方求婚,这个过程也可以叫做“求女”。在整个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男子也会怀抱唯恐失之的担心而寝食不安。可是这种尊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以礼相求”和“淫奔”模式的“自自媒”的“求女”,其过场是大为不同的。作为一位战国时期的上层贵族,屈原在其《离骚》中曾生动地描写了他三次求女从念头涌起到愿望落空的心态变化,很能够与《关雎》一诗里的男主人公的情绪作一相互诠释:“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11]离骚》里面的男主人公在求女过程中的渴盼、犹豫、狐疑、烦恼、担心、失望,一点也不比《关雎》里的男主人公的心情轻松,可是在诠释《离骚》时,几乎没有人将此段解说成是一段恋爱情事,那么为什么遇到同样的书写男子欲配佳偶并且婚前以礼相求、婚后琴瑟相合亲密友爱的作品,却往往倾向于要解释为一首恋歌呢?想来是出于以今例古、投合读者与学子心理的需要,可是此解却忽略了这首诗篇与《郑风》、《卫风》等恋爱歌诗在当事人地位身份、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迥然差异。
第二种近现代的创新之说,是认为《关雎》是婚礼上的祝贺歌曲。从诗篇的字面看去,这一阐释较之“恋歌”说显得更加合理些,加上《周南·桃夭》热烈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祝愿般的歌词相互印证,几乎难以对其非议。可是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孟子所倡导的“知人论世”说还是要坚持贯彻的。《仪礼·士昏礼》详细地述说了从纳采问名到迎娶再到新妇庙见的整个过程,丝毫未曾提及婚礼上奏乐放歌[12]。《诗经·大雅·韩奕》描写渲染婚礼车马之众、诸娣之多,亦不言音乐歌舞[6]。再者,婚礼不乐,不加庆贺,是当时礼仪的常识和通则。《礼记·郊特牲》明确讲道:“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人之序也。”[13]至于为何婚礼不用乐不庆贺,古代学者有各种解释。《礼记·郊特牲》云:“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孔颖达言:“若其用乐,则令妇人志意动散,故不用乐也。”[13]也即唯恐妇人听着音乐鸣奏之声,受其影响,在婚礼场合会做出一些不得体的动作,影响其内敛含蓄柔美谨慎的淑女形象,所以不演奏音乐。古人婚事不用乐,也当与当时的交通等密切相关,男方女方相距甚远,男方父母在男子前去迎亲前,要对他进行嘱咐和祝愿,然后男子与迎亲队伍风尘仆仆前往女方家,在女方那里还要举行拜庙仪式,女方父母亲戚还要对女子进行临行前的教诫和祝愿,再长途颠簸返回男方,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所以婚礼只好在黄昏时举行。再经过一系列繁多的成亲仪式,天色应该已经入夜,所以不可能像后代特别是今人那般早上迎娶、上午归来,还有充裕的时间锣鼓齐鸣、歌舞喧闹之声震耳欲聋。至于“昏礼不贺”的原因,《礼记·郊特牲》认为是出于婚姻乃“人之序”的考虑,也即“昏礼,舅姑授妇以室,子有传重之端,则亲有代谢之势,人子之所不忍言也,故不贺”[14]。也就是出于对人类新陈代谢规律的一种讳言,以表示对于长辈心理的尊重。
对于古人敬重长辈特别是父母心理的做法,今人恐怕觉得很隔膜,很遥远,如今婚姻当事人一般不会拒绝张罗鼓乐和亲友祝贺,父母也不愿冷落儿女的热望和喜悦,所以往往要大张旗鼓嬉笑沸天。这是现实,可是用这种现实景象去臆想古代贵族也是与今人举办婚礼一般,无视先秦两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恐怕不算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那么,《关雎》既不是恋爱之歌,又不是婚礼庆祝歌曲,它是什么性质的歌曲呢?对此,汉人毛亨、唐人孔颖达、宋人欧阳修和朱熹均认为《关雎》在内的《周南》、《召南》属于后宫之乐辞也即所谓“房中乐”。《仪礼·燕礼》郑玄注云:“《周南》、《召南》,《国风》篇也。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故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12]言本是天子与诸侯专享的歌曲,一般士大夫也可以在乡饮酒场合上分享。其内容自是抒发男女婚姻发于性情,成之以礼,婚后恩爱和谐的人生幸福感受与憧憬,表达的是社会各个层次人们共同的心声和追求,所以最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而且正如《礼记·昏义》所强调的,男女结成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是文明社会组成和维持的基础,婚姻幸福和谐,夫妻才会有情义,父母子女才能有浓浓的亲情,社会才能维持正常发展,君臣上下才会正常相处,所以婚姻之礼是一切礼仪的根本:“昏礼者,礼之本也。”[13]其本身如此重要,被置于《诗经》之首加以突出强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雎》是讲婚姻的,可它不是贺婚诗歌。它是作为歌颂夫妻和谐相处、婚姻幸福的颂歌而在天子诸侯和贵族宴饮场合上进行演唱的,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1][宋]苏洵.诗集传(卷一)[M].南宋淳熙七年苏诩筠州公使库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2][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一)[M].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
[3]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三十)[M].清咸丰十一年广州学海堂刊《清经解》本.
[5][清]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卷一)[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
[6][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周]左丘明,[晋]杜预,[唐]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0]韦氏高阶英语词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1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汉]郑玄,[唐]贾公彦.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清]孙希旦.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I206.2/.4
A
1007-905X(2011)06-0145-03
2011-08-11
王书才(1963— ),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