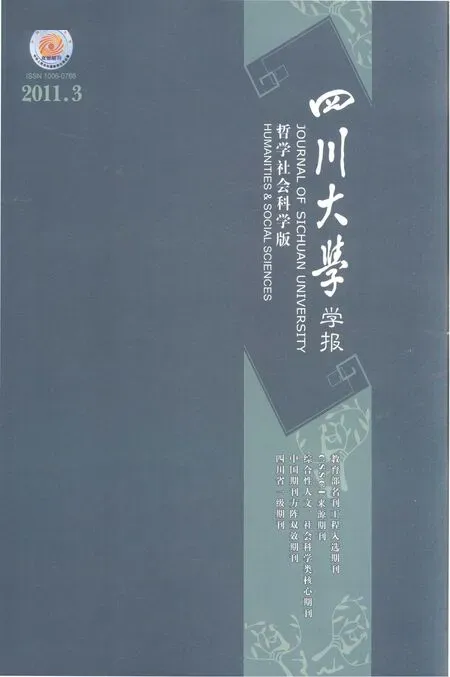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石 硕,邹立波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陕商作为历史上康区汉藏商贸的主要开拓者,直到民国时期,始终在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其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康区,对汉藏经济交流的贡献颇大。学术界对康区陕商的研究,大多侧重从经济角度,集中探讨具体的经商活动及其在汉藏贸易中的作用[1][2][3]。不过,陕商是以内地商贾的身份进入康区从事族际经商的,在与藏民的商贸交往中,陕商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交易网络,并通过主动强化自身与藏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族际互动,不断地调适经商方式,开拓更为广阔的藏区市场,无形中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沟通与了解。由此,当陕商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将内地事物与生活习俗引入康区的同时,也入乡随俗地吸纳藏民的生活元素,积极参与到康区社会生活中,成为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的实践群体,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的交融。
一、从“炉客”到“口外客”:近代康区陕商及其商贸网络的构建
明清以来,地域性商帮均有其经商区域,陕商的商业实力虽不及徽商、晋商之盛,面向西北、西南广大边疆地区的经商流向却颇具特色。康区作为连接内地与西藏商贸往来的通道,明末清初以降作用日益显著,官营茶马互市的衰落与汉藏贸易民间化程度的加深,吸引了包括陕商在内的大批内地商贾前往康区经商。近代康区汉商以陕、川、滇三省商贾为主,而陕商经营的广度与深度均是其他籍贯的汉商无法比拟的,且其具体的经商方式颇具独特之处。对于在西南地区经商的陕商,民间素有“一川客,二炉客,使不得的口外客”的谚语[4],表明陕商因经商地域的不同,有川客、炉客与口外客之别,善贾者多为“川客”,其次为“炉客”,经商实力不济者只得充作“口外客”。“客”意含非本土,体现出商贾的社会流动习性。陕人入川经商,以盐茶为大利。四川井盐主要面向贵州等地市场,经营盐业者有不少是陕籍“川客”,举凡井盐产区之自贡、射洪、三台等地皆设有陕籍商号。而茶之利则非边茶莫属。自明末清初,汉藏贸易中心逐渐南移至打箭炉(1908年改名为康定,沿用至今。)与松潘,南路边茶与西路边茶①明代嘉靖年间,川茶运销实行“引岸”制度,引票分“二边”(黎雅、松潘)“一腹”(四川内地),遂有“西路边茶”与“南路边茶”之别。西路边茶产自灌县、大邑、安县、什邡等地,以灌县为制造中心,销往岷江上游及甘青藏羌地区;南路边茶以雅安为制造中心,经康定运销西康与卫藏各地。成为四川边茶贸易的主要销售流向。南路边茶产地集中于四川雅安、天全、名山、邛崃、荥经五县,操茶业者,俗称“五属茶商”,其中以陕籍商贾经营实力最为雄厚。直到民国时期,陕商店铺约占半数[5][6]。川茶销藏仍然是近代汉藏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茶是藏族日常生活必需之物有直接关系,清人有诗云:“以有易无犹古制,谁居奇货是茶商。”[7]茶居“奇货”之列,因陕商以茶为其主要贸易种类,故而民国时期有人也认为:“陕西商人得深入康省即以运茶故也。”[8]
明末清初,汉藏商贸交易场所逐渐向西推移至大渡河以西的打箭炉。内地商贾云集,打箭炉遂因商而兴,逐渐成为川藏贸易的枢纽与中转站。对康区着墨不多的《西藏纪程》(成书于康熙末年)特别提到:“西安府作买卖人在此(打箭炉——引者注)甚多。”[9]雍正年间,作为边茶主要生产基地的荥经县从事边茶贸易的商贾中,“川陕各半,陕商行引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一张,川商行引八千四百六十三张”[10]。茶引的占有量足以体现清初陕商在南路边茶贸易中的商业实力。随着汉藏商贸接触的日益频繁,内地商贾为方便交易,在打箭炉设立商号,办理茶货屯运、交易、收购土特产、转运等事宜。乾隆年间,“邛雅荥天各州县商人领引运茶,皆炉城设店出售”[11]20。其中,陕商商号鳞次栉比,自成一街,俗称“老陕街”。至民国时期,康定的240余家坐商中,陕籍商贾占半数以上[12]。为保障商业运作的稳定与连续性,陕商商号内部有一套严格的进阶制度,从学徒到掌柜需历经多年的商场磨练,而且同乡籍色彩浓厚,大多集中在渭水南北两岸的泾阳、户县等地[3]149,时常引介与帮助同乡人前往康区经商。陕籍商贾老家乡间多有“打箭炉盛产黄金、鹿茸、麝香、虫草、贝母,遍地是钱”的传闻[13]94,这对于在乡间谋生不易的陕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致使新的陕籍商贾源源而来,“炉客”便成为此类陕商的代名词。
早期内地商贾在康区的经商活动,主要是固定于打箭炉,借助“锅庄”的引荐来完成与藏商交易。这种集食宿、货栈、商贸媒介于一体的商业场所,在汉藏交易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与催化作用[14]。但是完全依赖藏商与锅庄的经商方式无形中增加了商业运作的环节,影响利润,也使得汉藏之间直接的商贸接触程度减弱。为进一步拓展广阔的藏区市场,获取更为丰富的商业利润,以陕商为代表的一些资本雄厚的内地商贾便采取设分号、派坝充、长途贸易等商贸形式。实际上,清末民初以前,内地商贾已经在康南的巴塘、理塘,及康北的炉霍、甘孜一带从事商贸活动,设庄或分号,尤其以陕商最为突出。到18、19世纪,理塘、甘孜等关外主要城镇均有陕商的分号。而且,陕商分号无论数量,还是商业实力均占优势。以民国时期北路第一大商埠——甘孜为例,外埠在当地分设的16家商号中,利盛公、吉泰公、玉泰公、德聚和等陕商字号就占一半[15]。此类商号大多是打箭炉各大商号所设分号,属坐商性质,自行收购当地各类土特产,雇佣驮脚,运至康定。
除了个别主要城镇外,当时康区多数地区缺乏固定的交易市场,藏民商品意识淡薄,这极大限制了汉商的经商地域。面对此种经商环境,关外分号具体采取两类交易方式:一是预付现金或边茶,坐待藏民或采药者前往商号,以物易物,用药材、金香等土特产换购茶叶、布匹等。其中,尤以康北的交易做法最具典型性。牧区是康北陕商的主要经商区域,“其经营方式,系由康定购买茶叶出关,于每年农历正月,即携茶叶作为礼品,送各牛厂主人,待牛厂娃来城贸易,遂投素有交情之老陕处脱售金香等,各项货物,售价高低,悉由老陕定之,故老陕获利甚巨”[16]。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坐商并非是被动的交易,而是主动地利用年节时机,以藏民所需的茶作为“礼物”,推销自身,与其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争取与稳定土特产货源;二是由分号派熟悉业务的商贾,分住在各大村堡中收购黄金、麝香等,此类商贾藏语称作“坝充”,意为住乡商人,大多为散商,寄居在民户或寺院内,春去秋回,直接与藏民进行交易。对此,在康区任职多年的刘赞廷曾详细描述过稻城乡间陕籍坝充的经商方式: “此小贩悉行于乡间,经人介绍以某处为宜,即携货前往,至则择主而居,房饭不出分文,盖藏俗买卖出入,有主人三分手续费,以致殷勤招待,土人不敢歧视,以货掉货,春放秋收。”[17]坝充虽属小本经营、个体行为,却也能利用人际资源,深入乡间,与藏民之间略似“锅庄”关系,各取所需,备受当地藏民尊重。与坝充不同,长途贸易是有组织性的集体商贸活动。陕商擅长长途贸易的商业习性,是其在康区商贸活动的有效补充,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因交通不便而带来的货源短缺、货运不畅等困难,对于陕商控制商贸活动极为有利,如自青海玉树经康区输出之货物,多由陕商垄断[18]。
由此,陕商以商号—分号 (独立庄号)—坝充的层级贸易形式,辅助以长途贸易,在康区构建起商贸交易的网络。即在雅安设商号,收购茶布等,转运至打箭炉。打箭炉设有固定商号,负责与藏商进行大宗交易。与此同时,商号于关外设分号或散商独立设庄,以某一城镇店铺和货栈为中心,向周边农牧区辐射的方式,分派坝充,深入乡间从事商贸活动。因分号店员、坝充直接交易的对象是藏民,交易环境处于广大的康区社会之中,从而扩大了与藏民的社会接触面。这些置身打箭炉以西康区的陕籍商贾,俗称“口外客”,深入康区腹地拓展乡间市场,以小商贩或挑货郎的形式,将商业触角延伸到康区的乡间角落。早在清末光绪年间,理塘粮务同知查骞就曾感叹道:“陕客岁入草地,售卖零金,不惮荒险者,尤以户县人为甚。蹈蛮乡,弃亲爱,冒冰雪,犯虎狼,不知自惜者,其利薄也。”[19]赴康调停康藏纠纷的唐柯三在其日记中亦称:“关外经商多陕人,都以小贩起家,深入蛮荒,练习土语,往来各处,以货品互异,日久居然成为富商。”[20]这种开拓、冒险精神是其他汉商无法比拟的。对此,一份1935年的西康概况呈文中引用西康谚语称:“康谚云:‘老陕不至,草亦不生。’穷其实,虽草不生,老陕亦至。”[21]于是,与普通散商不同,从“炉客”到“口外客”,康区陕商的经商方式颇具组织与系统性,以此构建起犹如树状的商贸网络,愈往网络的末端,与藏区社会的接触愈直接、愈深入。
二、“老陕”形象的塑造:康区陕商的族际经商
与内地商贸活动不同,进入康区的内地商贾面对的是在文化与生活习俗方面与自己迥然有别的藏民。为克服族际通商的障碍,赢得藏民的信任,陕商还意识到在康区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交易双方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经济交往的层面,需要充分发挥各类文化与社会资源的作用,以便有助于其在康区的商贸活动。
熟练掌握藏语藏文是陕商进入康区经商的第一步。陕商在深入康区之前,需集中在康定学习简便适用的藏语藏文,视其为入康行商的基本条件之一。为此,专门编有易于记忆的对译韵书《藏语会话》,由“先生”早晚传授,令学徒习读:“天叫朗,地叫撒。驴叫孤日马叫打。酥油马[去声],盐巴擦[上声],大人胡子喀苏热。却是你,可是他。喝茶槚统饭热妈。来叫火,去叫热[入声],番叫白米汉叫甲。”熟读以上口诀后,便可直接与藏民接触、交谈,纠正发音,悉心揣摩,经数月后,即可进行简单的会话[22][23][13]96,98。在不同民族交往中,善意地习用对方的语言,可以缩小双方心理上的距离感,有利于经商活动的顺利展开,这是陕商重视学习藏语藏文的初衷。对此,民国文人张硕人曾写道:“陕商在康藏坐着第一把交椅,我曾研究他们致胜的原因,有人告诉我:陕西商人,未出关经商之前,在康定必须学好藏文藏语,这是他们出关经商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语文是他们成功的良好媒介。”[24]
语言交流障碍的消除,为陕商在康区的经商生涯开启了与藏民沟通的桥梁。但是陕商的经商活动为康区藏民所接纳与认可,还源自陕商对藏民生活习惯的尊重与效仿,真正参与到藏民日常生活中的努力。民国时期不少调查者与旅行家在描述康区陕商的经商方式时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长期在康区从事地质勘探的地质学家程裕淇总结陕商的经商之道称:“大致新从陕西来的学徒,先得学康人的语言,再慢慢的熟习他们的生活习惯,穿毪子大袍,吃酥油糌粑和生牛肉干,骑快马,养成原始的睡觉方式,或竟在很冷的地方露宿,康化的程度愈来愈深,这样才能和买主熟识,使得他们感觉到这些做买卖的简直就是较熟的朋友,不用多生猜疑。当一个学习成熟的学徒,骑着马带了货物到乡村去,大都穿上康人的衣服,到了目的地,晚上就睡在买主的房间里或牛毛帐篷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一块儿谈笑。”[25]而另一位康区经济调查者也指出,陕商“之所以能与康族融洽而经营致富者,良以老陕能摩仿康族生活习惯,穿康装 (俗称蛮装),说康话,并与之同饮同食,有若家人”[16]。
不同族群之间心理上亲和力的形成部分源自于外显文化表征的相似与彼此对对方生活习俗的尊重和模仿。陕商在康区经商时,往往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主动效仿和接近藏民,尽量消除因汉藏族别不同而造成的文化与心理隔阂,而且其态度和蔼,直接入住藏民家中,与之“同饮同食,有若家人”。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交流方式,将商贸活动巧妙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中,不仅可以获得藏民的认同,赢得良好的社会口碑,还能够使陕商较快适应与内地相异的康区生活环境,充分熟悉与利用康区本土的社会文化,保障商贸活动的顺利开展。
由于陕商将经商与文化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加之“和蔼忠实,货无伪诈,受藏人爱护,皆呼之老陕,成为风俗”[17]。川康地区流传着“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的俗谣,生动地勾勒出陕商足迹遍及整个川康地区的景象。陕商在康区经商之效果如程裕淇所言:“至于康人呢,对于这种买卖,实在相当欢迎,不用出门走远路,就有这批和自己的服装语言一样的商人,把急切需要的物品送上门来,拿走的不过是自己劳动所得到的东西。因此不论是多么偏远的一部落,往往是政府势力所达不到的地方,都曾有陕帮商人的足迹到过,就是在康藏感情极坏、政治形势非常紊乱的时候,他们还能渡过金沙江去,到西藏人管辖的地方做买卖去。”[25]
诚然,陕商不畏艰险,远道而来,主要目的是为了经商,获取商业利润。但是陕商在康区的商贸活动客观上却起到了沟通汉藏关系与促进双方文化交流的作用,特别是陕商与当地社会交往面极大,使更多的藏民熟知与认可“老陕”。故陕商的经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缓和民国时期因康藏局势恶化导致的汉藏紧张关系,对进一步稳固汉藏商贸关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面对广阔的藏区市场,陕商在经商过程中十分重视与当地各阶层的社会交往,以便结成广泛的社会联络网,发挥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资本雄厚的陕商常常是当地社会上层的座上客,出席地方官员、土司等参与的各类重要场合。民国时期特派西康考察员冯云仙至炉霍,当地设宴款待,“席上有格充呼图克图和另一年长之呼图克图,另有三人,陕西籍,系此间巨商,藏话很流利”[26]。有的陕商甚至与土司私交颇深,光绪二十年前后,炉霍陕商张锡台与章谷土司振基及土妇往来稔熟,振基殁后,土妇一度想以张承继土职①参见刘绍伯:《炉霍史轶》,载炉霍县史志办:《炉霍县史志资料选辑》(1),1992年。该书撰写于1944-1946年间。。陕商作为外来者,通过参与社交活动,保持与当地寺院、土司等上层人士的密切接触,已经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寻求到自身的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当地社会上层的认可,甚至超出经商范围之外,介入到政治生活中。
陕商与当地藏民最为直接和有效的互动途径是通婚。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解除经商后顾之忧,不少陕商选择在康区娶妻生子。民初,道孚境内“汉商颇多,饶裕者皆陕客。当炉文君,罔非蛮妇,非特乐尔妻孥,兼赖交通蛮侩耳”[27]。国民政府实业部之《经济年鉴》亦称:“陕人初到康地,多半孑然一身,数年之后,即成富商,遂在其地娶妻生子,因而成家。”[28]程裕淇也写道:“(陕商)在康属住得久的,还常有娶康属妇女做太太的,因此他们在西康的商业基础,更甚坚固,并且还能促进当地两族的感情。”[25]这样的姻亲关系,不仅增加陕商发展商业的社会资源,还使得陕商直接进入到当地社会生活圈中,获得与藏民认同和互动的衔接点。
陕商集中在康定学习藏语藏文等经商的前期准备,固然需要相应的组织和资金支持,并非所有的陕商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与康区其他汉商相异之处在于,陕商的经营方式贴近藏民生活,并深入农牧区的乡间,表现的是一种亲近藏民的汉人形象,从而深受藏民欢迎,无形中以文化为纽带,通过频繁的社会交往,与康区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了康区藏汉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而且,陕商的此种经商方式并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商贾群体约定俗成的经商习惯,因而此种习惯具有延续性与持久性,对汉藏文化交融与族际互动影响深远。
三、陕商对康区汉藏文化交融的影响
陕商在康区经商,既要主动适应当地藏民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又将某些内地事物与生活习惯引入康区,这使得陕商成为主动传播汉文化和接纳藏文化的双重载体。在陕商相对聚集的城镇内,汉藏文化习俗相互杂糅,逐渐在康区形成某些具有区域性特色的文化地理单元。
无论是在经商过程中主动效仿藏民风俗习惯,还是选择族际通婚,都使陕商能够较快地融入康区社会中,这固然有助于其经商活动的顺利开展,而经商过程中对藏民生活的熟悉和体验,也有助于陕商将藏区的某些文化因素融入其日常生活中。康区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陕籍个体散商,及陕商与藏人妇女组成的家庭,更易于趋向藏式的生活方式,并对后代影响颇深。1920年代初,英国驻华副领事台克满 (Teichman)在其旅康日记中称:“某次,有一全似藏人者,来至机结卜庄屋顶,用流利之汉话,对余招呼。余甚异之,结果方知彼非藏人,而为一‘老陕’(此系方言之来自陕西之商人)……彼等之习惯与衣装完全西藏化,其第二代第三代子孙,或将与西藏人一切皆相似,全无分别。”[18]。台克满所见显然并非个案。对于有的陕商而言,经商之路也是移民与本土化之路。一位内地旅康者在雅江西俄洛曾偶遇一祖籍陕西的汉人,“到康已三代,现有一儿学喇嘛,一女留赘,老者尚能说几句汉话,问其先人姓字,已不能举矣”[29]。可见,陕商进入康区后,自身的文化面貌逐渐与藏民趋同,难分彼此,乃至习从藏民习俗,改变其家庭继嗣观念,送子嗣入寺为喇嘛,以女留赘承袭家业。对藏民风俗习惯的接纳,并不局限于散商。据笔者实地调查所知,清末民国时期汉人相对聚居的巴塘县城内,陕商数量较多,临街铺面多为陕商开设,因与当地藏民通婚,其后裔在汉藏结合的家庭生活中,逐渐糅合汉藏生活习惯,接纳藏民饮食、住居习惯,穿着藏装,以藏话为生活常用语,取藏名,敬信藏传佛教,甚至有的第一代陕商就已大量接受藏民的生活习俗。
需要指出的是,陕商在经商过程中尽量尊重与效仿藏民风俗习惯,却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放弃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主要体现在生活于相对聚居的城镇内的陕商群体的文化选择上。康区主要城镇的兴起与川藏商贸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打箭炉、巴塘皆有因陕商而出现的街市,如打箭炉沿折多河边的“老陕街”,清道光年间姚莹在巴塘见到的陕西客民贸易的街市①巴塘“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参见魏源著,韩锡铎、孙文良点校: 《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232页,附《康輶纪行》。今本无,参见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合本,黄山书社,1990年。。这些街市时常掺杂着内地的文化设施,聚居陕商举行的各类传统仪式与娱乐活动常常在街头或固定的场所上演。会馆、庙观是包括陕商在内的内地商贾倡导并兴建的常见汉式建筑,打箭炉的山陕乡祠(秦晋会馆)——关帝庙、财神庙,巴塘的关帝庙均属此列[30][11]8[31]。具有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特征的商贾社团往往围绕会馆、庙观展开各种社会活动。在打箭炉,财神庙是正月初九山陕商帮举办财神会的聚会场地,三月十五则是巴塘商会在关帝庙内聚餐的俗定时间。祀神、议事、聚餐的同时,会馆或关帝庙内戏台是秦腔或川戏的表演舞台。类似的节庆表演活动还进入到社区生活中。自清代中叶,每届年节,聚集在打箭炉陕西街的山陕商号,要承办隆重的船灯、高跷、马马灯等,沿街演出[32]。民国时期,道孚县城的陕商在旧历新年时也要在县城内的衙署、正街口和几家大锅庄较宽敞的场地组织类似的彩船灯与马马灯的灯会[33]。这使得康定、巴塘、道孚等城镇内因汉式建筑与人文景观的存在,汉文化氛围显得相对浓厚,同时,川陕不同地域的乡土表演与康区本土的跳锅庄相映成趣。围绕会馆、庙观,陕商群体及其后裔,同其他汉人移民开展各种内地传统的仪式活动,对内地传统文化在康区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34]。因此,陕商往往在传统汉文化的延续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成为重要的民间社会支持力量。陕商组织及参与固定的社会活动,表明其不再是单纯的流动的外来商贸者,而是融入当地社区生活中的一个群体。
因陕商群体生活的影响与个体陕商的自我选择,康定、巴塘等地城镇内的陕商生活仍保留着较多的内地风貌,如巴塘、道孚、康定等县城内的陕商穿长袍马褂,戴博士帽,过春节时耍龙灯等。社会学家柯象峰在康定调查时曾拜访一家陕西店铺,“该店前部为石库门面,入堂为交易场所,有扇格窗门雕刻对联,坐位及秤盘等之设备,门后角有炕床一,想系招待客商食烟之处”[35]。商铺内部构造皆与内地相仿。将部分商业资本用于置地务农,可能是康区不少汉商的普遍做法,这既与汉人传统的重农观念有一定关系,也反映出在康区的特殊环境中,多种谋生手段是维持生活的重要保障。署名为苏里虚生的作者在描述一位陕商的后裔时提到,陕商王大于清末选择在瞻化 (今甘孜州新龙)日隆村成家立业。为谋生计,一面继续从商,一面在当地开垦荒地,置办家业[36]。巴塘汉商中居多数的陕商也大多兼营农商。由此,生活在群体与个体、家庭生活与会馆 (社会)生活之间,陕商及其后裔同时接纳与延续着汉藏文化因素,如衣食住行的汉藏习俗结合,汉式丧葬习俗中请喇嘛念经,参与放生活动等。与之相对应,某些汉文化因素潜移默化之中对周边藏民产生影响。康定藏民接受汉人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家中使用汉式桌凳、床帐等[1]。理塘藏民每届新年,效仿汉人作拜年状,“拜年一事,系陕商倡始”[37]。时至今日,巴塘县城内藏汉民众均有春节贴对联、门神,供灶神,及清明上坟、过中秋、端午节的习惯,据说均源自于陕商①调查地点:巴塘县老干部活动室;时间:2010年8月17日;被访谈人:HQP,71岁;访谈者:邹立波、李青。。因陕商经商的同时兼事农务,遂将一些内地农作物及生产技术传入康区。民国时期何许人在游历至巴塘时,获悉当地以前并不产麦子,清初在此经商的陕商“见巴安土质气候宜种,于是始由陕西携有种来,故至今土人,仍称巴安麦子为‘西麦子’ (即陕西麦)”[38]。麦种传入后,食用“巴塘灰面” (俗称“冒面”)的人数占县城居民的一半,甚至远销康定。因陕商之故,各类面食至今依然是巴塘县城藏汉居民饮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当地藏话中的“包子”、“面块子”等也是直接从陕西话中照搬而来的,从而形成与周边乡间不同的传统饮食文化,使康定、巴塘等城镇成为汉藏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
四、结 论
不同民族或文化的接触与互动有多种渠道,如宗教传播、移民活动等,而且各有侧重,或侧重物质方面,或偏于精神领域,或两者兼备。商贸往来的作用倾向于前者,此诚如著名社会文化学家陈序经所言, “由商业的交通而接触的文化,主要是偏于物质方面,而且这种的文化接触,往往是无意的,而非有意的”[39]。然而,康区陕商以文化模仿与社会交往为途径所从事的经商活动,已经超出单纯的商业运作范畴,而是有意地主动接触藏民,与之深层次地频繁交往,并效仿藏民生活方式,消减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从物质层面的交往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虽然其最终目的仍立足于商业利润,却深得康区藏民的认同,这一点从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可以得到集中体现,即“康女喜嫁陕商及陕商乐娶康女”[35]。这不仅归因于陕商不辞艰辛,远涉康区各处从事的商贸活动,对丰富藏民的物质生活大有裨益,而且因其积极参与到藏民社会生活中,展现给藏民以良好的“老陕”形象。陕商同时也是内地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播者,康定、巴塘等城镇内汉文化传统的保留与陕商有一定关联,陕商实则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在藏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4).[2]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商人与康藏锅庄关系探微[J].重庆商学院学报,2000,(6).
[3]李刚.陕西商帮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4]王振忠.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 (下)[J].读书,2006,(5).
[5]佚名.西康之茶叶调查[J].康藏前锋,1934,(2.1).
[6]高长柱.西康实业纪要[J].开发西北,1935,(4.1-2).
[7]李苞.嘉庆巴塘诗钞·卷上·巴塘[M].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8]吴文晖,杨锡福.如何建设西康经济[J].边疆问题研究会.青年月刊副刊·边疆问题,(6).
[9]吴廷伟.西藏纪程[M]∥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32.
[10]张赵才,等.民国荥经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413.
[11]乾隆打箭炉厅志[M]∥张羽新.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 (40),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12]来作中.解放前康区的商品交换[Z].甘孜州文史资料 (13),康定:中国政协甘孜州委员会,1993:128.
[13]杨益三.德泰合的盛衰[Z].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 (1),康定:中国政协甘孜州康定县委员会,1987:94.
[14]谭英华.说“锅庄”[G]∥赵心愚,等.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 (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15]腾蛟.开发康藏与三殖政策(续)[J].康藏前锋,1934,(1:5).
[16]陆予新.康北经济杂谈[J].西康经济季刊,1942,(1).
[17]刘赞廷.民国稻城县图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1990:804.
[18]台克满.西藏东部旅行记[J].高上佑,译.康藏前锋,1935,(2.4-5).
[19]查骞.边藏风土记·卷一·边地出产[M]∥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 (6),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0]唐柯三.赴康日记[M].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科印行,1934:28.
[21]巡员张懋昭关于西康概况呈文[M]∥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399.
[22]任乃强.西康图经[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418.
[23]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76.
[24]张硕人.康行散记[J].新中华 (复刊),1945,(3.5).
[25]程裕淇.西康剪影[M].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24-25.
[26]冯云仙.西康关外日记 (二)[J].蒙藏月报,1936,(6.6).
[27]朱增鋆.川边屑政[M]∥赵心愚,等.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 (上).成都:巴蜀书社,2006:161.
[28]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康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67.
[29]徐思执.康南旅行记[J].康导月刊,1938,(1.1).
[30]钱召棠.道光巴塘志略[M]∥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 (39),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506.
[31]刘赞廷.民国康定县图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1990:14.
[31]四川康定县志编撰委员会.康定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465,518.
[33]江裕兴,青镇东.解放前道孚县城汉团的习俗和庙会概述[J].道孚县文史资料选辑 (1),道孚:中国政协道孚县委员会,1985.
[34]石硕,邹立波.会馆、宗教信仰与汉藏关系——对巴塘关帝庙多重社会文化内涵的阐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6).
[35]柯象峰.西康纪行[J].边政公论,1940,(1.3-4).
[36]苏里虚生.被弃的异族女儿[J].新西康,1938,(1.3).
[37]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M].林超,校.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109.
[38]何许人.康南游记[J].康导月刊,1942,(4.2-3).
[39]陈序经.文化学概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7.